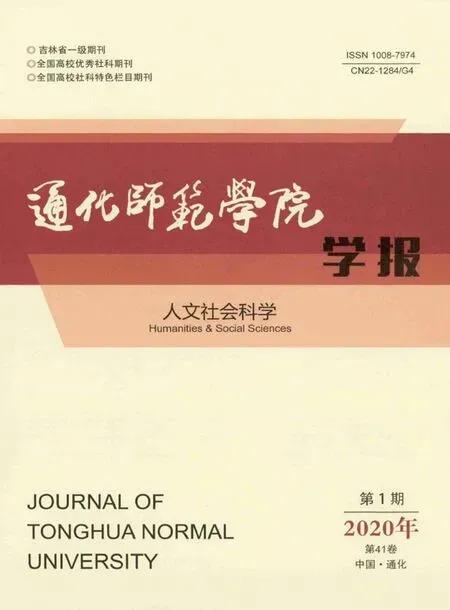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時(shí)間詞“剛才”的形成與發(fā)展
李惠超
“剛才”是現(xiàn)代漢語(yǔ)中使用頻率較高的常用時(shí)間詞之一。“剛才”在《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中的解釋為“剛過(guò)去不久的時(shí)間”,《現(xiàn)代漢語(yǔ)八百詞》中指出,“剛才”是時(shí)間名詞,表示“說(shuō)話前不久”[1]。例如①本文語(yǔ)料來(lái)自北京大學(xué)語(yǔ)言研究所CCL語(yǔ)料庫(kù)。:
(1)他說(shuō),今天上午拉奧總理與李鵬總理舉行了會(huì)談,剛才又會(huì)見了江澤民主席,雙方談得很好,說(shuō)明訪問(wèn)進(jìn)行得很順利,而且富有成果。(人民日?qǐng)?bào)1993年九月)
(2)就在剛才冠軍爭(zhēng)奪戰(zhàn)終場(chǎng)哨響之前,中國(guó)女籃還面對(duì)著巨大的威脅。(人民日?qǐng)?bào)1993年七月)
(3)陸小鳳道:“剛才是剛才,現(xiàn)在是現(xiàn)在,一瞬之間,往往就會(huì)發(fā)生很多變化。”(古龍《陸小鳳傳奇》)
語(yǔ)言學(xué)界對(duì)時(shí)間詞“剛”和“剛才”,以及“剛”的疊加式“剛剛”的意義和用法等方面進(jìn)行過(guò)很多討論。邢福義指出,不應(yīng)將“剛剛”僅僅視為時(shí)間副詞,而應(yīng)將“剛剛”分為“剛剛1”和“剛剛2”,其中“剛剛1”同時(shí)間副詞“剛”,而“剛剛2”則同時(shí)間名詞“剛才”[2]73-74。馮成林從辨析“剛剛”和“剛才”的詞性入手,提出了劃分時(shí)間名詞和時(shí)間副詞的4 條標(biāo)準(zhǔn)[3]。周小兵則討論了當(dāng)“剛”和“剛才”做狀語(yǔ)時(shí),動(dòng)詞后跟的表時(shí)間詞的差別,指出二者是兩個(gè)不同的時(shí)段標(biāo)志[4]。
然而以上文章更多著眼于“剛才”與“剛”“剛剛”之間在語(yǔ)義和用法之間的共性和差異,且更多地局限在共時(shí)層面上的比較分析,鮮有系統(tǒng)地研究“剛才”一詞的歷時(shí)演變的論述。我們認(rèn)為,如果沒(méi)有從歷時(shí)的角度研究“剛才”的語(yǔ)義及功能演變,就很難從根本上準(zhǔn)確地掌握其共時(shí)層面的意義及用法。在此我們擬探究時(shí)間詞“剛才”的形成過(guò)程及其生成機(jī)制。
一、“剛”和“才”的語(yǔ)法化
我們認(rèn)為,時(shí)間詞“剛才”的形成經(jīng)歷了兩個(gè)階段,先由排列上相鄰的兩個(gè)單音節(jié)近義時(shí)間副詞“剛”“才”固化為一個(gè)雙音節(jié)時(shí)間副詞,進(jìn)而再由時(shí)間副詞發(fā)展為時(shí)間名詞。
要了解“剛才”如何而來(lái),就不能忽視作為其構(gòu)詞語(yǔ)素的“剛”和“才”的發(fā)展和演變。通過(guò)研究副詞“剛”和“才”的語(yǔ)法化歷程,才能知曉時(shí)間詞“剛才”從何而來(lái),進(jìn)而闡明這一演變過(guò)程的內(nèi)在機(jī)理。由于“剛”和“才”遠(yuǎn)早于“剛才”一詞產(chǎn)生,且“剛”和“才”在古代漢語(yǔ)中也是常用詞,產(chǎn)生了豐富的義項(xiàng)和繁多的用法,限于篇幅,我們主要分析“剛”和“才”語(yǔ)法化的演變歷程
(一)“剛”的語(yǔ)法化歷程
1.先秦至唐末的發(fā)展
《說(shuō)文解字》對(duì)“剛”的釋義是:“強(qiáng)斷也。從刀岡聲。”按段玉裁注:“強(qiáng)斷也。強(qiáng)者,弓有力也。有力而斷之也。周書所謂剛克。引伸凡有力曰剛。”可見“剛”的本義為形容詞,我們記作“剛1”。“剛1”既可以指物質(zhì)的堅(jiān)硬,也可以泛指事物的某類特性或人的品性,此時(shí)的“剛”依其語(yǔ)境,語(yǔ)義有所差異,如:
(4)采薇采薇,薇亦剛止。(《詩(shī)經(jīng)·采薇》“剛”表“硬”義,指植物長(zhǎng)大時(shí)的樣子。)
(5)金,堅(jiān)剛之物。(《周易》王弼注“剛”表“堅(jiān)硬”之義)
(6)剛而塞,將而義。(《尚書·皋陶謨》。“剛”表“剛強(qiáng)”之義)
(7)旅力方剛,經(jīng)營(yíng)四方。(《詩(shī)經(jīng)·小雅·北山》。“剛”表“強(qiáng)盛”之義)
值得注意的是,形容詞“剛”本身在大多數(shù)時(shí)候是一個(gè)褒義或者中性詞,但當(dāng)形容個(gè)人品性時(shí),在語(yǔ)境的制約下,有時(shí)也會(huì)有“固執(zhí),不變通”的隱含義。如:
(8)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wú)恩,以短取敗,理數(shù)之常也。(《三國(guó)志·蜀書六》)
(9)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wú)謀,逢紀(jì)果而自用.(《三國(guó)志·魏書十》)
到了唐代,基于“剛1”衍生出了方式副詞“剛”的用法,即由“性格(品性)剛直,固執(zhí)”向“行為(手段)強(qiáng)硬”的轉(zhuǎn)化,我們記作“剛2”。如:
(10)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全唐詩(shī)卷七八三·悼妓詩(shī)》)
(11)低聲向道人知也,隔坐剛拋豆蔻花。(唐·馮袞《戲酒妓》)
例(10)的“剛留得”、(11)的“剛牽引”可理解為“強(qiáng)留得”“強(qiáng)牽引”,副詞“剛”表示“(行為)強(qiáng)硬”之義。
在“剛2”所處的語(yǔ)境中,即在“S+剛2+V+O”句中,施事者S 強(qiáng)硬地(“剛2”)實(shí)施了動(dòng)作V 以達(dá)成某種目的,由一般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可知,這一動(dòng)作V 造成的結(jié)果一般是受事者O 所不希望接受的——因?yàn)槿绻@一結(jié)果是O所希望見到的,則S 往往不需要使用強(qiáng)硬的方式即可實(shí)行動(dòng)作V。由此可以推知,在“S+剛2+V+O”這一結(jié)構(gòu)里,蘊(yùn)含著反意愿實(shí)現(xiàn)(對(duì)于受事者的)的語(yǔ)義成分,而這也是之后“剛2”向“剛3”轉(zhuǎn)化的重要原因[5]。
由于“S+剛2+V+O”這一結(jié)構(gòu)里,蘊(yùn)含著“反意愿實(shí)現(xiàn)”的語(yǔ)義成分,因此從受事者的角度看,基于轉(zhuǎn)喻機(jī)制的作用,人們?cè)谛睦韺用嫔蠈⑦@一結(jié)構(gòu)的標(biāo)志詞“剛2”與“不愿發(fā)生的事態(tài)”聯(lián)系到一起,進(jìn)而使“剛2”衍生出表轉(zhuǎn)折的“偏偏、卻”之義,我們將它記作“剛3”。自唐代開始,就有:
(12)剛有下水船,白日留不得。(唐·孟郊《留弟郅不得送之江南》)
(13)溪云洞鳥本吾儕,剛為浮名事事乖。(唐·皮日休《醉中偶作呈魯望》)
(14)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biāo)歸。(唐·盧肇《競(jìng)渡詩(shī)》)
由上述用例可知,自隋唐開始,方式副詞“剛2”開始逐漸向限定副詞“剛3”轉(zhuǎn)化。
2.宋元之后的發(fā)展
宋元之際是近代漢語(yǔ)的重要發(fā)展時(shí)期,也是副詞“剛”的重要發(fā)展階段,在這一時(shí)期,“剛”的含義和用法有了進(jìn)一步的拓展。
早在唐代,“剛3”就有如下用例:
(15)可憐夭艷正當(dāng)時(shí),剛被狂風(fēng)一夜吹。(唐·白居易《惜花》)
此處的“剛”當(dāng)然可以理解為“剛3”,即表示“偏偏、卻”之義,但將其理解為表示行動(dòng)或情況發(fā)生不久的表時(shí)間的副詞義同樣也說(shuō)得通。而到了唐末以及宋代,有了更加明確的用例:
(16)剛有峨嵋念,秋來(lái)錫欲飛。(唐·齊己的《思游峨嵋寄林下諸友》)
(17)剛被時(shí)流借拳勢(shì),不知身自是泥人。(唐·蔣貽恭《詠金剛》)
(18)剛被太陽(yáng)收拾去,卻教明月送將來(lái)。(宋·蘇軾《花影》)
(19)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南宋·《五燈會(huì)元》)
其中例(18)(19)的“剛”語(yǔ)義指向非常明確,表示前后句之間的動(dòng)作或狀態(tài)間隔時(shí)間短暫。因此,至遲到北宋中期,“剛”表示行動(dòng)或情況發(fā)生不久的時(shí)間副詞的用法已經(jīng)產(chǎn)生,我們記作“剛4”。“剛3”到“剛4”的演變很大程度上是語(yǔ)用環(huán)境造成的,語(yǔ)境吸收(аbsоrрtiоn оf соntеxt)是促進(jìn)其語(yǔ)義演變的主要機(jī)制。
ВYВEE,PERKINS & PАGLIUСА[6]和TRАUGOTT &TROUSDАLE[7]的語(yǔ)法化理論認(rèn)為,語(yǔ)義可以隨詞匯項(xiàng)或構(gòu)式語(yǔ)境的不同而發(fā)生改變,即詞匯項(xiàng)或構(gòu)式能夠?qū)⒄Z(yǔ)境意義吸收。我們稱之為語(yǔ)境吸收(аbsоrрtiоn оf соntеxt)[8]。如張誼生曾指出,“敢”原來(lái)只有“敢于、膽敢”的意思,后來(lái)由于“敢”經(jīng)常用在反詰句中,“敢”就有了“豈敢”的含義,成為評(píng)注性副詞[9]。
當(dāng)一個(gè)句子中出現(xiàn)兩個(gè)前后承接或者有邏輯關(guān)聯(lián)的事態(tài),而其中一個(gè)是“剛3+V”這種結(jié)構(gòu)時(shí),由于表“偏偏、卻”的關(guān)聯(lián)副詞“剛3”指向說(shuō)話者“不愿發(fā)生的事態(tài)”,那么從說(shuō)話者的角度看,由于說(shuō)話者需要表達(dá)對(duì)“剛3+V”情況出現(xiàn)的不滿或不希望其發(fā)生的感情,因此與之相關(guān)聯(lián)的另一個(gè)事態(tài)很可能是與其相對(duì)立或者沖突的,整個(gè)句子往往具有轉(zhuǎn)折的意味。由于“剛”經(jīng)常性地出現(xiàn)在轉(zhuǎn)折的語(yǔ)境下,在語(yǔ)境吸收的作用下,產(chǎn)生了表示“事態(tài)轉(zhuǎn)折”的隱含義。此時(shí)的“剛”的意義不僅僅是“不愿發(fā)生”,而更多的向“未期望發(fā)生”或“沒(méi)料到”轉(zhuǎn)化。如:
(20)三十年來(lái)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shī)。(唐·王智興《徐州使院賦》)
結(jié)合語(yǔ)境,此例中的“剛”依然表示“剛3”的“偏偏、卻”之義,但其中沒(méi)有“不愿發(fā)生”的隱含義,而只是表示“(事情)出人意料”的轉(zhuǎn)折義。
在人們的認(rèn)知里,表示轉(zhuǎn)折的兩個(gè)動(dòng)作或事態(tài)往往間隔的時(shí)間較短。一方面,作為說(shuō)話者如果要表示某一個(gè)事態(tài)的轉(zhuǎn)折,其選擇的上一個(gè)比照的事態(tài)在時(shí)間上往往相隔較近,而不會(huì)回溯很遠(yuǎn),這樣既方便聽話者更好理解,也更符合正常人的思維;另一方面,當(dāng)兩個(gè)動(dòng)作時(shí)間間隔時(shí)間較短時(shí),人們也往往會(huì)將其與事態(tài)的轉(zhuǎn)折聯(lián)系起來(lái)。比如英語(yǔ)的whilе 是從“同時(shí)”的意思演變?yōu)樽尣睫D(zhuǎn)折的意思,是一個(gè)主觀化的過(guò)程。演變是由如下的語(yǔ)用推理引起的:whilе 連接А 和В兩個(gè)動(dòng)作,表示在發(fā)生В 的同時(shí)發(fā)生А。由于說(shuō)話人還主觀上對(duì)А 和В 的同時(shí)發(fā)生感到意外(兩件事同時(shí)發(fā)生的概率不高),因而產(chǎn)生出轉(zhuǎn)折的意思[10]。這可以說(shuō)明,在人們的認(rèn)知心理上,“時(shí)間間隔短”與“事態(tài)的轉(zhuǎn)折”存在關(guān)聯(lián)。
綜上所述,在語(yǔ)境吸收的作用下,剛3在唐末開始逐漸產(chǎn)生了表示行動(dòng)或情況發(fā)生不久的時(shí)間副詞義“剛4”,且“剛4”一般出現(xiàn)在兩個(gè)分句中的前一句。不過(guò)在宋代,時(shí)間副詞“剛4”出現(xiàn)的頻率仍然較低。這一方面是由于關(guān)聯(lián)副詞“剛3”的用法依然存在而沒(méi)有被其他詞取代,因而“剛”一詞多義容易混淆;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與“剛4”同義的時(shí)間副詞“才”出現(xiàn)得更早(下文會(huì)有討論),使用也更廣泛。如在《全宋詞》中,“剛”總共出現(xiàn)過(guò)125 次,去除其中表名詞和形容詞的部分,僅有寥寥幾例可以被看作時(shí)間副詞“剛4”。而在《全宋詞》中,“才”出現(xiàn)共1022次,其中大約600例左右都可看作時(shí)間副詞,其數(shù)量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了時(shí)間副詞“剛4”。整個(gè)宋代文獻(xiàn)中,“剛”表時(shí)間副詞的可信用例也十分稀少。因此,我們認(rèn)為,在宋元之際時(shí)間副詞“剛4”雖然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并不常用,原因可能是由于同時(shí)間副詞“才”用法、意義接近,因其出現(xiàn)時(shí)間較晚而較少地被使用。
到了元代之后,由于副詞“剛”產(chǎn)生諸多其他衍生義(如表限定副詞義“僅僅”,在此不多贅述),其在文獻(xiàn)中出現(xiàn)的頻率增多,時(shí)間副詞“才”的使用頻率逐漸減少,“剛4”這一用法開始變得更為常見,如:
(21)那人家。我才剛?cè)ヒe米。他不肯糶與我。他們做下現(xiàn)成的飯。教我們吃了。(元·《老乞大新釋》)
(22)不看時(shí)萬(wàn)事全休,這一看,好似霸王初入垓心內(nèi),張飛剛到灞陵橋。(《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
同時(shí),“剛4”也產(chǎn)生了新的變體——重疊形式的“剛剛”如:
(23)剛剛騰朧睡去,忽聽得床前腳步響,抬頭起看,只見一個(gè)人揭開帳子,颶的鉆上床來(lái)。(《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七)
有時(shí)還在“剛剛”后面加助詞“的”,如:
(24)剛剛的打個(gè)照面,風(fēng)魔了張解元。(元《西廂記雜劇》)
因此,至元末明初,時(shí)間副詞“剛4”的用法又被重新激活了。
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元以前“剛”作時(shí)間副詞的用法主要基于“剛3”(偏偏、卻)的用法衍生而來(lái),“剛3”在語(yǔ)境吸收的作用下產(chǎn)生了時(shí)間副詞“剛4”的用法,但由于同副詞“才”用法、意義接近而不常用。到了元代,由于轉(zhuǎn)喻機(jī)制的作用,“剛”的時(shí)間副詞用法又被重新激活了,且產(chǎn)生了新的變體。
(二)“才”的語(yǔ)法化歷程
相比較“剛”而言,時(shí)間副詞“才”的語(yǔ)法化過(guò)程相對(duì)簡(jiǎn)單。按《說(shuō)文》:“才,草木之初也。”“才”的本義是“草木之初也”,引伸為“凡始之稱”,因而含有“開始,起點(diǎn)”這一義素。在人們的認(rèn)識(shí)中,表示“初始”“起始”的事物往往容易同“數(shù)量少”或“數(shù)量小”聯(lián)系起來(lái)。因此,在隱喻機(jī)制的作用下,先秦以及秦漢時(shí)期,表示動(dòng)作的量小或者動(dòng)作涉及的事物量小的限定副詞“才”已經(jīng)出現(xiàn),我們記作“才1”如:
(25)秦始皇計(jì)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無(wú)窮,然身死才數(shù)月耳,天下四面攻之,宗廟滅絕矣。(《漢書·賈山傳》)
(26)今虜使到才數(shù)日,而王廣禮教則廢;如略善收吾送匈奴,骸骨長(zhǎng)為豺狼食矣.(《后漢書·班超傳》)
隨著“才1”使用頻率的增加,其語(yǔ)義也逐漸泛化,開始從“動(dòng)作、數(shù)量少”開始向“(間隔)時(shí)間少”轉(zhuǎn)移。在唐宋時(shí)期,“才”作時(shí)間副詞的用例逐漸增多,我們記作“才2”:
(27)子細(xì)思量爭(zhēng)不怕,才生便有死相隨。(《敦煌變文集》卷七)
(28)今夕未竟明夕催,秋風(fēng)才往春風(fēng)回。(唐·白居易《短歌行》)
(29)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宋·楊萬(wàn)里《池上》)
元明之際,由于近義時(shí)間副詞“剛”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以及漢語(yǔ)詞匯雙音化的趨勢(shì),時(shí)間副詞“才2”的使用頻率逐漸減少,但至今依然存在。如:
(30)小二道:“我的雞才在籠里,不是你偷了是誰(shuí)?”(明·《水滸傳》第七十七回)
(31)“怎么才來(lái)就要走呢?”(現(xiàn)代·于晴《紅蘋果之戀》)
綜上所述,限定副詞“才1”由“才”的基本義引申而來(lái),之后由于語(yǔ)義泛化“才1”逐漸向時(shí)間副詞“才2”轉(zhuǎn)化。“才2”至遲到唐末已經(jīng)出現(xiàn),表示“兩個(gè)動(dòng)作距離時(shí)間短”,在元明之際逐漸被副詞“剛”取代,但這種用法至今仍然存在。
二、“剛才”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一)“剛才”的詞匯化
“剛”和“才”至遲到元末明初,都可做時(shí)間副詞,且作為時(shí)間副詞意思相近,都表示“兩個(gè)動(dòng)作距離時(shí)間短”或“動(dòng)作在不久前發(fā)生”,可用的場(chǎng)合也相似,因而在明代開始常作為同義副詞連用,強(qiáng)調(diào)“時(shí)間短”的語(yǔ)義,如:
(32)且說(shuō)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jìn)。剛才轉(zhuǎn)過(guò)山來(lái),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guān)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三國(guó)演義》第八十二回)
(33)剛才把辛環(huán)壓住了,聞太師勒轉(zhuǎn)墨麒麟,舉鞭照頂門上打來(lái)。(《封神演義》第四十一回)
在(32)(33)兩例中,“剛才”看似位于主語(yǔ)位置,和現(xiàn)代漢語(yǔ)“剛才”一詞相近,但實(shí)際上此處的“剛才”=“剛”+“才”,意義上仍然是兩個(gè)同義副詞的連用,在句中充當(dāng)狀語(yǔ),仍可視為副詞。結(jié)合上下文語(yǔ)境可知,(32)實(shí)際上是省略了主語(yǔ)“崔禹”,而(33)的主語(yǔ)是“聞太師”。 將(32)(33)兩例中的“剛才”替換成“剛”或“才”,句子的基本意義以及結(jié)構(gòu)都不變。以上2 例的“剛才”表示“行動(dòng)或情況發(fā)生不久”,其意義等于“剛”或“才”,但由于同義連用,其表示“時(shí)間短”的程度有所加強(qiáng)。
時(shí)間副詞“剛”和“才”組合而成的“剛才”原本應(yīng)為副詞。但由于副詞“剛才”原本就是兩個(gè)近義副詞疊加形成,因而從意義和用法上而言,從“‘剛’+‘才’”到時(shí)間副詞“剛才”之間的界限并不清晰。如以上的(32)(33)2 例,此時(shí)將“剛才”理解為一個(gè)詞或是兩個(gè)副詞“剛”和“才”的連用,都說(shuō)得通。“剛+才”的連用通常出現(xiàn)在句首,且往往出現(xiàn)在有一前一后兩個(gè)動(dòng)作的句子里,具體表示兩個(gè)動(dòng)作之間的間隔時(shí)間短。
明代中期“剛+才”開始逐漸凝固為一個(gè)詞,如:
(34)八戒道:“哥,你往那里去來(lái)?剛才一個(gè)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也。”(明·《西游記》第二十一回)
(35)剛才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rèn)不出來(lái)。(明·《金瓶梅》第四十回)
(36)我剛才分明夢(mèng)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著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明·《金瓶梅》第八十八回)
(37)事體總在剛才所言了,更無(wú)別說(shuō)。(明·《醒世恒言·喬太守亂點(diǎn)鴛鴦譜》)
而我們由上文可知,“剛+才”的同義連用表示時(shí)間短的程度加強(qiáng),但34-37例中,雖然勉強(qiáng)都可以用“剛”將“剛才”替換,但除37 外,其他幾例用“才”替換“剛才”非常勉強(qiáng)。更重要的是,例37中還出現(xiàn)了“在+剛才”這樣的名詞特有的搭配。可見此時(shí)再將上例中的“剛才”理解為兩個(gè)詞的連用已經(jīng)不妥。再如:
(38)玉樓道:“剛才短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沒(méi)皮襖,只取姐姐的來(lái)罷。”(明·《金瓶梅》第七十四回)
此時(shí)結(jié)合語(yǔ)境,且從語(yǔ)義和邏輯上來(lái)說(shuō),如果認(rèn)為“剛才”還是副詞連用,那么從語(yǔ)義上看此處“剛+才”連用以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短了一句話”這一動(dòng)作發(fā)生不久,但這并沒(méi)有實(shí)際的語(yǔ)用意義,只用一個(gè)副詞“剛”和“才”已經(jīng)足夠了。這里的“剛才”最合理的理解應(yīng)為表示某個(gè)過(guò)去的時(shí)刻。
但以上(34)-(38)5 例,除(37)以外,并不能有足夠的證據(jù)清晰地判定句中“剛才”屬于名詞或是副詞。因此,我們認(rèn)為,此時(shí)“剛才”已經(jīng)成詞,但還處于副詞和名詞的過(guò)渡階段。
明代中期出版的《三國(guó)演義》以及《水滸全傳》中,“剛才”分別只出現(xiàn)了2 例和1 例,但在同時(shí)期稍微刊行的《西游記》以及《金瓶梅詞話》中,“剛才”分別出現(xiàn)了16 例和63 例,而到了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緣傳》“剛才”一詞則出現(xiàn)了多達(dá)186 次。考慮到《三國(guó)演義》以及《水滸全傳》雖然出版時(shí)間在明中葉,但作者羅貫中、施耐庵應(yīng)為元末明初人,我們可以認(rèn)為,至遲到明代中期,隨著“剛”和“才”連用次數(shù)的頻繁,“剛才”逐漸凝固為一個(gè)可以單獨(dú)運(yùn)用的詞。
同義連用也是“剛才”的詞匯化重要?jiǎng)右颉M趿ο壬J(rèn)為:“漢語(yǔ)大部分的雙音詞都是經(jīng)過(guò)同義詞臨時(shí)組合的階段的。這就是說(shuō),在最初的時(shí)候,是兩個(gè)同義詞的并列,還沒(méi)有凝結(jié)成為一個(gè)整體,一個(gè)單詞。”[11]而這些“臨時(shí)的組合”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時(shí)間的推移等因素逐漸成為一個(gè)新詞。
(二)“剛才”的逆語(yǔ)法化
到了清代,時(shí)間詞“剛才”的用法已經(jīng)基本與現(xiàn)代漢語(yǔ)“剛才”無(wú)異,如:
(39)正說(shuō)著,只見狄希陳坐完了帳,出來(lái)陪他舅子。那賓相吃完酒飯未去,仍把剛才那些話又對(duì)了狄希陳辨白。(清·《醒世姻緣傳》第四十四回)
(40)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著笑臉兒說(shuō)道:“剛才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lái)了他就跟了來(lái)。我怕他鬧,所以才吆喝他回去,那里敢在這里罵人呢。”(清·《紅樓夢(mèng)》第八十四回)
(41)稚燕看著,方曉得鳳孫的繼母病故,一封報(bào)喪的電報(bào)。到此地位,也沒(méi)得說(shuō)了,把剛才的一團(tuán)怒火霎時(shí)消滅,倒只好敷衍了幾句安慰的套話,問(wèn)他幾時(shí)動(dòng)身。(清·《孽海花》第二十三回)
我們知道時(shí)間名詞可以充當(dāng)句子的主語(yǔ)、定語(yǔ),而時(shí)間副詞不能。在以上的例證中,出現(xiàn)了如(39)“介詞+剛才”的結(jié)構(gòu),也出現(xiàn)了如(41)里的“剛才”+結(jié)構(gòu)助詞“的”,以及(40)里的“剛才”+“是”這樣的搭配。這足以說(shuō)明,此時(shí)的“剛才”已經(jīng)具備了充當(dāng)主語(yǔ)和定語(yǔ)的名詞性功能。由此,我們可以說(shuō),至遲到清代中期,時(shí)間名詞“剛才”已經(jīng)形成,且語(yǔ)義和用法基本完善。“剛才”這種從虛詞(時(shí)間副詞)向?qū)嵲~(時(shí)間名詞)的轉(zhuǎn)化,在漢語(yǔ)史中并不多見,我們將其稱之為逆語(yǔ)法化(dеgrаmmаtiсаlizаtiоn)的一種[12]。這種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主要是基于轉(zhuǎn)喻機(jī)制的作用。
副詞“剛才”的本義是指“行動(dòng)或情況發(fā)生不久”,我們由上文可知,“剛才”最早出現(xiàn)在處于有前后兩個(gè)動(dòng)作的語(yǔ)境時(shí),在這一語(yǔ)境下“剛才”僅僅只表示“(某一動(dòng)作)發(fā)生不久”,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兩者間隔時(shí)間短”,或“前一個(gè)動(dòng)作在后一個(gè)動(dòng)作發(fā)生前不久發(fā)生”,如上述的例(33)中的“剛才”按語(yǔ)境而言,僅指“壓住”和“舉鞭……打來(lái)”這兩個(gè)動(dòng)作的間隔時(shí)間短。其時(shí)間參照點(diǎn)是后一個(gè)動(dòng)作發(fā)生時(shí),與說(shuō)話者當(dāng)前所處的時(shí)間點(diǎn)無(wú)關(guān)。
但是言語(yǔ)交際具有實(shí)時(shí)性,說(shuō)話者顯然更愿意提及正在發(fā)生的或不久前的事實(shí),而不是過(guò)去很久的事實(shí)。因此雖然副詞“剛才”的時(shí)間參照點(diǎn)只與后一個(gè)動(dòng)作相關(guān),但實(shí)際上言語(yǔ)交際里提及的后一個(gè)動(dòng)作發(fā)生的時(shí)間點(diǎn),經(jīng)常與說(shuō)話者的時(shí)間點(diǎn)非常接近,甚至有時(shí)就是在“說(shuō)話時(shí)”同步發(fā)生的。因此,隨著對(duì)“剛才”使用頻率的增加,人們?cè)谀X海中開始將“后一個(gè)動(dòng)作發(fā)生時(shí)”這一時(shí)間參照點(diǎn)與“說(shuō)話時(shí)(現(xiàn)在)”逐漸混同,隨之而來(lái)的就是“剛才”的意義逐漸從“后一個(gè)動(dòng)作發(fā)生前不久”向“距現(xiàn)在不久”轉(zhuǎn)移。如:
(42)我剛才分明夢(mèng)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著武松,是好傷感人也!
此時(shí)“剛才”已不僅僅出現(xiàn)在有前后兩個(gè)動(dòng)作的句子里,其詞義不再是“(某一動(dòng)作)發(fā)生不久”,而是表示“距現(xiàn)在不久”之義。這一語(yǔ)義的變化對(duì)“剛才”的逆語(yǔ)法化非常重要。原本副詞“剛才”的本義“動(dòng)作發(fā)生不久”或“兩者相隔時(shí)間短”是一個(gè)相對(duì)的概念,其對(duì)應(yīng)的時(shí)間范圍也很模糊;而“(動(dòng)作)距現(xiàn)在不久”則是一個(gè)更加確定的時(shí)間范圍。因此在人們的潛意識(shí)中,“剛才”所指向的動(dòng)作發(fā)生的時(shí)刻也更加容易確定。因此當(dāng)人們看到“剛才”時(shí),可以直接由動(dòng)作聯(lián)想到過(guò)去的某一段時(shí)間。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人們將“剛才”和過(guò)去某個(gè)相對(duì)確定的時(shí)間段相聯(lián)系起來(lái),開始直接用“剛才”表示原先其指向的動(dòng)作發(fā)生的時(shí)間段,其意義從“(動(dòng)作)距現(xiàn)在不久”向“過(guò)去某一段時(shí)間”轉(zhuǎn)移,進(jìn)而完成了從時(shí)間副詞到時(shí)間名詞的轉(zhuǎn)化。
綜上所述,至明代中期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剛才”由時(shí)間副詞發(fā)展為時(shí)間名詞。至清代中期“剛才”的意義以及用法基本趨于穩(wěn)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