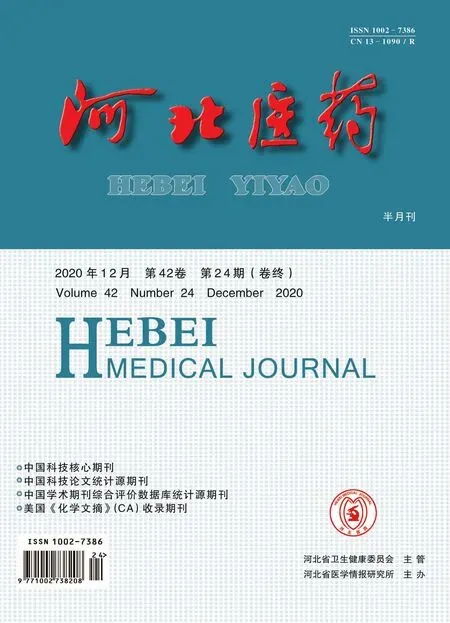肝素結合蛋白在感染中的應用及研究進展
趙芳麗 喬莉娜
感染是指病原菌(如:細菌、病毒、真菌等)侵入機體,并在機體內生長、繁殖,導致機體正常組織防御功能受損,從而引起組織損傷性病變和全身性炎性反應。隨著環境污染、社會壓力的增加,感染性疾病是引起人們機體受損的常見原因之一。全球疾病負擔研究(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顯示,在全球范圍內,2017年殘疾調整壽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DALYs)的前五大主要原因是感染性疾病(下呼吸道感染、瘧疾、腹瀉、艾滋病和結核)和新生兒疾病[1]。當機體防御功能下降(如:免疫缺陷、惡性腫瘤等),感染不僅容易發生,且容易加重為嚴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20%~30%的嚴重膿毒癥患者在入院時沒有出現器官功能障礙的跡象,而是在急診評估后的第一個24 h內進展為嚴重膿毒癥[2]。且嚴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一直高居不下,達30%~50%[3]。因此,可以快速判斷疾病嚴重程度,預測疾病發展趨勢及預后的生物標志物對臨床危重癥的診治及降低病死率具有重大意義。
1 肝素結合蛋白的結構、產生及作用機制
1.1 肝素結合蛋白的結構 肝素結合蛋白(heparin-binding protein,HBP)是一種由中性粒細胞衍生的無活性的絲氨酸蛋白酶同源物。早在1949年,HBP被分離并定義,1991年,發現其具有極強的結合肝素能力,將其命名為肝素結合蛋白。HBP是一種相對分子量為37 000的顆粒性糖蛋白,由222個氨基酸組成,也稱為CAP37/azurocidin,其屬于中性粒細胞陽離子蛋白serprocidin家族成員;該家族還有另外3個成員:HBP親近組織蛋白酶G、中性粒細胞彈性蛋白和蛋白酶3。
1.2 肝素結合蛋白的產生 HBP預先貯存在嗜中心粒細胞的分泌囊泡及嗜天青顆粒中。當中心粒細胞被激活時,前者可通過快速的胞吐作用或通過與中心粒細胞表面的β2整合素結合而釋放HBP;嗜天青顆粒的胞吐能力低,僅在中性粒細胞外滲到組織后釋放HBP。感染發生時,病原體與相應的受體結合,趨化因子(如IL-8)從感染部位釋放[4],激活中性粒細胞,并誘導HBP釋放。另外,細菌蛋白質也可以直接激活中性粒細胞,釋放HBP[5]。這些細菌蛋白包括來自金黃色葡萄球菌的酚可溶性調節蛋白[6]、來自化膿性鏈球菌的M1蛋白[5]和來自豬鏈球菌的溶血素[7]。而HBP是中性粒細胞分泌囊泡分泌到環境中的惟一顆粒蛋白。這就是細菌被吞噬30 min后總HBP被釋放80%的原因,內環境中HBP的比例遠遠超過其他中性粒蛋白[4]。
1.3 肝素結合蛋白的作用機制 當中性粒細胞與內皮表面的黏附分子接觸時,中性粒細胞被激活并釋放HBP;被釋放的HBP與內皮上的糖胺聚糖結合,導致選擇性蛋白激酶C(PKC)和Rho激活酶活化,以及鈣離子內流,引起內皮細胞骨架重組、細胞收縮變形,形成細胞間隙,導致內皮細胞屏障功能破壞、血管通透性增加,液體外流形成水腫和大分子外排增加[8]。循環中的白細胞通過破壞的內皮屏障外滲至感染部位。另外,HBP可靶向作用于內皮細胞中的線粒體,降低線粒體的膜電位[9]線粒體功能障礙是敗血癥誘發器官功能衰竭的重要作用因素[10]。HBP由中性粒細胞產生,亦可作為中性粒細胞的化學趨化因子,使更多中性粒細胞遷移至組織的感染部位;此時,大量(74%)貯存在嗜天青顆粒中的HBP被釋放到機體組織中,對多種細胞產生作用。HBP是一種多功能蛋白。首先,它可以趨化、激活單核/巨噬細胞,增加氧自由基的形成和釋放,起到殺菌作用;其次,可以通過旁分泌的形式結合特異的膜受體,激活并誘導單核/巨噬細胞合成和釋放非特異性的炎性因子,部分調節炎癥過程[11];另外,HBP可以誘導組織中成纖維細胞的遷移,在炎性反應的調節和傷口的愈合中起作用[12]、誘導平滑肌細胞的遷移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及發育[13]和角膜上皮細胞遷移[14]。然而,HBP引起這些細胞遷移的原因和機制尚不清除。最后,Fisher等[15]在研究中發現HBP還可誘導腎近端小管上皮細胞產生的IL-6的活化。
2 肝素結合蛋白在各系統、不同感染中的研究進展
2.1 HBP與呼吸系統 HBP通過與血管內皮上的糖胺聚糖結合黏附在肺微血管內皮單層細胞上,引起內皮細胞骨架重組,血管滲透性增加[8],大量白細胞及液體外滲至肺組織;在病原菌產物、煙霧等有害物質(如NO2)刺激下,巨噬細胞向肺組織遷移并釋放多種細胞因子,如:TNF-α、IL-8、IL-6、IL-1等;反過來這些細胞因子又可趨化中性粒細胞、T細胞、嗜酸性細胞等向肺組織遷移、聚積,這些細胞和炎性細胞因子是引起氣道炎癥慢性化和氣道嚴重損傷的重要因素。 研究證實HBP在肺部的聚積可誘導肺損傷;而從消耗中性粒細胞則可以完全消除了肺損傷,所以不論是急性肺損傷還是輸血相關肺損傷,血HBP濃度均明顯升高,可用來預測發生肺損傷的高風險患者[16]。另有研究指出血HBP水平在膿毒癥相關的ARDS患者及創傷后ARDS患者中亦呈現較高水平,且發現入院48 h內患者的HBP值對膿毒癥相關ARDS的預測價值最高,最佳臨界值為28.56 ng/ml[17]。而另一項納入278位(33人確診ARDS)入住ICU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果:發現入院時血漿HBP的濃度與ARDS的發生無相關性。雖然分析原因可能是未將胸片作為每日常規檢查,使ARDS患者漏掉,但HBP在其中的價值確實值得商榷[18];在近期針對AECOPD患者的研究發現,HBP有較高的診斷價值,特別是對痰培養陰性且臨床高度懷疑細菌感染AECOPD患者,血漿 HBP 水平比 PCT 更有抗生素應用指導意義[19]。不論在肺炎合并膿毒癥時,還是在呼吸機相關性肺炎時,血HBP較PCT均有更好的預測價值[20,21]。另有一組單中心前瞻性研究對179例胸腔積液患者胸腔積液的HBP水平進行檢測后發現,當HBP的截斷值為62.9 ng/ml時針對肺炎旁胸腔積液的診斷效能高,且明顯優于傳統的胸腔積液LDH、ADA、和TP水平,可作為一個新的標志物輔助胸腔積液鑒別診斷[22]。對于矽肺并發重癥感染患者中,HBP在矽肺三期中的AUC分別為0.932、0.977、0.964,高于WBC、CRP、PCT,有望成為矽肺重癥感染患者篩查及病程分析的檢查標志物[23]。支氣管擴張癥是呼吸內科常見疾病,主要致病因素為支氣管感染、阻塞和牽拉。Abo-Leyah等[24]對經胸部CT確診為支氣管擴張的121例患者進行了長達3年的隨訪后,并對他們痰上清液中的HBP濃度進行研究后認為,HBP可作為判斷支氣管擴張患者氣道炎癥和疾病嚴重程度的潛在生物標志物,同時指出HBP高于人群中位數與第一次住院和病情惡化的時間較多有關。
2.2 HBP與心血管系統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心血管系統疾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在我國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也給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其中,急性心肌梗死是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而炎性反應在急性心肌梗死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一項針對STEAMI的預測及預后的對照研究表明,認為HBP可作為預測STEAMI的敏感指標,且HBP水平越高,預示著患者的預后越差。而以臨界值8.55 ng/ml為標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則可降低病死率[25]。HBP參與了多種炎癥過程,且可誘導平滑肌細胞的遷移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及發育;另外,單核細胞在冠狀動脈粥樣硬化中起重要作用,而HBP可以趨化、誘導單核細胞活化,釋放炎性因子[26],破壞或侵襲硬化斑塊,引起急性冠脈綜合征。升高的HBP水平是心臟驟停后器官功能衰竭的早期指標,且心臟驟停后6 h和12 h血漿HBP水平顯著升高的患者預后不良[27]。Pan等[28]研究了心臟手術后并發心肌損害相關心源性心衰(myocardial injury-related cardiogenic shock,MIRCS)時血漿HBP的變化情況,指出血漿HBP是MIRCC的獨立危險因素,與肌鈣蛋白(cTnT)呈正相關。另有關于急性動脈夾層的研究指出血漿HBP陰性值對急性動脈夾層(AAD)早期篩查價值大,且HBP水平越高,AAD患者預后越差。急性腸系膜血管缺血性疾病主要是腸系膜動靜脈栓塞、血栓形成,繼發與低血流量狀態的血管收縮,其中腸系膜上動脈栓塞最常見(占40%~50%)。高通等[29]通過動物實驗表示血漿HBP水平在腸系膜缺血的第6小時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認為血漿HBP水平在急性腸系膜血管缺血模型中升高較慢,不過,但該研究選用的動物模型數量偏少(n<40),仍需進行大量的臨床研究。
2.3 HBP與泌尿系統 多項針對尿路感染的研究指出,尿HBP可作為對成人及兒童尿路感染的最佳診斷標志物,不同的是成人的尿HBP截斷值為69.2 ng/ml[30],而兒童的最佳截斷值則是>32 ng/ml[31]這2組研究差異(成人的尿HBP截斷值比兒童高2.16倍)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小兒機體防御能力弱,少量的炎性因子釋放即可產生比成人更明顯的炎性反應。然而在區分老年人無癥狀菌尿和尿路感染方面,尿HBP表現出比較差的特異性;但對老年人的癥狀性尿路感染,尿HBP具有較高的陰性預測值[32]。目前關于膿毒癥誘發急性腎損傷的機制,并不十分清楚,多數認為與血管滲漏/灌注不足、局部腎小管炎癥和細胞周期停滯的組合有關。并發現血漿HBP水平升高與急性腎損傷(AKI)發展風險增加有關[33]。考慮原因可能與HBP可能通過增加腎血管通透性(誘導腎小管上皮細胞產生IL-6,誘導炎性反應)和腎水腫(液體外流、水腫形成)直接損傷腎組織,改變腎小球濾過和腎小管的功能[34]有關。非泌尿系統感染所致膿毒癥患者的血漿HBP水平明顯升高、但尿HBP水平不一定升高,提示尿路感染患者在該局部感染灶存在中性粒細胞的活化。尿路結石是泌尿系統常見疾病,且上尿路結石發生概率大于下尿路;劉俊肖等[35]通過對64例上尿路感染性結石患者血漿HBP水平研究,認為HBP在上尿路感染性結石的預測中具有良好的真實性,對經皮腎鏡手術前抗生素的應用具有指導意義。另有一組針對腔內碎石術后并發尿膿毒癥的研究指出,血漿HBP可作為術后尿膿毒血癥的早起診斷指標,且其診斷效能優于PCT、CRP,以及白細胞計數[36]。
2.4 HBP與膿毒癥 膿毒癥是由感染引起的機體反應失調導致器官功能障礙;膿毒癥休克則是膿毒癥的一種表現形式——指在膿毒癥基礎上,合并有明顯的循環和細胞代謝異常,與白細胞的活化、內皮細胞損傷和血管通透性增高相關,病死率顯著高于一般膿毒癥。全球疾病負擔研究指出,2017年全球范圍內有11萬例膿毒癥相關死亡,占全球死亡總數的19.7%。膿毒癥的早期識別及疾病的預測至關重要[37]。多項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及薈萃分析證實血漿HBP是診斷及預測疾病進展、發生感染相關器官功能障礙較好的生物標志物,其敏感性和特異性優于PCT、CRP、WBC及LAC等;且隨著血漿HBP水平增加,危重感染的風險增加[38-40]。新生兒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免疫系統發育不完善,抵御感染的能力低下,膿毒癥在新生兒的致死率高達11%~19%[41],早期識別新生兒膿毒癥并積極治療對降低新生兒病死率顯得尤為重要。鄧永超等[42]將92例新生兒分成一般膿毒癥(37例)、嚴重膿毒癥(39例)和膿毒癥休克(16例),對3組間的血漿HBP、PCT及hs-CRP進行了比較后發現,嚴重膿毒癥組及膿毒癥休克組的血漿HBP水平顯著高于一般膿毒癥,而PCT及hs-CRP在3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且HBP診斷新生兒膿毒癥的曲線下面積大于PCT及hs-CRP,認為血漿HBP在新生兒膿毒癥的早期診斷以及膿毒癥分級方面有指導價值,且優于PCT及hs-CRP;另有一項針對小兒膿毒癥的研究指出,血漿HBP在膿毒癥被診斷前的72 h已開始升高,直到診斷前24 h才被PCT升高替代,認為HBP具有較寬的診斷窗口,可作為早期預測指標之一[43]。這兩項研究說明血漿HBP對兒童膿毒癥的早期診斷有預測、指導意義;但兒童方面的研究偏少,可作為后期研究的方向。 另外,發熱患者血漿HBP水平升高與短期病死率增加顯著相關—血漿HBP水平高于建議截斷值(15 ng/ml)的患者28 d病死率增加4倍;且隨著時間逐漸下降的血漿HBP濃度提示較好的預后[4]。但另一項研究指出血漿HBP水平作為創傷后敗血癥的早期生物標志物的辨別特性差[44]。生命器官組織微循環灌注不足是多數休克共同的發病基礎。HBP可介導血管通透性增加,液體及大分子物質外流,可能參與了休克的發生。多項針對膿毒癥休克患者研究發現HBP可能是誘發膿毒性休克的重要介質,且血漿HBP濃度與休克嚴重程度呈正相關;還發現膿毒性休克和其他原因導致的休克患者,HBP濃度無差異,說明血漿HBP的濃度高低與疾病本身無關、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相關[38]。肖薇薇等[45]通過動物模型研究,認為血漿HBP膿毒隨著大鼠膿毒癥嚴重程度增加而增加,而且指出抗生素的應用可以減輕血漿HBP的含量,具有臨床推廣應用價值。
2.5 HBP與其他感染 HBP是一種多功能蛋白,它參與了多種炎性反應。急性細菌性腦炎是一種嚴重的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性疾病,成人及兒童均易發病。腦脊液病原菌培養是確診細菌性腦膜炎的金標準。然而,抗生素的使用降低了微生物培養的準確率,Kandil等[46]在HBP對急性細菌性腦膜炎診斷的臨床研究中發現,即使在使用過抗生素治療的急性細菌性腦膜炎患者中,血漿HBP及腦脊液HBP均顯著升高,為臨床診斷及治療提供依據。另有多項針對急性細菌性腦膜炎的研究指出,血漿HBP在診斷及區分急性細菌性腦膜炎和中樞神經系統其他病原的感染時均有較理想的表現;且腦脊液HBP的升高程度與疾病嚴重程度及預后相關[47,48]。重癥胰腺炎病情進展迅速,治療困難且病死率高;合并細菌感染時,病死率會上升至少3倍。多項在急性重癥胰腺炎繼發感染的研究中也指出血漿HBP可作為診斷指標,且聯合PCT及IL-8共同檢測,可降低重癥胰腺炎繼發感染誤診及漏診的發生[49,50]。邱飛等[51]將142例重癥胰腺炎患者分成2組,繼發細菌感染組68例,未繼發細菌感染組74例,同時比較了2組血漿HBP及PCT,結果表示重癥胰腺炎繼發細菌感染組血漿HBP水平及PCT值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HBP與PCT呈正相關性,且HBP的ROC曲線下面積(0.93)大于PCT的ROC曲線下面積(0.8),認為血漿HBP更有利于評估重癥胰腺炎繼發細菌感染,可作為臨床指導臨床抗生素選擇的指針。丹毒是由溶血性鏈球菌引起的淺表皮膚的感染,表現為皮膚的強烈炎癥,伴有皮膚組織的水腫及疼痛的紅斑;鏈球菌M1蛋白可激活中性粒細胞,釋放HBP,誘導炎性反應。一項對12例單側下肢丹毒患者進行研究,發現HBP存在于從感染和紅斑出獲得的皮膚活檢中、而健側肢體均未檢測到HBP;考慮HBP可能與感染皮膚的水腫形成有關[4]。史克禮[52]通過對36例惡性腫瘤患者早期細菌感染的患者進行對照研究后指出,血漿HBP在這些患者中有較高的敏感度(91.67%)和特異性(80.56%),當聯合PCT時診斷的敏感度(97.22%)和特異性(83.33%)更高,臨床值得推廣。在60例急性盆腔炎患者的臨床研究中發現血漿HBP水平在細菌感染組的水平明顯高于非細菌感染組(P<0.05),且隨著細菌感染組疾病的嚴重程度增加而顯著增高,認為HBP不僅可以作為細菌感染性急性盆腔炎診斷及鑒別診斷的生物標志物,還可以用于判斷病情的嚴重程度,也可作作為評估治療效果的依據[53]。HBP作為一種多功能蛋白,在多中疾病都顯示了較好的預測及指導價值,但這些疾病的病原菌多系細菌感染;近日國內有一項關于血漿HBP在兒童流感方面的研究,對169例單純病毒性流感患兒及31例病毒性流感合并細菌感染的患兒進行對比發現,病毒性流感合并細菌感染組血漿HBP水平顯著高于單純病毒性流感患兒(P<0.01),敏感度及特異性分別為0.98、0.94;同期進行比較的PCT及CRP在2組間無統計學意義,認為HBP在病毒性流感合并細菌感染組有較高的早期診斷價值,對臨床醫師在病毒性流感時抗生素的選擇有一定的指導意義[54]。
3 肝素結合蛋白與靶向治療
血管通透性適度增加是正常炎性反應過程的一部分;然而,過度增加的血管通透性可導致有效循環血容量減少,肺泡中液體聚積及循環的不穩定性。HBP是PMN導致血管通透性改變的主要介質,是內皮細胞滲透的強誘導劑,在增加血管滲透方面起著重要作用[55];減少HBP的釋放可能降低HBP介導的血管通透性的增加;HBP可作為治療膿毒性休克、ARDS及其他有血管滲透性增加疾病的新的研究方向。HBP由中性粒細胞產生,抑制中性粒細胞的活化也可阻止HBP介導的血管通透性的增加;但中性粒細胞在免疫應答中起著許多重要的作用,抑制/阻斷中性粒細胞活化可能引起其他不良反應;故靶向干預HBP及其受體的相互作用可能效果更好。HBP是一種陽離子蛋白,聚陰離子的硫酸葡聚糖可完全阻止HBP對內皮通透性的影響。HBP可通過誘導選擇性蛋白激酶C和rho激活酶途徑的活化增加內皮通透性;非選擇性蛋白激酶C抑制劑和rho激酶抑制劑也可減弱HBP誘導的通透性的增加。肝素是一種與HBP結合的多功能帶負電荷的糖胺聚糖;普通肝素和低分子肝素在體外和小鼠模型中均阻斷了HBP誘導的內皮通透性、阻斷了HBP的線粒體作用和HBP誘導誘導的腎小管上皮細胞對IL-6的釋放[56]。有薈萃分析指出肝素治療可降低膿毒性休克的死亡率,這可能是其產生治療作用的重要機制[57]。另外,β2整合蛋白拮抗劑和肽Gly-Pro-Arg-Pro也可阻斷鏈球菌M1蛋白誘導的HBP的釋放[4]。內皮素-1受體抑制劑在豬內毒素血癥模型中也表達出了對HBP水平的抑制及HBP介導的通透性的降低[58]。 中性粒細胞是病原體入侵宿主后最早被募集的細胞;HBP預先貯存在中性粒細胞的分泌囊泡中,是最先被動員且惟一被釋放到環境中的顆粒蛋白,在血管滲透及水腫形成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健康人血中的HBP水平很低,一般不超過10 ng/ml。但當感染發生時,HBP水平會隨著病情的嚴重程度變化;多項研究指出HBP與多種感染有關,在多種感染中均有升高,且認為在預測重癥感染及感染性休克的發生發展及預后有較好的價值;可以作為臨床快速判斷危重病情的有效生物指標;有待繼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