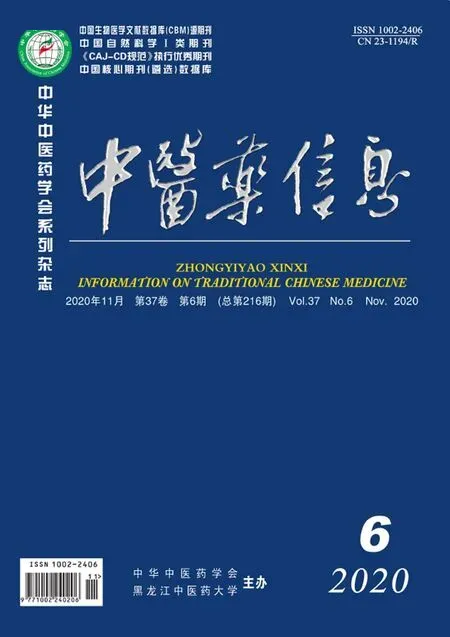從“一氣周流”論治血痹
周聰,譚艷,肖凡,劉秀,陳昱彤,喻嶸
(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 長沙 410208)
血痹病名現存最早可見于《黃帝內經》,在《靈樞·九針論第七十八》篇中記載有“邪入于陽則為狂,邪入于陰,則為血痹”。《靈樞·痹論》篇載:“陽入于陰,則為血痹”,《素問·逆調論》篇言“營氣虛則不仁”,血痹多是風寒之邪入侵,留于血分,耗傷人體氣血,發為麻木疼痛。至張仲景《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篇,則詳細論述了血痹的成因、臨床癥狀及鑒別要點。
黃元御是清代乾隆時期的著名醫家,尊經派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素靈微蘊》《四圣心源》《長沙藥解》《傷寒說意》《玉楸藥解》《傷寒懸解》《金匱懸解》和《四圣懸解》被稱為“黃氏醫術八種”,其中《四圣心源》是其“一氣周流”思想的主要體現[1]。他在書中提出中氣為一身之氣的樞軸,中氣運轉失常是疾病產生的原因,若陽氣不能上達導致“營瘀木陷”,引起周身不得充養,則會產生血痹,所以應重視培土建中、調理氣機,在治療時,采取“滋營血而清風木”“宣營衛而行瘀澀”的治法。
1 “一氣周流”的氣運行理論
黃元御認為氣左升右降的運動產生人體的各種生命活動。由于“土樞四象”,故在其過程中由脾胃中氣統領心、肝、脾、腎諸氣的升降出入,脾氣左旋則生木,木升而極則為火,胃氣右旋則為金,降則化水為寒。而中氣又產生于祖氣,祖氣抱含陰陽,清升而濁降,于是循環往復,左升右降,帶動全身的氣機。
1.1 人身之氣與中運之氣
氣是一種無形而又運動不息的精微物質,由精所化生,有升降出入等運動。人身之氣又叫“祖氣”。《四圣心源·精氣本原·臟腑生成》說:“陰陽肇基,爰有祖氣,祖氣者,人身之太極也”[2],祖氣來源于先天,是由先天之精化生的先天之氣,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決定人的天賦秉性。
中運之氣又叫“中土之氣”,是指先天祖氣所化生的脾胃之氣,就如《四圣心源·精氣本原·臟腑生成》所說:“祖氣之內,含抱陰陽,陰陽之間,是謂中氣”,先天祖氣以清濁升降而分陰陽,陰陽交感和合而化生中氣。中氣既由祖氣化生,就繼承了祖氣的部分功能及作用,亦有升降出入的變化,統領氣機。脾胃在五行屬土位于中央,土者能蘊萬物,為四象之母,所以中土之氣是氣機升降的樞紐。故《四圣心源·精氣本原·臟腑生成》說:“清濁之間,是謂中氣,中氣者,陰陽升降之樞紐,所謂土也”“中者,土也,土分戊己,中氣左旋,則為己土”“中氣右轉,則為戊土,戊土為胃,己土為脾”。土居中央,以灌四滂,通過斡旋氣機以助運氣血,氣血充足又可滋養祖氣,先后天之氣充盛則百病不生即所以“胃主受承,脾主消磨,中氣旺則胃降而善納,脾升而善磨,水各腐熟,精氣滋生,所以無病”。升降之間,中氣為之樞紐,中氣既為樞紐又是全身之氣運行的動力,“四象即陰陽之升降,陰陽即中氣之浮沉”。正是因為有氣機的升降出入才使得全身之氣暢行無阻、周流不息。若中氣運行受阻,五臟六腑都會受損是故“腎水下寒則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滯而氣病,神病則精怯而不寧,精病則遺瀉而不密,血病則凝瘀而不流,氣病則痞塞而不宣”。中氣不行,升降反作,則四維無所適從,是以氣血津液皆受病。
1.2 營氣與衛氣
黃元御認為營衛之氣由脾胃化生,《傷寒懸解·營衛殊病》[3]“脾為生血之本,胃為化氣之原也”,脾胃為中氣之所在,氣血之所化生也。營衛是氣血分布于經絡部分的名稱,其實質是氣血。《四圣心源·天人解·氣血本原》說“營衛者,經絡之氣血也”,氣血本化生于脾胃,但其運行輸布依賴于肝、肺兩臟中氣的有序升降是肝肺功能的基礎,肝者藏血,肺者藏氣,因此,營衛之氣實則中氣所化生。中氣的升降又以營升衛降的形式體現在營衛二者之上。營衛二氣與脾胃、肝肺和中氣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4]。
衛氣能顧護體表,有“溫分肉”“肥腠理”之功,營氣能充養周身,有“榮四末”“養臟腑”之能。若中氣受損,脾胃失調,化生營衛不足,或氣機受阻,營衛運行受限,則發而為病。營衛為經絡之氣血,營衛不足則血弱氣阻,導致營血凝澀,衛氣郁遏,四肢肌肉不得溫煦而漸生麻痹,久而枯槁無知,及至不仁。營衛二氣也有自己的運行方式,《靈樞·營衛生會》篇說“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如環無端,五十而復大會”,營衛不僅有環體的運行方式,還有升降運動,黃元御認為營雖屬陰,但卻為肝血所統,稟肝升散之性而上行,衛雖屬陽,卻為肺氣所統,稟斂降之性而下行。所以營衛二氣也有上升下降的氣機運動。
2 血痹的病因病機
血痹好發于尊榮人,這一類人因其養尊處優,往往不事勞動、嗜食肥甘,形有余而氣血不足,腠理不密,故動輒汗出,易招致虛邪賊風。仲景在《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篇詳細論述了血痹的成因、臨床癥狀及鑒別要點,“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澀在寸口,宜針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將營衛不足作為首要病因,外邪侵襲作為重要因素,并提出其脈證“脈自微澀在寸口”“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脈微為衛氣不行,脈澀為營氣瘀滯不足,脈緊為寒邪外束,衛氣不行則皮毛不固,營氣瘀滯不足則肌肉不充,寒邪外束則陽閉而不上達,營衛氣血不足則不能充養四肢百骸,久而久之則會出現肌肉枯槁無知,身體不仁,而成血痹。又以輕證重證分而論之,首次提出治療血痹的針刺法和黃芪桂枝五物湯。血痹的臨床表現類似于風痹,有局部肢體麻木脹痛感,故宜治益氣溫陽、行血通痹。
黃元御認為,血痹和虛勞的病因均是脾胃虛弱。“一氣周流”學說認為,人身之氣皆統于肺,人身之血皆統于肝,其皆源于脾胃中氣,在臟腑曰氣血,在經絡則曰營衛,故血痹之營衛不足,即是脾胃中氣不足。脾胃為全身氣機升降之樞紐,若中樞受損則會出現氣機亂作,衛氣不行,營氣不充。脾主四肢肌肉,脾胃共為后天之本,是水谷精微化生之所,能充養四肢百骸。若脾胃之氣充足,化生氣血旺盛,則身體健壯,賊邪弗能害也。脾胃虛弱則化生無源,脾胃之氣不足,化生營衛之氣衰,身形之虛加上虛邪外入,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故招致而為病。而尊榮人之所以患血痹不僅是因為脾胃虛弱,還有脾胃不足所導致的“營瘀木陷”。營血行于四肢經絡,若營血郁滯勢必會阻滯四肢經絡氣血的正常運行,此時邪氣亦留而不去則為血痹。肝木統攝營血,營血的異常變化會影響肝的升發之性,致使肝木不得左旋而下陷,氣機塞滯,陽氣不能通達,邪氣易犯,合而為病。
3 “營瘀木陷”與溫陽益氣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5]有云:“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張,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氣分陰陽,陽氣則司衛外,專以抵御外邪,驅邪外出,有如正氣一類。若衛氣的生成或運行出現異常,則會引起衛外功能失常,易感受外邪。邪氣阻滯,進一步困厄氣機,邪留于營血,則營氣阻梗,不能濡養周身。中氣不能運轉,升降功能失常,致使一身之氣不暢,四肢肌肉不得其養,日久則麻木不仁。根據黃元御的理論,人體之氣,肝氣主升發,肝木調達則氣血調和。而血痹病在四肢經絡營血瘀滯,營為肝木所統,營血為病則肝木必為其所累,而其病本在營瘀,故宜疏發四肢郁滯之營血,升散下陷之肝木。此乃溫陽益氣、通絡行瘀法之正要。
輕時可針引陽氣,通過針刺的方法激發人體正氣,增強衛外之陽氣,升提肝木之氣,通行營血,來達到祛除邪氣的目的。黃芪桂枝湯溫陽益氣之法就是通過黃芪桂枝的相須作用增強人體衛外之功,二者合用既能祛邪又能溫陽通痹,兩擅其功。黃元御認為[6]桂枝入肝經而能走血分,通達經絡之痹塞,宣發營陰之郁滯,舒筋絡,解攣急,利關節,能升發清陽,救肝木下陷于寒水,散外邪于表。黃芪走經絡而益營,善達皮腠,專通肌表;清虛和暢,專走經絡,而益衛氣。逆者斂之,陷者發之,郁者運之,阻者通之,是燮理衛氣之要藥,亦即調和營血之上品,衛旺則發,衛衰則陷,陷而不發者,最宜參芪,助衛陽以發之。生姜走肝脾而行滯,宣達營衛,行經之要品。芍藥入肝家而清風。營衛二氣皆來源于脾胃,若脾胃損傷較重,或受邪日久,營血虛耗,則在溫陽益氣之上又加和血通脈之法。白芍善補虛而生新血,與桂枝合用又有調和營衛之功,大劑生姜宣發在表之邪,又助白芍桂枝活血通絡之功。大棗、芍藥,滋營血而清風木,姜、桂、黃芪,宣營衛而行瘀澀,倍用生姜,通經絡而開閉痹也。而且現代藥理學研究也表明[7],風類藥如生姜等,具有增強活血藥的作用,所以生姜在本方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4 結語
血痹涵蓋的疾病范圍較廣,病情復雜,病變多樣,如周圍神經病變、周圍血管病變、不安腿綜合征等都可歸屬于血痹的范疇。張仲景雖在《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篇提出黃芪桂枝五物湯的治法及病機闡釋,但其言簡意賅,經后世醫家黃元御的論述,進一步拓寬了血痹病機和黃芪桂枝五物湯組方原理的理論支撐。本文從“一氣周流”理論出發,以“營瘀木陷”為血痹病機的主要切入點,明確溫陽益氣通絡法的理論基礎,同時還探討黃元御治病重視護脾胃中氣的觀點,從全新的角度理解血痹的證治機理。從現代藥理學及臨床研究發現,黃芪五物湯對關節疼痛性疾病、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等均有良好的療效[8]。所以其他痹證及四肢疼痛麻木性疾病、虛弱性疾病也可采取此種治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