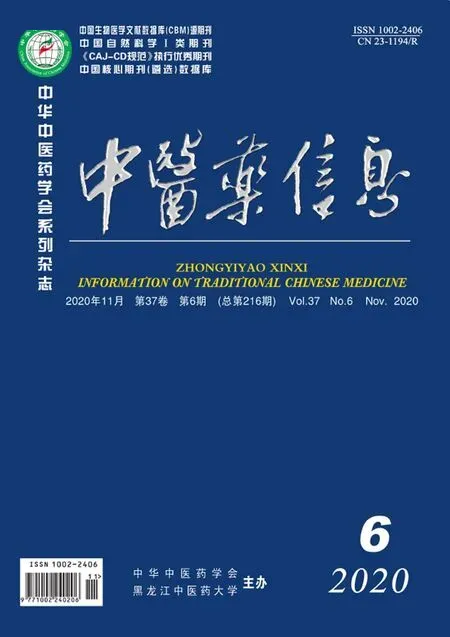透邪解毒法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踐
蔡秋杰,沈趙留,陳志威,張華敏,王樂,曹洪欣
(1.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藥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700;2.云南省德宏州中醫醫院,云南 芒市 678400;3.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4.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北京 100700;5.中華中醫藥學會,北京 10002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爆發,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顯著成效,已經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然而全球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疫情將在秋、冬季節二次全球爆發已成為共識[1]。疫情防控初期曹洪欣教授運用透邪解毒法治療不同階段的新冠肺炎患者,取得良好療效,為深化對新冠肺炎病機特點、證候特征與治則治法的認識,整理分析如下。
1 發病與病機特點
新冠肺炎是一種傳染性較強,以呼吸道病變為主的流行性疾病。其病因病性以“寒”為主,間挾濕邪,寒濕并作,屬“寒疫”“濕疫”范疇[2]。寒邪疫毒染易,病邪既有毒邪致病性質,又具有寒邪發病特點,且因地域與人群體質差異,發病后形成“寒、濕、毒、熱、虛”等證素特點[2-3],病機有外襲內伏之合,病勢有緩急不同。
1.1 首要病因“疫毒”
新冠肺炎的病因為“疫毒”,致病特點與主要表現:一是暴戾猛烈,體虛之人觸之即病;強壯之人接觸可即發病或邪伏入里而漸發,初起患者病毒核酸檢測多為陰性,雖無癥狀但邪漸入肺,出現胸部CT炎性改變;二是具有流行性和傳染性,其性穢濁,交相染易,表現為較以往的呼吸道傳染病傳染性更強,潛伏期長,病勢轉變迅速,纏綿難愈;三是毒邪致病多化火,損傷肺絡或迫血妄行,火熱灼津致瘀,或離經之血成瘀,故患者有咳痰帶血癥狀,死亡病例解剖發現肺部有淤血的現象[4];四是毒邪傷肺挾濕化痰,痰濕阻肺、肺失宣降則氣促喘憋,毒火煉液故痰少而黏,難以咳出而口干,與報道解剖病例肺部見大量黏凍樣物質一致[4]。
1.2 主要病性“寒”邪
新冠肺炎疫情發病流行于己亥冬、庚子春時節,冬令寒水主氣,春初寒氣未退,寒疫為陰邪易傷陽氣,故部分患者發病初起肢冷、惡寒、甚則寒戰、低熱、乏力較甚;寒邪凝滯收引,阻礙氣機運行,故發病多見肌肉酸痛。此外,部分患者服抗生素、抗病毒藥或清熱解毒中藥后,更傷脾之陽氣,氣機升降失常,出現腹瀉、嘔吐等癥狀。
1.3 常挾“濕”邪
全球疫情始于秋冬、將于秋冬二次爆發已成共識,縱觀全球新冠肺炎爆發的地區,多見海鮮市場和屠宰場聚集性爆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指出,這類地點“有共同的潮濕、低溫環境,適合病毒存活”。綜合分析環境特征、發病特點、癥狀與舌象、脈象等,新冠肺炎病因病性以“寒”為主,間挾濕邪,寒濕并作。寒邪與濕邪同為陰邪,易傷陽氣,濕邪困脾、清陽不升故見舌淡胖苔白膩、頭暈、嘔惡、胸悶等癥。
1.4 傳變迅速,化火致瘀
疫毒致病,易從熱化致瘀,邪熱與瘀結既是疫毒發病的病理產物,又是致病原因而使癥狀復雜多變,部分患者高熱不退、毒熱灼傷肺絡致咳血或痰中帶血;部分患者舌淡紫或紫暗,伴見口唇青紫、胸悶、胸痛等癥狀,胸部CT可見肺部出現磨玻璃樣、云霧狀、纖維化樣改變。
1.5 疫毒傷氣,正虛邪伏
寒疫毒邪挾濕化熱致瘀,發病過程耗傷人體正氣,正氣不足無力抗邪,一是體虛之人或年高體虛或素體多病,觸之即病,發病更傷陽氣則迅速轉為危重癥,甚至死亡;二是邪氣傷正,正不勝邪,正邪交爭纏綿難愈,患者病毒核酸檢測陰性陽性反復;三是正虛邪伏,部分患者病毒核酸檢測陰性半月后發病[5]、或經治療病毒核酸檢測多次轉陰、肺部CT檢查正常,復現病毒核酸陽性等復雜現象[6]。
2 透邪解毒法及應用
透邪解毒法是中醫臨床常用治法之一,曹洪欣教授結合2003年SARS發病與臨床特點,提出運用該法治療六淫邪氣或疫毒邪氣侵襲導致的外感病及疫病并進行深入系統研究[7-8],透邪解毒法注重驅邪與扶正并舉,使邪有出路,正氣得復。新冠肺炎疫毒之邪勢猛,侵犯人體,或感邪即發,或感而不發,或病勢纏綿,或愈后復發,取決于毒邪與人體正氣相搏的狀況,人體正氣不足或毒邪勢盛則發病,臨床上對各種疫毒,“解毒”為首要治則,否則毒邪極易化熱而熱毒壅盛。無論感而即發或毒邪內伏均宜透邪解毒,一是透邪解毒,針對疫毒邪氣性質,從溫解論治,截斷病邪傳變路徑;二是顧護正氣,扶正祛邪,防止疫毒侵犯臟腑與疫病愈后復發。臨床上新冠肺炎癥狀表現錯綜復雜且變化迅速,以透邪解毒與扶正并舉為主,根據證型及癥狀變化加減用藥,隨證治之,能顯著提高臨床療效。
2.1 疫毒寒邪襲表
癥見惡寒、乏力、周身疼痛,苔白或白膩,脈浮或浮緊者,治以辛溫解肌、透邪解毒,方選荊防敗毒散加減。藥物組成:荊芥15 g,防風10 g,羌活15 g,柴胡15 g,獨活15 g,川芎15 g,桔梗10 g,前胡10 g,枳殼10 g,茯苓15 g,生甘草10 g。咽痛者加金銀花30 g,連翹30 g,增強解毒之力。
2.2 邪入少陽,邪正交爭
以高熱反復或寒熱往來為特點,兼見咽痛、咳嗽、周身酸痛、頭暈、惡心、苔白、脈弦,治以透邪解毒、和解少陽、扶正驅邪,方以小柴胡湯合桂枝湯加減。藥物組成:柴胡15~25 g,黃芩15 g,清半夏9 g,黨參15 g,桂枝10 g,白芍20 g,金銀花30 g,連翹30 g,浙貝母10 g,黨參15 g,茯苓15 g,生甘草10 g。
2.3 邪毒化熱,毒熱壅盛
以高熱不退、惡寒或寒戰、咳吐黃痰、氣促胸悶、乏力日甚、舌淡紫或舌紅、苔黃膩或黃厚為主要表現者,治以透邪解表、清熱解毒,方用小柴胡湯合大青龍湯化裁。藥物組成:柴胡15~25 g,麻黃10 g,桂枝6 g,黃芩15 g,法半夏9 g,苦杏仁10 g,生石膏30 g,連翹30 g,蒲公英30 g,生甘草6 g。
2.4 疫毒化火傷陰
癥見干咳、氣促、無痰或痰少而黏、咽癢而痛、舌淡苔黃而干,治以透邪解毒、養陰潤肺,方用小柴胡湯合桑杏湯加減。藥物組成:柴胡15 g,黃芩15 g,法半夏9 g,連翹20 g,桑葉15 g,浙貝母15 g,淡豆豉10 g,生梔子10 g,苦杏仁10 g,北沙參10 g,生甘草10 g。
2.5 濕邪疫毒化痰,痰濕阻肺
癥見咳嗽,咳吐白色大量粘痰,咳甚則嘔惡,伴氣促、胸悶,舌苔白膩或黃膩,治以透邪解毒、清肺排痰,治以小柴胡湯合千金葦莖湯加減或柴胡陷胸湯加味。藥物組成:柴胡15 g,黃芩15 g,法半夏9 g,連翹20 g,瓜蔞20 g,桔梗10 g,生薏苡仁20 g,蘆根10 g,生甘草10 g。
2.6 毒熱入胃與寒邪傷脾
寒熱錯雜于中焦,見腹瀉、腸鳴、腹脹、呃逆、惡心等,治以透邪解毒、寒熱平調、調和肝脾,方用小柴胡湯和半夏瀉心湯加減。藥物組成:柴胡15 g,黃芩15 g,法半夏9 g,連翹20 g,黃連10 g,干姜10 g,生甘草10 g。
2.7 毒傷氣陰,氣陰兩虛
癥見心悸、氣短、胸悶、乏力、動則尤甚,治以透邪解毒、益氣升陷,方用小柴胡湯與升陷湯化裁[9]。藥物組成:柴胡15 g,黃芩15 g,法半夏9 g,連翹20 g,麥冬10 g,桔梗10 g,升麻10 g,生黃芪20 g,生甘草10 g。
3 驗案舉隅
3.1 病例1
陳某,男,17歲,浙江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家屬、密切接觸者。
2020年2月3日初診:因“發熱1天,胸部CT提示肺下葉背段胸膜下見片狀影,邊界模糊,雙肺肺紋理增多”于2020年2月1日收住云南省瑞麗市某定點醫院。經阿比多爾片0.2 g,日2次口服;布洛芬緩釋膠囊300 mg,日3次口服等常規治療,癥狀未見好轉。發熱,體溫37.9 ℃~38.5 ℃,流清涕,量多不止,胸悶,呼吸急促,咳嗽、痰白量多,惡心嘔吐,咽干,腹脹滿,便溏,飲食正常,精神尚可,舌質淡紅,舌苔薄白。辨證為外感疫癘,邪入少陽。治以透邪解毒、和解少陽、扶正祛邪。方用小柴胡湯化裁:柴胡20 g,黃芩15 g,法半夏9 g,黨參15 g,茯苓20 g,葛根20 g,蟬蛻15 g,荊芥15 g,金銀花20 g,連翹20 g,桂枝10 g,藿香12 g,厚樸15 g,甘草10 g,生姜3 g。2劑水煎服,每日3次口服。
2020年2月5日二診:患者服藥一次熱退,咽干、鼻涕量多不止等癥狀好轉,精神佳,飲食睡眠尚可,二便調。2月3日停用布洛芬緩釋膠囊、2月5日停用阿比多爾片,繼用上方2劑水煎服,每日3次口服。
2020年2月6日,患者癥狀消失,囑其將已有中藥服完。2月7日、9日核酸復查兩次陰性。2月8日肺CT復查,對比2月1日右下肺感染灶吸收消失。隨訪半年,無明顯不適。
按語:患者年輕男性,感受新冠肺炎疫毒,邪入少陽,故以小柴胡湯截斷病勢、透邪外出,以辛開苦降,寒熱并用,和解表里,透邪轉氣而驅邪氣外出,并截斷邪氣入里傷及臟腑;針對寒邪病邪及致病傷陽的特性,加桂枝、荊芥辛溫解表助陽、葛根辛甘升陽;針對疫毒,重用金銀花、連翹佐以浙貝母解毒痰,蟬蛻疏散助透邪之力;因毒邪累及胃腸,故用藿香、厚樸化濕和胃;兼用黨參、茯苓、生甘草等扶正化濕驅邪、調和諸藥;全方寒熱并用,解毒化痰,宣肺益氣,共奏截斷病勢、扭轉病機、扶正助陽、透邪外出之功效。
3.2 病例2
趙某,女,52歲,武漢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家屬、密切接觸者。
2020年2月9日初診:因“發熱2日”,患者于1月28日收住武漢某定點醫院,肺部CT顯示:雙肺下葉感染。經連花清瘟膠囊、金葉敗毒顆粒、鹽酸阿比多爾片、昔洛韋、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等藥物治療(具體用量不詳),低熱4日后,繼則反復高熱7日,上午體溫37.3 ℃,午后至夜間體溫38 ℃~39 ℃,癥狀未見明顯好轉。2月2日肺部CT顯示:雙肺下葉感染,較1個月28日有進展,右側胸膜局部增厚,粘連;2月7日肺部CT顯示:與2月2日結果一致。1月30日、2月4日、2月7日核酸檢測陽性。既往慢阻肺、頻發早搏史。現用莫西沙星0.4 g加入0.9%氯化鈉100 mL,每日1次靜脈滴注、人血白蛋白50 mL(10 g),每日1次靜脈滴注。癥見咳嗽陣作,痰粘難咯,呼吸急促伴痰鳴音,心悸,活動后胸憋悶、胸痛。血氧飽和度90%,吸氧后仍在92%~94%之間。舌淡紫,苔白膩。辨證為外感疫毒,濕邪疫毒化痰,痰濕阻肺。治以透邪解毒、清肺化痰。以柴胡陷胸湯加味,組方:柴胡15 g,法半夏9 g,瓜蔞15 g,半枝蓮20 g,桔梗10 g,浙貝母10 g,北沙參15 g,麥冬15 g,茯苓20 g,魚腥草30 g,桂枝10 g,黃芪30 g,杏仁10 g,生甘草10 g,生姜5 g。5劑,水煎服,分早晚服。
2月15日二診:服藥1劑后熱退,5劑后呼吸急促不顯,咳嗽明顯好轉,活動后胸悶、胸痛減輕,偶心悸,乏力,氣短,肢冷。2月13日肺部CT顯示:肺部炎癥較前吸收,核酸檢測陰性,血氧飽和度95%~97%。2月11日停服莫西沙星、人血白蛋白等藥。舌淡稍紫,苔白。辨證為疫毒邪氣漸去,正氣未復,氣陰兩虛。治以益氣升陷、透邪解毒。以升陷湯合柴胡陷胸湯加味,組方:生黃芪30 g,麥冬15 g,桔梗10 g,升麻10 g,柴胡15 g,浙貝母10 g,茯苓15 g,杏仁10 g,半枝蓮20 g,瓜蔞15 g,川芎15 g,赤芍15 g,苦參10 g,生甘草10 g。7劑水煎服,分早晚服。
2月16日、18日核酸檢測陰性。2月18日肺CT復查,肺部感染灶基本吸收。后隨訪半年未復發。
按語:患者中年女性,既往慢阻肺、早搏史。素體心肺兩虛,感染新冠疫毒后,遷延不愈。患者素體正虛,患病初起大量抗生素及苦寒中成藥,損傷陽氣,無力驅邪,寒疫邪毒入里化熱,出現午后及夜間高熱反復、咳嗽嚴重,痰粘難咯;素體心肺兩虛,疫毒進一步損傷心肺,大氣下陷,因虛致痰、致瘀,痰瘀互結,見呼吸急促伴痰鳴音,心悸,活動后胸憋悶、胸痛。急則治其標,初以柴胡陷胸湯加味,透邪解毒、清肺化痰,給邪氣以出路。用魚腥草、半枝蓮增強清肺解毒之功,北沙參、麥冬、浙貝母、杏仁養肺陰止咳化痰,桂枝溫陽驅寒邪疫毒又防苦寒藥物損傷陽氣,黃芪、茯苓、生甘草、生姜扶正驅邪。緩則治其本,邪氣漸去,扶正為主,兼清痰瘀,治以升陷湯合柴胡陷胸湯加味。生黃芪,麥冬,桔梗,升麻,柴胡益氣升陷,半枝蓮清肺余熱,杏仁止咳祛痰;茯苓,生甘草扶助正氣;苦參祛痰濕而寧心定悸;赤芍、川芎活血行氣,配合浙貝母、瓜蔞共奏痰瘀同治之功。
4 結語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中醫藥處于不斷深化認識與探索有效防控方法的過程。中醫藥認知疾病的模式與幾千年防控疫病的理論與實踐,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奠定堅實基礎。本文通過新冠肺炎治療實踐,證實透邪解毒法具有良好的退熱效果,對改善臨床癥狀、促進肺部炎性改變吸收、促進病毒核酸檢測轉陰、縮短病程具有積極作用,特別是控制輕型向重癥轉變、控制并發癥等作用優勢凸顯。深入探討新冠肺炎的發病和病機特點、證候特征與辨證論治思路,對豐富中醫疫病理論與實踐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