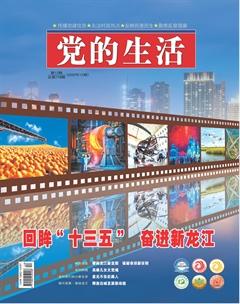雪冷血熱·第24章這是最后的斗爭
張正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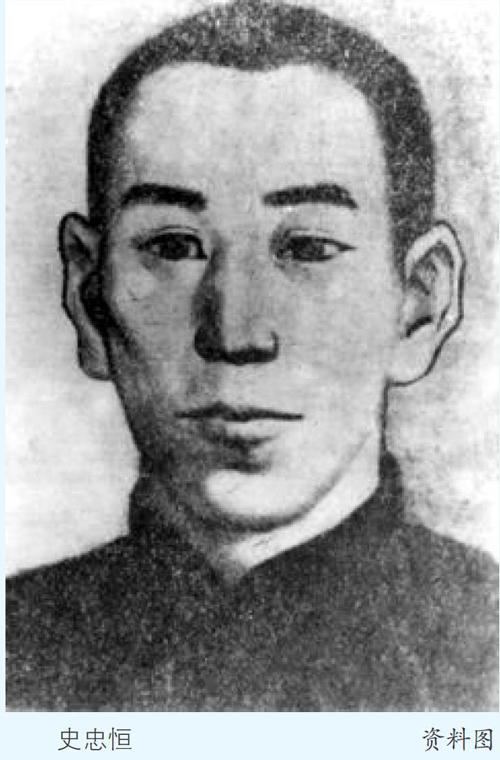
第24章 這是最后的斗爭
兩位軍政治部主任
李學忠,又名李宗學,1910年生于山東省,十多歲闖關東謀生,在磐石縣參加革命活動。九一八事變后,他被派往蘇聯學習,1934年冬回國。1935年2月,他被選為東滿特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3月,任二軍獨立師政治部主任;5月,任軍政治部主任。
8月,李學忠率二團的兩個連南征,到濛江縣那爾轟與一軍會師。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舉動和成功——兩大游擊區溝通聯系,兩個軍協同作戰,并為后來組建一路軍打下基礎。
已知的一次重要戰斗是獨立師成立不久,在敦化縣大蒲柴河與敵遭遇。李學忠帶領九個人掩護主力轉移,打到后來就剩他和一個女兵,他的一條腿也負了重傷。他命令女兵,不要管他。女兵奮力把他拖到一個草棚子頂上,用亂草將他遮蓋住,然后向林子里跑去,邊跑邊回頭射擊,把敵人引向自己。
1936年夏,李學忠在撫松縣老堿廠密營養傷,遭敵襲擊,突圍時中彈犧牲。
四軍政治部主任何忠國,湖北人,1909年出生,1927年入黨,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曾被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1934年秋與吳平一起回國。
1935年年初,何忠國率部轉戰密山、勃利、穆棱、依蘭等地,炸毀了滴道河子的日軍軍火倉庫和三道河子大橋。4月底,在途經依蘭重鎮閣鳳樓時,何忠國給駐鎮的偽軍連長寫信,勸其反正,或者讓路。偽連長自恃工事堅固、火力強大,拒絕了。何忠國不動聲色,暗中部署部隊,當晚兵分三路開展猛攻,將敵打垮。
6月18日清晨,奎山守備隊的七個鬼子攜機槍、擲彈筒到附近的何家屯偵察。何忠國正帶著三團和“自來好隊”在那兒宿營,當即卡住敵人退路,發起攻擊,六個鬼子被消滅,只跑掉一個鬼子。戰斗結束,部隊立即轉移,行至馬鞍山時被乘汽車的敵人追上。戰斗中,何忠國胸部中彈犧牲。
這個軍政雙全的“九頭鳥”,倘非過早犧牲,四軍后來應該不會有那么多坎坷。
十九歲的師長兼政委
周樹東,1918年生于山東省平度縣北滾泉,1925年全家闖關東到琿春縣,1930年考入琿春鎮東關中學,1932年4月參加救國軍,同年10月加入琿春游擊隊,不久入黨。他歷任團琿春縣委書記、團東滿特委書記、二軍一團政委、一師政委。1936年9月,周樹東任四師師長兼政委。
1937年4月,周樹東和六師師長金日成率四師、六師各兩個團,從撫松挺進安圖、和龍,準備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他們先在安圖縣荒溝嶺截擊了敵人的運輸車隊,又在升平嶺與日軍展開交戰,將其擊退。24日,先頭部隊在大沙河上搭便橋時,遭到安圖縣偽治安隊的襲擊。這是一群效忠日本人的瘋狗,隊長李道善的雙手沾滿了抗日軍民的鮮血。周樹東以部分兵力正面牽制敵人,主力部隊穿過樹林繞到敵后,搶占制高點,兩面夾擊,將敵打垮。此戰斃傷敵百余,惡貫滿盈的李道善也被打死。
周樹東在指揮戰斗時,不幸中彈犧牲。
從照片上看,這個十九歲的師長兼政委,英俊、帥氣,充滿活力,成熟、老練中,一張明顯的娃娃臉上也不無稚氣。
不知掛過多少彩的師長
安圖縣北部,有個叫翁聲砬子(今明月溝)的小鎮,布爾哈通河從旁經過,吉(林)敦(化)、天(寶山)圖(們)鐵路在這里交會。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張作霖統治時期這里就有駐軍。九一八事變前后,駐防此處的是東北軍29旅676團3營,營長就是后來的國民救國軍總司令王德林。
日俄戰爭后,日本提出要修筑一條從中國吉林到朝鮮會寧的鐵路,并于1909年9月與清廷簽訂了《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由于遭到國人的反對,后來只建成吉敦、天圖兩段,敦化至天寶山之間未接通。九一八事變后,熙洽代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主持吉林一切官民政務,淪為漢奸后,出任偽吉林省長官公署長官。為了向主子表忠心,熙洽把修筑這段鐵路當作一份禮物,獻給日本人了。
1931年11月,江橋抗戰正酣,三營也在翁聲砬子開火了。
這天,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下稱“滿鐵”)的一支測量隊,在一個小隊日軍的護衛下,來到三營營部。王德林向他們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說,這是熙洽同意的,吉興旅長也跟你通了電話,還要什么公文哪。
王德林說:“這是俺的防區,沒有省府公文,誰也不能進入。”
言來語去之間迸出火星子,日軍就要動硬的,向山頭上三營的炮臺奔去。這天的值星班長史忠恒兩次鳴槍警告無效,一聲令下,一陣槍聲響過,兩個鬼子當場斃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縣,九歲給人放豬,二十歲參軍。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當兵吃糧”不好說,可以斷言的是,面對入侵者,像許許多多有血性的中國人一樣,就是為保衛國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為放下鋤頭拿起槍的農民義勇軍中,像史忠恒這樣有多年行伍經歷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堅、骨干。從救國軍副連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到抗聯二軍二師師長,他參加了攻打敦化城、墻縫伏擊戰、磨刀石阻擊戰、八道河子保衛戰、兩打三岔口等重要戰斗,而且經常獨當一面,關鍵時刻執行、完成關鍵任務。
史忠恒第一次負傷,有文字記載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寫了,是汪清游擊隊把他從戰場上搶回來的。這次傷在哪兒、傷情如何,不詳。1933年3月,在八道河子保衛戰中,團長史忠恒率隊沖擊時胸部中彈。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彈頭挖了出來。這時,一顆手榴彈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傷。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雙目圓睜,吼道:“別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二師在圖(們)佳(木斯)線老松嶺伏擊軍列時,雙腿被打斷,腹部受重傷,血肉模糊。戰士們以為他犧牲了,高呼“為師長報仇”,將敵大部殲滅。
大小輕重,不知道史忠恒負過多少次傷、掛過多少次彩。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三處重傷前半年,周保中給王明、康生寫信,說明“若不實行解剖治療絕不能好”,希望能安排史忠恒去蘇聯手術治療。這年冬天終于成行,但是已經晚了。
“踏著犧牲同志的血路”
張文偕,1907年生于山東省掖縣,大革命時期入黨,之后被派到蘇聯學習。1933年6月他回國,在四軍的前身——抗日救國游擊軍任政委。1934年5月,他任饒河游擊大隊大隊長,威望高,受擁戴。七軍的老人說,要是他不犧牲,七軍后來不會有那樣的“內部問題”。
李斗文,比張文偕小兩歲,也是掖縣人,學生出身。他曾在哈爾濱做地下工作,從蘇聯學習回國后任饒河游擊大隊政委、四軍四團政治部主任,與樸振宇、趙清和在新興洞戰斗中犧牲。
樸振宇,1908年生于朝鮮咸鏡北道,延吉龍井大成中學畢業,曾任饒河中心縣委書記、游擊大隊政委、四軍四團副團長。
趙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闖關東到饒河縣開荒種地,1934年初參加游擊隊。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寫過幾筆,此處再寫簡歷,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這篇寫于1935年(無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題目是《饒河反日總會悼文——追悼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四團犧牲同志》。
張大隊長,文偕同志!你的膽包括了天地,領導著幾十個拿著砂槍、別列旦的武裝同志,時常進攻敵人的鎮市,你把敵人看作小兒,直著腰在最前線上指揮如意。結果,因此而犧牲!能不使人追憶!你紅的臉兒,黑的眼睛,頎而長的個子,時常在我的腦海里!山林隊說,假設有你的存在,游擊隊的發展,尚不致如此!
樸團副,振宇同志!包圍抱馬頂子會房子時,你首先跑到敵人的墻壁。西通之戰,你堅決主持,你說:“找不到這樣的好機會,來奪取敵人的武器!”你雖然是犧牲了,可是,這次戰爭使滿軍確信,革命軍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國人情,且會利用社會關系,你曾在山林隊里工作,他們都喜歡你、服從你,至今提起你,誰不說可惜!
趙排長,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隊員說:“我使匣子蓋住,你去搶機關槍!”隊員有點兒遲疑,你又說:“不行就給你匣子,你蓋住敵人,我去搶!”政治員說:“趙同志!小心!”你說:“怕死不作革命!”敵人一彈,竟把同志命中!你雖然是犧牲,你這句話永遠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沒有一點兒個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從你到來,起了很大的轉變,提高了同志們的政治水平。你曾幾次說退了敵人,“請你再講,我們很樂意聽!”這是滿軍兵士的回應!西通戰后,有多少群眾打聽,我知道群眾對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對群眾說明,只說你在旁處養傷,并未犧牲!
一切為革命而犧牲的同志們!你們不是為自己的利益,你們是為的中國領土的完整,中華民族的復興。你們用自己的熱血頭顱精神,驚得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發抖,喚起了弱小民族的沉夢,開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們雖然是犧牲了,你們的言語、容貌、行動,不能不使后死的我們,腦海里不起反應!我們民族英雄的芳名,是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我們追悼犧牲的同志,用不著燒香燒紙,也知道用不著哭,但是禁不住嗚咽!
我們追悼犧牲的同志,要學著犧牲同志的精神,踏著犧牲同志的血跡,去與敵人拼命,以完成犧牲同志所留給我們的任務——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滿洲國,使滿洲四千萬同胞脫去亡國奴的帽子,過著人的生活,這樣才對住犧牲的同志。
我們高呼:犧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犧牲的代價;犧牲是成功之母!為革命而犧牲是無上的光榮!誓死為犧牲同志報仇!只有在血泊中爭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著犧牲同志的血路去與敵人拼命!要完成犧牲同志留給我們的任務——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一窩子人打日本子”
王云慶老人說,王貴祥原是東北軍的,九一八事變后參加救國軍。救國軍垮臺后,自己拉起隊伍打日本。
早晨起來,他先喝碗水,大煙泡燒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塊似的抽一陣子才下地,那是多大的癮啊。
他是負傷后用大煙止痛上癮的,參加抗聯后硬是給戒了,那得多大的毅力啊。
王貴祥中上個頭,長得精瘦,走路飛快,左手拎槍,人稱“王左撇子”,那槍打的,說打左眼不中右眼。
他老婆姓池,槍法也好。她那支連珠槍使起來“啪啪啪”,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飛空的時候。為了打日本,這一家人都上隊了。
王鐵環到密營后,我常見到她,叫她“大嬸”。解放后,我在沈陽工作時去看她,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們這些人,誰會想到她當年的樣兒。
離休前為沈陽毛紡廠機關黨支部副書記的王鐵環老人,中等個頭,清秀、文雅、沉靜,說話不緊不慢。
老人說,1935年6月,有一天夜里,像做夢似的,聽見馬蹄聲,人也像在馬上“顛達”。天亮時我醒了,躺在一個柳條筐里,那筐綁在馬背上;山溝里面人呀馬呀的很熱鬧,好多鄰居都在,還有紅旗。我問我媽這是什么地場,我媽告訴我——頭幾天抗聯在我們屯子跟鬼子打了一仗,鬼子吃虧了,要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帶隊伍趕回來,我們就連夜上山了。
我們家住在密山縣馬鞍山,屯子里有十幾戶人家,這天晚上都人走家搬——老人孩子、小腳女人投親靠友去了,青壯年和半大腳的女人都“上隊”了,有些人家是一窩子“上隊”。密營被敵人破壞后,死冷寒天的季節,能住人家的時候不多,大冬天的在山里鉆來鉆去,就是大人也受不了啊。我的小弟當時還沒斷奶,年底就在我媽背上“顛達”死了。
1937年,我爹給我發了支小馬槍。1938年后,隊伍上的人越來越少,槍都背不過來了。
新中國成立后,干部需要填個表,有一欄“何時參加革命”,我填了“1935年”。有領導問:“你怎么能七歲就參加革命呀?”我也覺得是個問題,于是加了10年,寫成“1945年”。
前面說過,先后任蘿北縣鴨蛋河和湯原縣太平川、洼丹崗區委書記,后來為六軍保安團團長的李鳳林,父母趕大車拉腳賺錢,用作黨的活動經費,并給區委、縣委送文件、情報。李鳳林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都是黨員、團員,連舅舅也幫著湯原游擊隊奪槍。
見諸文字,這樣的家庭通常叫“紅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當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則是“一窩子人打日本子”——東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說“一窩子一窩子的”。
開頭,這一窩子一窩子的幾乎都是朝鮮(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學福等。后來漢族人就多起來了,像王鐵環家一樣,全家上隊了。楊靖宇每次落腳的“堡壘戶”,大多是這種情況。
各地的“紅地盤”,這一窩子一窩子抗日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偽眼里,“紅地盤”就是“共匪窩”。受日偽宣傳的影響,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紅地盤”當成“胡子窩”了。
在全家投身抗日的家庭中,有的一家人都犧牲了,比如六軍被服廠廠長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謝興華、五軍二師四團團長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順福、黃桂清和王惠民等,就是一門忠烈了。
不知東滿有多少,僅在湯原游擊隊被處死的“民生團”中,就有三對夫妻——參謀長張仁秋和隊員劉恩淑,中隊長柳東鎮和隊員李銀淑,隊員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國人管結婚叫“成家”,在那個出生入死、四海為家的特殊年代,雖然他們沒有一個穩定的住所,是不是也稱得上一門忠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