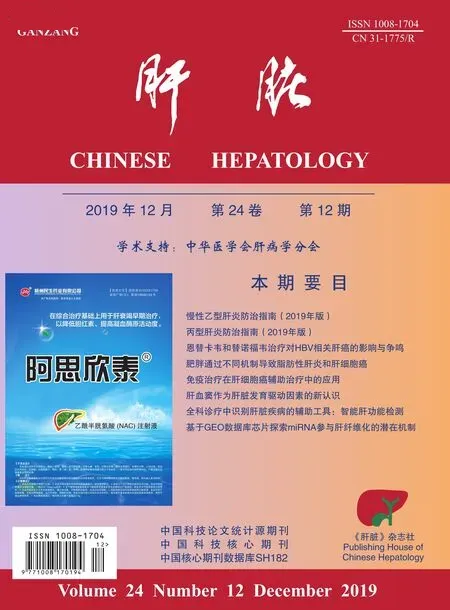肝血竇作為肝臟發育驅動因素的新認識
王嘉睿 詹淑華 馬世武
肝損傷后的再生一直是肝病領域關注的問題,許多研究從不同方面探尋肝臟發育和再生機制,其中肝血竇及相關細胞、細胞因子和調控信號在該過程中的作用也是研究的熱點[1-2]。
中胚層能夠發育成血液細胞,而內胚層能夠發育成肝臟細胞。來自心臟中胚層的信號可以啟動肝臟的發育,并且肝臟的形態形成和生長需要內皮細胞的調控[3]。在小鼠研究中,胚胎肝發育到8.25 d時(E8.25),內皮細胞通過Wnt和Notch信號調控,誘導來自內胚層的肝母細胞的分化和增殖[3]。小鼠胚胎肝內新生血竇和原始血管結構在發育到E9.5和E10.5之間開始連接起來,以引導可遷移肝細胞的定位,并建立起肝臟構架。在肝臟發育的初始階段,肝細胞生長因子(HGF)對肝臟的擴增并不是必需的;而在肝臟發育的后期,主要是在E14.5之后,缺乏HGF表達會導致胚胎死亡[4]。 因此,在E10.5和E14.5之間,驅動肝臟指數增長的因素還不完全清楚。
Lorenz等在2018年發表的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新穎而簡潔的機制來解釋胚胎肝生長和控制它在E11.5和E13.5之間的血管分泌信號(圖1)[1-2]。 他們研究發現,通過血液灌注對肝臟血管系統的體內控制以及肝竇內皮細胞(LSECs)的體外機械拉伸實驗,揭示出來源于LSECs的β1整合素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3 (VEGFR3) 參與了發育中的肝臟生長和存活。選擇性內皮細胞β1整合素或VEGFR3基因缺失的小鼠的肝臟較小,且肝臟內皮機械轉導功能也是缺失的,這證實了LSECs在肝臟發育中的關鍵作用。
在E10.5時,肝血竇形成并可檢測到造血細胞浸潤的第一征象。Lorenz 等[2]研究證實:在E11.5時,發育中的小鼠肝臟出現外周灌注;在E12.5時,開始發展為中心灌注。在 E11.5時,外周也有大量的增殖細胞,并顯示出高度的β1整合素和VEGFR3激活,這表明肝血竇灌注對肝臟擴增至關重要。為了證實這一假說,Lorenz 等設計了一個全胚胎培養的灌注得失實驗,使用2,3-丁二酮單肟(BDM)來停止胚胎心跳(灌注損失), 以及使用含有或不含阿托品的腎上腺素來加速心率(灌注獲得),結果發現,灌注不足可抑制β1整合素和VEGFR3活化,導致HGF表達降低。血液灌注量增加能顯著增加VEGFR3磷酸化,上調β1整合素活化及HGF的產生,提示血液灌注能使肝臟內皮細胞活化。作者用Krebs-Henseleit緩沖液灌注成年小鼠的肝臟,以驗證血管分泌信號是否與血液成分有關,或來源于灌注的機械效應。結果顯示,較高的灌注量能擴大肝血竇腔,參與β1整合素的激活,促進VEGFR3和c-Met(HGF受體)磷酸化,提示肝竇機械拉伸直接觸發內皮細胞活化。
在人LSECs體外實驗中[2],將LSECs貼在一個拉伸室中,并在無額外補充培養基的情況下,進行1.5 h機械拉伸實驗,結果顯示,這種拉伸也可誘導β1整合素和VEGFR3激活,增加兩個蛋白質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導致HGF、促炎細胞因子和MMP-9釋放。 研究還發現,機械拉伸LSECs后的條件培養液能誘導肝細胞的增殖和存活,而用活化的β1整合素抗體能證實β1整合素足以觸發內皮細胞的機械轉導。
在人體內驗證實驗中,Lorenz 等[2]對42例未服用降壓藥、BMI < 30 kg/m2、肝脂肪< 5. 5%的糖耐受的志愿者的血壓和肝臟體積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受試者的收縮壓在97.5 ~157.5 mmHg,舒張壓在57 ~101.5 mmHg。其肝臟大小的變異率分別為20%和16%,表明血壓和肝臟體積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主要歸因于收縮壓和舒張壓的變化。對9名肥胖(BMI > 30 kg/m2)且肝脂肪變性(肝臟脂肪 > 5.5%)的志愿者進行相同的分析,發現血壓和肝臟體積沒有相關性。值得說明的是,在沒有肝病的人群中肝臟大小與收縮壓存在的關聯,在脂肪肝的人群中卻沒有被發現,提示在不同肝損傷人群中這一現象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除了胚胎肝的發育外[2],Lorenz等的研究結果補充了對于肝臟再生的理解,提示在肝再生過程中,LSECs或其骨髓祖細胞誘導肝細胞增殖的血管生成信號的來源是必需的。肝再生被分為兩個階段:(1)誘導性血管生成,以肝細胞增殖為特征;(2)增殖性血管生成,以肝血管擴張為特征。在誘導性血管生成過程中,LSECs或其祖細胞可分泌血管分泌因子[5]。在誘導性血管生成階段之初, 在殘剩的肝臟中血管和血竇數量的減少可能會增加肝灌注壓力,擴張肝血竇腔和觸發VEGFR3-β1的信號轉導,這會增加LSECs 分泌的血管分泌因子。
總之,Lorenz等的研究為LSECs的生物學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提高了對VEGF受體在肝臟內環境穩態中的作用的認識,并為機械拉伸和剪應力對LSECs的影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機會[1]。

圖1 控制小鼠胚胎肝臟發育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