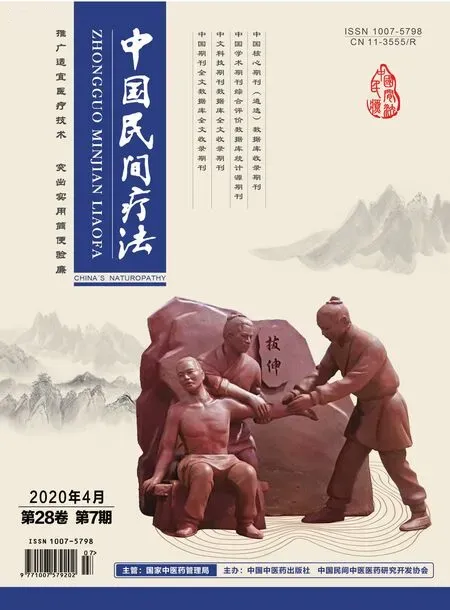關于罐斑研究方法的思路解析
袁勝康,徐 曦,陳朝金,李 瑞,韓 杰
(1.湖北中醫藥大學,湖北 武漢430065;2.湖北省中醫院,湖北 武漢430061;3.湖北省中醫藥研究院,湖北 武漢430074;4.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中醫醫院,湖北 武漢430300)
罐斑又稱罐印,指拔罐后吸拔部位出現的點片狀紫紅色瘀斑、瘀點,甚至出血點,或水皰,皮膚凸起,罐壁內出現的水汽和皮溫改變也可視作罐印的一部分[1-2]。罐斑是拔罐后給人的最直接的感官體驗,罐斑的研究作為最有效的切入點,對于指導臨床有重要意義,也可推動拔罐療法的單獨運用[3]。現代研究發現,罐斑的產生與局部血流動力學改變密切相關[4]。筆者在臨床運用腹部拔罐治療單純性肥胖時發現,同部位的罐斑表現不一,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受試者體質量和體脂比例不同,脂肪層比肌肉含有更少的血管,但是目前對此研究甚少,亦或部分研究深度不夠,導致罐斑診療及拔罐療法整體學術地位及臨床價值亟待提升。
筆者以近10年拔罐機制、罐斑研究的相關文獻為基礎,從罐斑色差原因的研究方法角度,匯總分析不同團隊對罐斑研究方式方法的改變,梳理罐斑研究脈絡,現陳述如下。
1 對罐斑研究的初步認識
《本草綱目拾遺》中提出“火罐氣”,謂“罐得火氣合于內,即牢不可脫……肉上起紅暈,罐中氣水出,風寒盡出”[5],即描述罐斑產生過程。《刺法灸法學》描述“罐斑色鮮紅,多見于陽證、實證、熱證;罐斑色暗紅,為陰證、血瘀、寒證……罐斑無變化,示病情尚輕,或接近痊愈”[6],說明罐斑是機體病證的外在表現,通過觀察罐斑的顏色、局部溫度、感覺等變化,對局部或全身病證進行初步診斷。正如《靈樞·本臟》載:“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使得罐斑的研究更具意義。筆者臨床以拔罐治療單純性肥胖,發現罐斑對其診斷及治療周期的評價都極具重要意義,正如《丹溪心法》記載“欲知其內者,當以觀乎外;診于外者,斯以知其內,蓋有諸內者形諸外”,亟須我們充分研究罐斑的機制。
目前對罐斑產生因素主要從負壓、拔罐時間、溫度、施術部位及健康狀況等方面研究,其次在免疫功能、神經功能、血流動力學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研究進展[2-3]。
2 罐斑的研究方法
2.1 從外觀角度研究 趙喜新團隊[7]最早實現罐斑顏色圖譜,以顏色深淺評價刺激強度,不僅應用于課題組的諸多實驗,也被其他課題組借鑒[8-9],為罐斑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他們運用自制拔罐負壓檢測儀(專利申請號200710054746.0)研究發現,拔罐參數達到10 min×(-0.04)MPa的刺激強度以上時,毛細血管就會破裂,皮膚出現瘀斑,負壓越大,出現的罐斑顏色也越深[7]。田宇瑛[10]團隊使用高光譜成像儀技術對拔罐后皮膚的顏色變化進行定量觀察,在方法學上是一個創新。他們發現在-0.02 MPa的較小負壓到-0.04 MPa時,橙光成分也開始減少,表明皮膚顏色向紅黑的方向發展,在-0.05 MPa作用5 min后,多處波長成分顯著下降,說明皮膚向著無顏色(黑色)方向變化,而此過程與臨床拔罐的實際情況吻合。武燕靜等[11]借鑒趙喜新圖譜經驗,建立罐斑顯色量化分級。Ⅰ級(L0、L1):罐斑不明顯,設定為1~2分;Ⅱ級(L2、L3):罐斑為淡紅色,設定為3~4分;Ⅲ級(L4、L5):罐斑為紅色,設定為5~6分;Ⅳ級(L6、L7):罐斑為紫色,設定為7~8分。蘆煜等[12]利用色量分級實現多信息融合、多物理屬性集成低頻負壓循經臟腑調理裝置(發明專利號No:201310532658.2)的合理調理模式、調理量、調理時間的決策機制,此裝置實現了拔罐原理的轉化,為中醫療法的量化評價提出創造性的解決方案,這給研究拔罐療法規范化、標準化提供了新思路。
2.2 從血流動力學角度研究 金蘭等[13]則從血流動力學方向使用激光多普勒血流儀監測拔罐前后的皮膚血流量變化,拔罐期間拔罐部位的皮膚血流量明顯增加,可能是產生罐斑的重要因素,并且發現當負壓超過-0.05 MPa后,受試者會因吸附力太強產生不適感。李超群、孟向文團隊[14-15]隨后采用相同的方法觀察大椎的血流速度,探討拔罐對血流變化的影響,孟向文等[15]采用自制復合式氧分壓傳感器及智能型四通道氧分壓測試儀觀測大椎、肺俞的變化,發現腧穴在拔罐改善能量代謝方面表現出一定的特異性。同時期唐曉等[16]則采用高頻彩色多普勒超聲技術分析罐斑組織血流動力學變化,揭示了罐斑的形成及罐斑組織血流灌注增加與拔罐“吸拔泵”作用的直接關系。
2.3 從學科交叉角度研究 孔林濤等[17-18]從HSV(色調、飽和、度亮)色彩空間中分析罐斑顏色特征與性別有關,為罐斑研究提出新角度、新方向。這期間關于罐斑研究相對密集,但后續未見各團隊更新相關研究,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李旭東[19]從有限元角度建模解釋負壓、溫度共同作用對表面皮膚及毛細血管產生影響。
3 罐斑研究的影響因素
罐斑顏色的判斷目前多為主觀肉眼觀察,存在局限性,且受環境光線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對罐斑的諸多研究不能更進一步。王艷麗等[9]在罐斑研究中發現,如果背俞穴聯系的臟腑或相關組織可能有“病”或近期有相應的病史,其背部罐斑則存在差異,既說明罐斑具有一定診斷意義,也展示出研究罐斑中遇到的干擾因素,具體則是由個體體質及“臟腑疾患”狀態決定的。也有研究觀察人種體質差異對拔罐治療的影響,發現不同人種對拔罐的耐受性、適應性和療效都存在差異性,包括不同季節、不同人種或不同地域等因素對罐斑影響較大[20],但目前對此研究甚少,方式方法模糊,使得罐斑標準化研究受限。
4 討論
拔罐療法因其簡、便、效、廉的特點不僅在中國各級醫療單位廣泛應用,還被世界上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盡管現代研究發現,拔罐療法可緩解疲勞、增強代謝產物輸布,輔助提高運動能力[21-23],然而對于拔罐療法、罐斑的基礎研究卻顯得投入不足,亦或研究深度不夠。既往研究多數集中于臨床療效觀察,對拔罐療法的規范化、標準化研究較少。盡管隨著科學的發展和醫學模式的改變,罐斑研究方向從客觀干預的負壓、時間等逐漸轉移至皮膚光譜、罐斑標準化研究等方面,使罐斑的研究取得一定進展,但動物實驗研究開展相對不足。這可能由于大多實驗動物皮膚松弛導致吸附面積不夠,一定程度限制了罐斑研究的動物實驗發展,所以如何設計更好的動物模型、選取更好的研究方法切入點顯得異常重要。
筆者通過梳理罐斑相關研究文獻,發現罐斑的機制研究及研究方法都存在很大切入空間。如利用現代科學技術與理論揭示各種罐斑的意義,應用較先進的光學相干斷層掃描技術[24]探討罐斑色彩差異,對拔罐療法及罐斑機制進行再認識,以便臨床工作者將拔罐療法及罐診更好地運用到臨床實踐中,這不僅是其自身作為診療手段的需要,也是中醫傳統外治法現代化、標準化、國際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