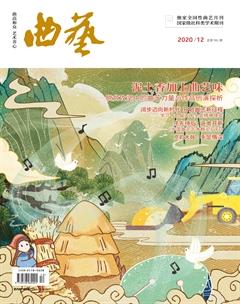山高水長路更長
近期,由四川省曲藝研究院創演的大型原創曲藝音樂劇《山高水長》,聚焦精準扶貧的時代題材,從駐村書記張文成的角度,講述在扶貧一線的廣大扶貧干部帶動村民致富脫貧的感人故事。張文成通過摸家底,找準貧窮背后的不同根源,根據脫貧對象的不同性格、不同觀念、不同命運,以“扶志”和“扶智”為主要手段,逐步鏟除了村民貧窮的根源,帶領村民走上物質富裕的同時,也實現了群體價值觀念的提升。該劇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舞臺形象,展現精準扶貧工作中價值的重塑和人性的光輝。該劇融入音樂劇、話劇等藝術元素,在保留曲藝根基的基礎上,其唱詞的口語化,拉近了觀演雙方的距離。四川曲藝唱曲藝術家們在該劇中實現了從表演節目到演活人物的成功轉換,拓展了四川曲藝唱曲藝術未來的發展空間。
一、曲藝音樂劇《山高水長》塑造了精準扶貧干群雙方鮮活的人物群像
從宏大的歷史背景來說,國家精準扶貧工作影響深遠。從中央到地方,一批又一批的扶貧干部下沉到鄉村,為“致富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的歷史進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曲藝音樂劇《山高水長》作為反映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主題作品,塑造了精準扶貧干群雙方鮮活的人物群像。
首先是駐村書記張文成。他是有別于某些“口號+臉譜”黨員干部形象,親切、鮮活。觀眾在看到“這一個”駐村書記的時候,猶如看到四川省各系統各單位下派的每一個扶貧干部。據統計,四川全省共有15133個駐村工作隊,56000多名駐村干部。他們往往年輕,以共產黨員的身份肩負使命與責任,走向農村、走近群眾,為精準扶貧謀出路找項目。但是,他們是人,不是無所不能的神。劇中的大河村駐村書記的張文成,正是這樣一個鮮活的人。他以年輕人的吃苦耐勞,跋山涉水,在摸清大河村每個貧困戶的“家底”后,針對不同的脫貧對象精準施策:為獨自帶著孩子生活的寡婦王秀蘭從城里請來專家指導她成立油紙傘工作室,打開網上銷售渠道;觀察好吃懶做、嗜酒如命的孫勤奮,知道他喜歡王秀蘭,便以“愛情”為媒介,一步步引導其完成人格的提升;遇到刁鉆刻薄愛鉆空子的李春花,他讓先富起來的王秀蘭網店火紅的生意使她“眼紅”,最終李春花也加入了勤勞致富的隊伍。他的這些幫扶,可謂精準施策,效果顯著。但是,劇中駐村書記張文成也有過不去的坎。為帶動全體村民致富脫貧,張文成準備引進八號甜橙在村里大面積種植,但缺乏當地水文氣象與甜橙相結合的數據。村里曾經的致富帶頭人孫守田種植過八號甜橙,擁有詳細的數據,而他卻因兒子在銷售八號甜橙的途中遭遇車禍,果毀人亡,留下了難以化解的心結。張文成主動提一壺菜籽油去看望,卻遭遇孫守田的冷遇。當孫守田因為孫勤奮偷拿自己當年和兒子寫下的數據本而暴怒,當眾撕掉能夠給八號甜橙提供重要數據的本子,推倒“山高水長”牌坊的時候,我們年輕的駐村書記張文成一時間也是束手無策。該劇的這個情節處理,有異于某些高大光鮮的類型化作品,使“這一個”駐村書記張文成的形象鮮活起來。在中國文化中,尤其是邊遠的山區,其輩分長幼,“輩高望重”,往往是族群的規則。所以,作為年輕輩的駐村書記的張文成,不被長輩孫守田接納也在情理之中。同時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廣大駐村干部工作的艱辛,因為他們往往面對的是孫守田這樣的長輩。這個駐村書記形象的成功塑造,增強了觀眾對像張文成一樣在精準扶貧一線的扶貧干部的理解和認同。
該劇同時重點塑造了一批扶貧對象在脫貧過程中,由被動變主動的心路歷程。漂亮的寡婦王秀蘭,為照顧兩個孩子和一個老人,不愿改嫁。她為人善良,勤勞肯干,一心想過好日子,但又認為命運無常,凡事只有自己咬牙扛。扶貧工作組的到來點燃了她的希望,她主動與工作組接近,在駐村書記的支持下,積極開網店,發揮自己做油紙傘的專長,成為了村里最先脫貧的榜樣。但是,面對剛剛改過自新的孫勤奮的追求,雖然內心喜歡,但是依然堅持“我們不是一個命數”,“我從沒見過花果能同樹”,拒絕孫勤奮。筆者認為,她這里的拒絕可以理解為孫勤奮還沒有達到讓她真正動心的“勤奮”。而當孫勤奮積極參加果園的勞動后,她也并不在乎花果能否同樹,就開始了和自己心上人的戀情,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劇中,觀眾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曾經的貧困戶王秀蘭,在駐村書記的重點幫扶下,一步步改寫先前伶仃孤苦的命運,在脫貧致富的過程中,收獲了愛與幸福。王秀蘭的改變代表了在脫貧致富路上積極進取的鄉村婦女形象。
古語云:“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即便是因為山高路遠,區域環境帶來的貧困,也往往會因“勤”而不會太“匱”。但是,在扶貧工作中遇到的一部分人的貧困卻與此相反。他們等政府、靠幫扶、要救濟,渾渾噩噩,虛度光陰。對于這部分人的扶貧應該先扶志,使其由被動變主動,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山高水長》塑造了這樣一個小人物,并展示了這個小人物逐漸褪去懶惰外衣的蝶變過程。他,就是被年輕觀眾譽為“承包全劇笑點”的孫勤奮。他是大河村的孤兒,從小吃“百家飯”長大,在村民善良的救助中養成了好吃懶做的惡習,堂堂一條年輕力壯的漢子,卻靠政府救濟金度日。兼有嗜酒如命、偷雞摸狗的惡習,夢想著和村里漂亮的寡婦王秀蘭相好。駐村書記的張文成看出他真心喜歡王秀蘭,就不斷激勵他改過自新,特意安排他給王秀蘭的油紙傘工作室做廣告模特,讓他趁機求婚。雖然當時沒有成功,但是他從此卻真正“勤奮”起來,最終也收獲了愛情。這個人物無論從外形的變化(最初的蓬頭垢面,到后來的英俊瀟灑)、思想品質的變化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改變在脫貧致富過程中也非常具有典型性。
劇中還塑造了掌握甜橙種植好技術的大河村曾經的致富帶頭人孫守田,從城市返鄉搞建設的村委會主任孫雪梅,愛唱山歌的女孩朵朵,一輩子沒有走出大河村“不曉得成都長啥樣兒”卻能夠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鎮住和喚醒孫守田的周奶奶,被清理出貧困戶就撒潑在地上打滾的李春花等。這些性格鮮明的人物,構成了駐村干部精準扶貧工作的底色,展示出扶貧工作的艱辛與挑戰,形象地闡釋了國家精準扶貧工作深遠的歷史意義,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二、唱詞和唱腔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作用
不同于以往傳統的曲藝劇,《山高水長》以四川曲藝唱曲藝術為載體,植入音樂劇的現代意識和現代審美,以曲藝音樂劇的形式進行舞臺呈現,具有時代氣息,符合當代人的藝術審美。其唱詞的口語化,在塑造特定人物形象的同時,更拉近了觀演雙方的距離。
《山高水長》的唱詞通篇沒有華麗的辭藻,而是接近口語化。把四川話的鄉土氣息融入唱詞,其句式也不拘于工整的結構,而是長短交錯、靈活運用,足見其功。比如唱段《命》:“這是我的命/命是一口井/這是我的命/命是一種病/老人在病床上呻吟/孩子在鍋臺前哭醒/我叫天天不靈/我叫地地不應/命啊命,命啊命/我用盡渾身力氣/還不是咬著牙,擦干淚/再出門笑盈盈。”這段唱詞用口語化、長短句交織,把一個貧困山區普通農婦的苦悶和抗爭形象生動地展現出來。再如在《我從沒見過花果同樹》唱段中:“你是個孤兒,沒父母/我是個寡婦,沒歸宿/你有你的路,我有我苦/但我們不是一個命數。”“你不在乎,我在乎/從來先有花啊再有果/沒有開花,果子怎么掛滿樹。”用特定環境中特定人物的口語化唱詞,娓娓道來,抒發一個因為丈夫的離去,而信“命”可能是早已注定,雖然她已經走在致富的途中,但是還沒有從思想上“脫貧”的鄉村婦女形象。其唱詞起到了塑造特定環境中典型人物形象的作用。
《山高水長》集四川清音、四川揚琴、四川車燈、四川盤子等四川曲藝的唱曲藝術于一體,在保留曲藝根基的基礎上,使多種唱曲藝術無縫對接,完美呈現。比如該劇《一場大風刮起來》唱段:“(周奶奶唱)一場大風刮起來/吹斷了樹,吹落了花/吹得人啊睜不開眼/一場大風刮起來/吹不走石頭,吹不跑山/吹不亂大路通天邊/守田啊守田/你這個明白人怎么也/糊涂了一年又一年。(孫守田接唱)不是我糊涂了一年又一年/不是我喝醉了一天又一天/是我碰不得心里那道坎/是我忘不了兒子那張臉/是我心里有一萬把刀啊,鉆我心尖尖,鉆我心尖尖……” 此唱段的劇情是該劇矛盾和情感沖突的焦點。它位于雖經駐村書記和眾人苦勸,仍然沒有能夠阻止住孫守田撕掉他自己和兒子曾經辛苦記錄的數據本,推倒自己當年立下的、象征村民富足美好的“山高水長”的牌坊之后。作為長輩的周奶奶婉轉的規勸,鏗鏘有力飽含深情;面對長輩周奶奶的規勸,孫守田終于敞開心扉,如泣如訴地唱出了深埋在心底的痛。唱段在現代編曲中融入揚琴伴奏,四川揚琴演員唐瑜蔓飾演周奶奶,四川荷葉傳承人李哨兵扮演李守田,他們的唱腔保持了四川揚琴、四川荷葉的根基,同時又結合音樂劇劇情做了戲劇化的處理。兩種唱曲的對接流暢,沒有違和感,演員的傾情演繹直擊人心,征服了觀眾。
多年前,筆者曾對四川曲藝的唱曲藝術進行了一次摸底調查,當看到其中最古老又最具藝術傳承價值的唱曲藝術的新創作品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時,感觸良多,寫下了《四川曲藝的根失狀態與對策思考——對四川曲藝部分唱曲藝術及其相關曲種的調查報告》,論文從演出場館缺失、用人制度滯后、人才狀況等方面提出問題,意在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從今天推出的《山高水長》中,筆者欣喜地看到四川曲藝唱曲藝術新的希望。《山高水長》云集了四川省曲藝研究院唱曲藝術的主力軍,飾演張文成的張曉東、飾演王秀蘭的吳瑕、飾演孫勤奮的王晟培、飾演孫守田的李哨兵、飾演孫雪梅的胡酈伽、飾演周奶奶的唐瑜蔓等,他們都是該院優秀的中青年唱曲藝術家。劇中他們的演唱可謂是字字清晰動聽,字頭、字腹和字尾低回婉轉,在繼承傳統藝術優秀基因的基礎上,使四川曲藝唱曲藝術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為者常成,行則致遠。雖然《山高水長》在主要人物的形象特征進一步個性化、牌坊的存廢寓意挖掘、花果同樹意象的豐滿和開拓等方面,還存在提升空間,但是它打開了四川曲藝唱曲藝術從表演節目到演活人物這條路子,希望這條路能夠走得更遠更長。
參考文獻:
[1]洪霞:《四川曲藝的根失狀態與對策思考——對四川曲藝部分唱曲藝術及其相關曲種的調查報告》,《四川戲劇》,2006年01期。
(作者:四川省藝術研究院文化遺產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