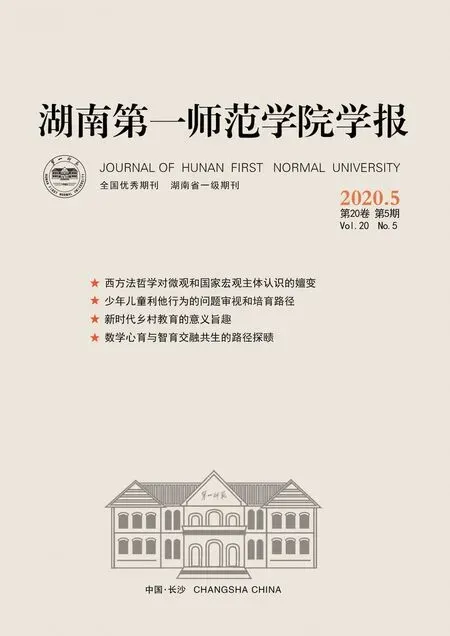論中國歌劇之“戲”與“情”
——從歌劇《小二黑結婚》改編談起
楊慧瑩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一、中國歌劇的發展現狀與研究問題
上世紀20年代,歌劇自意大利傳至上海以來,在我國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因歌劇源于西方,提及歌劇,人們的思維定勢便傾向于將“正統”歌劇歸于西方文化的范疇,似乎難以被廣大民眾接受,于是,中國歌劇就面臨著被束之高閣的危機。針對這種局面,歌劇工作者以中華民族的藝術文化為根本,借助于中國傳統戲曲的養料與西方歌劇之經驗,形成了頗具中國特色的歌劇藝術表現形式。1945年歌劇《白毛女》成為了中國歌劇的里程碑。此后,《草原之歌》《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婚》等一系列經典劇目紛至沓來。但在中國歌劇藝術不斷發展的同時,我們也需看到中國歌劇在發展歷程中的偏頗,如重“樂”輕“戲”、重“形”輕“質”等。
學者陳絢曾言明:“只要聯系到我們的國情——中華民族的藝術土壤,中華民族的欣賞習慣,以及中國歌劇成敗優劣的事實,立即就會發現:‘音樂至上論’是個似是而非、十分有害的歌劇理念。”[1]歌劇中的“樂”與“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較量或對抗,或者可以說“樂”與“戲”的孰輕孰重問題僅是深層內涵的表層顯現,我們更應深入思索的是歌劇在現實發展中是否依然存有“水土不服”的現象。對此我們不能避而不談,更不能因此丟失信心。有待解決的問題逐漸生成,就說明其必有可供理解的更好方式。于是,近年來多有學者將中國歌劇的重心回歸到歌劇劇本的戲劇性問題。如戈曉毅所言:“作為一種戲劇形式,戲劇性在歌劇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和其他的戲劇文學一樣,它必須具備基本的戲劇品格,戲劇性作為歌劇文學創作的根本特性,是歌劇文學創作理論研究的重要方面。”[2]以上的顧慮與建議是眾學者對于我國歌劇發展現狀的警醒之語,研究者則需立足于中華民族傳統與現實土壤去感受經典,如果摒棄有“戲”可看的審美經驗,顧此失彼的效仿也只是東施效顰。
其實,無論“樂”與“戲”,還是“形”與“質”,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割據狀態,歌劇發展所強調的重心并非是確定一個精確的平衡點,而是在具體的情境下將天平搖擺在相對平衡的位置。當把焦點由天平的重心移至其背景,所看見的便是整個時代、文化、社會環境的外圍景觀,這樣寬闊的視野則是中國歌劇在探索道路上值得擁有的資本。但若想跳出固定的認知范圍,不僅依賴于智力的強弱,更在于以何種情感方式來觸及世界,如果以抵觸的姿態去感受外界而限定范圍,必然是無法脫離認知的局限,因二元辯證的前提中已包含不可調和的因素。于是,本文在研究中國歌劇的“戲”與“情”的問題時認為,針對中國歌劇現實發展所面臨的具體狀況,不能簡單地用以“樂”顯“戲”或以“形”顯“質”來規約,真正的“戲”與“質”是可被真情所觀感的,而帶有真情的“樂”與“形”對于歌劇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歌劇經過本土文明的培育,本應有足夠的自信與實力在“戲”中連接古今的火種,孕育高雅之“情”的時代文明。由此,本文從經典歌劇《小二黑結婚》的改編談起,從劇本文學的層面研究同名小說《小二黑結婚》改編至歌劇的成功之處,從“戲”與“情”兩方面探討歌劇《小二黑結婚》獲得經典地位的原因,由此以小見大,在涉及關于歌劇改編的藝術技巧的同時,探索這種改編策略對中國歌劇發展的相關啟示。
二、歌劇《小二黑結婚》的改編——“一劇之本”的“戲”與“情”
《小二黑結婚》是趙樹理的知名小說,通俗易懂,頗具感染力。小說自發行后,為群眾喜聞樂見,有一定的受眾基礎。中央戲劇學院歌劇系在1952年根據此同名小說集體改編出當代歌劇作品《小二黑結婚》,并于1953年由郭蘭英、張揚主唱上演,轟動一時,至今仍為經典。該歌劇的文學劇本便是由田川、楊蘭春等人改編的《小二黑結婚(五場歌劇)》。此劇本在尊重小說原著的基礎上,將小說的平面化描寫以立體的展現走向舞臺,對小說中的人物塑造、情節發展做了改動,同時借鑒中國傳統戲曲形式以表現山西地方特色,復現原著情感氛圍。一部優秀的劇本創作,會有些許別樣的藝術特點,但終究離不開“戲”與“情”的精髓,“戲”可勾起回旋往復的情感脈絡,而“情”則帶有“繞梁三日,余味不絕”的文化意蘊。本文之所以從歌劇《小二黑結婚》的成功改編談起,不但因其兼具“戲”與“情”的特質,也因其同名小說所具有的可供改編的空間,并且根據2011年歌劇《小二黑結婚》的復排版,也可聯系至中國歌劇發展面貌以及需要注意的方面。
(一)“戲”中之精華
1.論“增添”與“刪減”的文本策略
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可以將敘事與抒情有效地表現于文字描寫中,可用多種敘述視角與敘事手法融于小說的想像性創作,從而突破現定時空的限制。一部優秀小說的完成是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建構的,小說的文字描寫所提供的想像空間便于滿足讀者的心理期待,其中的“空白圖式”需讀者與作者一同經營。讀者在閱讀欣賞與審美想像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創造,依據自身的審美經驗對小說內容進行藝術再加工。小說所具有的開放性想像可以使作者更精于語言疆域的描摹,為使描寫的事物在適度的約束中可被讀者自由地感知,成熟的創作者可巧妙地把握小說語言的“力度”。例如,作者在對某一小說人物進行塑造時,會適當地給予一些“關鍵詞”,讀者可根據人物的主要特征加入自身對于人物的想像性期待。
但是,當平面的敘述文字走向立體的舞臺表演時,讀者想像的主動性則會讓位于觀者定向的接受過程。由于表演舞臺的封閉性與有限性,劇情的發展和人物形象的展現方式則會隨之改變。不同于小說的自由創作,歌劇舞臺表演所具有的統籌關系與集體概念,將個人的創作上升至眾人的合作,上至編劇、導演,下至演員、舞美,以及攝影、音效、燈光等方面的情景規劃皆需多方洽談協商,這就會產生更為復雜的臺上幕后關系。由此,編劇在改編劇本的過程中需面對更為復雜的情境溝通,改編時不僅需有群體意識,也需面對原版與改版之間的多方商榷,此絕非易事。并且,在歌劇創作中,如果“一劇之本”的位置無法獲得其應有的重視,這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劇本改編者水平的發揮。
但另一方面,封閉的舞臺場景雖然對表演的空間進行了限制,但此限制卻非僵死。“小說敘事向舞臺呈現的轉換過程中,小說的情節線索并不局限于一般所指的時間或者空間線索,這里更強調作品里的人物之間的矛盾所構成的具有戲劇沖突性質,且足以推動情節發展的線索。”[3]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場景中有詳有略地安排劇情的發展,如何增強觀眾的“入戲”意識,如何促進臺上臺下的情感回旋,這“一劇之本”就顯得越發重要。
歌劇《小二黑結婚》將戲劇性表演在舞臺的“立體”效應中表現得恰到好處。首先,是在劇情與人物的添加與刪減上。田川等人在尊重趙樹理小說的原初設定的同時,對符合舞臺表演的具體情境進行補充。例如,小說《小二黑結婚》在人物介紹時更注重于邏輯性的敘述,開篇則以“神仙的忌諱”與“三仙姑的來歷”作為前兩節,即從三仙姑、二諸葛等父輩,引出小芹、小二黑等晚輩,并由故事發展情節帶出金旺、興旺、村長、區長等人,小說的構思線索十分清晰,直白簡明的語言與明晰的人物關系符合趙樹理小說通俗易懂的特色。而歌劇劇本《小二黑結婚》則在簡明易懂的故事情節的基礎上抓住“一對多”三個主要矛盾。歌劇以小芹去河邊洗衣為始,歌唱一曲“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道出其與小二黑的微妙情愫。這是在先明確小芹與小二黑的戀愛關系后,再分別上演金旺、二諸葛、三仙姑等人物對婚姻目標的阻礙行動。并且,在歌劇的改編中刪除村長這一角色,以及小說第六節的“斗爭會”,即村長幫助“小二黑、小芹”開脫一事。在小說中,此節可起到激化矛盾與推進情節的作用,但由于舞臺表演的時間限制,刪去非重點的情節可為其他主要劇情留出更為富裕的時間,也使劇情發展更為緊湊。而“隨著故事的發展,各種交錯關系被梳理清楚后,人物的戲劇行動領域越來越窄小,矛盾的指向性越來越清楚,這時就出現一場‘必要戲’。”[4]于是,歌劇在小芹、小二黑與父母發生爭辯,并被金旺逮捕以后,直接進入第五場“必要戲”:區長審判環節。在第五場的編排中取消了小說中區長教育二諸葛、三仙姑、懲罰金旺的線性推進情節,而將此三個場景集中在同一舞臺上演,使此劇的所有人物集于一地,三組沖突并于同一時間,從而使矛盾達至高潮,觀眾也會隨劇情的起伏流轉而獲得更為深刻的“入戲”體驗。
需注意的是,《小二黑結婚》歌劇的改編與原著相比新增了多個角色,如小榮、喜蘭、老董、年根等,但新添的角色并不顯累贅或生硬。這些人物的出現不僅起到交代劇情發展的作用,也具象化了普通民眾的形象。但置換角色的改編方式并不適用于多數劇本,要看劇本中是否還留有余地為完整的故事情節增添新角色。如果原劇中已有多種角色,且角色關系多已定位,或人物行動與行動目的不相干或相悖,在這樣的情形下增添人物也只能是畫蛇添足。歌劇《小二黑結婚》添加新角色有其天然優勢,第一,同名小說以第三人稱敘述,并留有大量可以填充的空白,本就留有劇情發展的線索可供改編時添加人物和事件;第二,歌劇中添加的人物皆不是處于固定人物關系鏈的主要角色,且都是與矛盾發展的線索相適應,這是與劇情發展“順向相應”的人物刻畫。有時,為推動舞臺效果或集中矛盾沖突,編劇會對劇情進行“刪減”或“添加”,但卻容易忽視人物關系的總體線條。任何一個人物不是單獨出現的,每個人物都是在劇情的人物關系鏈中得以存在的,人物關系鏈之間的矛盾沖突必不可少,但是矛盾沖突背后所傳達的思想深度更需注意,不能為矛盾而制作“矛盾”,矛盾需是原版的珍品,而不能是缺失“靈韻”的影像。
總之,一個角色的塑造必然有生成的緣由,即“于情于理”是否留有需求空間。“于情”在于劇情的情感回環是否連貫,是否可起到對主導情緒渲染或增強的作用;“于理”則是考慮劇本的主要線索是否已形成鏈條,或者劇中的支線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顯然,許多由小說走上舞臺的腳本是沒有富裕空間為新角色讓位的。對于《小二黑結婚五幕劇》而言,新角色的添加是“畫龍點睛”之筆。但對“于情于理”不能恰如其分的劇作而言,生硬的添加卻會產生“做作”的效應。
2.矛盾的“經營”與“入戲”的體驗
居其宏認為:“歌劇劇情要簡約,但拒絕簡陋,拒絕蒼白……歌劇情節往往要作跳躍式展開,省略那些無關緊要的枝蔓,但拒絕毫無邏輯、使情節支離破碎、讓觀眾不知所云的‘庸醫’式切除手術。”[5]由此,為避免“庸醫”現象,對歌劇的“主干”更需用心“經營”。在歌劇《小二黑結婚》中,抓住二黑與小芹的自由戀愛無法進行這一矛盾,就簡要明了地抓住了貫穿全劇的“一對多”的三個阻力。
其一是金旺致力于破壞二黑與小芹的美滿姻緣。無論歌劇、小說,甚至是電影,金旺無疑都是個十足的惡霸。但是在歌劇中,金旺的出場與三仙姑一般,為劇場氛圍增添了滑稽的色調。歌劇將金旺調戲小芹一幕改為小芹與小榮、喜蘭在河邊洗衣的情節。這改變了小說中原情節發生的地點:小芹家中的封閉場景。首先,河邊的地點置換,上接小芹的自白,下接小二黑的歸來,并為群眾演員的表演提供施展的空間。在河邊洗衣時小芹等人使金旺中計摔倒,金旺在惡霸的威嚴之上增添的滑稽的丑角形象,起到加劇矛盾的功效。并且,小芹等人可在戶外的環境中,將農家女孩的洗衣、歌唱、玩耍的日常生活呈現出來,這就與劇中的經典唱段“樹上的柿子圓又圓”相呼應,將書面的俗語轉為展現民風民俗的歌詠。
其二,小二黑與其父二諸葛的沖突,通常意義上多理解為新舊思想間的矛盾。但除此之外,更有父子雙方爭奪話語權的意味,即雙方在思想與情感層面的碰撞。如二諸葛所唱:“我也是半身入土的人。兒大就該說媳婦,我不操心誰操心?我不操心誰操心?”這里的確有二諸葛對于傳統思想的守舊,但也不乏一位父親對孩子的擔憂與疼愛。尤其是在歌劇唱段“了卻我老人的一片心”中,這份親情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但二諸葛對于這份情感的傳達卻與二黑所持之觀念相抵觸。若跳出劇本的具體事件,這樣的情形在現代社會中并不鮮見,年輕人與老一輩的思想沖突與此又是何等相似,而這老一輩也曾是年輕的一輩,如此則引出不限于時代的思索與追問。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時代環境的變遷有著密切聯系,在現代社會高速運轉的社會文明中,我們審慎自身,也許我們所癡迷的不是二諸葛的八卦易算,也不是三仙姑的求神拜佛,但是卻以別樣的“變形”來寄托內心的空虛,在崇尚智力之時,更容易遺忘自然人性中所流淌的真摯情感。智慧的星火讓人們更多地去關注于外界所給予我們的,卻不是我們自身所能付出的。這就如同當二諸葛聽到“烏鴉叫了”便認為這是在預示兇兆的來臨,其第一反應便是息事寧人的躲避,生怕鬧出一點亂子,而不是反觀自身去尋求更為恰當的解決途徑。
此外,第三組矛盾便是三仙姑與小芹這對母女的爭執。在小說中,三仙姑與小芹的關系更為微妙,三仙姑與小芹的隔閡更多的在于青年們以及小二黑的情感糾紛上。趙樹理在刻畫三仙姑之時,描繪了她較為扭曲的人性。三仙姑與二諸葛不同,如果說二諸葛希望以思想的管制而延續“復刻”的生命,那么三仙姑則是以極端的手段去排除小芹成長給她帶來的競爭壓力,從而延續其畸形的生存空間。這近似于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在近乎極端的、變態的窺探與控制中體驗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式。三仙姑雖不至如此,但也正是出于同樣扭曲的心理,以拒絕“復制”的心態去阻礙小芹的幸福。小說中,在二黑與小芹被押送到區里后,三仙姑裝模做樣地去找二諸葛理論,其內心的真實想法是希望小芹吃些苦頭。因此,二諸葛與三仙姑雖皆反對二黑與小芹的結合,但此二人的出發點卻是相悖的。二諸葛雖然迷信,但出于父愛的一片真心卻是顯而易見;三仙姑則是出于迫害女兒的陰暗心理,顯現其人性的扭曲。若按此悖論情形改編歌劇劇情,從現實的角度而言,三仙姑的行為畢竟是與大眾所接受的文化經驗相悖,并且在當時的具體社會情境中更需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若從舞臺表演的經驗而言,由于三仙姑的前后轉變反差過大,也可能會影響觀者的審美體驗。當小說人物以具象的演員形象公之于眾時,劇情的矛盾沖突本會激化觀者的“入戲”情緒,三仙姑的陰暗心理也勢必會使觀者期待惡有惡報的審判,那么痛改前非的三仙姑是否可以贏得觀眾的認同則存有疑問。如何把控三仙姑在“善”與“惡”中的“度”則需仔細斟酌。于是,田川等人抓住矛盾沖突的焦點:結婚,巧妙地改變了矛盾沖突的內涵,將三仙姑對青年們的占有欲改為對金錢的權衡。因此,三仙姑與小芹在歌劇第三場的沖突是真情實意與金錢利益的較量,更是精神與物質的博弈。如此改編則為三仙姑做了個圓場,也避免了對二黑和二諸葛之間新舊思想沖突的重復。由此,歌劇中的三仙姑因迷戀金錢,逼迫小芹嫁給吳廣榮,更多的是出于財迷心竅的無知,而非是特意傷害自己女兒,此種無知在區長與眾人的教育提點下進行更正是可以自圓其說的,其最終以一名長輩的身份作樸素打扮參加二黑與小芹的婚禮也是值得欣慰的。并且,歌劇改編中為使人物形象更為鮮活,在第三場小芹與三仙姑的爭吵中加入媒婆的摻和與三仙姑滑稽的“下神”表演,不但增添了歌劇的喜劇氛圍,緩解了觀眾緊張的情緒,而且對于一個如此滑稽的角色,觀眾在潛意識中也更趨于諒解。
總而言之,編者不能為突顯矛盾之“戲”而忽視“戲”后的思想與情感,這也是歌劇《小二黑結婚》在矛盾沖突的焦點之下卻不顯“戲”勝于“情”的造作的原因。其實,刪減或增添新人物、新劇情的方式除了對具體劇本的構建外,更是為增強觀眾的“入戲”感受,但這需劇組臺前幕后的悉心經營,這里尤需注意如何巧妙地讓觀眾共情,且不以直白的方式表現出共情的目的。若從接受心理而言,觀眾是善于自欺的。當進入劇場觀演之前,凡是樂于欣賞的觀眾,則會為接下來的劇場表演鋪墊心理預設,比如當有觀眾得知觀看的是悲劇主題時,便已提前準備好紙巾。這說明不僅是舞臺表演中的演員需要在劇情發展中醞釀情緒,觀眾即便身處劇外,但其內心依然希望醞釀情緒而與演員情感、劇情發展保持相應的頻率。凡是有興趣進入劇場,排除附庸高雅的特殊目的外,觀者的內心是期待“入戲”的,他們期待可以跳出自我的局限,以共情的方式感受別樣的人生。觀眾雖是愿意自欺,但卻不愿被欺,這可聯系至人們關于生存與自由意義的界定。比如“我”以自欺的方式陷入瘋狂的愛情,“我”可以原諒或忽視自欺的可能,但卻無法撫平被欺的憤怒。因自欺是“我”的生命意志對于生存自由的掌控,而被欺則是他者對“我”的生命自由的干預。于是,在自欺與被欺的審視中,觀眾會敏感地感知舞臺表演中的真與假,這真假的分辨并不是限于“戲”之真假,而是關乎“情”之真假。觀眾會以審美情感去清晰地分辨此劇是否有“戲”可看或有“情”可審。于是,除了改編劇本的有“戲”可看外,以情動人也同樣重要。
(二)“戲”與“情”的流轉
歌劇《小二黑結婚》的成功改編,不但在于眾藝術家在“戲”中的精心研磨,還在于以情感人的心意相通。在中華民族重“情”的文化底蘊中,“情”這一字可謂是貫穿于詩詞歌賦之始末,所謂“觀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情溢于海”,物我皆有情,況乎人與文?或者說,在中華文化的流傳中,早已將審美與審“情”融為一體,于是情之所動,金石為開,即便“戲”中有著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差異,但“情”的觸動卻是對“戲”最為深刻的理解,再加之歌劇本身的音樂性,對于“情”的需求則更為濃烈。歌劇《小二黑結婚》巧妙地在劇本的改編中將“情”的光亮再次點燃。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以其時代為背景,講述了對于舊制度與惡勢力的批判,以及年輕人對于自由婚姻的向往,其在小說的描寫中多為陳述性的事實與關于正義的描述。而在歌劇改編中則增添了更為觸碰人心的具體事件。例如,由小說中僅以“近兩三年,(小芹)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小二黑結婚:小芹》);“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小二黑結婚:小二黑》)的簡單概括表明二黑與小芹的關系。但在歌劇中則以唯美的歌唱遞增了二人在相處與溝通中的情感互動。小芹在開場時表現出對二黑的思念;而后二黑與小芹互通心意;以及小芹與二黑在山崖上互訴父母的計謀,并給予對方承諾。從歌劇唱段“咱們的婚姻自做主”“別把我當搖錢樹”“怎么不見你在這崖畔上”等都可以看出二人真摯的愛情。并且,小二黑與小芹這兩位主人公的形象在歌劇中被詮釋的更為真實可感。二黑由打死幾個鬼子的長相漂亮的少年,變為保護全村的英雄,而小芹也從不與旁人胡來的簡單描述至“不愛金,不愛銀,專愛二黑這樣的人”的獨立女性。“從人物到形象的發展是一個過程,在歌劇中,這個過程往往表現人物情感發展與變異的過程,也即人物的心路歷程。如果一部歌劇對其人物的心路歷程作了生動有力的揭示,那么它的人物也就達到了形象的高度。”[6]小芹與二黑正是通過扭轉的“心路歷程”而達至“形象的高度”。值得說明的是,這并非以主角光環而突顯其形象,相反,正是二人的真誠品行,使他們擁有可成為主角的資本。如二黑抗衡金旺等惡勢力的勇氣,小芹對于父母之命與金銀珠寶的摒棄,他們正是代表了有血有肉的中華好兒女形象。其中,小芹與喜蘭、小榮的友誼,二黑與年根、老董的交情,熱心的區長也成為此婚姻的見證者,還有村中眾鄉親明辨是非的助力,這不僅增添了歌劇表演的豐富性,也彌補了小說中眾人懼怕惡勢力的遺憾。歌劇《小二黑結婚》給觀眾留下的最為深刻的“情緒記憶”,是流淌在超越時代之外的脈脈溫情,這種溫情使其成為停留在歷史中的紅色經典。
正如黃奇石在關于“紅色歌劇經典啟示錄”的論析中所言:“經典并不是自封的。古今中外,似乎還沒有自詡為‘經典’便成為經典的先例。”[7]50《桃花扇》中李香君血染桃花扇的剛烈,《牡丹亭》的“至情至愛”,這些形象至今仍為人所吟誦。多年之后,也許觀眾會忘掉劇中的臺詞,甚至劇中的人物名字。但是,有一份情懷,是忘不掉的。當“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的唱調再次響起,人們會憶起那段純粹的愛情,記起兒女情長中的英雄大義,記起二諸葛與三仙姑為兒女忙碌的心情,記起金旺滑稽而又丑陋的嘴臉,而使我們憶起此情境的正是中華文明底蘊中對于美好情感的渴盼。
三、“情”之高雅與“戲”之通俗
歌劇《小二黑結婚》的改編是成功的,無論是劇情的安排、人物的刻畫,還是情感的傳達,皆可在“戲”與“情”的脈絡中流轉自如。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在當今的社會中,歌劇似乎已與大眾的日常生活相分離,正如眾多學者所憂慮的那般,歌劇逐漸被牢固地劃歸為高雅的精英藝術。所謂“精英”的內涵也亦有多指,其中不免有淪為邊緣的悲觀意味。然而,不得不承認中國歌劇與中國戲曲或話劇的知名度相比是有差距,歌劇曾作為西方藝術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與西方文化緊密相連,作為舞臺展現的方式之一,其所運用的藝術經驗與思維范式皆與中華文化有異質性的差異,要使此舶來品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枝繁葉茂,則必須與本土文化交融。
(一)“情”之高雅
馬可1954年在談及歌劇《小二黑結婚》的創作經驗時曾表明:“當前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在歌劇創作上的語言貧乏。我們必須加強向民族戲曲學習,以豐富我們在戲劇音樂上的語言、語匯和表現方法。”[8]因傳統戲曲已是中華“文化形象”的標志,并在源遠流長的文化底蘊中獲得廣大群眾的認可,將歌劇與民族戲曲相結合自有其適用性的優勢。但需注意,形式是外化的表現,心靈的溝通才是創新的目的。相比于其他舞臺表演形式,歌劇所帶有的歌唱性質更利于渲染“戲”中之“情”。歌劇的藝術形式與民間戲曲相結合,拓展了歌劇與觀者“視域融合”的范圍。歌劇《小二黑結婚》經典地位的確立則足以說明中國歌劇的發展潛力。一個人的視野會影響其認知,而認知又固化了視野。當我們重溫經典,所看到的應該是經典中所蘊涵的文化與審美藝術,而不是將視野聚焦于具體環境,或苛責于具體事件的現實性。因此,中國歌劇的發展對于傳統戲曲的借鑒正是《小二黑結婚》確立其歌劇經典地位的原因之一。
傳統戲曲的借鑒促進了歌劇中的情感流轉,而這“情”中之高雅正是我們需要商討的話題。例如,如果外國原語戲劇在中國各大劇院上演,試問有多少觀眾可以真正領略外國原語戲劇的內涵。高雅之“情”也必須以語言為媒介,過于追捧外國原語戲劇也不免有附庸風雅的嫌疑(當然不包括精通外國原語的觀眾)。正如朱壽桐對在中國上演的外國原語戲劇的評價:“如果不將其載體語言和文化精神中國化,必不能繁盛多長時間。應該在漢語語言和漢語文化的機體上開發更多適合于漢語觀眾的新劇。”[9]語言是人們進行溝通的必要途徑,語言背后所隱現的正是外部環境所孕育的思維方式。漢語照亮于古今,并孕育出中國現實的文明土壤。正因為傳統戲曲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傳承關系,增強了民眾與“陌生化”的歌劇之間的精神共鳴與親切感,這種精神共鳴正是與“情”之高雅相關聯。
如施旭升對“審美文化”的闡釋:“在人類的廣泛的文化經驗中,審美經驗也許更直接關乎人的感性實踐本身;審美本身就代表著一種現實關懷、世俗精神,審美經驗并非只是一種精神上的高蹈,不止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而上的體驗;作為審美的文化也就必然體現為一種感性生活的境界與質量,表現出現實的大眾情懷。”[10]而今,“審美文化”與“大眾情懷”在中國歌劇的發展中更是難能可貴。如果歌劇觀者將“看不懂”與高雅相連,則是混淆了高雅本應具有的特性,這是對高雅二字的誤讀。優秀的歌劇所表現的高雅是對人性中美好情感的共情,是對于美好人性的關懷。高雅的并非必須是雄壯的、崇高的,更不必然是晦澀的。歌劇《小二黑結婚》是以趙樹理的通俗小說改編,以傳統戲曲為養料,而劇情更是“下里巴人”的民間生活,卻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表達出深切的真情實意。這就是對“現實的大眾情懷”的真實顯現。回想當年那幾位剛接手歌劇改編任務的青年,在請教趙樹理改編問題的時候也曾受到質疑。趙樹理擔憂的是這幾個洋學生如何能做好這些“俗”的創作工作。但是,結果卻是出乎意料的。此改編成果不但令趙樹理改變了原先的態度,更是在一代人中反響頗深。中國歌劇的發展也是如此,無論是面對傳統的典范,還是西方的精品,都不應以外觀上的“雅”與“俗”進行界定。因高雅絕不在于的外在形式,只有內心空虛的人,才會著重于外在的“高雅”。歌劇《小二黑結婚》正是以一種簡單質樸,卻易于被人們所忽視的生活現象而感動一代又一代的觀眾。真正的高雅不是為分化的雅俗二元而產生,更不在于外在的堂皇形式。在一份日常的歡樂中,也能感受到人性中的高雅與情感的價值。這份價值可涉及到歌劇創作的各方面,更可具體于歌劇的舞美效果。2011年,由中國音樂學院在國家大劇院復排了《小二黑結婚》歌劇。這是對于經典劇作的再度回味,而對此復排的表演效果自是評價不一。但這眾多的評價也正說明眾學者對此一文化藝術現象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和肯定。例如,黃奇石以“神”與“形”對復排《小二黑結婚歌劇》進行評道,其中談到:“我覺得設計者雖是高才,但恐怕沒有好好地讀原劇本,也許也沒有認真地讀趙樹理的原小說,不了解舊時代貧窮山村的情況,就很難在舞臺傳神地(不論虛實)表現其風貌。”[7]53若對此評價進一步分析,則會從“神”與“形”的表述上升至關于真與假的合理性辨析。此處的真與假是探討形式上的是否合理。也許花費心力而精心打造的華麗舞臺效果并不適宜于歌劇劇情“本應如此”的特色,這樣的形式追求,因與“情”的真相悖而顯出不合時宜的假,反而事倍功半。又如“貧窮劇場”看似物質的“貧窮”,卻可展現出“本應如此”的真,這與觀者的情感認知是相互呼應的。
從此可以看出,復排時舞臺與布景的鮮亮色調,反而無法使劇作獲得更為質樸的情愫。這是因為不僅演員的演出需有“神似”之氣質,歌劇的總體編排中亦需有“神似”之自然。復排的歌劇雖尊重于劇本的改編,吳碧霞等演員的自我修養也十分到位,但相信如果場景的布置能夠與演員的氣質相搭,則歌劇的表演效果會更為得當。然而,并非所有觀眾皆能分辨何為“情”之高雅。如果人們更傾向于把華貴當作高雅,或者把玄虛捧為高雅,而漸漸與平凡的生活、純樸的感情相背離,那我們不禁要審視,時尚的定義是否已與原初的真實相偏離。人們是否可以真正分清“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限定,而非僅僅將它當作一句茶余飯后的玩笑戲謔之言;人們是否可以在精神上獲得真情的觸動,而非是不屑一顧的唏噓。
(二)“戲”之通俗
上文中探討了歌劇藝術的“情”之高雅,而與此相連的則是“戲”之通俗。當然,通俗絕非庸俗,通俗中有充滿機緣巧合的意味,也有大眾喜聞樂見、易于理解的含義。正如歌劇中的“戲”與“情”的相輔相成關系,此處的通俗與高雅并非對立,而是側重于不同的展現方式。通俗側重于故事的“戲”上,高雅側重于體驗的“情”上。
以文學劇本而言,“戲”之通俗不僅表現在歌劇劇本中,在優秀的話劇劇本、電影腳本中皆有顯現。例如,曹禺的話劇《雷雨》可謂是家喻戶曉,各版本輪番登場,觀者可以看出《雷雨》的“戲”是經過明顯的經營與構造,其中包含著陰謀與亂倫。這似乎與普通人的生活很遙遠,但卻與人們對編纂題材的喜愛很接近。這是一種假定性的生命體驗,“戲”中包含著技巧與通俗,我們看的是假定性的“戲”,體驗的卻是如同“先驗共通感”的“情”。“戲”雖然是假的,甚至是與常理相悖的,但卻是通俗的、易于理解的,觀者可以從表層看到周家的愛恨糾葛,看到命運弄人的悲劇,也可從更深層面探討關于生命、情感等哲學范疇,更可與時代背景聯系,從社會文化的角度進行深解。也許我們會為《等待戈多》《禿頭歌女》的荒誕而遐想,但卻不會因“戲”的通俗而摒棄那些“接地氣”的作品,因“戲”的通俗并非意味缺乏深度或情感淡泊。通俗是一種喜聞樂見的表現方式。又如經典電影《重慶森林》。這是一部詩化電影,但是劇本卻“戲”感十足。電影情節以“愛情”雙線展開,第一個故事與第二個故事之間的關系,則可以從“戲”的接續與阻礙兩個方面進行,而擴大到整部電影,這是對于橫向與縱向的匯總。有的愛情是巧合之下的一面之緣,而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正是王家衛詩化電影的出彩之處,利用鏡頭的跟拍,利用近距離的觀察,影片中的故事可以聯系至現實生活中的某個人的某兩段不同的經歷,也可以理解為不同的人的不同經歷。正如其影片名字所帶有的泛指意義,人生也是在某種若即若離中戛然而止,又在各種虛實與選擇中搖擺不定。無論是從電影技巧還是劇情本身,兩段“戲”之間有線索可言,但卻總有一些小的驚喜或謎題等待解答,類似于希區柯克式謎題,但卻可上升到更深層面的探討。高妙的“戲”可從近景中悄然地顯現出聚焦背后的遠景,從而使“情”置于另一層面的探討,這也為“戲”之通俗蒙上了另一層深意。由此可見,在文學劇本中“戲”的通俗十分重要,尤其是對于中國歌劇這種存有遠離生活的誤解的劇種而言,“戲”之通俗更需關注。
其實,《白毛女》《草原之歌》《王貴與李香香》等這些經典歌劇也正是以“戲”中故事的通俗性而被觀眾喜聞樂見的。《白毛女》中飽經風霜,少小白頭的喜兒;《草原之歌》中“苦海灘”上的藏族人民;《王貴與李香香》中的紅色戀人與“三邊”人民等,這些劇目皆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中展現“戲”的通俗與豐滿,這也是為何這些經典劇目可傳為佳篇的原因。這些“戲”并不是全篇刻意為之的經營,而是通過矛盾的經營與文本的建構,展現出時代、國家、人民、語言、習俗的可理解性,在劇情上觀者有“戲”可看,在思想上也能獲得相應的共鳴。與此類似,歌劇《小二黑結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劇情精彩卻不晦澀,故事通俗卻不庸俗。張春娟曾在文章《經典歌劇〈小二黑結婚〉在當代演出的現實意義》中談及:“凡是經典的作品,都需要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能夠反映出一個時代作為常人之境的文化精神和社會現實,它不僅代表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還代表了我們民族的智慧和心靈。”[11]而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心靈”也體現在平凡生活中的可貴品性,這正是時代應當給予敬意的。在人們追尋美滿人生的時刻,溫馨的情感益發重要。試問當經過所謂的現實的權衡后,還有多少女子如小芹一般的堅守精神的契合;當經由三仙姑與二諸葛的苦心經營后,又有多少年輕人能不忘初心;當承受金旺的欺壓后,又有幾人可為正義而勇往直前。所謂“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歌劇《小二黑結婚》改編的成功之處正是在“戲”與“情”的恰當結合中,將“陽春白雪”融入“下里巴人”,并在具體事件的呈現中牢記這關于美好品質的永恒話題。這是在任何時代的人們都需思考與審視的,這也是中國歌劇在不斷發展與創新中所應追求的價值與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