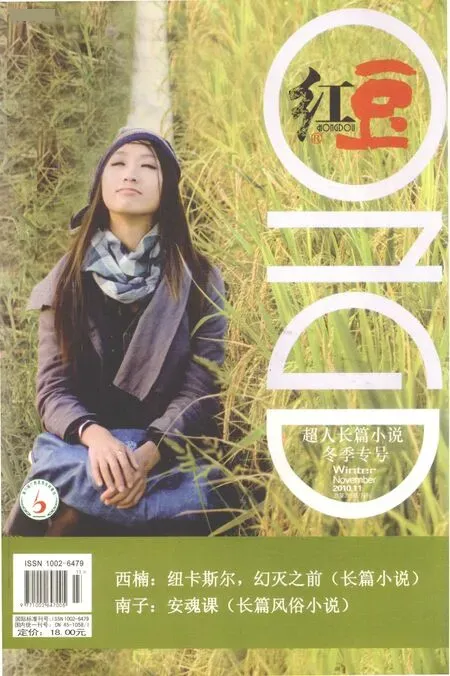記在心頭
粟克武
引子
壬妹不是家生女兒,她是過繼過來的。
當年蘇家兄弟倆從黃毛界下來另尋住所,看上了大槽里一個所在。他倆沿著老紙廠旁邊的水溝上行,幾經(jīng)盤旋,來到山腰一塊不大的平地,倏忽間驚起一對白色的大鳥。哥子駐足觀望良久,見山勢蜿蜒,腳下一片緩坡恰如臂肘的拐彎處,背靠高峰、左環(huán)右抱、竹木林立,形似鳥巢。哥子仰望天空飛翔的白鳥,脫口說了一句“天鵝抱(孵)蛋”。
兄弟倆擇期動工,在“天鵝抱蛋”的地方建起了三間簡陋的燕子屋,定居下來。
此后不久,哥哥在山下邂逅一個外鄉(xiāng)逃難的年輕女子,兩人年貌相當,遂結為夫妻。數(shù)年之后,妻子一直沒有生養(yǎng),反倒是后來成婚的弟弟先后生下了一男二女三個孩子。兩兄弟商議,弟弟將排行老二的女兒過繼給哥哥承續(xù)香火。
這個女兒生于1920年,農歷壬戌狗年,小名壬妹。她就是我的奶奶。
遷徙
壬妹是在大槽里出生的。
壬妹伯爺,也就是后來她的爺佬(父親)選中“天鵝抱蛋”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有個地理先生馬后炮的說法是,此地貌似仙居、蘊含靈氣,其實水弱土薄,木火旺而金缺。上山難走、下山難行,除了砍柴燒火方便,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
爺佬奶奶的過世,終于讓爺佬下決心離開大槽里。
那一年的年景極為艱辛。山嶺上種的苞谷稀稀落落,房前屋后的瓜菜剛剛結締就打蔫掉花,山上的野獸、野果也比往年少了許多。老奶奶忍饑挨餓支撐了小半年,終于一病歸西。
給老奶辦喪事犯了難。爺佬跑了幾十里山路,跨過三縣界,從永福一個老同家里借來三斤大米。他吩咐老婆洗干凈平時熬豬潲的大鐵鍋,煮了一鍋白米粥,從菜園里摘了一把辣椒豆角,炒了一盤小菜,請來自家屋里的幾個親戚幫忙料理后事。這幾個人和爺佬家里一樣,多時不曾見到白米了,看見白米粥眼睛都發(fā)綠。拿起碗筷,一陣風卷殘云,祭到粥滿咽喉才放碗,走一步路都能聽見肚子里稀粥晃蕩的聲音。
棺材出門的時候出了大事。幾個腳力喝飽了粥,肚子發(fā)脹、腳下發(fā)軟,反倒使不出力。一聲吆喝,肩上的壓力一沉,前面的幾個人跌翻在地,嘴里噴出混著辣椒豆角的東西,滿堂屋散發(fā)著還沒有完全消化的食物的臭味。棺材被顛翻在堂屋里,裹著黑色壽衣的老奶滾落下地。
這個詭異的情景讓所有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從壽材里甩出來的老奶剛好落在跪守靈前的爺佬跟前。爺佬幾乎是面對著面地清楚地看見老奶灰暗蒼白、毫無生氣、似乎痛苦異常的臉。老奶的一只手彎曲著壓在身下,五指直伸,指向門外。
安葬老奶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爺佬的眼前經(jīng)常晃動著老奶那張蒼白痛苦的臉和伸向門外的手指。爺佬終于恍然大悟,離開此地。
爺佬看中了大槽里沿河下游五里以外的蛇頸。
小溪水從大槽里更遠的山里嘩啦啦地淌下來,沖出爛石口,流經(jīng)老虎沖以后,碰上了對面山上長長伸出的一道山梁。河水順著山勢拐了一個彎,沖到對面的山根又急速地拐回來,形成了一個長長的帶狀河灣,形似長蛇急速回頭的樣子,這就是“蛇頸”。
蛇頸是上天賜予當?shù)厣矫竦囊坏烂谰埃x予了這片土地天然柔婉的靈性。可是這道美景在后來大躍進的運動中被生生破壞了。當時有人出了個餿主意——圍河造田。這個貌似創(chuàng)造性的提議,一下子點燃了山民們愚蠢的孽火,他們用鋼釬、鐵錘和炸藥在山梁上打開了一個口子,上游筑起了一條攔河壩,河水跨過打開的缺口、穿過山梁直接進入了下端河床。蛇頸像是被猛然砍了一刀,柔軟彎曲的部分被硬生生地分離開來。河床被改造成了20多畝農田,也打了一些糧食,可悲劇的結局從蛇頸被截斷的那一刻就開始了——蛇頸的靈氣再也不復存在。
爺佬把新家安在靠近蛇頸河邊的山坡上。這個地方大致也算得上是依山傍水,只是水不在近前,山也離得蠻遠。從家門口到蛇頸河邊要下一個陡坡,大概走里把路;屋后遠處是摩天寨,兩座渾圓挺拔的山峰緊緊相連、高高聳立,極似帶仔農婦凸出的雙乳。站在半山坡上的家門口放眼望去,蛇頸河谷凈收眼底,空曠寬闊,滿眼翠綠。
蛇頸在還沒有被截斷的時候充滿靈氣。壬妹盡得青山秀水的滋潤,出落得花枝招展,水靈如熟透的山桃。壬妹從小跟隨長輩謀生活,山上田里、農活家務、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跟爺佬出山趕圩,壬妹來回挑八九十斤擔子不在話下。周圍都曉得蘇家老大有個能干的妹仔。
壬妹17歲那年,爺佬決定給她招郎。上門提親的媒婆踏破了門檻。爺佬最終選擇了獅子口外頭朗村石家的一個后生石天友。
獅子口是舊時鄉(xiāng)公所所在地。解放以后,鄉(xiāng)公所改為鄉(xiāng)政府,后來叫公社,再后來又改做鄉(xiāng),鄉(xiāng)又改為鎮(zhèn)。
由獅子口往南是桂北架橋嶺北支的崇山峻嶺,以北是喀斯特地貌間雜的平原地帶,在這里自然形成了“山里”和“外頭”的分界線。大江河從山里奔騰而出,越過石壁嶺下的狹窄河道瞬即趨于平緩。河西是一條地勢平坦、綿延數(shù)里的土嶺,叫做馬嶺山。河東是一座兩端高聳、中間凹陷、形似一頭威嚴端坐的巨大的雄獅的石山,名為獅子山。后來人們在石壁嶺截斷小河,修建了一座水庫,這就是桂北有名的臨桂大江水庫。
獅子口的來歷頗有韻味。傳說很久以前,在大江河兩岸生活著一只獅子和一匹天馬。河東是獅子,河西是天馬。天馬每天自由自在地在嶺上快活地奔馳,山頂因此踏成了一片寬闊的平地,即為馬嶺山。有一天,河東的獅子乘其不備,把天馬一口吞進了肚子里。可是天馬的個頭太大,獅子吞下天馬以后,張開的大口怎么也合不攏,嘴巴里的口水嘩嘩直流。恰好趕山圍海的觀音老母路過這里,見此情形,說了一句“好一個獅子口”,于是獅子化作石山定在那里,“獅子口”因此得名。
獅子口圩場向北,有一座奇特的石山。此山上尖下圓,腰部以下忽然圓滾凸出,極似懷孕待產的婦人,當?shù)厝嗣榔涿弧懊琅畱烟ァ薄J煊炎婢拥睦蚀寰蜕⒙湓诿琅畧A肚之下的周圍。
招郎
壬妹的夫婿石天友是爺佬選的。
那天爺佬趕六塘圩。看見有人在當街“過硬”,后來一打聽才知道是朗村石天友和圩上有名的爛仔劉歪嘴。
“過硬”在當?shù)鼐褪菦Q斗的意思,誰贏誰有理,生死不論。不到矛盾不可調和的最后關頭,不會輕易選擇這種處理方式。
天友“過硬”是被逼無奈。那天他挑著菜園邊上自家唯一的一棵黃皮果樹摘下來的果子趕六塘圩。賣完黃皮果,來到大街上清真寺的米粉店吃米粉,被街上的爛仔劉歪嘴盯上了。劉歪嘴端著一把破茶壺蹭到天友的身后,在天友轉身的時候把茶壺摔在地上,隨后他一把揪住天友,要天友賠錢。天友誠惶誠恐,一個勁地賠禮道歉。劉歪嘴開口就要賠兩塊光洋。這個數(shù)目在街上雜貨鋪買十把新壺都有余,天友就算拿出今天全部賣果子的錢都不夠。
天友看清了劉歪嘴故意找碴兒耍賴的用意之后反倒冷靜下來。幾番論理之后,劉歪嘴使出狠招,把預先準備好的兩根木棍丟在地上,“要么賠錢,要么‘過硬。”
這時候,清真寺前圍上來一大群看熱鬧的人。這種場面不是經(jīng)常能夠看到的,都愿意看大熱鬧。
天友和劉歪嘴在大街上面對面站著,中間兩條木棍擺在地上。天友眼睛掃過周圍,見幾個幫閑的爛仔在一旁躍躍欲試,肯定是劉歪嘴的同伙。他知道只要制服了劉歪嘴,那幾個散仔不足為慮。一暼之間,天友看好了退路。
公證人一聲“架勢”(開始)。天友右腿跨出半步,一腳踩在木棍的前端,那木棍嗖地跳將起來。天友雙手一抄抄在手里,還沒等彎腰取棍的劉歪嘴直起身來,手里的木棍已重重地砸在劉歪嘴的右臂上。只聽咔嚓一聲脆響,劉歪嘴右臂耷拉下來,嘴里發(fā)出痛苦的號叫。天友踏上一步,右腳飛出,將劉歪嘴踢倒在地,手里的木棍迅疾頂住劉歪嘴的咽喉。劉歪嘴見不是對手,躺在地上叫道“好漢饒命”。天友松開腳,丟下木棍,撥開人群,揚長而去。
按照“過硬”的規(guī)矩,天友打在劉歪嘴右臂上的那一棍完全可以直接砸在劉歪嘴的腦袋上,那樣的話劉歪嘴早就小命不保。或者在后來天友踢倒劉歪嘴以后,再加上一棍也會要了劉歪嘴的命。天友手下留情,沒有那樣做。
這一切正好被那天擔柴趕圩的爺佬在一旁看在眼里。回到家里,爺佬托人找來媒婆,讓她去朗村石家傳話。
壬妹是在成婚之后,才發(fā)現(xiàn)丈夫竟然身懷絕技。
有一天,壬妹和丈夫一起上七婆太嶺上鉤油(采松香),天友忽然童心大發(fā),發(fā)掌劈向路邊一棵鼎鍋粗的杉樹,震得樹上的枯枝敗葉嘩啦啦地往下掉。壬妹細問端詳,天友這才簡略地說了自己習武的大概。
這以后每天鉤油路經(jīng)此地,天友公總是要停下來劈掌練功。長年累月,大杉樹齊胸高的位置硬生生被打掉一層皮,數(shù)年后竟枯死了。
按照當?shù)卣欣傻牧曀祝胭樥弑仨毟拿麚Q姓,成為女方家的兒子,今后生出的兒女也必須隨女方家姓。于是石天友變成了蘇宗富。
我母親秋英和奶奶壬妹一樣招郎在家,于是我管自己的外公叫公。在當?shù)兀褪菭敔敗?h3>喪亂
壬妹成婚的第二年生下了頭胎秋英。那一年,壬妹剛滿18歲。
年輕的少婦壬妹盡情地享受著初為人母的喜悅,可她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之后的日子她竟然要經(jīng)歷那么多常人難以承受的巨大苦痛。
壬妹生下頭胎之后,在后來的20多年中連續(xù)生下了8個孩子,可是最后長大成人的只有3個:老大、老四和老九。老二是個男丁,長到已經(jīng)能說話喊人的時候,一場突然的發(fā)賴(發(fā)高燒)就夭折了。老三是個女兒,聰明伶俐,養(yǎng)到7歲的時候給了木橋頭的劉家做童養(yǎng)媳,送過去沒一年就病死了。之后的五、六、七、八也都因為各種毛病一個個地在壬妹的懷里夭折,被天友公葬到了后山的亂樹林里。
最令壬妹傷心的是老七的病逝。那是個女孩,農歷乙未羊年出生,取名乙秀。這個娘娘我見過,是個美麗活潑、敢作敢為的姑娘。有一次,我跟乙秀娘娘去新紙廠河邊的水車兌坎舂米,村里和乙秀同齡的男生水富跑來插隊,乙秀不肯,兩個人動起手來,乙秀把對方的頭殼都打破了。乙秀因此在同齡人中很有威望,好多人都愿意跟她又怕她。
乙秀死的時候大概是15歲。
乙秀是得大葉肺炎死的。農村人都這樣,得了病先是硬扛,最多熬點姜湯、拔個火罐或者點根麻繩來灸灸腦袋,之后病勢厲害起來了,再找草醫(yī)把脈診病、開方吃藥,再后來人快要不行了,這才送醫(yī)院。壬妹家距離最近的六塘圩衛(wèi)生院有30多里,抬到醫(yī)院的時候人已經(jīng)快不行了。一個部隊轉業(yè)的女大夫給她做人工呼吸,清理出乙秀喉嚨里的濃痰,乙秀緩過來了一陣子。當時乙秀很清醒地用家里的土話跟陪在旁邊的大姐秋英說:“我要窩尿。”這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話。
按照當?shù)氐娘L俗,未婚的女兒短命死了是不能進家門的。從醫(yī)院抬回來,乙秀被放置在底下菜園的空地上,裝在用幾塊薄木板釘起來的簡易棺材里。第二天,她被埋在老屋對面蛇頸灣的山坡上。
壬妹送走了好多個自己生下來的孩子,有仔也有女,每次都使她備受煎熬,而這一回最是讓她心痛如絞,像是天塌地陷,因為七妹已經(jīng)眼見著長大成人了,而且還那么的美麗健壯,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映山紅花。壬妹插在心里邊的那把刀子不停地在攪動,讓她沒有一刻的安寧。她長時間呆在房間里,不吃不喝不說話也不理人。
埋葬乙秀之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奶奶喊我去菜園摘一把辣椒回來炒菜。菜園里剛剛停放過乙秀的尸體,我的小腦袋瓜里浮現(xiàn)著聽過的鬼故事,看著陰沉的天空,我心中發(fā)緊,對奶奶說:“我怕”。奶奶看了我一眼,沒有生氣,她把我摟在懷里,說:“不怕,乙秀娘娘不會嚇唬我們的。”
奶奶說話的時候聲音很平靜,大滴大滴的眼淚滾落下來,掉在我的額頭上,冰涼冰涼的。
壬妹9次生子,6個夭折。每一次失去親生的孩子,對于壬妹來說都如同走過一次鬼門關。家婆安慰她說,“這個仔天生不是我們家的,留不住的,看開點。”于是,壬妹也認為是上輩子自己造了孽,這輩子來還債。
壬妹年近50歲的時候,更大的災難降臨了——丈夫天友突然死于非命。
天友公死于20世紀60年代末,壬妹的親哥子,他揭發(fā)天友私藏槍支子彈。其實私藏槍支子彈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解放初剿匪的時候,他從一個散匪的手里買了一支七九步槍和兩排子彈,用油布包裹起來藏在屋檐下面的墻筋上。天友知道這個事情,曾勸過他主動上繳,免得以后惹麻煩,哥子執(zhí)意不肯。這時候他害怕被揭發(fā)出來,于是倒打一耙,反過來誣陷天友私藏槍支子彈。
這個頭一開,好些人一哄而上。他們把解放初期清匪反霸,入社交農,大躍進砍樹燒荒,甚至于某家與某家的矛盾糾紛等等統(tǒng)統(tǒng)歸因罪于天友。
更要命的是,有人檢舉天友當過國軍的兄弟天山從臺灣給天友寄來過一封信,被朗村人拿走了,是特務活動。
大隊里的人把天友公關押起來,簡單地開了一個所謂的群眾大會,把天友定性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然后拉到大隊部外面更樓邊的河灘上,執(zhí)行槍決。
刑場是河邊的一片沙灘。天友被押著跪在沙壩上,3個槍手站在他身后幾十步遠的地方。他們端著鳥槍,槍膛里裝填了黑硝和鐵砂,還特意裝上了打野豬用的一寸多長的熔鉛碼子。3個人同時瞄準開槍,3顆碼子全部打在天友的背脊上。
槍響之后,天友歪倒在沙壩上,還沒有馬上斷氣,在地上痛苦地扭動著。3個槍手中一個姓王的走上前去,抵近補了一槍。天友不再動彈。
天友公被打死在更樓邊的時候,大女兒秋英在外面當干部的丈夫正好被關進了牛棚。壬妹和秋英帶著一家老小給天友收尸。
壬妹給橫躺在沙壩上的丈夫的尸身換上一套干凈的衣服,在他腦門前的沙土上點起3炷香、燒了兩打紙錢,然后把他裝進棺材,抬到山上埋葬。
蓋棺之前,壬妹叫來自己的滿仔古子和秋英的3個兒子,對他們說,你們好好看清楚你叔(父親)、你們公的樣子。壬妹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異常平靜,聽不出一絲一毫的悲傷與憤怒,就好像在交代一件最平常不過的事情。秋英帶著四妹和乙秀兩個妹妹跪在天友公的棺材前面,她們沒有哭,也沒有說話。
那時候壬妹的滿仔古子剛剛6歲,秋英的3個兒子,一個7歲、一個5歲,最小的一個剛剛會走路。壬妹引著4個孩子,圍著棺材,眼睛看著天友公的尸身,慢慢地走完一圈,然后吩咐蓋棺。
埋葬了丈夫回到家里,壬妹吩咐秋英和四妹拖來幾個大柴蔸,在灶門口的火塘里燒著大火。壬妹和家婆、秋英、四妹、乙秀五個女人,帶著四個孩子圍在陰暗窄小的灶膛邊取暖。熊熊的火苗燃起,胸前暖和起來,后背卻依然是一片冰涼。四妹首先抽泣起來,秋英、乙秀跟著大放悲聲,壬妹再也止不住淚如泉涌。
屋子里一片哀傷與悲涼。
起屋
天友死后第二年開春,解放軍進駐靖遠村,給天友平了反。壬妹和大女兒秋英拿到了300元賠償費。
她們在老屋子旁邊不遠處建了一座新屋。堅決不與燕子屋那邊那個伯爺同在一個屋檐下。
秋英清楚地記得出事那天的情景。天擦黑的時候,秋英在河邊收被子。隔壁的伯爺回來報信,他幸災樂禍地在河對岸大聲喊:“秋秋,你老子的腦殼開了花了哦。你看拿來哪門搞哦!”秋英心頭大震,自己預想到的最壞的結果真的出現(xiàn)了。秋英強壓住心中的悲憤和怒火,惡狠狠地回了一句:“拿來哪門搞?拿來吃!”轉身回到家里,和壬妹抱頭痛苦。
解放軍進駐村里,秋英敏感地意識到給父親翻案的機會到來了。秋英到大隊部找?guī)ш牭膹埌嚅L。大隊支書攔住不讓見,他對張班長說:“別理她,他們家是反革命。”秋英說:“我們家不是反革命。我們是被冤枉的。我丈夫是退伍軍人。”張班長聽到秋英的后半句話,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好感,讓她進屋里說話。秋英對張班長說:“我的父親被他們打死了。我父親是冤枉的。請解放軍給我們伸冤。” 張班長說:“人命關天,我們要認真調查。你慢慢說。”
調查很快有了結論。大隊那一伙人給天友羅列的反革命罪行查無實據(jù),所謂的臺灣特務來信,也只是聽說,誰也沒有看見過。
天友之死屬于錯殺。
解放軍給天友公平了反,專門在大隊部召開了一場批斗大會,懲辦開槍殺人的兇手。張班長主持大會,3個槍手和大隊支書被五花大綁跪在臺上。秋英瞧準機會,從屋檐底下的柴堆上扯了一根劈柴,沖上臺去,劈頭蓋臉就是一頓亂打。站在臺邊的解放軍戰(zhàn)士上前攔住,說不準拿棍子打人。秋英就用腳踢、用手抓,一邊打一邊哭訴,狠狠地發(fā)泄積蓄已久的滿腔憤恨。3個槍手和大隊支書被打得頭破血流,跪在臺上不敢吭氣。
壬妹和秋英起房子得到了靖遠村所有人家的支持。每天都有好幾十人來做事,而且是自帶瓜菜、背米打工。那陣子家里到處都是堆起的南瓜冬瓜,基本上都是周圍鄉(xiāng)鄰和親戚朋友送來的。
按照原先的設計,房子應該是兩丈一尺高的,但是建成了以后只有一丈九尺多一點。壬妹一說到這個事情就忍不住要罵木匠王老六,說他是個懵懂鬼,下料的時候把堂屋前面的兩根大柱的石墩忘記了,都下短了一截。等到發(fā)現(xiàn)問題的時候已經(jīng)晚了,只能將錯就錯,改成了現(xiàn)在的樣子。
住進新房子以后,家里接連發(fā)生了很多驚險的事情。
壬妹的滿崽古子那天上樓喂貓,下來的時候一腳沒有踩穩(wěn),從一丈多高的樓上像倒樹一樣摔到地上。壬妹嚇壞了,以為自己寄托全部希望的這個男丁就此了賬,是不是就要追隨他的父親而去?聽得兒子的慘叫聲沖過去的時候心里都涼了半截。沒料想古子大哭一場之后,吃了個壓驚的雞蛋很快就安靜下來。壬妹摸遍了古子身上的每一部位,反復問他有哪里不舒服,又對他觀察了好半天,在確信沒有大礙之后,心中一塊石頭這才落了地。
古子摔下樓梯后不久,秋英的老二西毛爬到新屋子旁邊的梨樹上摘梨子,樹枝折斷,從3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來。那時候,新屋子剛剛建好不久,梨樹下零零落落堆滿了建屋子挖出來的石頭,可巧的是,西毛掉下來的地方恰好是一小塊沒有石頭的草地,雖然摔倒地上的聲音極響,但西毛身體毫發(fā)未傷。他在地上躺了不到3秒鐘,一個翻身爬起來,轉身去撿樹上掉下來的梨子。
秋英的老大東毛被劇毒蛇竹葉青咬傷的那次就沒有這么幸運了。那天他上山裝耗子坎,一條兩尺多長的竹葉青蜷縮在路邊的樹葉上,東毛走過的時候碰中了它,迅即被咬了一口。跛子天福叔正好路過,趕緊幫他用水清洗傷口,扯下身上的一條破布扎住傷口上端,把他背回家中。天福叔敲爛一個飯碗,在灶膛火口烘烤破碗的邊緣,用它割開傷口,擠出幾滴黑血,采了幾蔸草藥敷上。東毛的手臂腫起圓溜溜的,像個棒槌,痛了半個月竟然沒事了。
進新屋的那年冬天,東毛、西毛和古子帶著老三小林在屋后山上砍樹學燒炭。4個小孩根本不懂砍樹要領,不知道應該從樹倒方向的陰面砍而是從坡上順手的陽面砍。砍過樹心的時候,大樹被風一吹,發(fā)出嘎嘎嘎嚇人的一陣爆響,隨即從砍口處裂開兩半,樹干帶著樹枝樹葉,像犁頭一樣重重地向幾個人站的位置飛快地鏟過來,轟隆一聲倒下。那棵米椎樹好像長了眼睛,沒有碰一下當中的任何一個人。當天夜晚壬妹聽4個孩子興高采烈地講白天砍樹的經(jīng)歷,嚇出了一身冷汗。
壬妹將搬新家以后平安渡過種種波折歸結于祖宗保佑。逢年過節(jié),壬妹極重視敬神祭祖。先是堂屋,次在大門,后在門外的坪子上,擺上祭品,斟上燒酒,點起香燭,燒過紙錢,壬妹口中喃喃自語:太公太婆來吃哦,保佑我們一家平平安安哦!
苦難
天友公死的時候我才5歲多一點,我對公的記憶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模糊了。
給公收尸的那天,奶奶叫我們幾個小孩圍著公的尸體走了一圈,吩咐我們看清楚公的樣子。當時我看得很清楚,也記得很清楚,可是到我長大成人以后,公的樣子在我的印象中反倒越來越模糊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抬公的棺材上山的那條山路,特別難走。那條路從雙岔河肖家屋背后上山,路很窄也很陡,在我看來幾乎是直直往上,像爬樓的筆直的梯子一樣。我緊跟在棺材的后面,手腳并用地爬行,沒走多遠便大汗淋漓。我覺得自己的心臟怦怦亂跳,幾乎喘不過氣來,眼看著前面的棺材越走越遠,我急得快要哭出來了。這時候,老廠七奶的小兒子石生從我的后面趕上來,他彎腰抱起我,飛快地向前跑去。我雙手摟著石生叔的脖子,在他的懷里慢慢地恢復過來,心里對這個小叔充滿了感激。
埋葬公的墓穴在埋人坪頂上一塊不大的平地,背靠蛇頸,面向他的老家南邊山朗村。那天,早早就有人預先上山選好地方,打好了井穴。公的棺材抬上來,在井穴旁稍稍停留了一陣子就安放下去了。那井穴很深,高高的棺材沉下去還有好長的一段距離才到地面上。我站在旁邊的高坡上,眼看著家屋里的幾個親戚揮動著鋤頭鐮鏟用泥巴把裝著公的尸體的棺材蓋住。泥巴蓋平地面以后繼續(xù)堆高,最后形成一個松糕的形狀。母親搬來一塊大石頭安放在墳堆前,掛上一張紅紙、一沓紙錢,點著一把香,然后跪下叩頭。
奶奶凝望著墳前的石頭,說:“以后你們要給他豎一塊石碑。”
直到50年之后,奶奶也已經(jīng)作古了。古叔和我們3兄弟把公的墳遷到了朗村石家的墓地里,用花崗巖青石豎起了一塊石碑。
埋葬了公以后,我跟隨奶奶上了七婆太嶺。
第一次上山,我就被七婆太嶺的雄奇俊美深深地震撼到了。七婆太嶺極頂是兩座巨大的渾圓挺立的山峰,就像農村奶孩子的少婦碩大而直立的雙乳。更為奇特的是,山上的植被自然分布為上下兩段,線下是綠浪翻滾的竹林,線上是千姿百態(tài)的混交林。
七婆太嶺上最高最大的樹自然是松樹。大多數(shù)松樹比水桶還粗,最大的幾棵兩三個大人牽著手還抱不過來。站在幾里路以外的沖水塘,可以遠遠看見嶺頭上那棵大松樹堅硬如鐵伸向天空的樹冠。
松樹油性大、耐腐蝕,其最大的用處是做修鐵路的枕木,此外就是采集松脂,那是制造油漆、肥皂、紙、火柴的工業(yè)原料。在我們當?shù)兀巡杉芍Q為鉤油。
鉤油類似于割膠。先用刮鏟除去松樹表皮粗糙的部分,露出深紅色的嫩皮,再用一種特制的鐵鉤,分左右45度將松樹的表皮各開出一道斜槽,沿兩道斜槽匯合的中央自上而下鑿一條通道,下端裝上小橋板,橋板下方釘一個竹筒接引松脂。松樹開槽以后,創(chuàng)口迅即流出一種黏性極高的液體,這種液體即為松脂。松脂凝固后蒸餾所得的物質就是松香。
奶奶是教我鉤油的師傅。第一次傳藝,她特意選在一個相對陡峭的斜坡上。奶奶一邊比畫一邊說,鉤油最要緊的是站穩(wěn)腳跟,特別是在險火(危險)的地方,搞不好跌下去小命就挨撿起了(死掉)。鉤油的時候,鉤子入木的深度要恰到好處,一般以一顆米的厚度為宜,太淺不出油,太深則費勁,還浪費;推鉤子用力要均勻,節(jié)奏要適當,動作連貫,一氣呵成。
多少年以后,奶奶的那次傳藝依然恍如昨日、清晰難忘。多年以后我才領悟到,奶奶講的是鉤油的動作要領,其實蘊含著為人處世的道理,令我終身受益。
我最喜歡看松脂冒出來的樣子:剛剛鉤過的松樹,新開的溝槽里先是冒出零星的細小的油點,漸漸地由少變多、由小變大,像汗珠、像黃豆、像深紅色的珍珠,隨后珠兒相互碰撞、聯(lián)起手來,形成一道細細的線流,沿著溝槽向下飛奔,最后跨過橋板、躍進竹筒。那情形,猶如魔術般令人心動。
一天中午,我爬上摩天寨懸崖邊上那顆高高的鳥柿子樹摘果子。撥開密集的樹葉,四周美麗的景色一下子撲面而來:一道道山梁層次分明、錯落有致,遠山近樹郁郁蒼蒼、黛如墨染。左看是樹木蔥蘢的老虎沖,右望是蜿蜒起伏的架橋嶺,山腳下我們家像個小小的火柴盒。再往遠看,可以清楚地望到二十幾里外的圩鎮(zhèn)。我興奮地大聲喊:“奶奶,我看見獅子口了。”
奶奶問我:“獅子口外面呢?”
我說:“看不清楚了。外面是什么地方?”
奶奶說:“是六塘圩,再過去是雁山。”
我問:“六塘圩、雁山過去呢?”
奶奶說:“再過去就是桂林啊。”
我問:“桂林再過去呢?”
奶奶說:“那我就曉不得了。你長大了自己去看吧。”
奶奶的話深深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好長時間我一直在想,桂林的外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那個地方有多大?是什么樣子?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天友公死的時候,奶奶已年屆五旬,她依然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領來了隊里放牛的差事,帶著我們幾個小的上七婆太嶺鉤油,有時還參加割田基、出牛欄糞、守倉庫、收山嗆子、摘紅花草籽,等等,能掙工分的事情她都做。
秋天到了,田里的晚稻打回來,在秋陽下曬干,收進了生產隊的谷倉里。那是一個豐收的年景,壬妹心里高興,她盤算著這次分新谷子,一定要給家里的老小吃一頓不摻紅薯的白米飯。
那天下午,奶奶帶著我去生產隊倉庫出谷子。家里早就沒有大米煮稀飯了,一家人已經(jīng)連續(xù)吃了幾天紅薯、芋頭。一路上想著金黃色的稻谷和香噴噴的白米飯,奶奶和我都特別開心。輪到我們出谷子的時候,生產隊管賬的會計對奶奶說:“表姑,你們家還有一百多塊超支款沒有還,不給出谷子。”奶奶說:“先給我們出了嘛,超支款我們以后還,肯定會還的。”會計說:“隊里定了,不給出的。”
滿懷希望就這么泡湯了,奶奶的心情壞到了極點,她臉色灰白,拉著我轉身就走。跨過門檻、走上倉庫對面的山梁,奶奶悲愴地破口大罵:“我操你們的娘,餓死人你們要負責。我看你們哪個能坐一萬世!”
那是我看見奶奶最傷心的一次。
講古
奶奶從未念過一天書,大字認不得一個,但奶奶講話卻頗具文采,往往出口成章。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天色將晚奶奶趕雞進籠的時候,總是一邊趕雞、一邊念叨:
小小雞公你莫雄,
好生圍你進雞籠;
若還哪天客來了,
殺倒你來擺盤中。
有一年過春節(jié),住在隔壁永忠大隊的姨婆來我們家住了一夜。吃過早飯不久,奶奶和姨婆剛剛聊了一陣子便起身去忙午飯,姨婆笑著說奶奶,急什么,一天到晚就講吃。奶奶笑著吟出一首順口溜:
人在世間不講吃(桂林話ki),
累生累死又何必;
幾時閻王勾了簿,
最多占得五尺泥。
奶奶講故事總是有由頭的。
有一次跟奶奶到山里放牛,我們把牛往山上一趕,奶奶帶著我在河邊的水溝里討豬菜。她一邊做事,一邊給我講了一個放牛娃遇龍的故事:從前有個小孩,每天和小朋友一起到山上放牛。有一天,大家玩捉迷藏的時候他一不小心掉進一個地洞里。洞里有一條修煉成精的大蛇,靠舔一個夜明珠維持生命。小孩和大蛇在一起呆了幾天,大蛇答應帶他出去并一起去看大海。這一天大蛇終于修煉成龍了,小孩騎在龍的脖子上,抓住龍角飛出了地洞。經(jīng)過家門口的時候,小孩進屋去和母親告別,母親煮了兩個雞蛋給他吃。可是等他再出門口的時候,龍已經(jīng)不見了,原來雞蛋是葷腥,神仙是絕對碰不得的。
當時我就想,要是我能遇到那顆夜明珠就好了,我肯定不吃雞蛋,那樣我就可以騎著龍去看大海了。
黃毛界老水伯家討媳婦擺酒,奶奶叫古叔和哥哥帶著禮性去吃酒,我和奶奶、太婆守屋子。奶奶給我講了一個關于吃酒的故事:
從前有戶人家,母子二人相依為命。有一天兒子去親戚家吃酒,席上的好菜他都不舍得吃,打了個包帶回家去給老娘吃。走到半路上廁所,一不小心菜包掉進了茅廁里。他急忙撈起來,可是菜已經(jīng)被弄臟了。兒子舍不得扔掉,就到河邊把菜洗洗干凈,帶回去煮好給老娘吃。老娘毫不知情,吃得津津有味。這天晚上,忽然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電閃雷鳴。兒子認為是自己給老娘吃了不干凈的東西,老天要懲罰他。于是跑到屋外的大樹腳跪下,述說事情的原委。這時候,天上傳來一聲巨響,一道耀眼的閃電過后,前面的大樹被連根掀起。兒子安然無恙,大樹根部現(xiàn)出一個小小的壇子,打開一看,里面全是銀元。兒子高興地把銀元帶回家中,用這些錢蓋了新房子,和母親過上了好生活。
隔壁家有個懶漢,看到這家人生活變好了感到很納悶,就過來問是怎么回事。兒子是個老實人,就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經(jīng)過告訴了懶漢。懶漢聽了以后來勁了,他也想有這樣的好事。這一天他去親戚家吃酒,也打了一個包回來。半路他也去上廁所,故意把菜包掉進茅坑,然后撿起來洗干凈拿回家里給自己的老娘吃。這天晚上,果然也是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電閃雷鳴。懶漢跑到自家屋外的大樹腳跪下,等著拿銀元,不料一個大雷劈下來,大樹沒有倒,壞心眼的懶漢被劈死了。
奶奶還有好多好聽的故事,諸如貪吃的、占便宜的、壞良心的、講鬼作怪的等等。她的故事肯定是從上一輩的老人口里流傳下來的,這是民間百姓借以普世教人的不二法寶,難得的是她的故事講得如此動聽,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上大學以后,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啟蒙》,主題是奶奶是我的啟蒙老師。
我一直覺得奶奶是一個全能的廚藝大師,沒有什么好吃的東西是她不會做的。
奶奶最拿手的美食是炒糯米飯,盡管她展示這個手藝的機會一年也沒有幾次。糯米飯煮好之后,用豬油爆炒,加入板栗或花生,再經(jīng)文火反復翻炒半個時辰,起鍋之前撒上少許蔥花、香菜就成了。那份油膩鮮香柔軟和黏糊,對于饑餓年代的人來說,是最美好的享受!
奶奶另一樣拿手的美食是罐子煨豬尿泡。每到殺豬的時候,奶奶將豬尿泡洗凈,塞進一把糯米,放在瓦罐中加清水慢火煨煮。約半個鐘頭,豬尿泡混合糯米那種又臊又香的特殊味道慢慢地彌漫開來,直沖味蕾,讓人饞涎欲滴、欲罷不能。每到這個時候奶奶就會笑著說,哪個是夜晚賴尿(尿床)的啊?于是我們4個小孩不約而同地大聲嚷嚷:“我賴尿、我賴尿!”
治賴尿奶奶還有一個絕活偏方。碰到從屋角落跑出來的蟑螂,老奶迅即一個鞋底揮過去將蟑螂拍死,然后用火夾夾住塞到灶門口的紅灰里。紅灰剛剛從灶膛里刮出來,非常燙,蟑螂的翅膀和觸須很快被燒掉,發(fā)出一股難聞的焦臭。這時候奶奶用一根樹枝,把蟑螂來回翻滾幾遍,然后撩出來,放在手心里拍拍幾下,就可以吃了。據(jù)說,這招治賴尿也很管用。古子叔和哥哥對此非常著迷,而我嘗過一次之后就敬而遠之了。我對奶奶說我不賴尿。
甜酒、酸壇和楊梅醋也是奶奶的拿手好戲。可惜那時候不明白奶奶這些看似尋常實為珍貴的手藝的價值。奶奶去世以后,她的這些絕技也都帶走了。
西去
苦難的歲月,慢慢地漸行漸遠。
1979年,我考上了大學。我是家族里的第一個大學生,在整條河水的人家中也是第一個,全大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長時間成為被議論的話題。每一個見到我奶奶的人,都熱切地對她說著羨慕和恭維的話,都說她有福氣。
再后來,我的哥哥考上了中專,弟弟也參加了工作。有好事者傳說我們家的風水好、出人才。于是好幾家人跑到我們家周圍建房子。本來是單家獨戶的我們家,前前后后都有人住,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
生產隊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先是搞承包,后來分田到戶搞單干。田里的收成全是自家的,自留地里隨便種什么再也沒有人來管,山上的竹木賣得的錢也歸自家所有。鍋頭里餐餐都是白米飯,偶爾想換一下口味才吃一次紅薯、芋頭。隔三岔五的,滿仔古子都要趕圩買肉回來打牙祭。
自從天友公死后,奶奶帶著一家苦熬10年,終于雨過天晴、看見天亮了。奶奶這時候真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輕松自在。
奶奶真正放手不管家事是在古子娶妻生子以后。她把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都交給兒子,除了帶帶小孫子、煮點飯、喂喂雞,基本不過問家里的大政方針和柴米油鹽。
奶奶在侄孫女結婚的時候表現(xiàn)出來的寬宏大度再一次贏得了整個村的尊敬。
世間的事情就這么巧,幾十年過去了,當年殺害天友公那個補槍的槍手的兒子,要和奶奶的侄孫女結婚。對這件事,奶奶至始至終沒有說一句阻攔的話。
成親那天,奶奶的侄媳婦邀請我去接新人。他們覺得請我這個家族里的第一個大學生,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外面當官的人出面迎親很有面子,沒料到我黑著臉一口回絕。
聽到小嬸請我?guī)退佑H,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當年更樓邊沙壩上天友公那張蒼白灰暗的臉,想起那天奶奶讓我們圍著棺材盯著天友公轉圈的情景。我渾身熱血滾燙,滿腔憤懣撐得我的身體似乎要炸裂開來,我覺得自己要是去接了這個新郎,我就無法面對死去的天友公和身邊年邁的奶奶。我毫不留情地斷然拒絕了。
父親在一旁看在眼里,他心里雪亮,出來給我打圓場說:“老二沒有合適的衣服,就不去了。”
奶奶的侄媳婦悻悻地走了。奶奶拉著我的手,小聲地說:“仔耶,以前的事情過去了就罷了!”
奶奶是在2009年的秋天去世的,距離她89歲生日還差7天。
整村的人都來了,有三四百人,流水席吃了四五十桌。參加葬禮的人大部分都沒有表現(xiàn)出什么悲傷,按當?shù)氐牧曀祝擅脡壑?0(虛歲),是喜喪。吊喪的人們在壬妹的靈前點上一炷香、磕過頭、燒過紙錢,便談論起壬妹的為人,說她命丑命好、大起大落、先苦后甜,這一輩子也不枉了。
奶奶下葬的時候我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那時我出差在菲律賓馬尼拉。中午導游把我們帶到中華義山(陵園)參觀。這個計劃是導游自己安排的,也許他認為義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地點,應該給來自中國的客人看一看。車停下來,我抬眼一看,四周都是陰森森的房子,里頭是各式各樣的墳墓和墓碑。我心中忽然有很短暫的一下震動,腦子里閃過一絲不祥之兆——奶奶走了!
奶奶正是在我感受震動的那天過世的。接到妻打來報喪的電話,我已在印尼雅加達。從豪華的婆羅浮屠大酒店往北眺望,南中國海波濤洶涌、碧浪連天。憶及奶奶,我不禁悲從中來,詩如泉涌——
我下南洋覓梭羅,
無奈老奶西駕鶴。
慈顏梵音今何在?
黃土一抔桃子窩。
八十九載風雨路,
淡飯粗茶苦益多。
磨難經(jīng)年尋常事,
大度包容天地闊。
才憶別時人落淚,
又見新墳鬼唱歌;
歸來倚門人不見,
黯然傷神嘆蹉跎!
(注:桃子窩,奶奶的墳塋所在地。)
責任編輯? ?丘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