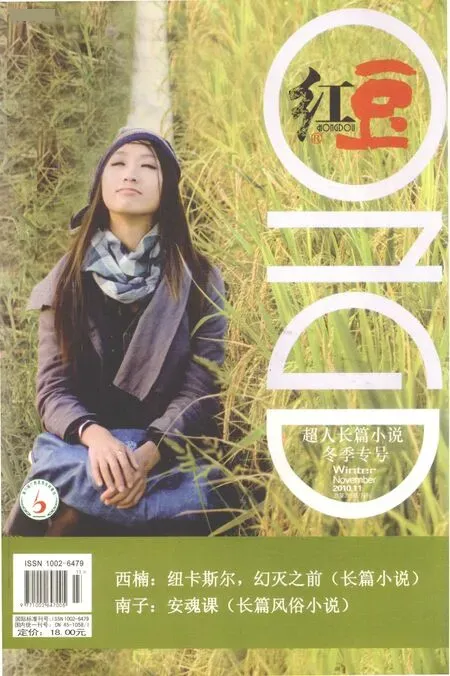鐵線草
李沛新
我的家鄉在桂南郁江南岸。這里丘陵眾多,平地不少,氣候炎熱,雨水充沛,植被茂密,插根拐杖也能長出一棵大樹來。剛剛翻過的土地,用不了幾天,又會長滿雜草,尤其是當地有一種草叫鐵線草,根系發達,主干粗壯,枝丫多,把頭貼著地面,緊緊扒著泥土,賤生賤長,任憑人畜踩踏,牛馬啃食,只要風一吹,雨一淋,又是滿目蔥蘢,綠油油一片,軟綿綿的像地毯。我們常常在風和日麗的傍晚,躺在鐵線草長成的“地毯”上,凝望著亂云飛渡的天空,麻雀成群結隊地在低空飛舞;雄鷹在高空翱翔,突然像閃電一樣俯沖而下,刺向雀群;一陣尖叫聲過后,麻雀們紛紛躲到草叢里去,雄鷹則振動著碩大的翅膀往遠處的大樹飛去。麻雀的慘叫聲最終消失在遠處的樹林里,藍天白云也漸漸地變成了漫天彩霞。
一
奶奶生于1911年農歷四月二十五日,娘家在貴縣東津鄉甘寺村寺聯屯。奶奶命苦,出生沒幾多久就死了父親,母親改嫁后,由她的大叔叔收養。在那個年月,人們活得都不容易,奶奶的大叔叔家人口眾多,生活也很艱難。沒娘的孩子像根草,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寄養在大叔叔家的奶奶特別早就懂事,從小就勞作,常常以瘦弱的身軀干著各種繁重的農活,以此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盡量不增加大叔叔家的負擔。超強度的勞作,加上嚴重的營養不良,奶奶從小身體就瘦弱,落下了一個肺結核病,每天都像小草一樣卑微而頑強地活著,人們干脆給她取了個很形象的名字“鐵線草”。長大后,在出嫁前才正式取名叫甘寒妹。嫁給我爺爺后,奶奶先后生育了五兒一女六個孩子,我父親是老大,姑姑是老四,最小的兩個是雙胞胎叔叔,當地叫孖仔,大的叫大孖,小的叫細孖,他們倆比我大哥也沒大幾歲。
在我出生前,我們家就和爺爺奶奶分家單過了。
從我有記憶的那一天開始,奶奶就是一個老奶奶了。她身材瘦小,額頭上布滿了皺紋,滿臉愁容的樣子,總是佝僂著腰,圍著灶頭轉,似乎有永遠也干不完的家務。
天生好動的我,一刻也閑不著,只要不用幫家里做家務,就會滿村跑,除了找小伙伴們玩耍,就是經常跑去奶奶家玩,尤其是早上,早早地等著奶奶起床,在旁邊看奶奶梳頭。奶奶永遠是把頭發梳順之后,在后腦勺卷一個發髻,插上一枚長長的銀針,然后戴著一個狗耳帽箍,頭頂和發髻都露在帽箍上面。一切處理妥當后,便撿起梳頭時掉在桌上和地上的長發卷成一個小團團,一邊遞給我,一邊說:“要是給你嬸嬸知道你就死!”
我知道奶奶是疼我的,只是她也有很多說不出的苦衷。我默契地接過那一小撮發卷,飛也似的跑回家去,把這個小小的發卷塞進一個兄弟姐妹們看不到的墻洞里。每當貨郎挑著籮筐進村,敲著撥浪鼓喊:“收雞毛鴨毛、雞腎皮鴨腎皮牙膏皮啰!”我們村的小孩便紛紛跑回家去,把平時攢下來的東西從各個角落里摳出來,向貨郎飛奔而去,用各自的東西換取貨郎的橄欖果、彈子糖或木薯糖。偶爾,奶奶也會拿一兩個雞腎皮或鴨腎皮出來,換一包有紅黃藍綠白五種顏色的彈子糖分給我們和在場的鄰居小孩吃。看到孩子們興高采烈的樣子,她才把最后一顆孩子們不太喜歡的白色的彈子糖放進嘴里,笑瞇瞇地回家去。
二
據我父親說,他剛剛懂事時,爺爺、奶奶和叔爺、叔奶還沒有分家,兩兄弟各有6個小孩,一個大家庭。我爺爺年輕時經常外出做事,叔奶身體也不好,在這個大家庭里,犁田耙地的事主要是叔爺在干,插秧、種地、挑糞水、種菜、淋菜的事都是我奶奶在操勞。她經常是忙完田里的活再去淋菜園里的青菜,往往勞作到深夜,等她回到家時,家里的大人小孩早已吃完晚飯,洗漱上床睡覺了,晚歸的奶奶只能將就著吃些冷粥冷菜,就算是一餐了。
在一個夏天的晚上,一大家人都已經吃完晚飯了,奶奶依然沒有回來。我那生性膽小怕事的父親心疼奶奶,思母心切,便硬著頭皮去找奶奶。
通往菜園子的小路彎彎曲曲,兩旁的雜草都沒過我父親的頭頂了,草叢里蛙鳴蟲叫,小路上時不時還有蛇鼠出沒。父親戰戰兢兢地走近菜園子時,朦朧的月光下,遠遠地看到我奶奶瘦小的身影孤零零地在晃動,她還在忙碌地淋菜。父親心頭一酸,淚水都差點兒要掉下來,一踏進菜園就叫了一聲:“娘!”
奶奶一愣,看清是自己的大兒子找來了,驚訝地問:“你來這干嗎?”
“叫你回去吃晚飯。”父親怯生生地說。
“誰稀罕你來叫?趕緊回去!”奶奶沒好氣地說。
“那你也要回去吃晚飯呀,都深夜了。”父親勸道。
“不做工,哪來的吃?”奶奶又用她的口頭禪來吼父親。
奶奶的一頓嗆聲,讓我父親無以言對。他原本想著,來的時候害怕一點,回去的時候有母親陪伴就不怕了,沒想到,被奶奶一頓嗆,他完全不知所措地呆在那里。
奶奶又挑了一擔水回來,看見兒子還原封不動地站在那里,更火了,吼道:“你還不回去?在這里找打呀?!”
遭到如此“絕情”的吼罵,我父親只能含著淚水,戰戰兢兢、擔驚受怕、默默地回去了。從此,無論奶奶晚上回來得多晚,他再也不敢晚上去找母親了。
斗轉星移,光陰飛逝。轉眼間,我父親結婚了,我的大哥也出生了。
在農村,有了孫子之后,當奶奶的,一般都不用下地干活了,而是留在家里含飴弄孫,地里的活就交給兒媳婦去干了。大哥滿月后,我母親便找我奶奶商量,讓她老人家不要下地干活了,留在家里照顧兩個孖叔和我大哥。我母親想,這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既能照顧好兩個孖叔和大哥,也符合孝順老人的禮制,奶奶應該不會拒絕。不曾想奶奶一口拒絕了我的母親,說:“我才不會在家閑著呢,我這兩個孖仔由老二、老三幫帶。你兒子也交給老二、老三幫帶吧。”
“那怎么行?你那兩個孖仔都三四歲了,交給老二、老三帶當然可以,我兒子剛剛滿月,哪里放心得了交給他們帶?”我母親申辯道。
“要是不放心給他們帶,你就自己帶吧。”奶奶還是拒絕了我母親的請求,挑起那對與她瘦小身材極不相稱的大尿桶淋菜去了,一邊走一邊嘟噥著:“不做工哪來的吃?”
沒辦法,我母親只能與我父親輪流在家帶孩子。我二哥出生后,便和爺爺、奶奶分家單過了。
奶奶依舊是夜以繼日地勞作,為他們那一大家子的生計而忙碌著。沒有父母疼愛,寄人籬下的奶奶,似乎從小就悟出并始終信奉一個道理——不做工就沒得吃,不停勞作的習慣早已滲入了奶奶的骨髓。
三
在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和姐姐因湊熱鬧,跟著鄰居幾家人到貓兒嶺,遠遠地看他們家挖墳,把撿起來的骨頭裝到一個瓦甕里。
在回家進門之前,他們幾家的老老少少,先在一個裝著滾燙的檸檬樹葉水的木盆里洗手,接著在一個燒得通紅的犁頭鐵上澆上酸醋,瞬間騰起一股酸醋煙霧,每個人都迅速把手伸到煙霧里熏一下,一邊熏一邊喊:“解晦啰!解晦啰!”最后每個人都默默地從一個燒得旺旺的火炭盆上跨過去。據說跨過火盆后,那些鬼魂就不能跟著人回家,被擋在家門之外。做完這三道手續后,就可以自由出入家門了。
我們把這些見聞在奶奶家的廚房里告訴她時,奶奶馬上警覺地問:“你們跟著他們去解晦了沒有?”
“沒……有,他們沒叫我們,我們也不敢跟過去做呀。”我們知道奶奶對此很忌諱,也只能如實回答。心想奶奶也許會有什么辦法補救呢。不曾想,奶奶馬上暴跳如雷,指著廚房門口喊:“趕緊走開!別把晦氣帶到我這里來。”
面對突然變態般怒吼的奶奶,我們姐弟倆都愣住了。
“走呀!”
在奶奶再一次的驅趕下,我們流著委屈的淚,默默地離開了。
奶奶因從小體弱多病,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晚上經常咳嗽,難以入眠,她的咳嗽聲,整個村都能聽見,需要長年累月吃藥。她經常在咳得最難受的時候對人們說:“我的命就像鐵線草一樣賤,咳了這么多年,就是死不了,藥米(指西藥)都吃一籮筐那么多了,真是活受罪!要是哪天能死了,我死眼都閉了。”
奶奶不是說說而已,她在為自己的死做著準備。
一天早上,一個當地有名的木工師傅來到奶奶家,把此前爺爺從外地運回來,靠墻堆在門口旁邊的一堆松木翻下來,扛到他們家廳堂里去。我覺得很奇怪,便跑去問奶奶:“奶奶,你們家準備用這些木頭來做什么?”
“別多嘴,什么都想問。”奶奶沒好氣地回我。
“我就是想知道嘛!”我纏著奶奶問。
“做一副長生,知道了吧?百厭鬼(孩子因多事而討人嫌的意思)!”奶奶嗔怒道。
“長生是什么嘛?”我更好奇了,在我見過的家具中,從來沒有見過一種叫“長生”的。
“長生就是壽,知道了吧?”奶奶耐著性子給我解釋,我卻越發糊涂了。
回到家里,我就奶奶請人做長生的事問父親。原來在我們當地,人們為了避諱,討個吉利,故意把“一副棺材”叫作“一副長生”或“一副壽”,“長生”就是“長生不老”,“壽”就是“長壽”。人們提前為生人做好“長生”,就是 “為了攔命”,這樣就能健康長壽了。
一天中午,我帶著小弟弟去看木工師傅做長生,恰逢師傅去吃午飯了。看著擱在兩個長凳上像船一樣的長生,我突然想看看里面跟船艙有什么區別,便爬上長凳,沿著長生的邊沿翻進去。正在好奇地左看右瞧的時候,聽見奶奶那碎碎的腳步聲已經要到廳堂門口了,要爬出去已經來不及了,只好趁勢躺下去,這樣奶奶就看不到我了。
奶奶進了廳堂,只見小弟弟一個人站在那里,便好奇地問:“你哥呢,去哪啦?”
我正著急的時候,只聽見小弟弟奶聲奶氣地說:“在里面。”
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這小子出賣我了,早知道不帶他來就好啦。正要坐起來,奶奶那布滿皺紋的臉已經從另一頭探進來了,一看見我就罵開了:“你這個百厭鬼,也不怕晦氣,爬進去干什么?”
“我父親說了,長生就是長壽,長生不老,怕什么?”我理直氣壯地回著奶奶話,從長生里面爬了出來。
“哧……”奶奶樂了,笑著說,“你別聽他的鬼話,凈教壞小孩。”
“如果我父親的話沒道理,你現在還好好的,為什么就讓人來做長生啦?”我有些不服氣地問。
“哎,你這個百厭鬼,事兒就是多。”奶奶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說:“奶奶這兩年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也不知道還能活幾天。”
看著奶奶難過的樣子,我只好反過來安慰她說:“奶奶沒事的,我父親說等這副長生做好了,攔住你的命,你就能長生不老、健康長壽了!”
聽了我的話,奶奶露出了微笑,摸著我的頭說:“要是真能這樣就好啰!”
做好了的長生就放在奶奶家廂房的閣樓上,奶奶隔三岔五地爬上去擦拭,就像她平常擦拭一件別的家具一樣。所不同的是,她每次擦拭完了之后,都要站在旁邊凝視一陣,神情安詳而滿足。
四
我的爺爺李帶賢是貴縣東津公社衛生院的中醫,用當時的話來說,爺爺是“吃皇糧的”,家里的經濟狀況好于鄰居。在村里有這種條件的人家,要擱在別的老太婆身上,肯定會自覺高人一等,趾高氣昂,走路都會起風。我奶奶在村里并沒有怎么拋頭露面,她整天駝著背,圍著灶頭轉,為一家老少一日三餐而忙碌。公社供銷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送戲下鄉,就在奶奶家背后演出,汽燈亮如白晝,鑼鼓喧天,歌聲嘹亮,奶奶也沒有出來看戲。
原本應該幸福的奶奶,卻經常被我那剛過門不久的嬸嬸罵。每當這個時候,奶奶便怕得渾身發抖,坐在床沿上默默流淚。
有一次,暴雨過后,奶奶一邊燒火煮豬潲一邊對站在門口的嬸嬸說:“豬欄后面的糞坑又滿了,你去把糞水挑去淋菜,免得再下一場雨,糞坑里的糞水就會溢出來。”
奶奶的話音剛落,嬸嬸便扯著嗓子罵道:“你這個老不死的,這么會吩咐,你自己為什么不去挑?天剛剛下過幾場雨,這個時候挑糞水去淋菜,能滲得下去嗎?”
要是在平時,奶奶早就馬上噤聲,像鐵線草那樣把頭貼到地上去了。可是今天,奶奶也許是太心疼那一池的糞水了,便輕輕地回了一句:“只要你淋下去就能滲得下去的。”
“怎么不得?把你剁了漚成糞水拿去淋,照樣能滲得下去!”嬸嬸幾乎是跳起來叫罵,隔壁鄰居都能聽見。
經此一罵,奶奶馬上噤聲,獨自默默地流淚。
嬸嬸剛走,隔壁一位伯奶就來了,她氣憤地對奶奶說:“十六嬸(我爺爺排行十六),你這媳婦也太無禮啦,你應該把她的不孝行為告訴十六叔或者你兒子,讓他們好好修理她!”
奶奶一聽,馬上阻攔道:“這個使不得,他們父子倆都在外面做事,別讓他們為家里的事情操心。尤其是我兒子,更不要讓他知道,免得他們夫妻倆吵架。”
“你難道就這樣讓她繼續欺負下去嗎?”伯奶不解地問。
“哎,我這個人,你也懂的,從小沒有了爹娘,受人欺負的事還少嗎?忍忍就過了,別讓他們父子倆為難。”奶奶無奈地說。
“總是忍忍忍,這種日子何時是個盡頭!”伯奶憤憤地說。
“還有什么盡頭?我渾身是病,也不知哪一天眼睛一閉就過去了。”奶奶傷感地說。伯奶無奈地搖搖頭,走了。
奶奶怕這位嬸嬸,就像老鼠怕貓一樣。別說被罵了,就是遠遠聽見嬸嬸的腳步聲或是說話聲,有時甚至一提起這位嬸嬸,奶奶都會條件反射地瑟瑟發抖。在這位嬸嬸面前,她是那樣卑微地活著,像鐵線草一樣任人踩踏。
我經常幫奶奶干一些諸如放鵝之類的事情,奶奶為了犒勞犒勞我,時不時給我一個煨玉米棒或者是剛煮熟的紅薯、芋頭之類的小食品,一邊給一邊說著她那句亙古不變的口頭禪:“要是給你嬸知道你就死!”
每當這個時候,我也不多說什么,很默契地拿起奶奶給的燙手的煨玉米棒或者是剛煮熟的紅薯、芋頭就往外沖。實在是太燙手了,只能是一邊跑一邊像拋皮球一樣,讓玉米棒或紅薯、芋頭在兩只手之間來回倒騰,減少燙手的時間,直至涼下來為止。
我知道,那不是我要死,而是奶奶怕被嬸嬸罵。其實這位嬸嬸對我也是不錯的,她逢年過節回娘家省親時,經常把我帶上,有時還住上一兩個晚上。奶奶也知道這些事,可還是要這樣講。
奶奶在1975年12月去世,離她為自己做好長生也就兩年多一點時間,看來她對自己身體的感覺是準的。
去世了的奶奶靜靜地躺在他們家廳堂地面的長生里,戴著一個黑色的狗耳帽箍,穿著一身黑色壽衣,頭朝里,腳朝外,神態安詳,一如她平常睡著了的樣子。
我突然想起了奶奶那句“死眼都閉了”的話,說明她并沒有抱怨,她對爺爺這么多年來對她的不離不棄并盡力治療,是滿意的、感激的,她所經受的疾病折磨是痛苦的,死對她來說是一種解脫,了無遺憾,所以走得安詳。
奶奶最終被葬在貓兒嶺的北面。按照當地習俗,老人下葬后,要在其墳前持續供一個月的香火。這本來是叔叔們的活,孖仔叔叔卻把責任轉交給我,大孖叔叔哄我說:“沛新,給你個任務,你每天早上上學時,順路給奶奶供香,奶奶就會保佑你讀書進步,將來就能考上大學。”
我知道大孖叔叔那些話就是七月十四燒報紙——糊弄鬼的!我只是想著奶奶平常對我的好,才接受了這個任務。接下來,連續一個月,我每天上學時都要繞一下路,給奶奶供香,碰上星期天不上學時,還要專程去給奶奶供香,祝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安息!
很快,在奶奶的新墳上,又長滿了鐵線草,整個墳塋綠油油的。
責任編輯? ?梁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