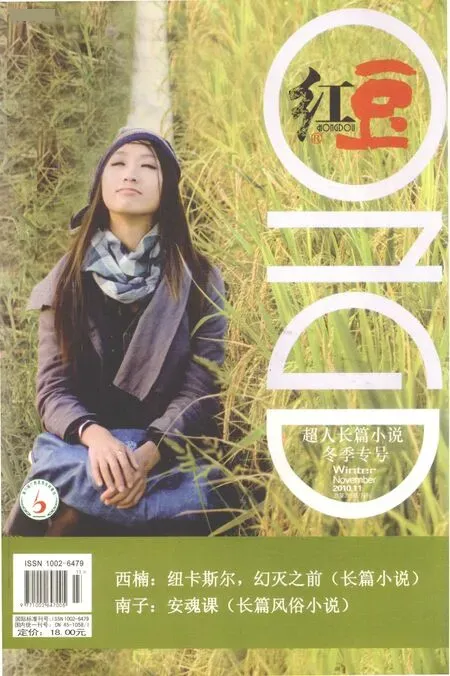眼里流出兩條河
盧致明
一
2002年春節剛過,我和愛人一起,離開老家,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車,來到了廣西天峨。那時天峨正在修建西部大開發標志性工程——龍灘水電站。
這是我第二次來天峨,與初來天峨相比,我的心境大是不同。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來,我像一只小鳥,充滿歡樂。而這次,我像一只烏龜,縮著腦袋。
我兩次來天峨,都與一位李姓老板有關。2000年初,我在老家認識了一位小老板,姓李,溫州人,和我算還有點親戚關系。在我家鄉,溫州人的精明和富裕早就是盡人皆知。他來我們家,經常也是買貴重禮品,一副很有錢的樣子。親戚朋友坐在一起聊天,都是他在說,我們在聽。他常說,搞工程建設,架橋與修路這兩樣最賺錢的。有一天,大家在客廳聊天,他突然說,他要去廣西天峨,那里正在建一座大型水電站,幾百億元的大工程,公路都要修十幾條,有很多發財的機會。他的老鄉已經在那里投資了,買下一座石山賣石頭,很賺錢。正好客廳墻壁上有一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我便來了興趣,在地圖上尋找天峨。找了很久,才找到天峨兩個小字,一量距離,還真夠遠。過了一段時間,他從廣西回來了,又說起那里的情況,鼓動我與他一起去廣西,合股買山,開采石場,賣石頭賺錢。
聽著他如百靈鳥般動聽的語言,我的心底仿佛蕩起了漣漪。那時我才20多歲,從學校出來后,就一直在家鄉的一個啤酒廠工作,鮮有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社會經驗幾乎為零。當他的語言像水彩筆,在我這張白紙上涂涂畫畫時,我的心底燃起了彩色的希望。他見我猶豫,接著說道,如果投資失敗了,我的錢他也會一分不少地退回給我。他這句話,像一團火在我心底燃燒,我的一汪心水汩汩地沸騰了。
那年年底,趁著冬季廠里停產檢修,我隨他來到了天峨。第一次坐火車,車窗外的風景把我的心撥拉得癢癢的。年少時,我所了解的廣西,是課本上的桂林山水,是一幅壯錦,是電視劇里的劉三姐、阿牛哥和韋拔群……遙遠而神秘。現在車輪飛馳在八桂大地,我觸摸到了真實的廣西。
在幾天的實地查看中,李老板陪著我這里走走,那里轉轉。他煽情的說辭,激勵著我。他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要發財就要膽大。我腦子一熱,就把積蓄全交給了他。
原本以為,我找的是一條閃閃的“金光大道”。可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合作以后才發覺,這哪是什么金光大道,分明是荊棘密布的小路。他三天兩頭打來電話,說買設備要錢,開進山的路要錢,請人吃飯要錢,請人做工也要錢,如果不繼續投資,先前的投資就收不回來。我想想也是,做事業哪有不投資的呀?可是自己又沒有錢,怎么辦?只能借了。于是我向親戚朋友借,向隔壁鄰居借,陸陸續續,我又借到了幾萬元寄給他。父親母親看著我一筆一筆將錢辛苦借來,再一筆一筆匯給他,臉愁得像天上的烏云。他們辛勞一輩子,也沒見過這么多錢,勸我不要再寄錢去,說那像一個無底洞,填也填不完。聽了父母的話,我忽然間醒悟了,不再借錢了。當他再次打電話要我寄錢時,我便說,我已經借不到錢了。他頓時生氣了,音量提高,語速也加快了,他說你借不到錢的話,之前的投資就要打水漂了!隔著話筒,我都能感覺到他在千里之外的憤怒。我無奈地說,你再想想辦法吧,我這邊實在是借不到錢了。
也確實是借不到錢了。這一年,我原先紅火的單位,突然出現效益下滑的狀況,機器半開半轉。同事們都在傳說銀行不再給貸款,工廠要倒閉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效益不好,大家遲早會下崗。
天峨的投資沒有回報,工廠又要倒閉了,這些狀況親戚朋友知道后,來串門時就借口說沒有錢過年,要我還錢。話語像苦澀的風沙刮在臉上,烙得我眼眶濕潤,鼻子發酸。父母親不時嘮叨,說我笨,罵我傻,白白送錢給別人花。我只能是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言。
春節臨近,我的心和天氣一樣,一天比一天冷。無奈之下,我寫了辭職報告。我想過完年就去廣西,把投資的錢拿回來。
二
對于我們的到來,合伙人沒有我想象中的熱情。他安排我和愛人住在堯里溝,守著我們買下的石頭山以及機械設備。
堯里溝是龍灘水電站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住有十幾戶趙姓人家。溝里還沒有通電,進溝的山路也是新挖的,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不堪。我們住的房子都稱不上是房子,而叫工棚,是自己用木板搭的,四處漏風,里面蒙上油彩布,外面就看不見里面。
山溝像一個峽谷,右側是喀斯特地貌山峰,高大、巍峨,山頂常常被云霧遮掩,仿若“仙境”;左側是丘陵山地,灌木叢生,從半山腰到山腳,村民插縫開墾出旱地,種上玉米。而溝底則是用石頭壘成田埂的稻田,采石頭的老板們把村民的稻田租來,開成道路,搭建工棚。
晴朗的日子里,經常能看見一朵朵云,雪白雪白的,從左側的山頭飄過來,如鳥兒一般,悠悠掠過。風景雖美,我也無心欣賞。我督促合伙人早日開工。可合伙人說,開工需要找工人,需要找銷路,現在還在聯系中,再等等吧。
他既然這樣說,也只能如此了。等吧!我安慰著自己。
在等待的日子里,我像戈戈和狄狄等待戈多一樣,無聊,寂寞。一同等待的不只是我們,還有很多老板。整個堯里溝右側綿延幾公里的石頭山,都被各地端著發財夢的老板承包,運來各種設備開采石頭,大家心里都充滿了期望,等待分得龍灘水電站建設的一勺羹。此時,我走遍了堯里溝的每個角落,把溝里的情況摸了個遍。
進溝遇上第一座山,是南寧武宣梁老板承包的,他是所有采石老板中,來得最早的。進溝的山路是他請挖機開的,花了一大筆費用。他在溝口設了一個卡,外來的車輛要進溝拉石頭,就要先交納過路費。后來進溝的車輛實在是太少,他就又把卡撤了。
我住的工棚左邊,是一家磚廠,老板有兩個,一個是博白人,另外一個是南寧人。博白老板住在溝里,兼生產和管理,南寧老板住在縣城,負責銷售。
工棚右邊,住的是一家柳江人,我叫男主人韋哥。他本是幫老板守工地的,但工地一直沒開工,他就去龍灘水電站工地找活干,他愛人釀玉米酒賣,他們有一個兩三歲的孩子。
沿著工棚后面的山路往溝里走1公里,就是村民的房子。村民看到商機,就開臺球店、麻將館、小賣部或餐館,吸引做工的守機器的外地人去消費。無聊的時候,我也去看他們打臺球、打麻將,有時三缺一,他們問我打不打,我搖頭說不懂得打。其實,是口袋里沒錢罷了,來了一個多月了,我帶來的生活費要節約著用。看多了,便覺無趣。我沿著山路,往山溝深處走。山路原是羊腸小道,去年一位湖南老板買下溝尾的一座山,把路拓寬,運來大型設備,希望能大干一場。可是卻與我們一樣,沒有等到開工,只能繼續接受無休止等下去的命運。
山路寂靜,不時能聽見小鳥“唧唧”“咕咕”“啾啾”的鳴叫聲,也不時從草叢中“撲騰”飛出一只大鳥,把路人嚇一跳。我離開山路,踩著青草走到山腳下,一條小溪,潺潺流水,溪水清澈,倒映藍天白云。坐在溪邊,望著水面的云朵,感覺我也像云朵,沉入了水底。溪水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的憂愁。
三
夏天很快到了。戈多沒有出現,我們的工地依然沒有開工,我帶來的生活費已所剩不多,坐吃山空。我需要找點事情做,增加收入。出溝三公里,有一個集市,既是勞動力市場,又是商品集散地。每天有很多工人像我一樣去市場找工做,某位老板臨時需要工人,都在集市找。好幾次我遇見老板選工人,一大幫人立刻靠上去,爭著說自己力氣大,是熟練工。老板點上幾位,用皮卡車拉走,剩下的人像牲口一樣,等待下一次挑選。開始我以為是我運氣不好,后來,我發現,是我長相的問題,皮膚白,身材瘦,口音不一樣,老板識人無數,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人能干重活。幾次沒有被選中,我漸漸也就絕了念頭,不再去市場找工作了。
合伙人知道我想找工作,幫我找了一份在隧道里的工作。隧道里能見度極低,粉塵如蝴蝶翩翩飛舞,挖掘機、空壓機、重型卡車等機器發出的噪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響。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我很沒有安全感,只做了兩天,我就放棄了。
再去集市,就剩買菜了。其實菜也很少買,愛人在門前開辟了一塊地,種有蒜苗、蔥花、豆角、瓜苗。現在它們蓬蓬勃勃生長。偶爾要買的是大米和豬肉,但囊中羞澀,賣肉的情形也是極少。
生活就是這樣,它在為你關閉一扇門的同時,又為你打開一扇窗。在我帶來的盤纏即將用完之際,隔壁博白老板的水泥磚有人來買,他叫我和他的工仔一起裝車,上一塊磚六分錢,我們每人就是三分錢,裝一車磚,每人可以得六元錢。上車時,四五十斤重的水泥磚,剛開始是兩手提著,丟進車廂,但到后來,手臂越來越酸,就只能抱起水泥磚,把它挪進車廂。夏天的太陽,毒辣辣的,我臉上、手臂上、身上出的汗越來越多,渾身濕透。我咬牙堅持著。之前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活,但是現在,我必須做,生活就是這樣,容不得你挑剔。
待到一車磚裝完,我長噓一口氣,回到家,猛灌幾碗涼水,休息一陣,又漸漸恢復了氣力,等待下一輛車來裝。運氣好,一天能裝十車,不過這樣的情形很少,而且累得第二天都不想起床。大多數時候,每天裝三四車,得十幾二十元,夠幾天的生活費。之前我從來沒有干過重活,搬磚的磨煉,讓我明白,天無絕人之路,人在重壓之下,能激發出巨大潛能。
以為裝車能夠維持生計,解決眼前的缺錢困難,但雨季來了,從七月底到八月初,雨陸續下了20多天,山路被沖毀,車輛進不來,老板的水泥磚賣不出去,我又斷了生活來源,重新為生計發愁。數數口袋里的錢,從來沒有超過20元。沒有收入,我又去菜市場附近找工干,結果,找了幾天都沒有找到。有一次,我和溝里一幫外地工人去,回來時他們都拎著肉回來,而我則空著雙手,隔壁韋哥叫我也買一點回去,我說我愛人早上買了。其實早上買的只是青菜,肉有一兩個星期沒吃了。說這話的時候,我的心里發虛,想想孔乙己都能排出九文大錢要一碗酒、幾顆茴香豆,而我酒喝不起,肉更吃不起。
我又去找合伙人,他住在縣城,已經20多天沒有到山溝來了。見到他,他臉黑得像關公,像是我欠了他許多錢似的。我問他什么時候可以開工,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已經找到一個項目了,但沒有錢開工,想找貴州的工人來做工,但沒有錢,他們不干;想再找一個老板來投資,可是還沒有找到……這樣的話,他重復著說了許多遍,像《等待戈多》里的那個小男孩一樣,告訴我,戈多終究會來的。我說我沒有錢了,他翻開錢包說,你看我也沒錢。說完從口袋里摸出一張20元的鈔票遞給我,說你先用著,等我借到錢了,再給你。捏著這20元,我忍住不落淚,我投資了這么多錢,全交給他管理,現在他打發我像打發叫花子一樣,都怪自己,當初欲望太強,妄想當老板,賺大錢。
走出他住的房子,我沒有立即回山溝,而是去圖書館借書。我在圖書館辦了一本借書證,一次可以借兩本書。現在只有書可以慰藉我的靈魂,使我忘記憂傷、苦悶、憐憫,我也只有在閱讀中找到支柱。圖書館里,好書很多,我挑選了兩冊厚書來借,這樣我能閱讀打發的時間就更久。走出圖書館,我猶豫了一下,沒有走向車站,而是走上二級公路,步行回去。步行可以省3元錢,夠我和愛人一天的伙食費。
書看完,無事可做,便想喝酒。酒去隔壁韋哥那里買,自釀的玉米酒,1元1斤,當地人稱為土茅臺。買來酒,我拿出兩個小碗,一碗滿上酒,一碗裝下酒的花生米,一個人,慢慢喝,慢慢品。我想走,離開這個鬼地方,到山外去謀生。如果我走了,意味著在這里的所有投資都打水漂。兩種選擇,兩種艱難,戈多,你在哪里?
四
8月底,一個漆黑的深夜,隔壁磚廠突然來了兩部大貨車,我以為是夜晚來拉磚的,起來一看,是博白老板正在把他的設備裝上車。忙乎了大半夜,凌晨時分,車開出了山溝溝。此后,博白老板再沒來過,連剩余的磚都不要了。
老板走了,沒有人來買水泥磚,我的收入徹底斷了,生活陷入了更加困頓的境地。
無聊的時候,我就去工地上轉,一個月未見,兩臺破碎機銹跡斑斑。那條坑道,被雨水沖刷的粉石填充,淺了許多。我突然感覺,我和這些粉石一樣,不知不覺就跳入了別人早已挖好的坑。
幾場秋雨下過,陣陣秋風把山溝里原先綠色的稻谷,撫成了金黃。中秋節那天,村民趙老板趁著學校放假,幾個兒女回來,收割稻谷,叫我去幫忙。收完谷子,趙老板邀我吃晚飯。
山區的夜來得早,秋天的月升得早,還沒有開飯,圓月已經掛在東山頂,月光皎潔,灑在趙家院子里,如鍍了一層銀光。這是我第一次在外鄉過中秋節,沐浴月光,我突然想念家鄉,想念親人。這幾個月來,我像是漂泊在茫茫大海里的小舟,不敢和親人聯系,不敢打電話回家,我怕他們知道這里的真實情況,更加傷心。
酒入愁腸,化做相思苦。那個夜晚,鄉愁像波濤一樣,不停地侵襲我。我喝醉了。
也許,只有大醉才能大醒。第二天,酒醒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不應該再等了,貝克特在《等待戈多》這部悲喜劇中,早就告訴觀眾:有些等待,沒有任何的意義。而我卻還在如戈戈和狄狄,對等待戈多充滿幻想。我應該離開這里,重新生活。
我把想法告訴愛人,她也支持我離開這里,去廣東打工賺錢還債。說走就走,我收拾好行李,告別愛人,踏上了出溝的山路。
太陽升上了山頂,溫暖的陽光灑在山路上,照耀著我。遙望前方,我的眼里涌出了兩條河流。
我想,新生活就要開始了。
責任編輯? ?藍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