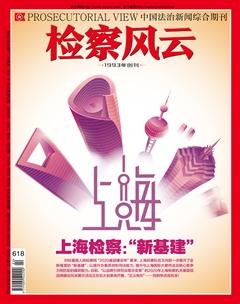期貨市場開放需完善域外監管立法與執法

杜濤
《期貨法》立法步入快車道
我國期貨市場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期貨業對外開放步伐加快。2014年,為落實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證監會發布《期貨公司監督管理辦法》(證監會令110號),將開放范圍擴大至與證監會簽訂監管合作備忘錄的國家和地區。2017年,中美兩國元首北京會晤后,《外商投資期貨管理辦法》正式頒布,期貨業外資股比放寬至51%,2020年1月1日起不限制投資比例。2020年6月22日,繼原油、鐵礦石、PTA、20號膠期貨之后國內第五個對外開放的境內特定品種——低硫燃料油期貨在上海期貨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掛牌交易。而今,我國期貨市場共有78個期貨期權品種,直接對外開放的品種已有5個,QFII/RQFII可以參與我國的股指期貨交易。
當前,我國商品期貨成交量已經連續十年位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第二大期貨期權交易市場。對外開放的市場規模發展迅速,參與者結構更趨于合理。我國期貨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已發展到以原油期貨等特定品種的全方位制度型開放。經濟社會進入新時代,爭奪要素市場資源配置權、定價權和規則話語權,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水平亟待提升。市場競爭,在相當程度上是規則競爭、制度競爭。規則的權威、公開、透明、規范,具有公信力、權威性和穩定性,有利于明確和穩定市場預期,就會吸引全球投資者參與,一個境內外市場人士均樂于參與的市場,其全球價格影響力和規則話語權就自然形成。
立法始終堅持問題導向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看到我國期貨市場與國際成熟市場在跨境監管方面的現實差距。境內特定品種對外開放的外部政策制度也間接說明了期貨市場對外開放需要系統性的支持。《期貨法》立法需要與外部法律之間建立銜接關系,以減少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外部制度障礙。《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的調整范圍局限于境內市場,在期貨交易的流程中沒有考慮對境外機構活動的監管安排,僅僅規定了中國證監會的跨境監管協作機制,難以適應不斷擴大的期貨市場國際化要求。期貨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客觀上要求將參與跨境期貨的境外主體及其行為納入《期貨法》調整范圍,需要《期貨法》對境外主體的監管加以規范化調整。
與此同時,境內主體走出去,對我國的海外合法利益如何保護,也是制定中的《期貨法》需要考慮的問題。境外交易也需要《期貨法》的保障和支持。境內單位或者個人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規范缺失,境內期貨經紀機構申請境外期貨經紀業務的具體管理規定缺失,導致境內市場主體“走出去”缺乏切實可行的路徑。目前走出去的是期貨公司在境外設立的子公司,其與境內母公司的聯動方面也存在問題,如母子公司之間不能提供協助,將會帶來監管套利和監管空缺,從而引發系統風險。
破題思路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需要從國家立法層面確定跨境期貨交易的法律適用,協調與《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和《民法典》之間的關系,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這對穩定市場秩序和當事人預期至關重要。從廣義上說,期貨交易本身也是合同關系的一種,應當允許當事人選擇適用的法律,但是期貨交易作為特定市場內的交易,應遵守交易所的相關規則和法律框架。立法上應當正確區分私法關系和公法關系,為當事人提供合理預期,這也是國際上較為通行的做法。實踐中尤其要注意避免用公共政策來否定當事人之間期貨合同的效力。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倫敦糖業協會仲裁裁決案的復函》中明確指出:“依照我國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境內企業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從事境外期貨交易。中國糖業酒類集團公司未經批準擅自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行為,依照中國法律無疑應認定為無效。但違反我國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不能完全等同于違反我國的公共政策。”
其次,應當完善我國期貨監管配套立法的域外實施機制。在跨境交易的監督管理中,對境內交易所走出去進行監管,按照境外監管機構的要求,需要向境外機構報送與索取相關信息。我國對期貨交易實行穿透式監管,需要采集境外客戶信息。這就需要期貨法對于交易所、期貨結算機構獲取終端客戶信息予以授權。我國正在審議中的《數據安全法(草案)》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開展數據活動,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該條規定雖然規定了域外效力,但相比于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而言,范圍極為有限,僅適用于追究法律責任,而不適用于平時監管。對于金融監管機構就存在執法依據上的空白。《期貨法》應當對此加以完善。此外,《網絡安全法》對于信息出境施加了限制,這對金融領域建立國際性的互通機制造成了一定障礙。《期貨法》在這方面如何與《網絡安全法》相配套,也需要加強研究。
建設有國際影響力的期貨市場需要加快期貨立法進程,加強和完善跨境監管的立法配套和執法力度,妥善處理好期貨市場開放和國家金融安全之間的關系,為全面對外開放提供法律保障。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境外機構參與境內期貨市場的信心、提高交易積極性,最終將我國建設成為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宗商品定價中心。
第三,應當加強我國期貨監管部門與境外機構在等效監管原則基礎上的監管合作。等效監管,是根據監管和執行的質量的好壞,在結果相似情況下,通過非歧視的方式,各轄區和監管機構相互認可對方的監管,適當尊重母國的監管制度。G20自2013年推廣該原則以來,歐盟采納了該原則并實施了認證。截至2019年8月,歐盟認可了來自美國、日本等15個國家(地區)的33家CCP提供清算服務。美國CFTC通過等效監管原則,要求申請豁免的境外監管機構在制定或者實施法律過程中,落實美國監管要求,間接實現了美國法的域外適用。歐美關于清算原則爭執了很多年,最終通過等效監管原則得以和解。在金融監管方面,我國目前尚不具備與美國和歐盟實現等效監管的實力,但與證券市場相比,我國期貨市場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更大,開放程度更高。在充分吸收國際間競爭和合作的經驗基礎上,我國在期貨領域完全可以與歐美國家建立對等的監管合作和互聯互通機制,借助西方國家的成熟經驗健全我國期貨監管制度。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監管合作體系。《期貨交易管理條例》規定中國證監會“可以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期貨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合作機制,實施跨境監督管理”,為期貨跨境監管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據。截至2019年6月,中國證監會已相繼同66個國家和地區的證券期貨監管機構簽署了73份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于2007年4月簽署《磋商、合作及信息交換多邊諒解備忘錄》。但是,一方面《期貨交易管理條例》本身屬于行政規章,法律效力較低,對法院和其他司法機關的約束力不強;另一方面,證監會與其他國家簽署的備忘錄也不屬于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條約,在我國國內可能無法得到順利執行。因此,我國有必要在《期貨法》中單獨設立跨境監管合作的章節。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