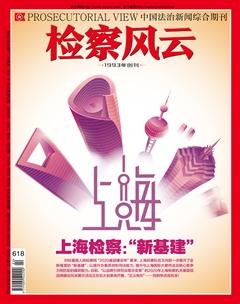同案同判的逆向思維
陳侃

每個判決都有一種生殖力,按照自己的面目再生產。
——本杰明·卡多佐
說到公平正義的標準,或許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一條準則可能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同,那就是同案同判。事實上,不僅僅是普通老百姓,許多專家學者也在追求和呼吁實現同案同判的道路上付出了不少努力,力求實現司法的公平和正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論界,也有一些學者站在反向審視同案同判的角度提出,所謂同案同判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其只不過是一個虛構的法治神話而已。那么在司法實踐中,究竟應當如何看待所謂“同案同判”“同案不同判”的問題呢?
所謂同案
值得探討的問題在于,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同案嗎?答案毫無疑問是否定的。同樣一起盜竊案——甲和乙都在居民住宅區內偷了一輛價值2000元的電瓶車,從表面來看,甲和乙的行為都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均構成盜竊罪。這就是我們觀念中的“同案”。但是,對于最終的量刑結果而言,卻可能因為案件中存在的其他因素而產生差異。比如,行為人的犯罪動機及目的可能存在不同,臨時起意和蓄謀已久,對待兩種不同的動機顯然需要適用不同的評判準則;比如行為人是否存在自首、坦白,或者認罪悔過等犯罪后的悔罪態度,對于既不認罪也不悔過的犯罪嫌疑人,很難認定其不具有社會危險性或再犯可能性;比如是否存在累犯情形,對于一個初犯偶犯的行為人和對于一個慣犯的評價顯然也會存在不同;再比如,是否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進而使得受損的社會關系得到修復等。這些不同的因素必然會存在于不同的個案中,進而對最終的量刑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絕對意義上的同案并不存在。
當然,關于是否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同案,還有一點同樣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現如今是一個自媒體空前發達的網絡時代,不得不承認的客觀事實是,有些自媒體的確存在“帶節奏、博眼球”的現象,對于一些刑事案件,尤其是社會輿論反響較大的案件,進行一味地夸大某一兩處爭議點的報道,從而獲得更大的流量。在沒有正確輿論引導的情況下,民眾對于法律的直觀感受,對于公平正義的感知難免會被帶偏。同案不同判的問題也是同理。媒體在進行案件報道的過程中或是受限于專業因素,或是出于追逐熱點等其他因素的需要,也容易出現一味突出相同案件沒有得到相同處理的情況。對于這種現象,作為司法辦案人員來說,還是應當正確看待這一問題,應當準確識別何為同案,找準不同的個案中,不同的法律爭議點何在,在同與不同之間找到背后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依據,對于其中合乎情理的依據應當予以接受,而對于不合理的,則應當予以糾正,這才是法律人對待刑事案件判決結果所應持有的態度。
雖然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同案,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類似案件或者同類型案件的存在。對于類似案件的處理,應當作出類似處理,或者說,同類案件同類處理,這也是提升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徑之一。目前得到更多認同的是,對于類似案件的處理應當做到求大同、存小異。所謂求大同,就意味著對于類似的案件,在定性方面要體現出絕對的同。以前文所述的盜竊電瓶車案為例,如果有的法院作出盜竊罪的判決,有的則作出詐騙罪的判決,這樣在定性方面的差異顯然就很難服眾,司法公信力也無從談起。至于量刑方面,則可以體現求小異,每一起個案之中,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不可能完全相同,也正是因為這種不同,必然導致量刑存在差異。只要在堅守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情況下,作出合理的解釋、找到合理的依據,這樣的“小異”就有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不能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同案同判,更不能認為判決結果的不同就存在爭議性。
基于以上分析,以同類案件同類處理來替代我們傳統觀念中所謂的同案同判似乎更為科學,也更為合理。
不同判之根源
前文已經明確,同類案件同類處理是一個更為科學的概念。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也不乏類似案件出現不同的處理結果。作為不同判之根源,或許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尋。
首先,法學是一門人文學科,因而難免會存在價值的判斷。張明楷教授曾經指出,法律人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任何法律問題上總會站成意見相左的兩隊。在鸞翔鳳集、云起龍驤的刑法學領域,何止兩隊,經常可以見到三隊、四隊、五隊乃至更多的隊伍。對于司法辦案人員,尤其是法官而言,當然也會出現相類似的情形。同時,在人文學科領域里,一個研究者提出的種種問題與觀點,肯定并不獨立于他的整個人格,因而也并不獨立于他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生活狀態、社會地位、閱讀范圍、正義感覺以及法律意識等,甚至,司法辦案人員在學生時代所繼承的學術流派都有可能對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產生影響。因此,不同的司法辦案人員對于法律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現象。
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法律應當明確,但法律又難免存在模糊之處。就刑法而言,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是類型化的具體事實,換言之,每個法定的構成要件都表現為一個類型。既然是類型化的問題,難免會存在邊界的界定,更何況,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哪個犯罪嫌疑人在實施犯罪之前會先對照翻看刑法條文,因此,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就需要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既然是解釋,就會存在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發點,這些都會成為“不同判”的原因所在。
其次,在每一起個案中,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大小同樣也會對最終的判決產生影響。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我國有學者提出,刑事責任是罪刑之間的調節器,通過刑事責任的調節功能以及綜合評價功能的發揮,從而實現犯罪類型到刑罰裁量之間的順利過渡,進而保障刑事司法公正性與個別化之間的平衡。對于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其中的合理依據就在于刑事責任這個罪刑之間的“調節器”功能的充分發揮。前文所述的電瓶車盜竊案中,諸如對于犯罪動機及目的、悔罪態度、累犯情節等,都屬于對行為人刑事責任考量的標準。刑事責任的不同,最終刑罰也必然不同。
解決之途徑
絕對意義上的同案同判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其實也沒有必要得出完全相同的判決結果。但是另一方面,類似案件類似處理必須得到保證。這不僅僅關系到司法的權威,也關系到司法的公信力。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布了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力求進一步統一法律適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同案不同判的問題。
在上海,檢察機關也對同類案件同類處理進行了實踐探索。記者從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檢察院處了解到,該院根據“上海市檢察機關司法案例研究基地”的工作計劃,與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共同研發了“司法案例智能檢索系統”。
據了解,該系統將嵌入辦案流程,建設成一個面向檢察人員辦案為主,輔以向法律研究者和社會公眾開放使用,兼顧案例檢索、宣傳、研究等作用,為檢察人員加強案例運用、檢察機關探索推進類案強制檢索工作機制、擴大檢察工作社會影響力提供支持保障的綜合性平臺。
作為一項全新的系統,司法案例智能檢索系統具有兩大核心功能:第一,強制檢索。辦案人員將案件審查報告導入系統,系統對報告進行掃描后與案例庫進行匹配,推送具有一定關聯度的案例,關聯度根據報告所匹配的關鍵詞層級予以設定。根據設定的案件等級,辦案人員必須查看并參照或者可以參照,對于應當參照而未參照的情況應說明理由。第二,自主檢索。辦案人員自發地進行案例檢索,是強制檢索的有益補充,提供較為全面的辦案、研究參考,對是否參照適用推送案例不作強制性要求。
司法案例智能檢索系統還整合了“兩高”指導性案例、公報案例、典型案例,本市市檢察院、市高級人民法院內部或者公開發布的對本市司法辦案有重要參考意義的案例,以及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或者具有引領性、影響性作用的境內外案例等。目前,已收錄可供查詢的案例共760個。
此外,對案例進行深層解構,全面梳理案例的發布背景和相關法律、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從案例的法律適用、辦案方法和辦案理念三個方面提取案例的關鍵詞和規則,形成“案由—案例主題—關鍵詞—規則”四層級解構表格,運用系統技術形成檢索圖譜。目前,已對最高檢第1至21批指導性案例共計80個進行深度解構,并對417個兩高指導性案例、公報案例、市院檢委會通報案例進行關鍵詞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