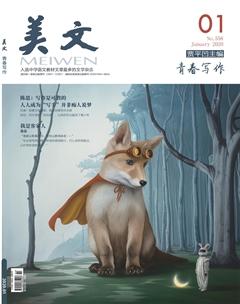我是客家人

燕茈
“客家山歌真好聽,句句山歌有妹名……”
“東邊落雨西邊晴,新做田唇唔敢行。燈心造橋唔敢過,心肝想妹唔敢聲……”
是春天。白云掛在藍天上。風是輕輕柔柔的,陽光也是溫溫柔柔的。客家公園開滿了桃花。這時候,我居然在廣場上聽見幾個大叔大嬸唱山歌。這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歌讓我遽然生出許多溫暖的情懷。
郎在對面唱山歌,妹在山頭把草割。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它產生于客家勞動人民中間。人們在山上砍柴、鏟松油、挑擔及田間勞動時,或為尋覓同伴以驅野獸強盜,或為消除疲勞對歌打趣,或表男女愛慕之情等等。“唱戲一半假,山歌句句真”,其豐富多彩的內容是客家人民生活的一面鏡子。
我是聽著父輩的山歌長大的。此時此刻,我仿佛回到那些舊時光,看著隔壁的阿媽在鍋頭灶尾、田頭地尾唱著同樣的歌謠。她們曾一邊割草,一邊和身邊的“女姑(姑娘)”談論著那個喜歡自己的小伙,聽他在山頭唱歌;也曾盤起頭發,柴米油鹽,背著小孩,在灶臺旁轉來轉去,哼幾句年輕時唱過的歌。
我記憶中最深刻的是在花生地里,忙忙碌碌,卻依然可以聽見父親唱山歌:“石榴打花紅津津,嫁人就唔好嫁讀書人,讀書阿哥冇腰筋,算盤厲啦吵死人。”我一邊摘花生,一邊編一段歌詞和父親對唱:“石榴打花紅津津,嫁人就唔好嫁耕田人,耕田阿哥冇文化,寫信捉筆愛求人。”這時候,父親這個耕田人哭笑不得,只好呵呵地笑,罵我忘本,然后表揚我對得還挺工整。
我常常回憶這段時光,父女兩人一唱一和,唱著世間最樸實、最純美的歌。
我喜歡聽老人講那些山歌的故事:一男一女在不同的山頭砍柴割草,對了一上午的山歌,結果什么都沒有做,一個忘了砍柴,一個草沒有割。有的回到家才發現,和自己對唱的那個人原來是自己的另一半。兩個人哈哈大笑,一上午就掙得一場歡樂。
我覺得最可愛的歌詞是蜘蛛和蟑螂吵架:“蜘蛛罵蟑螂,日爬夜爬,爬到沒下巴。蟑螂罵蜘蛛,日織夜織,織得一件爛衫巾。”幽默風趣,讓人忍俊不禁。
我最喜歡的歌是《看月光》:“八月十五看月光,看見鯉魚跟水上;鯉魚不怕飄江水,探妹不怕路途長。八月十五看月華,阿哥出餅妹出茶;吃哥月餅甜到肚,喝妹細茶開心花。”這首歌熱情洋溢,富有文采,委婉押韻,能夠引起所有恩愛著的男女強烈的共鳴。
這就是客家人自己的歌。在這美妙動聽的歌聲面前,很難想象客家人曾經經歷過的苦難。記得剛剛懂事的時候,我常常覺得父親很傻,因為他把我的爺爺奶奶叫作叔叔嬸嬸,叔公叔婆又喚作爹和娘。后來發現傻的人不止我父親,還有人叫自己的父母叫得更生分的:“阿舍”“阿奶”。“阿舍”意思是鄰舍的孩子。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后來聽說,客家人的祖先是戰亂時期遷徙過來的,在逃亡的路上,怕被滅門殺害,叫得生分一點,可以保住一些人。這樣的解釋讓我開始心疼我的祖先,他們為了逃避戰亂,背井離鄉,隱姓埋名。最開始的時候,他們肯定也是叫爹娘的吧?是有人全家遇難,悲傷的故事讓其他人吸取教訓——只是這一聲改口,經歷了多少血和淚的痛苦。
“要問客從哪里來?客家來自黃河邊。要問客家哪里住?逢山有客客住山……”誦讀著這多少年來銘記在心的歌謠,我卻總是對“客家”這個稱謂有些陌生。迄今為止,有不少學者對其進行考證研究,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流傳最廣泛的是:歷史上,客家人經歷了5次大遷徙,先后流落南方。遷移規模之大,范圍之廣,讓今天的我們僅憑想象,都對期間的艱難困苦感到懼怕。
飽受戰亂之苦的客家人一次次拖家帶口,遠離自己的家鄉,艱難地走在他鄉的路上,尋找他們夢中的桃花源。多少次在途中回望,盼望硝煙退去,可以回到最初的地方,像從前一樣和樂融融。可總是在一次次的回望中失望,他們只能走向離家園越來越遠的地方。而作為客家人,我總是非常敏感地記住和“逃難”有關的故事。
端午節,在客家人的門楣上,除了懸菖蒲、艾葉,還會掛上紅線,捆住葉片如蝶的葛藤。據說唐末黃巢起義中,一名中原女人獨自帶著兩名年幼的孩童徒步千里,流亡到寧化石壁。奇怪的是,她將年紀稍大的孩子背在身上,卻將幼小的男童牽在手里,小男童走在路上踉踉蹌蹌,這有悖常理的行為引發了黃巢的好奇心。一問才知道,婦人背上的大孩子是她兄嫂的遺孤,手中牽著的幼童才是她的親生兒子。在顛沛流離的亂世里,中原女人為保存兄嫂的一點血脈,只好做出如此犧牲。
這位中原女人千里奔亡的悲壯,觸動了黃巢內心最柔軟的部分,黃巢便私下囑咐中原女人落戶后在家門口掛上葛藤,并承諾她一定會平安。黃巢回去后立馬下令不準砍殺門前掛著葛藤的人家。一傳十,十傳百,老百姓們都在門口掛上葛藤,因門口的葛藤,很多百姓在兵荒馬亂的殺伐里得以平安。故事的結局雖也算是個好結局,卻不免唏噓。
聽說,所謂的故鄉,是我們的祖先漂泊的最后一站,而我們客家人的祖先在流落他鄉的旅途中,永遠不知道哪里才是漂泊的最后一站。這樣長年累月的遷移什么時候是個頭?他們心里相信,在中國南部一定有遠離戰亂的桃花源。而多數人在沒有找到桃花源之前就已經離開人世,彌留之際千叮嚀萬囑咐自己的親屬:“你可不能把我丟在荒山野嶺,一定要將我的老骨頭帶回老家去。”于是客家人有了非常特別的二次葬習俗。在近千年來流離轉徙的生活中,客家人的祖先每轉移一處地方,便要把已故親人的骸骨帶上,一起遷到新居留地,再行選地安葬或建墳場,不讓親人的骸骨遺落他鄉。戰亂中,他們拖家帶口,扛著先人的骨頭,背負著祖先的期待,背負著整個家族的命脈,背負著對未知生活的向往,繼續流亡。
這些逃難的客家人所去之處,好的土地與資源早有人占有和居住,他們只能尋求偏僻和不適合居住耕種的山區和丘陵地帶,所以有“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之說。
除了生存環境惡劣外,還要防外敵及野獸侵擾,這讓客家人對居住環境的安全性非常在意。既要群居族群在一起,還要把房子建得牢靠、結實、安全,于是形成了圍龍屋、走馬樓、五鳳樓、土圍樓、四角樓等大型一體建筑,其中以圍龍屋存世最多和最為著名,是客家建筑文化的集中體現。
客家圍龍屋始于唐宋時期,客家人采用中原傳統漢族建筑工藝中先進的抬梁式與穿斗式相結合的技藝,選擇丘陵地帶或斜坡地段建造圍龍屋,主體結構多為“一進三廳兩廂一圍”。配套的還有曬坪和水塘,具有防火、防盜、防野獸等功能。
一間圍龍屋就是一座客家人的巨大堡壘,最多可以容納幾百人在此居住。屋內分別建有多間臥室、廚房、大小廳堂及水井、豬圈、雞窩、廁所、倉庫等生活設施,形成一個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的小社會。
安全的家才是真正的家,圍攏起來的房屋才是客家人的溫暖,客家人的平安天下。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響,由家族這種血緣姻親關系網,發展到鄉里、鄉黨這種鄉土情誼,共同的流浪命運和族群文化凝聚力,讓客家人和睦共處,守望相助。
這些故事無不體現客家祖先逃難的悲痛以及創建、守護家園的艱難。我們的祖先相信總有一個地方是沒有你爭我斗、沒有爾虞我詐、沒有戰爭沒有硝煙的凈土。于是,一支支動人心弦的山歌從客家人的心靈深處蕩漾開來,是那樣自然淳樸的真情流露,夾雜著濃濃的鄉土韻味,帶著農耕生活的煙火,藏著客家人對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與憧憬,在高山上、在田園間、在流水旁……隨風而歌,婉轉悠揚。
那些不幸與苦難終究成為過去。我們的生活離戰爭遠了,離野獸遠了,離排斥遠了。在漫長的融合過程中,客家人終于找到了“漂泊的最后一站”,生活在夢中的桃花源。
現如今,我又聽見那熟悉的歌聲,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唱著平安幸福,唱著美好和平的新時代,唱著偉大可愛的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