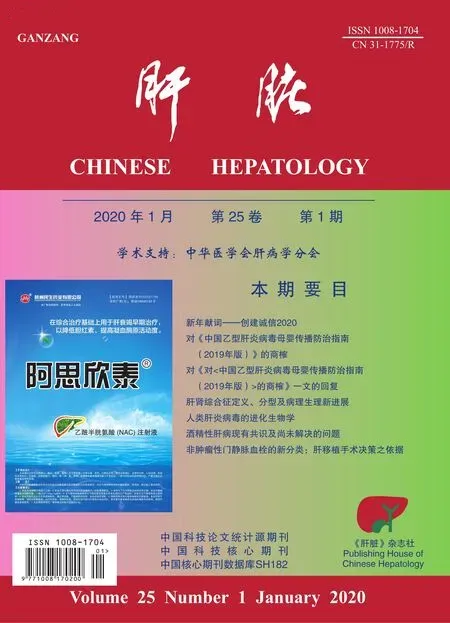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療重癥藥物性肝損傷療效觀察
朱紹華 郭長存 劉志國 武建 張靜 尹芳 韓英 周新民
近年來,藥物性肝損傷(DILI)發病率不斷攀升,作為最常見和嚴重的藥物不良反應之一[1], 輕度DILI僅有肝功能指標的異常表現,而嚴重的病例可以發展成急性肝功能衰竭(ALF)甚至死亡[2]。對于DILI患者重癥病例的治療,特別是膽汁淤積型或者常規保肝治療效果不佳的患者,有研究認為,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給予糖皮質激素或者非生物型人工肝血液凈化治療[3-6]。本研究回顧性收集既往所治療DILI患者的相關數據,評估非生物型人工肝(以下簡稱人工肝)在重癥DILI患者治療中的效果,并對影響治療效果的因素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為DILI的診治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通過醫院病案管理軟件查找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消化內科于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間收治住院的DILI患者共172例,住院期間采用了藥物和人工肝的單獨或聯合的治療。納入標準:(1)符合2015年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發布的《藥物性肝損傷診治指南》中對于DILI定義的標準[7];(2)DILI的診斷評估則采用Roussel Uclaf因果關系評估法(RUCAM)進行評分[8],所有入組分析患者的RUCAM評分均大于3分。(3)采用人工肝治療的適應證及治療方式依據我國2016年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發布《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療肝衰竭指南》[9]及《肝衰竭診治指南(2018年版)》[10]中的相關適應證施行。根據治療前患者的一般狀況和實驗室檢查指標選擇行血漿膽紅素吸附(PBA)模式或是血漿置換(PE)模式治療。治療前患者均需簽寫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感染性肝病及合并酒精性、自身免疫性或非藥物性導致的膽汁淤積性肝病;孕婦及哺乳期婦女;伴有惡性腫瘤、結核、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骨質疏松、嚴重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嚴重合并疾病者。
二、研究方法
記錄患者入院時的年齡、性別、住院時間、服藥開始到發病的時間、既往病史、服藥史、飲酒及過敏史,入院時的主要臨床癥狀、體征;實驗室檢查包括血常規、肝腎功能、凝血功能;評估項目:藥物性肝損傷的嚴重程度及分型、RUCAM因果關系評分、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評分;出院時的臨床癥狀和預后轉歸情況,包括好轉、無效自動出院、死亡等。其中對于治療好轉、有效、無效等療效判斷依據《肝衰竭診治指南(2018年版)》[10]標準。
三、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或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治療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量資料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概率法檢驗;傾向性評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過程利用SPSS的PSM擴展程序實現:以是否采用人工肝治療為應變量,各協變量為自變量,采用1∶1臨近匹配法進行匹配,該過程通過卡鉗值為0.1來保證匹配結果的優良性,當標準差異絕對值<0.1(10%)時,認為組間變量的均衡性較好;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法對影響治療效果的各混雜因素分別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一般情況
收治住院DILI患者172例,RUCAM因果關系評分均大于3分。其中男62例,平均年齡(43.5±15.8)歲;女110例,平均年齡(42.8±9.1)歲。采用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療的患者共27例,其余為藥物治療的患者共145例。統計所有患者使用的導致肝損傷的確定及可疑藥物中, 中草藥及中成藥所導致的病例數最多, 共96 例(55.8 %),其次為各類“抗感冒藥”、抗生素及非甾體類解熱鎮痛藥物使用者, 共36 例(20.9 %);以下分別為抗焦慮、癲癇藥物9 例(5.2 %), 皮膚病治療藥物11例(6.4%),抗結核病藥物7例(4.1%),農藥、劇毒類藥品及化學品7例(4.1%),其他包括免疫抑制劑、降壓藥、甲亢治療藥和化療藥共6例(3.5 %)。
二、治療效果分析
通過對兩組患者入院時的ALT、總膽紅素、凝血酶原活動度及MELD評分等反映肝功能情況的實驗室檢查指標的基線水平進行比較(表1),兩組患者在總膽紅素、MELD評分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故采用傾向性評分的方法對兩組患者進行匹配。采用1∶1最鄰近匹配法,卡鉗值取0.1,以人工肝組患者入院實驗室檢查指標的基線水平為基準組進行匹配,2組共25對匹配成功(模糊匹配)。在2組間不平衡的協變量經匹配后均達到平衡(P>0.05)。
對匹配后的2組患者治療后的各項實驗室檢測指標進行統計對比,結果如表2。與未采用人工肝治療的患者相比,采用該治療的患者在白細胞、血紅蛋白、ALT、AST、總膽紅素、直接膽紅素、堿性磷酸酶、谷氨酰轉肽酶等各項肝功檢測指標均有明顯下降,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凝血酶原活動度、國際標準化比值等反映凝血情況的檢測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人工肝治療能明顯改善DILI患者肝臟相關實驗室檢測指標,改善血液內環境,清除肝臟代謝廢物,減輕肝臟負擔,為DILI患者特別是重癥患者提供更有利的治療方式,而對患者血液的凝血狀態無影響。
三、影響治療效果的因素分析
為探討所有入組的DILI患者中,究竟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患者的治療效果,以便為患者提供更精準的治療方式,為臨床醫師提供更好的治療決策。將入組患者的基線資料與治療效果的相關關系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法進行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我們以治療效果作為因變量,納入的單因素包括:性別、年齡、治療分組、ALT、總膽紅素、堿性磷酸酶、谷氨酰轉肽酶、凝血酶原活動度、國際標準化比值、MELD評分等。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自變量為國際標準化比值。見表3。

表1 2組患者匹配前、后協變量比較

表2 2組患者(匹配后)治療后實驗室指標對比

表3 logistic回歸單因素分析影響治療效果的相關因素
將上述自變量全部納入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中做多因素分析,以治療效果作為因變量,非條件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總膽紅素(OR:0.085;95%CI:0.010~0.691;P=0.021)和凝血酶原活動度(OR:0.029;95%CI:0.003~0.340;P=0.005)是影響DILI患者治療效果的獨立因素。見表4

表4 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影響治療效果的相關因素
討 論
DILI是藥品的常見不良反應之一,可以引起肝臟組織及功能損害的藥物多達1 100多種,在我國主要以中草藥引起的肝損傷最為常見,且多以膽汁淤積型為主[9]。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感冒藥物,特別是含有對乙酰氨基酚的抗感冒藥物、抗生素及非甾體解熱鎮痛藥物所引起的肝損傷也越來越常見,這一點與歐美發達國家常見的DILI原因逐漸相似[11-12]。本研究亦有所體現。
DILI患者中特異質型在臨床比較常見,由于個體差異性明顯,臨床表現多樣化,且常與藥物劑量無相關性,因而往往無法預測。本研究所納入的患者入院前都存在全身乏力的主訴癥狀,部分患者出現惡心厭油、食欲減退、上腹脹痛等消化道癥狀,少數病例出現全身皮膚黃染、發熱,伴或不伴有皮膚瘙癢及皮疹。重癥病例可出現急性或亞急性肝功能衰竭。因而針對DILI的治療并無固定不變的模式和方法,除了及時停用可疑肝損傷藥物和根據經驗使用“保肝藥”以外,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療是常見的輔助治療手段。作為一種血液凈化的治療方式,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療通過聯合或單獨使用血漿置換、血漿吸附、血液灌流等多種模式,清除體內由于肝功能失代償而堆積的膽紅素、膽汁酸、炎癥介質、內毒素和殘存藥物等毒性物質,凈化內環境,為肝臟的恢復創造一個相對良好的環境,對于包括藥物性在內的多種原因所導致的膽汁淤積性肝病、肝功能衰竭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和安全性[13-15]。在本研究中,相比單純藥物治療來說,人工肝治療組的入組患者肝功能評級更低,DILI嚴重程度分級更重。提示根據不同疾病發展程度的DILI患者,給予積極有效的個體化治療方案尤為重要。本研究亦觀察到,與非人工肝治療的患者相比,采用了該治療的患者,其治療后肝功能相關實驗室檢測指標有了更明顯的好轉,證實了人工肝治療對于重癥DILI患者治療的有效性。而治療前的總膽紅素及凝血酶原活動度水平有助于更好評價DILI患者的預后。以上結果可為臨床醫師在制定治療決策方面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