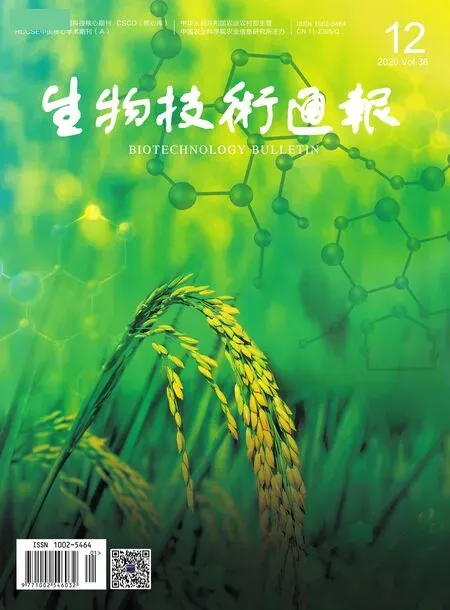植物表皮蠟質合成及調控因子WIN/SHN的研究進展
李曉佩 王思寧 史晶晶 高志民
(國際竹藤中心 竹藤資源基因科學與基因產業化研究所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北京市共建竹藤科學與技術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102)
植物的失水方式主要依賴于氣孔的蒸騰作用,但是在遭遇非生物脅迫時,植物的氣孔關閉,此時的失水方式轉變為角質蒸騰,因此植物角質層對于體內的水分調節在此時顯示出極為重要的作用,對維持植物的生命活動具有重要意義[1-3]。成熟的角質層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分泌到最外側的表皮蠟質也可以稱作蠟質層;二是由角質和鑲嵌在細胞內的蠟質共同組成的聚合物構成所謂的角質層,它可以與細胞壁相連接[4]。植物表皮蠟質作為覆蓋在植物最外側與空氣水分直接接觸的一層保護屏障,其組成成分較為復雜,由烷烴、醛類、酯類等有機物混合而成,其中以酯類為主[5]。研究發現,蠟質的微觀結構多樣,有桿狀、柱狀、管狀、絲狀、片狀、顆粒狀等26類[6-7]。但是,隨著植物的生長發育,蠟質形態也隨著植物的生長而改變,使植物更加適應環境。
在不同植物、不同器官中,雖然蠟質的結構和組成都具有一定的差異,但都具有相似的蠟質合成途徑。由于蠟質在應對干旱、鹽、溫度、強光等多種非生物脅迫以及防止病蟲害侵襲等生物脅迫均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了解植物表皮蠟質合成的途徑及其調控轉錄因子對于深入理解蠟質的形成和其生物學功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介紹植物表皮蠟質合成的基礎上,重點對參與蠟質合成調控的轉錄因子WIN/SHN進行綜述,包括WIN/SHN的結構特點、表達模式,以及轉錄調節對植物生理與表型的影響,對逆境的應答反應等,最后對蠟質合成的復雜性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以期對開展作物育種、栽培及病蟲害防治等提供參考。
1 植物表皮蠟質的合成
蠟質主要是由C20到C34之間的長鏈脂肪酸組成的混合物,其中包括一些醛、醇、烷烴、酮和酯類[4,8]及其他一些萜類等次級代謝物。一般組成酯類的碳鏈較長,最長可以達到60個碳原子,主要是通過酯鍵將甘油、苯丙烷和二羥酸聚合在一起形成蠟質[9],最后運輸到細胞壁當中。蠟質的起始合成是在表皮細胞的質體中進行的,乙酰CoA在乙酰輔酶A羧化酶(Acetyl-CoA carboxylase,ACCase)的催化作用下形成二碳的供體丙二酰-ACP[10],之后是脂肪酸合成酶復合物(Fatty acid synthase complex,FAS)發揮作用,使碳鏈長度達到C16/C18,在酰基-ACP硫酯酶(Fatty acyl-ACP thioesterase,FAT)的作用下釋放出來[11-12],并且運輸到細胞質當中,與CoA結合。酰基-ACP硫酯酶調節表皮聚酯單體的鏈長分布,由其將酰基CoA引導至蠟和角質單體生物合成的不同途徑。脂肪酸的伸長和細胞色素P450依賴的羥基化發生在內質網上,酰基CoA在脂肪酸延伸酶復合體(Fatty acid elongase,FAE)的催化作用下形成超長鏈脂肪酸(Very long chain fatty acids,VLCFAs)[2],然后將VLCFA直接導入修飾它們所必需的不同酶復合物中,經過酰基還原途徑生成偶數碳鏈的伯醇和酯類,脫羰途徑生成偶數碳鏈的醛和奇數碳鏈的烷烴等不同的蠟質成分[13-16]。另外,蠟質數量和組成在不同物種、不同器官及不同發育階段存在著很大差異,如烷烴是擬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莖和葉蠟的主要成分。但在玉米(Zea mays)和水稻(Oryza sativa)葉中含量很低;仲醇和酮在擬南芥莖蠟中含量豐富,但在葉蠟中含量很低或檢測不到[17]。
到目前為止,通過研究擬南芥、水稻等植物及其突變體,蠟質合成途徑所涉及的酶相對比較清晰[12,18],但仍有新的酶被發現。如利用水稻突變體株系CM1337,克隆到了控制葉片沾水表型的WSL5基因,它編碼一個烷烴末端羥化酶,以烷烴為底物催化產生超長奇數碳鏈伯醇的合成[19]。另外,除了各種酶外,蠟質的生物合成還有許多轉錄因子參與,如AP2、MYB、bHLH和HD-ZIP等家族的轉錄因子對蠟質合成途徑中的信號傳導與調控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20-22],其中WAX INDUCER(WIN)/SHINE(SHN)是AP2家族的一類重要成員,參與蠟質合成的調節。
2 蠟質合成調節因子WIN/SHN
蠟質合成途徑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代謝過程,有許多調控因子參與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WIN/SHN由兩個團隊同時報道出來[23-24],是在擬南芥中第一個被確定下來用于負責蠟質產生和沉積的轉錄因子,同時它也是一個乙烯響應型的轉錄因子。WIN/SHN屬于AP2/EREBP超家族ERF亞家族,ERF B-6[25]或者ERF V[26],在轉錄水平上參與蠟質的合成調控。隨著越來越多的WIN/SHN被鑒定,對其結構特點、表達模式以及對蠟質合成調節功能的認識也逐漸清晰。
2.1 WIN/SHN的基因結構與保守域
一般來講,WIN/SHN的基因結構相對比較簡單,都含有1個內含子與2個外顯子,如擬南芥中有3個重要的WIN/SHN同源基因(SHN1、SHN2和SHN3)[23-24]。隨后在水稻中鑒定獲得了4 個與擬南芥WIN/SHN同源的基因OsWR1-OsWR4,OsWR1-OsWR4均含 有1個內含子[27]。在大 豆(Glycine max)中的10 個同源基因(GmSHN1-GmSHN10)中,除GmSHN3與GmSHN4含有2個內含子與3個外顯子外,其他GmSHNs的基因結構與擬南芥相似[28]。番 茄(Solanum lycopersicum)中3 個WIN/SHN同源 基 因(SlSHN1、SlSHN2和SlSHN3)[29],其 中SlSHN2除了在起始密碼子處含有一個82 bp的內含子外,在距離起始密碼子897 bp處還另有一個內含子[30]。內含子數量和位置的差異,導致基因結構不同,可能是影響其具體生物學功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WIN/SHN基因編碼的氨基酸序列包含1個位于N端高度保守的ERF/AP2結構域,并在其中心部分和C末端共享另外兩個結構域[21,25],即CMV-1和CMV-2結構域[31]。水稻中OsWR1與擬南芥WIN1/SHN1、SHN2和SHN3蛋白序列的相似性分別為68.8%、58.0%和57.8%,而與OsWR2、OsWR3和OsWR4的相似性分別為81.0%、41.4%和41.7%,但都包含3個保守結構域[27]。大豆中的GmSHN1-GmSHN10與擬南芥WIN/SHN的相似性達到80%以上[28],而番茄中的SlSHN3與擬南芥中SHN3的相似性為75%[30]。不同植物中WIN/SHN的氨基酸序列雖然存在差異,但是它們都具有3個保守結構域,因此其功能也具有相似之處,而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也造成了各自的功能獨特性。
2.2 WIN/SHN基因的表達模式
研究發現,WIN/SHN基因家族的不同成員具有不同的組織表達模式。一些WIN/SHN基因表現為組織表達特異性,如大麥(Hordeum vulgare)中HvNud是類似于SHN1/WIN1的一個基因,缺失17 bp的自然變異導致了裸(無殼)大麥籽粒表型的出現,具有種皮特異性表達模式[32]。而擬南芥WIN1/SHN1在花序和根中表達,在莖、成熟蓮座葉和莖葉中不表達;SHN2的表達模式與花藥和角果開裂相關[23]。水稻中的OsWR1與黃瓜(Cucumis sativus)中的CsWIN1表達模式相似,都在葉中的表達量較高;但是水稻根中的OsWR1表達量較弱,黃瓜的根中CsWIN1卻幾乎不表達[27,33]。OsWR2在水稻莖、葉片、葉鞘、穗和幼苗中的表達量較高,而在根和種子中的表達較低[34]。番茄中SlSHN2與SlSHN3表達模式相似,均在未成熟的綠色果實(IG)外果皮中表達,而SlSHN1在發育過程中表現出與外果皮相關的特異性表達模式[30,35]。在大豆的10 個同源基因中,大部分都具有組織特異性,如GmSHN1與GmSHN2只在花器官中表達[28]。
而另一些WIN/SHN基因表現為組成型表達,如擬南芥中的SHN3基因表達最廣泛,在所有器官當中都具有活性,在維管系統和側根尖部均有表達[23];大豆中的GmSHN5在各組織中表達均較弱[28]。還有一些基因表現明顯的時空性,如蘋果(Malus pumila)中的MdSHN3的表達分析被擴展到果實的成熟綠色期和收獲期,結果發現表皮受損的品系在成熟綠色期MdSHN3表達降低70 倍,而收獲期則更低[36];MdSHINE2在幼葉、果皮、根和花瓣中顯示出較高的表達,而且幼葉的表達量要明顯高于成熟葉片,表明同一器官發育的不同階段MdSHINE2的功能也存在差異[37]。由此可見,不同物種的WIN/SHN基因家族的各成員在組織當中的表達有所不同,同一個物種中的各基因成員在不同組織中的表達量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表現出表達模式的多樣性,表明各自對蠟質的合成可能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2.3 WIN/SHN的轉錄調節作用
2.3.1 WIN/SHN的正調節 作為轉錄因子,WIN/SHN通過對蠟生物合成相關基因的表達調節來影響其生物合成。通過染色質免疫沉淀(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CHIP)和電泳遷移率改變分析(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s,EMSA),結果顯示水稻OsWR1與OsLACS2/OsFAE1'-L基因啟動子的DRE和GCC-box順式元件結合,直接調節其基因的表達,在OsWR1過量表達的轉基因水稻中,OsLACS1、OsLACS1-2、OsFDH1/2、OsCER1/2、OsCUT1、OsKCS1、OsFAE1-L和OsFAE1'-L等 基 因的表達上調了2倍[27],表明OsWR1是水稻中蠟質合成相關基因的正向調節因子。在煙草(Nicotiana tabacum)中過表達大麥HvSHN1,同樣上調了啟動子含有DRE和GCC-box元件的抗逆應答基因的表達[38]。在擬南芥中有3個基因(CER1、CER2和KCS1)被鑒定為受WIN1/SHN1的調控,參與表皮蠟的生物合成,其中過表達WIN1/SHN1對CER1基因的上調作用最強,而角質層生物合成相關的另外3個基因CER6/CUT1、CER3和FDH的轉錄水平沒有改變[24]。在擬南芥中過表達大豆GmSHN1/GmSHN9,發現AtLACS1/CER8和AtLACS3(編碼酰基輔酶A)、AtGPAT4和AtGPAT6(編碼甘油3-磷酸酰基轉移酶)、AtCYP86A4和AtCYP86A7(編碼脂肪酸ω-羥化酶)及AtCD1(編碼角質合成酶)的表達均上調,其中在GmSHN1-OE1和GmSHN9-OE1轉基因植株中AtLACS1分別增加3.5倍和6.5倍,AtCD1分別增加5.1倍和4.8倍,引起了葉片角質含量和組成發生了變化[23-24],表明GmSHN1和GmSHN9可能都對脂肪酸延伸過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8]。
此外,利用抑制基因表達的方法也證明了WIN/SHN的轉錄調節作用。對大麥接種病原菌的研究中發現,敲除HvWIN1,提高了病害嚴重程度和真菌生物量,降低了亞油酸和棕櫚酸等游離脂肪酸的豐度,證明HvWIN1可以調節表皮生物合成中的基因表達從而防御大麥鐮刀菌赤霉病[39-40]。用RNAi沉默SlSHN3構建表達載體,轉化番茄植株,導致與角質代謝的多個基因下調,其中MG時期番茄表皮中編碼5個轉錄因子的基因表達均顯著降 低,包 括SlSHN2、SlMIXTA、SlGL2、SlHDG11a和SlANL2c[30]。在OsWR1的RNAi沉默轉基因水稻RI-WR1中,OsLACS1、OsLACS1-2、OsFDH1/2、OsCER1/2、OsCUT1、OsKCS1、OsFAE1-L和OsFAE1-L’等基因的表達均顯著下調[27]。另外,SlSHN3可以激活2個轉錄因子基因(SlMIXTA和SlGL2a)和2個 細 胞 色 素P450(SlCYP86A68和SlCYP86A69)的啟動子,由此表明SlSHN3可能是直接作用于角質生物合成基因和表皮細胞構型相關調控因子,從而影響果皮形成和表皮構型[30]。
2.3.2 WIN/SHN的負調節 WIN/SHN作為轉錄因子參與調控蠟質合成的同時,其自身的表達也受到其他轉錄因子的負調控,NFX1-LIKE2(NFXL2)和SPY是目前發現的2個主要的WIN/SHN負調節因子。研究發現,擬南芥NFXL2基因的缺失導致ABA和過氧化氫水平升高,氣孔開度減小,抗旱性增強;在fxl2-1突變體中SHN1、SHN2和SHN3的表達量較高,是可能導致角質層特性的改變,氣孔密度降低,提高抗旱性的部分原因;在fxl2-1突變體中過表達NFXL2-78,NFXL2-78與SHINE1(SHN1)、SHN2、SHN3和BODYGUARD1(BDG1)基因的啟動子直接結合,介導這些基因的表達減弱[41]。SPINDLY(SPY)編碼一種乙酰氨基葡萄糖轉移酶,可以修飾靶蛋白并調節細胞中的蛋白活性。在擬南芥spy-3突變體中,SHN1/WIN1、DREB1E和DDF1的表達上調使其維持較高的水分含量,從而使耐旱性增強;而轉基因擬南芥中SPY基因的過表達則降低了WIN1/SHN1基因的表達水平,降低了耐鹽性和抗旱性[42]。因此,NFXL2和SPY均對WIN/SHN起到負調控作用,進一步影響蠟質合成。
3 WIN/SHN的轉錄調節效應及其對逆境的應答反應
3.1 WIN/SHN的轉錄調節對生理及表型的影響
利用突變體是研究基因功能的重要手段。擬南芥突變體Shine(shn)與野生型相比,表現為葉片表面呈現明亮、發亮的綠色,蠟質含量增加,抗干旱脅迫能力增加[43];生化實驗顯示,該突變體總角質蠟含量增加了6倍,主要是因為約占蠟質總量50%的烷烴增加了9倍,其中所有蠟質成分都有所增加,烷烴、仲醇和酮類的增長幅度較大,而C30脂肪酸、C30醛和C27/C29烷烴也有所增加[23]。利用RNAi沉默技術所構建轉基因植株也是研究基因功能的另一種方法,對科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例如,SlSHN3的RNAi轉基因番茄果實呈現出特有的表型,其中果實的表面光澤度更高,分離角質層時所需的酶更少。通過對果實成熟綠色(MG)期表皮的透射電鏡觀察,證實RNAi果實的表皮比野生型薄的多。同時,RNAi系MG階段的果實角質層中的總角質單體豐度降到了野生型的40%,其中芳烴、二元羧酸、中鏈和末端烴基化脂肪酸以及2-羥基化脂肪酸的含量顯著降低,導致SlSHN3RNAi系角質單體顯著減少,酶法分離的MG果實角質層中的蠟總量也顯著減少[30]。
過表達AtWIN1/AtSHN1擬南芥的葉表皮蠟質含量比對照植株高4.5倍,改變了葉片和花瓣表皮細胞結構、毛狀體數量及氣孔指數,增加了角質層的通透性,轉基因植株表現出顯著的抗旱性[24]。AtSHN2基因在水稻中過表達,使表皮蠟適度增加,水分利用效率提高;同時纖維素含量提高、木質素含量降低,但是莖稈強度沒有明顯改變[44]。過表達OsWR1水稻Ox-WR1在開花期株高明顯低于野生型,但葉片的蠟質含量增加了約26%;而OsWR1的RNAi沉默轉基因水稻RI-WR1幼苗葉片蠟質降低了21%;與RI-WR1相比,Ox-WR1植株葉片的C30脂肪酸增加了36%,而伯醇含量略有下降[27]。在擬南芥中過表達番茄SlSHN3和大豆GmSHN1-GmSHN7,產生了與過表達AtSHN1相似的表型,葉片較小而有光澤,但葉指數(葉長/葉寬)與野生型相似[23-24]。然而,GmSHN8、GmSHN9和GmSHN10的轉基因系葉片呈現出黃綠色且伴隨著卷曲,葉柄細長,葉片指數高于野生型;而轉GmSHN1與GmSHN9的株系葉片上毛狀體減少,光澤度增加,轉GmSHN1的2個株系蠟質的含量分別增加了7.8倍和9.9倍,其中C31和C29烷烴對蠟含量增加的貢獻最大[28]。
3.2 WIN/SHN對逆境的應答反應
WIN/SHN除了參與蠟質生物合成調節外,還參與植物對逆境的應答反應。水稻OsWR1與擬南芥蠟質/角質調控逆境調節因子WIN1/SHN1高度相似,受干旱、脫落酸和鹽誘導,干旱脅迫條件下OsWR1表達量在1 h后逐漸升高,2.5 h達到最高;高鹽和ABA脅迫分別在處理6 h和9 h后達到最高表達水平[27]。小麥(Triticum aestivum)TdSHN1編碼一個受非生物脅迫誘導的轉錄因子,鹽(NaCl)、干旱、脫落酸(ABA)和寒冷(4℃)等脅迫強烈誘導TdSHN1的表達,其中鹽和ABA在脅迫1 h就達到峰值,而寒冷和干旱脅迫誘導峰值出現在6 h;在酵母中表達TdSHN1能提高轉基因酵母的抗旱、抗寒和抗氧化能力[45]。大麥中HvSHN1的表達明顯受到鹽(NaCl)、干旱、冷(4℃)和熱(37℃)脅迫的誘導,其中鹽和干旱處理6 h后HvSHN1的表達達到最高,而冷和熱脅迫24 h后HvSHN1的表達達到最大值[38]。
另外,對過表達WIN/SHN轉基因植株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支持了該類基因能夠增強轉基因植株對脅迫的應答能力。對SHN1過表達擬南芥植株進行自然干旱處理,隨后復水監測顯示,野生型植株沒有恢復過來,而過表達SHN1/WIN1的所有植株都能恢復,且更綠、更強壯,抵抗干旱的能力更強[23,46]。對過表達OsWR1基因水稻研究表明,在干旱脅迫后發現,OsWR1通過調控蠟質合成相關基因的表達來調節長鏈脂肪酸(C30)、烷烴(C25和C31)和酯(C48)等蠟質的組成成分,進一步提高植株的耐旱能力[27]。OsWR1的過表達還導致了不參與角質層生物合成的基因的上調,例如編碼抗壞血酸過氧化物酶(Ascorbate peroxidase,APX)、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過氧化氫酶(Catalase,CAT)的基因,但這些基因有可能獨立地發揮作用來提高耐旱性;而在OsWR1基因的RNAi轉基因株系RI-WR1中,僅CatA和CatB轉錄水平降低,表明OsWR1可能參與氧化應激反應和膜穩定性的調節,并且這種調節可能是對干旱反應中OsWR1調節的補償[27],這意味著OsWR1可能通過調控活性氧清除酶系統來提高水稻的抗旱能力。
4 問題與展望
植物表皮蠟質的生物合成途徑涉及的酶相對比較清晰,但該合成途徑的調控則是一個復雜的調控網絡。雖然有許多轉錄因子參與到蠟質合成調節當中,但是目前所鑒定到的轉錄因子也非常有限。因此,一方面需要認識到蠟質合成的復雜性,對WIN/SHN的研究需要深入開展,并繼續尋找和篩選其他調控因子;另一方面需要發掘蠟質對農業生產實踐的價值,看到其應用前景。
研究發現,擬南芥中MYB106和WIN1/SHN1調節相似的基因集,主要是參與蠟和角質生物合成的基因,MYB106可以正調控WIN1/SHN1,它們協調調節角質的生物合成和蠟質積累[47]。在水稻中表達AtSHN2基因,能夠協調木質素生物合成的下調和纖維素及其他細胞壁生物合成途徑基因的上調,影響到細胞壁的生物合成調控,并與NAC和MYB轉錄因子結合,調控細胞壁中木質素與纖維素的合成[48]。因此,WIN/SHN的功能可能具有多樣性,它需要和其他的轉錄因子共同作用調控蠟質合成。另外,WIN/SHN所參與的蠟質合成調控除了受植物內在因子的影響外,還受到生物與非生物因素的影響,進而影響蠟質的合成與分泌。WIN1/SHN1可能是間接的通過調節蠟質合成相關基因,來提高蠟質的累積,從而完成對生物以及非生物的響應,提高植物的抗逆性[23-24]。由此表明,WIN/SHN參與的蠟質合成與調控是一個復雜網絡,對于WIN/SHN以及其它轉錄因子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
蠟質對植物生命活動具有重要作用,參與植物應對干旱、鹽、溫度、強光等多種非生物脅迫,使得植物更加適應環境的變化[49-55],同時對預防病蟲害等生物脅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7,56]。我們相信,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將有更多的現代先進生物技術和手段幫助我們深入開展包括WIN/SHN在內的多種類型遺傳因子及環境因子對蠟質合成、調控與運轉的機制研究,解析植物蠟質在生命科學中的意義,這將對未來農業生產實踐產生重要的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