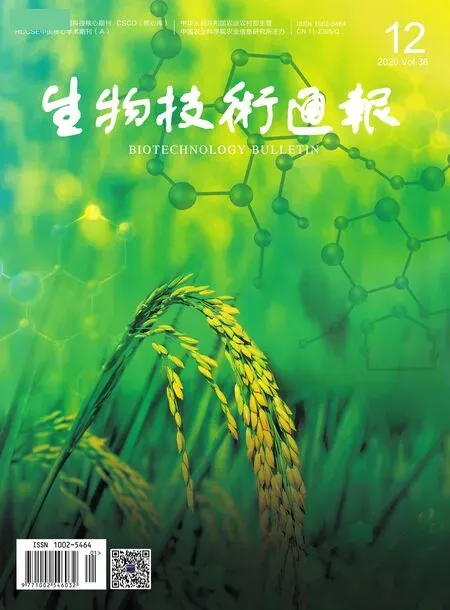水稻重要農藝性狀調控基因及其育種利用研究進展
張海淼 李洋 劉海峰 孔令廣 丁新華
(山東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泰安 271018)
水稻(Oryza sativa)是全球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也是我國三大主要糧食作物之一。2019年我國水稻總產量達到了世界水稻總產量的29.8%,繼續保持了水稻生產第一大國的地位。目前我國種植的水稻以亞洲栽培稻(Oryza sativaL.)為主,亞洲栽培稻主要包括粳稻(Oryza sativasubsp. geng)和秈稻(Oryza sativasubsp. xian)兩個亞種[1-2]。1956年,黃耀祥院士培育出的矮桿秈稻品種“廣場矮”大幅提高了水稻單產,率先完成了中國的第一次“綠色革命”。1973年,袁隆平院士利用三系雜種優勢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秈型雜交水稻,進一步推動了水稻研究的進程,三系雜交水稻的面世和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推廣解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二十多個國家的溫飽問題。當面臨作物品質需求日益多樣化和人均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矛盾時,傳統育種技術周期長、效率低、預見性差等局限性開始暴露。世紀交替之際,我國相繼啟動了“水稻分子育種計劃”、“水稻功能基因組計劃”等項目,推動了水稻優質農藝性狀功能基因的鑒定進程,為分子育種提供了理論前提和基礎。理想株型基因IPA1的鑒定為平衡水稻免疫和生長提供了新的育種思路,同時攜帶IPA1優異等位基因ipa11D或ipa12D的嘉優中科綠色超級稻的培育和推廣標志著水稻研究邁入分子育種時代[3]。
1 水稻的起源
從分子學角度來說,水稻起源的探究本質上是野生稻到栽培稻馴化相關基因的鑒定,水稻株型、粒型、穎芒、產量和品質等農藝性狀馴化的過程是為了適應環境變化、滿足人們需求不斷進行基因變異的過程。目前,關于水稻起源的假說主要有兩種。單一起源假說認為秈稻和粳稻是從同種野生稻馴化而來,多地起源假說認為秈稻和粳稻是從多地獨立馴化而來[4]。Tan等[5]對87份秈稻和95份粳稻的基因序列進行比對,發現這182份水稻均存在PROG1基因的變異,這種共同的變異使野生稻由匍匐狀進化成直立狀,株型更加緊湊,同時也支持了單一起源假說。Molina等[6]對多份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第8、10、12號染色體上630個基因測序,并得出中國長江流域是粳稻和秈稻唯一起源地的結論。sh4是影響水稻落粒性的主效數量性狀基因,Zhang等[7]對sh4單 核 苷 酸 多 態 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點進行分析,發現所選取的41份野生稻第237位SNP位點均為G,而30份亞洲栽培稻SNP位點均為T,進一步證明了sh4是多態性較低的單一起源基因,這一研究成果被認為是水稻單一起源假說強有力的證據。直到2017年,Civáň和 Brown[8]發現sh4和PROG1等位基因在栽培稻馴化之前就已經出現在野生稻上,否定了之前的單一起源假說。Singh等[9]對野生稻和栽培稻中的果皮色澤基因(Rc)、粒長粒重主效控制基因(GS3)和 淀 粉 合 酶 基 因(GBSSI,SSSI,SSIIa,SSIIb,SSIIIa,SSIIIb,SSIVa,SSIVb)進行了遺傳進化分析,研究發現Rc、SSSI、SSIIa、SSIIb、SSIIIa和SSIVa為雙系起源,其余基因為三系起源。隨著分子檢測技術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證據開始向水稻的多地起源假說傾斜。中國啟動了對3 010份水稻基因組深度重測序的項目(3K Rice Genome Project,3KRG),該項目對所選取的水稻材料進行了SNP分析,并于2018年在Nature上分享了研究成果,研究表明秈稻和粳稻均攜帶自身特有的基因家族,并提出秈稻和粳稻是獨立多地起源,同時更正了多年來日本對秈稻和粳稻拉丁文的錯誤命名[1]。水稻馴化過程的解析為科研工作者定向選擇馴化相關基因進行分子育種提供了重要依據。
2 農藝性狀功能基因及其分子育種研究進展
相對于傳統雜交育種,分子育種目的性更強,可以通過改變一個或幾個基因來獲得目的性狀,并且打破了傳統育種的生殖隔離,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兼顧品質、抗性、營養高效等多種性狀的改良。基因組重測序技術的廣泛應用加速了我國對水稻多種農藝性狀調控基因的克隆,為分子育種提供了技術支撐。最新數據顯示,Yong等[10]對3K-RG中IR 64等12份沒有參考基因組的亞洲栽培稻進行了三代測序,并對基因組進行組裝、校正,所得的高質量基因組進一步推動了科研工作者對種質資源的深度挖掘和高效利用。中國科學院對1 275份水稻進行群體分析并獲得了146份調控株型、粒型、抗性等29個農藝性狀的表型數據,鑒定出143個SNP位點,為進一步利用優異等位基因進行水稻品系改良奠定了數據基礎[11]。
2.1 營養高效利用調控基因
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水稻產量持續增長的部分原因是化肥施用量的增加[12]。化肥投入過高會導致水體富營養化,并且目前農業生產過程中化肥利用率普遍較低[13],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違背了農業可持續發展理念。因此,鑒定水稻營養高效利用調控基因、提高肥料利用率,對發展綠色農業具有重要意義。
氮、磷、鉀是水稻生長和繁殖所必需的三大營養元素,提高營養元素利用率、減少化肥施用量成為科研工作者新的育種目標。20世紀60年代攜帶sd1半矮桿水稻的推廣大幅提高了水稻單產,但半矮稈水稻赤霉素合成受阻,導致生長抑制轉錄因子DELLA在植物體內不斷積累,降低了水稻對氮肥的響應和吸收[14-15]。2018年,傅向東研究組鑒定到正向調控水稻銨態氮吸收速率的生長調控因子GRF4,DELLA蛋白通過抑制GRF4-GIF1復合體對下游靶基因的調控來抑制水稻對氮的吸收。攜帶半矮基因sd1和GRF4優異等位基因GRF4ngr2的高產水稻品種9311在保留了半矮化性狀的同時具有較高的氮元素吸收率。此外,GRF4還能誘導OsCAB1、OsTPP和OsSWEETs等碳代謝相關基因的表達。GRF4-DELLA拮抗機制的發現對調節水稻生長和碳氮代謝具有重要指導意義[14]。近日,傅向東研究組從9311背景的ngr5突變體中克隆出氮元素響應基因NGR5。研究表明,NGR5和PRC2復合體亞基LC2在細胞核中產生相互作用,并通過提高下游分蘗抑制因子(D14、OsSPL14)的H3K27me3修飾水平抑制其表達,進而實現正向調控水稻對氮肥的響應同時促進分蘗數的增加。同時,NGR5還是赤霉素信號路徑關鍵調控因子,DELLA蛋白可以和NGR5直接互作并競爭性結合NGR5的負調控因子GID1,當赤霉素受體GID1感知到赤霉素信號時NGR5可免遭降解,從而提高水稻對氮肥的利用率,實現低氮高產的可持續發展理念[16]。
磷酸鹽(Pi)是植物唯一能吸收的磷形態[17]。位于細胞質膜(PM)的轉運蛋白(PTs)是Pi吸收和轉運的關鍵,OsCK2通過磷酸化OsPT8來抑制其從內質網(ER)向PM的轉運,從而避免Pi攝取過量[18],但轉運蛋白的去磷酸化機制一直不明確。毛傳澡研究組[19]釣取到和OsPT8互作并且能夠調節PTs可逆磷酸化的關鍵蛋白OsPP95。當Pi缺乏時,OsPP95快速積累與OsCK2相互抑制并使OsPT8去磷酸化,促使PTs從ER轉運到PM;當Pi富足時,OsPP95被E2泛素結合酶OsPHO2快速降解,同時大量被磷酸化修飾的OsPT8滯留在ER無法完成對Pi的轉運,進而減少對Pi的吸收,最終得以平衡水稻體內Pi的吸收和轉運。該研究組同步揭示了OsCK2對OsPHO2的負調控機制,OsCK2的亞基OsCK2α3在內質網對OsPHO2的磷酸化修飾加速其降解,并維持OsPHO2及其靶蛋白OsPHO1或磷酸鹽轉運蛋白OsPHF1在Pi富足時仍處于適當水平,從而確保Pi從根到芽的轉運和芽的正常生長[20]。
鉀離子(K+)是限制作物產量和品質的因素之一,在穩定植物代謝、提高植物抗逆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1]。研究表明,在低鉀濃度(< 0.2-0.5 mmol/L)和高鉀濃度(1 mol/L-10 mmol/L)下OsCBL1-OsCIPK23復合體的形成能促進OsAKT1介導的水稻根部對K+的吸收[22]。近日,章文華研究組發現OsAKT2具有弱內流型鉀通道活性,可以阻止H+/蔗糖協同誘導的細胞膜去極化,OsAKT2的功能突變會導致水稻幼苗在短日條件下生長緩慢,磷脂酸可通過直接抑制OsAKT2來影響水稻生長發育,該研究揭示了水稻磷脂信號和K+通道調控的直接聯系,對改良水稻K+利用率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3]。
2.2 激素調控基因
激素在植物先天免疫、營養生長以及生殖生長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包括獨腳金內酯(Strigolactones,SLs)、油菜素內酯(Brassinolides,BRs)、茉莉酸(Jasmonic acid,JA)、水楊酸(Salicylic acid,SA)、脫落酸(Abscisic acid,ABA)和赤霉素(Gibberellic acid,GA)等[24],不同植物激素信號各自獨立或交叉調節植物生長與防御的平衡。
SLs是20世紀60年代在棉花中發現的抑制植物分蘗的新型激素[25]。目前已鑒定出水稻中多個SLs信號路徑的關鍵組分。當感知到SLs時,SLs信號傳導抑制子Clp蛋白酶的核蛋白D53被D53-D14-SCFD3復合體泛素化修飾并特異性降解,進而激活下游相關基因對SLs信號的響應[26-27]。李家洋研究組對粳稻Nekken 2和秈稻恢復系華占的重組自交系進行差異分析,在華占中發現了SLs合成基因HTD1的優異等位基因HTD1HZ,HTD1HZ在SLs生物合成中部分功能喪失,能夠緩解SLs對分蘗和側芽生長的抑制作用。并且,在培育“綠色革命”產物半矮化品種IR8的過程中SD1DGWG和HTD1HZ被共同選擇并穩定遺傳,我國雙桂、MH63等秈稻品種也攜帶HTD1HZ[28]。分蘗調控基因HTD1HZ的發現充分證明了華占在雜交育種中的優勢,為雜交育種親本的選擇提供了新的依據,并對利用SLs信號路徑上的基因來改良水稻株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BRs可以調節植物株高、葉片傾角、籽粒大小、分蘗、開花等多種性狀,在提高植物產量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力[29]。當BRs信號被OsBRI1和共受體OsBAK1感知后,通過一系列磷酸化事件將信號依次傳遞到OsBSK3和OsBSU1,并拮抗OsGSK2對轉錄因子OsBZR1的抑制作用,最終通過OsBZR1對BRs信號下游相關基因的調節實現對BRs信號的響應[30-32]。目前在水稻中還發現了其他調節BRs信號的關鍵基因,如DLT和OFP8均正調控BRs信號[33-34],LIC通過與OsBZR1互作負調控BRs信號[35],OFP19通過與DLT和OSH1形成復合物負調控BRs信號[36]。同時,激酶OsGSK2是協調BRs信號和SLs信號的關鍵組分,可通過磷酸化CYC U2抑制中胚軸的伸長。研究表明,BRs和SLs分別通過抑制OsGSK2的磷酸化修飾和降解OsGSK2的底物來調節水稻中胚軸的伸長生長[37]。最近,儲成才研究組[38]發現OFP3通過和多個OsGSK2的靶蛋白發生相互作用抑制BRs的合成和傳導,同時OsGSK2 對OFP3的磷酸化修飾不僅增強了OFP3蛋白的穩定性還增強了OFP3和靶蛋白之間的相互作用。錢前研究組[39]發現OsGSK2可在細胞核內磷酸化OML4并負調控水稻籽粒大小和粒重。卜慶云研究組[40]發現OsMED25通過和靶蛋白OsBZR1共同調控BRs信號下游基因的表達正向調控水稻對BRs信號的感知。張啟發研究組[41]鑒定到可以同時調控水稻生長和免疫的基因OsALDH2B1。OsALDH2B1不僅具有轉錄調控功能可參與調節水稻的抗性、產量等多種性狀,還具有乙醛酸脫氫酶活性可以調節水稻育性。OsALDH2B1通過抑制JA合成途徑OsAOS2的表達來負調控JA介導的水稻對條斑病菌(Xanthomonas oryzaepv.oryzicola,Xoc)、白葉枯病菌(Xanthomonas oryzaepv.oryzae,Xoo)和稻瘟病菌(Magnaporthe oryzae)的抗性,并通過拮抗BRs信號路徑中位于其上游的OsBZR1對其下游OsLIC的抑制作用來降低水稻對BRs的敏感性,同時還可負調控粒長、粒重主效調控基因GS3的表達來影響水稻的產量。以上研究成果對尋找能夠協調植物防御和生長平衡的新節點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JA主要參與調節植物對死體營養型病原菌的抗性,而SA介導對活體、半活體營養型病原菌的抗性[42-43]。JA和SA在擬南芥和水稻中均具有拮抗作用[44]。在擬南芥中,JA可以通過調控多個NAC轉錄因子來抑制SA的積累。JA信號關鍵調控蛋白MYC2與NACs的啟動子結合后激活NACs的轉錄,并進一步抑制SA合成基因ICS1的表達[45]。在水稻中,超量表達SA信號路徑關鍵調控因子OsNPR1會強烈激發SA信號并提高對Xoo和M. oryzae的抗性,同時抑制JA信號[46]。近日,劉俊研究組鑒定了可通過動態調節SA信號和JA信號來提高水稻對M. oryzae抗性的關鍵基因OsbHLH6,OsbHLH6主要分布在植物細胞核中,部分位于細胞質中。在M.oryzae入侵早期,OsbHLH6被誘導表達并競爭結合到JA信號抑制子OsJAZ的靶蛋白OsMYC2上,隨后激活JA信號,并阻止TGAs激活SA信號。當M.oryzae入侵超過24 h后,OsbHLH6和被病原菌誘導表達的OsNPR1在細胞質中互作,并無法進入細胞核中激活JA信號,最終解除了JA對SA的抑制[47]。該研究對揭示SA和JA動態調控水稻抗性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GA和ABA是一對在植物生長發育過程中起拮抗作用的激素。GA能促進植物開花、莖的伸長和種子萌發,而高濃度ABA抑制植物莖的伸長、種子萌發,并通過誘導腋芽休眠對干旱、低溫等非生物脅迫做出應激反應[48-50]。在GA信號路徑中,GID1和SCFSLY1/GID2復合體共同促進DELLA的降解,緩解DELLA對GA的抑制[51-53]。在ABA信號路徑中,受體二聚體PYL/PYRs/RCARs識別ABA后以單體的形式和蛋白磷酸酶PP2Cs結合并伴隨SnRK2s的解離,SnRK2s通過磷酸化下游ABF和AREB等轉錄因子誘導ABA應答[49]。2015年萬建民研究組確定赤霉素和脫落酸之間的拮抗機制受SnRK2-APC/CTE的調控。SnRK2s被ABA激活后通過磷酸化修飾分蘗抑制基因(Tiller Enhancer,TE)抑制其編碼的APC/CTE的活性,同時干擾TE和ABA受體OsPYL/RCARs的相互作用,解除APC/CTE對OsPYL/RCARs的降解,并通過正反饋機制進一步增強ABA信號;此外,當植物感知到GA信號時,SnRK2s被抑制表達并促進OsPYL/RCARs的降解,從而干擾ABA信號的傳導[54]。近日,萬建民研究組發現高水平GA可通過促進APC/CTE介導的MOC1或OsSHR1的降解,抑制水稻分蘗或根的生長,低水平GA可以在根分生組織中激活APC / CTE以促進根的生長。而ABA可拮抗GA介導的APC / CTE降解路徑,并通過SnRK2-APC/CTE樞紐穩定MOC1或OsSHR1,從而維持分蘗或根的生長[55]。APC/CTE介導的ABA和GA拮抗機制的不斷完善對改善水稻株型提出了新的育種思路,在GA和ABA交叉調節路徑中或許可以通過適當增強植物ABA信號來促進根系生長和分蘗數的增加。
2.3 生物脅迫調控基因
分別由稻瘟病菌(Magnaporthe oryzae)、稻黃單胞菌稻生致病變種(Xanthomonasoryzaepv.oryzicola,Xoc)和稻黃單胞菌水稻致病變種(Xanthomonas oryzaepv.oryzae,Xoo)引起的稻瘟病、細菌性條斑病和白葉枯病是造成水稻產量和品質損失的三大病害[56-57]。目前,水稻病害的防治多以噴施化學藥劑為主,農藥的殘留和蓄積不僅會影響作物的生長發育、造成土壤污染,同時還會給人們的健康帶來隱患。因此,培育并應用廣譜抗性品種是替代化學防治的有效措施。
全面了解水稻和病原菌的相互作用,尋找主效抗病基因是研究水稻抗病機制的關鍵。目前,科研工作者已經克隆了大量的水稻抗性基因并進行了功能鑒定。其中包括Pi2、Pita、Pib、Pigm和bsr d1等28個抗稻瘟病的主效基因以及Xa1、Xa10、xa13、xa25和xa41等11個抗白葉枯病的主效基因[58-60],并鑒定出13個抗條斑病的主效數量性狀位點(Quantitative trait loci,QTL),其中位于5號染色體上的qBlsr5a可以解釋表型變異的14%[61-62]。異源表達玉米抗性基因Rxo1的水稻對條斑病的抗性顯著提高[63-64]。
由于Magnaporthe oryzae、Xoo和Xoc生理小種的多樣性,尋找特異性和非特異性廣譜抗病基因是育種工作的重要目標。編碼硫胺素合成酶基因OsDR8通過促進維生素B1的積累正調控水稻對Xoo和M. oryzae的抗性[65]。轉錄因子OsWRKY45-1表達時產生的小RNA會抑制ST1的表達,從而負調控水稻對Xoo和Xoc的抗性;OsWRKY45-2表達時沒有小RNA的產生,從而正調控水稻對Xoo和Xoc的抗性[66-67]。沉默OsHDT1顯著提高水稻對Xoo和M. oryzae的抗性[68]。E3泛素連接酶OsPUB15與Pid2互作激發植物細胞超敏反應(Hypersensitive response,HR)和基礎免疫應答,從而正調控水稻對M. oryzae的抗性[69]。OsMPK15通過抑制PR基因的表達和活性氧的爆發負調控水稻對Xoo和多個M. oryzae生理小種的抗性[70]。秈稻地谷對1 000多個M. oryzae生理小種具有較強的抗性,這種廣譜抗性是由其3號染色體上的bsrd1介導的。bsrd1的啟動子可以和MYBS1緊密結合且被抑制表達,并進一步抑制過氧化氫酶的活性阻止H2O2的降解,從而提高地谷對M. oryzae的抗性。近日,陳學偉研究組[71]發現地谷bsrd1表達量的降低會上調OsMYB30的表達,OsMYB30作為水稻對M. oryzae抗性的正調控因子,直接結合Os4CL3和Os4CL5的啟動子并誘導其表達,促進木質素在細胞壁的積累,提高了水稻對M. oryzae的抗性。此外,研究表明攜帶多個抗性基因的品種往往具有更強的廣譜性,比如攜帶Pi2/Pi1或Pi2/Pi54的品種對M. oryzae的抗性遠遠高于單基因系水稻品種,含有Pi9/Xa23或Pi54 / Xa21的品種可以同時提高水稻對Xoo和M. oryzae兩種病原菌的抗性[72]。
植物和病原菌互作通常會觸發激素的生物合成和信號傳導等防御反應[73]。促植物生長激素(如生長素和赤霉素)的積累往往是水稻容易受病原菌入侵的易感因素,而抑制生長的激素(如水楊酸和茉莉酸)則是提高植物抗性的因素[74]。例如,OsHsp18.0CI通過激活JA和SA信號路徑相關基因的表達正調控水稻對Xoo的抗性[75]。OsBGLU19通過激活OsAOS2等JA信號路徑相關基因的表達正調控水稻對Xoc的抗性[76]。小肽激素PSK候選受體OsPSKR1通過激活OsPR1a、OsPR5等SA信號路徑相關基因的表達正調控水稻對Xoc的抗性[77]。和野生型相比,SLs缺陷型突變體d17和d14的細胞壁合成基因被抑制表達,同時H2O2和可溶性糖含量明顯降低,對M. oryzae敏感性增加,表明SLs可能通過調節細胞壁防御、過氧化氫酶活和糖代謝等途徑正調控水稻對M. oryzae的抗性[78]。但這種廣義概念也有例外,比如GH3-8通過催化生長素-氨基酸復合物的形成抑制生長素的積累,從而保護植物免遭由于細胞壁防御能力下降受到的損傷,介導了依賴于生長素信號路徑的抗病機制[73]。BRs信號路徑相關基因OsSERK2不僅可以改良水稻株型還可提高水稻對Xoo和M. oryzae的抗性[79]。
植物細胞壁由纖維素、半纖維素、胼胝質、果膠、木質素等組成,是阻擋病原菌入侵的天然屏障[80]。超量表達OsSUS3可以促進細胞壁多糖和胼胝質的沉積,降低纖維素結晶度和半纖維素中阿拉伯糖的比例,并以此提高水稻對Xoc的抗性[81]。PGs是一類Xoc在入侵初期分泌的能夠降解植物果膠、軟化細胞壁的半乳糖醛酸酶[82],并能夠正調控Xoc在水稻上的致病力[83]。為了防止病原菌對細胞壁的降解,植物會通過誘導多聚半乳糖醛酸酶抑制蛋白PGIPs的積累來抑制PGs的活性,緩解PGs對植物細胞壁中多聚半乳糖醛酸的水解[84]。水稻基因組編碼7個PGIP蛋白,其中OsPGIP1、OsPGIP4和qBlsr5a定位于5號染色體上的同一區間,但對于OsPGIPs是如何介導水稻對Xoc的抗性還知之甚少。2016年丁新華研究組首次鑒定了OsPGIP4通過誘導OsAOC和OsAOS等JA信號通路相關基因的表達增強水稻對Xoc的抗性,并利用 RNAi 技術對OsPGIP4進行抑制表達顯著降低了攜帶qBlsr5a的中抗品種Acc8558對RS105的抗性,進一步證實了OsPGIP4可能參與qBlsr5a介導的水稻對Xoc的數量抗性[62]。近日,該研究組又揭示了OsPGIP1介導的水稻對Xoc的抗性依賴于植物細胞壁的先天免疫能力和JA信號通路的激活。研究發現不同于OsPGIP3、OsPGIP5、OsPGIP6和OsPGIP7,OsPGIP1被Xoc生理小種RS105誘導后表達量顯著上調,并通過轉錄組分析進一步證實沒有病原菌入侵時OsPGIP1超量表達轉基因植株和野生型植株基因表達無明顯差異,但RS105會顯著誘導OsPGIP1超量表達轉基因植株JA的積累和編碼細胞壁纖維素合酶基因OsCesAs、木質素合成相關基因OsPALs等的表達,揭示了OsPGIP1介導的防御反應依賴于PGIP-PGs復合體的形成。同時,超量表達OsPGIP1不影響水稻農藝性狀,是抗性品種培育過程中可選擇的優質基因[83]。
2.4 非生物脅迫調控基因
冷害、高溫、干旱和土壤鹽堿化等非生物脅迫是限制水稻生長的重要因素。植物通過調節自身的生長發育來適應環境的變化[74],比如可通過基因差異表達、改變酶活、降低氣孔導度和激活激素信號通路等應對非生物脅迫。因此,確定關鍵的遺傳決定因素、提高作物的抗逆性對滿足水稻生產需求具有重要意義。
低溫會影響水稻過氧化氫酶的活性和代謝平衡,甚至會導致種子休眠,嚴重影響水稻的生長發育。類受體激酶CTB4a與ATP合酶β亞基AtpB相互作用,并通過提高ATP合酶活性和ATP含量正調控水稻在低溫脅迫下的結實率和產量[85]。OsMADS57和OsTB1產生相互作用并共同介導水稻對低溫脅迫的抗性。在低溫條件下,OsMADS57和OsTB1共同與OsWRKY94的啟動子結合并促進其轉錄,同時解除對D14的抑制,最終提高植物抗寒性并抑制分蘗的形成;在常溫條件下,OsWRKY94和D14被抑制表達,植物分蘗正常形成[86]。黃榮裕研究組發現在籽粒發育過程中,LGS1的表達提高了籽粒灌漿率,增加了籽粒長度和胚乳細胞數,正向調控水稻產量;同時,LGS1轉錄本在低溫下的積累又提高了水稻幼苗的抗寒能力[87]。儲成才研究組發現水稻在孕穗期遇到低溫脅迫時,粳稻9號染色體上的bZIP73Jap和bZIP71形成的復合體可通過抑制OsNCED3和OsNCED5等ABA合成基因的表達降低ABA水平,同時過氧化氫酶活性的增強加速了H2O2降解,最終提高水稻對低溫的適應性。在生殖生長階段,二聚體的形成激活了抗低溫主效QTLqLTG31Nip、單糖轉運基因OsMST7和OsMST8的表達,并促進葡萄糖、蔗糖等向花粉的輸送,從而提高水稻種子在冷脅迫條件下的結實率[88]。種康研究組發現低溫顯著誘導OsCYP202的表達,OsCYP20-2通過在葉綠體和細胞核中招募不同的靶蛋白來協調植物生長和對低溫的耐受性。位于葉綠體中的OsCYP20-2通過靶向OsFSD2加速細胞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清除,增強水稻對低溫的抗性;同時,位于細胞核中的OsCYP20-2通過降解SLR1解除DELLA蛋白對植物生長的抑制,從而保證植物在低溫環境中的正常生長[89]。
高溫脅迫會破壞植物細胞膜的流動性和蛋白質穩定性,植物通過誘導熱激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HSPs)的積累提高自身蛋白質正確折疊的效率,從而提高耐熱性[90]。HSPs按蛋白質分子量可分為小熱激蛋白(small heat shock proteins,sHSP)、HSP60、HSP70、HSP90和HSP100五個家族,sHSP是一類不依賴ATP有助于提高蛋白質正確折疊率的伴侶蛋白[91]。近日,張恒木研究組發現超量表達OsHSP20促進水稻種子萌發和根系伸長,并明顯提高水稻對高溫和鹽脅迫的適應性[92]。林鴻宣研究組從突變體aet1中成功克隆編碼tRNAHis鳥苷轉移酶基因AET1,AET1與兩個靶蛋白RACK1A和eIF3h共同調控生長素應答因子OsARF23和OsARF19 的翻譯效率,從而提高水稻對高溫的耐受力[93]。劉建祥研究組發現OsbZIP74參與調節OsNTL3介導的應激反應。OsbZIP74前體蛋白bZIP74P定位于內質網膜。OsNTL3前體蛋白NTL3P定位于質膜,可以感知熱脅迫時細胞膜流動性和完整性的變化,并將熱應激響應信號傳遞到細胞核。在高溫脅迫時,OsNTL3從質膜遷移到細胞核,OsbZIP74可變剪切產生bZIP74A并進入細胞核,誘導OsNTL3上調表達,OsbZIP74和OsNTL3協同調節水稻的耐熱性[94]。
干旱脅迫會造成水稻花粉敗育、氣孔關閉、光合速率和生長速率下降,是限制水稻產量的因素之一[95]。雖然已在水稻生產中大面積推廣節水灌溉,但總體運行成本過高、農業勞作人員接受程度較低,因此探究水稻對干旱脅迫的響應機制是利用分子育種技術提高品種抗旱性的關鍵。干旱脅迫會誘導ABA快速積累,水稻中超量表達ABA 合成基因OsNCED3會顯著提高葉片中ABA的含量,并增強過氧化氫酶和抗氧化酶的活性,最終提高水稻對干旱脅迫的抗性[96]。儲昭輝研究組發現OsDT11可通過降低氣孔導度減少水分的散失來提高植物的抗旱性。此外,在干旱脅迫條件下OsDT11可通過誘導BURP、GRAM和HVA22等基因的表達觸發植物對ABA信號的響應,并受ABA信號路徑上游基因OsbZIP23和Os2H16的調控[95]。OsASR2通過特異性結合到順式作用元件GT-1激活靶基因Os2H16的表達來提高水稻對Xoo和干旱脅迫的抗性[97-98]。近日,劉煒研究組發現干旱脅迫誘導OsESG1的表達,OsESG1抑制表達轉基因水稻過氧化氫酶活性降低,H2O2的積累影響了苗期根冠發育并導致H2O吸收速率下降,同時編碼生長素轉運體基因OsPIN1b、OsPIN2和OsPIN10a上調表達,說明OsESG1可能通過調節生長素的分配和運輸影響植物根系對干旱脅迫的適應性[99]。
全球約有6%的土地存在鹽堿化的問題。在高鹽脅迫下,高濃度Na+和Cl-在植物體內不斷積累極易產生二次脅迫,導致鹽離子中毒,甚至引發植物死亡[100]。水稻屬于非鹽生植物,對鹽脅迫表現出高度的敏感性[101]。水稻已經進化出多種適應性防御機制,以保護自身免受鹽脅迫的傷害,分離和鑒定鹽脅迫相關基因對培育耐鹽新品種具有重要意義。黃驥研究組發現,鹽脅迫會誘導水稻AP2和bHLH等80個轉錄因子上調表達,1 055個功能基因上調表達,1 030個功能基因下調表達,其中大部分生長發育調控基因下調表達,如SCL33(LOC_Os07g0633200)、NADPME2(LOC_Os01g0723400)和SAUR76(LOC_Os08g0452500)等[102]。研 究 表明在鹽脅迫下水稻中超量表達OsSTLK會降低氣孔導度減少水分蒸發,并通過增強超氧化物歧化酶、過氧化物酶和過氧化氫酶的活性減少ROS的積累,同時降低Na+和K+的比值以及MAPK磷酸化水平,進而增強水稻對鹽脅迫的抗性[103]。在鹽脅迫下,OsMPT3突變體增加了脯氨酸合成的前體谷氨酰胺的積累,降低了Ca2+、Pi、ATP、可溶性糖和脯氨酸的積累,同時增加了Na+和K+的比值,并對外源ATP高度敏感,該研究表明OsMPT3可通過調節植物細胞能量供應,并引起鹽脅迫下參與滲透調節的離子和代謝物積累的變化,正調控水稻的對鹽脅迫的抗性[104]。謝先芝研究組發現OsSRK1編碼非典型的S類受體激酶(S-receptor-like kinase),超量表達OsSRK1會提高水稻對ABA的敏感性,并通過促進葉原基細胞分裂增加葉片寬度,同時誘導OsMyb4、OsDREB1A、ZOS3和OsWRKY08等基因的表達提高水稻對鹽脅迫的耐性[105]。楊志敏研究組發現Na+/H+反向運輸蛋白OsNHAD介導鹽脅迫條件下水稻亞細胞Na+的穩態。OsNHAD抑制表達轉基因水稻對Na+敏感性增強,Na+在葉綠體中的積累導致葉綠素含量下降、光系統Ⅱ光化學效率降低、生長發育遲緩,而異源表達OsNHAD可以回補擬南芥突變體atnhd11鹽脅迫下生長異常的表型,說明OsNHAD 通過介導葉綠體中Na+的外排提高水稻對鹽脅迫的耐受力[106]。盡管水稻對鹽脅迫的耐受性受多個基因調控,但引入編碼關鍵效應蛋白的單基因可能會改善這一復雜的農藝性狀,超量表達OVP1可增加液泡膜焦磷酸酶和ATP酶的活性,從而為逆向轉運蛋白MHX提供質子驅動力并將Na+隔離在液泡中,減少了Na+對細胞質的損傷,最終提高了水稻對鹽脅迫的適應性和耐受力[107]。OVP1超量表達轉基因植株已經過研究者4年的田間試驗,其分蘗、產量等綜合性狀明顯優于野生型,OVP1可作為提高品種鹽脅迫耐受性的重要候選基因。
2.5 產量調控基因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我國對稻米的需求量也居高不下,不斷提高水稻單產滿足人們基本需求一直是育種工作者的首要目標。單位面積上的穗數、每穗粒數、千粒重和結實率是影響水稻產量的決定性因素[108]。隨著基因組測序和功能基因組學的發展,目前已經鑒定了多個調控水稻粒型、粒重、結實率的主效QLT,如GW2[109]、GS3[110]、GS2[111]。近日,高振宇和錢前研究組鑒定出TGW2也是調控籽粒大小的主效數量性狀基因,并通過與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抑制因子KRP1互作抑制水稻穎殼細胞分裂,最終負調控粒寬和粒重[112]。已鑒定的QTL主要通過影響小G 蛋白信號通路、植物激素水平的變化、MAPK級聯反應等來調控水稻細胞的伸長[113-114]。TGW6通過影響IAA-葡萄糖水解酶的活性來調節生長素的含量,進而影響水稻的產量[115]。MAPK級聯反應主要通過MAPKs激酶將磷酸化信號逐級傳遞到細胞核并引起防御基因的差異表達,從而介導植物的免疫反應,研究表明OsMKK4不僅影響植物抗性,還是MAPK信號通路和BRs信號通路交叉調節的關鍵因子,是水稻的株高、粒長、粒寬等產量影響因素的正向調控因子[116]。此外,在水稻中超量表達OsMKKK10也顯著增加了株高、粒重[117]。而GSN1通過對OsMAPK6去磷酸化修飾抑制MAPK級聯反應對產量的正向調控,是產量影響因素的負調控因子[118]。GS5通過促進細胞分裂和外稃的發育正調控籽粒大小[119-120],并且影響BRs信號的傳導。細胞分裂素主要分布于植物根分生組織、葉片、果實和種子等部位,能夠促進植物莖頂端分生組織的細胞分裂和細胞增殖[121]。OsCKX2主要在花器官中表達量較高,并通過抑制細胞分裂素在植物體內的積累,負調控水稻的粒數,從而降低水稻的產量[122]。DST等位基因DSTreg1通過抑制OsCKX2的表達,緩解細胞分裂素的降解,從而促進水稻籽粒的伸長和產量的提高[119,122]。
OsmiR156[123]、OsmiR397[124]、OsmiR396[125]和OsmiR408[126]等均參與調控水稻生殖生長。謝先芝研究組[127]發現OsmiR530是潛在的產量調控因子,OsPIL15通過與OsMIR530啟動子的順式作用元件結合促進OsMIR530在細胞核內的轉錄,OsmiR530的積累抑制了下游OsPL3的表達,并進一步抑制小穗穎殼的細胞分裂從而負調控水稻產量。分蘗角度在水稻育種中可作為培育理想株型以提高產量的主要目標性狀之一,可塑性較強。miR167在不同植物中高度保守[128],吳昌銀研究組[129]發現OsmiR167a可以通過抑制生長素應答基因(OsARF12,OsARF25,OsARF17)的表達來增大水稻分蘗夾角,并且這種調控依賴于HSFA2D和LAZY1介導的生長素不對稱分布途徑。
主莖和分蘗的均勻生長不僅是影響水稻株型和產量因素之一,還能確保同步成熟便于收獲,DWT1是這一性狀的關鍵調控因子,DWT1的突變導致水稻頂端優勢增強并引起矮化現象[130]。梁婉琪研究組[131]發現DWTI及其同源蛋白DWL2均可與磷脂酰肌醇單磷酸激酶OsPIP5K1在細胞核內互作,并促進OsPIP5K1和其產物磷酸肌醇第二信使PI(4,5)P2在細胞核內富集,OsPIP5K1突變后使dwt1突變體的頂端優勢消失,即DWTI是通過影響OsPIP5K1和磷酸肌醇信號通路共同調控水稻的均勻生長。
2.6 品質調控基因
淀粉含量、蛋白質含量、氨基酸含量、堊白等是評價水稻營養品質和外觀品質的重要指標[132],高產與優質一直是科研工作者力求兼得的兩個育種目標。稻米的質量取決于品種、生產和收獲條件、采后管理、碾磨和貯藏條件等。利用組織特異性Oleosin-18啟動子和RNAi技術沉默表達LOX3延長了稻米貯藏期,減少了營養損傷,同時還不影響水稻的產量[133]。目前,市場上最受歡迎的是長粒、白色透明的稻米。GIF1在自身啟動子的驅動下持續表達導致水稻產量增加,而在Waxy啟動子的驅動下表達GIF1則會導致水稻小粒的產生[134]。在水稻中超量表達OsmiRNA397抑制了OsLAC的表達,并增強了水稻對BRs的敏感性,產生了比野生型更多的分蘗,籽粒也顯著增長[135]。超表達GW7促使籽粒變長變窄,從而改善水稻籽粒的外觀品質,GW7啟動子可與GW8編碼的OsSPL16直接結合并被抑制表達,最終負調控水稻的產量[136]。雖然堊白不會影響稻米的口感,但是消費者在購買稻米的時候會更傾向于堊白度低的品種,溫度、土壤肥沃程度、土壤含水量都是影響堊白產生的因素之一[137]。Chalk5編碼液泡膜質子轉運焦磷酸酶,超表達Chalk5導致蛋白質合成受阻,胚乳堊白率顯著增加[138]。備受歡迎的泰國香米因含有2-乙酰-1-吡咯啉(2-acetyl-1-pyrroline,2-AP)而具有獨特的香氣。OsBADH2則是影響2-AP合成的關鍵基因。在普通品種中,OsBADH2氧化2-AP的前體,進而抑制2-AP的合成。但在類似泰國香米等具有獨特氣味的品種中,OsBADH2的突變解除了對2-AP合成的抑制作用[139]。
水稻營養成分包含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纖維素等,蛋白質含量約占籽粒干重的7%,淀粉含量約占籽粒干重的80%[137]。RSR1[140]、OsBP5[137]、OsbZIP58[141]等都是影響籽粒淀粉含量的關鍵基因。近日,萬建民研究組[142]發現在水稻中異源表達玉米GLK基因可使植物葉綠素得到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在田間的光合效率,經多代穩定繁殖后產量可提升30%-40%,糖、淀粉以及氨基酸等代謝物的含量也明顯高于野生型。錢前研究組[143]鑒定到OsMADS6等位基因突變體afg1,AFG1的功能突變導致水稻籽粒變小,總淀粉和直鏈淀粉含量降低,蛋白質和可溶性糖含量增加,對水稻產量和品質具有重要影響。
3 展望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稻為先。水稻養育著我國60%的人口,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作物。因此,提高水稻單產仍是未來育種的首要目標。當前,我國不僅面臨人口不斷增加、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局面,還存在農業生產和環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現代稻作生產過程中生物脅迫或非生物脅迫等因素限制了水稻品種的增產潛力,雖然商業化肥和農藥的投入在短時間內可以改變這一窘境,但依靠化肥和農藥助力水稻生產不僅違背了綠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也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長久之計,因此利用分子育種技術培育綜合性狀優良的新品種是未來水稻研究的重點發展方向。此外,對水稻基因進行改造的同時不能只注重單一性狀的改良。比如超量表達OsNPR1雖然會提高水稻的抗性,但卻以犧牲水稻的正常發育為代價[144]。因此,像IPA1理想株型基因的發掘和在“嘉優中科”的應用就很好的化解了生長和防御不可兼得的矛盾[3]。位于3號染色體上的bsrd1未與任何農藝性狀調控基因有連鎖關系,對bsrd1的利用可在不影響水稻品質的前提下提高對Magnaporthe oryzae的抗性[72]。上文介 紹 的NGR5[16]、OsPGIP4[83]、OsALDH2B1[41]等都是品種培育過程中可以兼顧多個性狀改良的優質“候選者”。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滿足人們對水稻品質的多樣化需求、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成為市場新導向。除了生產者關注的高產、高抗等性狀,消費者也越來越注重稻米的外觀品質和營養品質。近年來,隨著水稻基因組序列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利用轉基因等技術對水稻品質進行了改良,比如集高抗、高產、優質于一身的“中科”系列品種就是良好的成果[145],還有利用TALEN靶向基因敲除技術對OsBADH2進行功能突變,在短時間內即可獲得2-AP含量較高的水稻品種[146]。但目前最大的挑戰是世界范圍內消費者對轉基因技術的質疑。因此,稻米安全性的監督和評價應該更有力、更透明,同時在育種過程中還可利用組織特異性或誘導型啟動子減少基因持續表達對水稻的影響。
科學研究的最終意義是為國所用、為民所用。基因組技術的不斷發展為我們挖掘更多農藝性狀調控基因提供了技術支撐,但水稻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于功能基因的鑒定,如何將科學技術轉化成為民所需的第一生產力才是科研工作最關鍵的一環。將雜交育種技術、分子育種技術和現代化信息技術相融合,加速發展可持續、現代化水稻生產,培育營養高效、高抗、高產等綜合性狀優良的品種成為新時代的重要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