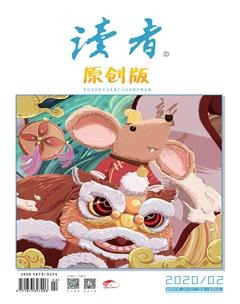我死皮賴臉,還是喜歡
2012年冬季的某夜,我和打算共同創業的同班女生一起,推著一輛裝有制作蘭州小吃“雞蛋牛奶醪糟”所用食材的玻璃柜子的電動三輪車,到達我的大學附近的小吃街邊,開始當天的課后營業。
生意很是慘淡。初創小業,選料一定是精挑細選,利潤也自然微乎甚微,且因為地域口味不同,兩個禮拜過去了,我們連200元的凈利都沒賺到。我繼續吆喝,同伴已經無心戀戰。她告訴我,高我們一級的薛胖子此時正在學校小禮堂里演出他們新排的話劇,雖是贈票,但也是座無虛席。我問她是否想去看,她沉默一下,說:“沒事兒。”
蜀地的冬寒自腳底透上身來,這時的我多希望能再來幾位客人,好打發走心中的不甘。
熬過新年,迎來畢業季,我們的小吃攤位草草收場,大家開始專心于畢業作品,已然畢業的薛胖子卻在小吃街盤下一間鋪子開了家私房菜館。出乎預料,所有喜歡薛胖子的老師都以為他會奔赴遠方,投身于導演事業,但同班女生轉述他的話說:“再喜歡也不能讓自己累著。”

比我更羨慕、嫉妒或者鄙夷薛胖子的大有人在,其中很多人選擇去了北京,他們懷揣夢想,低著頭、貓著腰試圖鉆進中國影視圈子里。可惜,中國電影市場只紅火了三四年,便像熱鍋一下子端進雪地里,降了溫。寒冬可不是一個對新苗子們友善的季節。大前年年初的某一夜,我寄宿在北漂同學的“隔斷房”里,問他:“你還打算在編劇這行干多久?”他說:“沒想過。”我說:“眼下你得想一想了,也不能一直拿5000塊過活吧。”他說:“那沒關系。我還是喜歡電影,死皮賴臉地喜歡。”
還是喜歡,多么卑微,又多么決絕。
寄宿北漂同學家時,我正跟隨一位編劇劉哥在北京接活兒。在這個圈子里,他在人脈交際上并非左右逢源,甚至有點兒用力過猛。每次與制片方交流時,他都會表現出比能力更豐沛的行業熱愛感,同時,也要求我盡量用最專業的詞匯來闡述劇本,給對方一個好印象。一切談罷,他甚至會借故避開我,從自己的雙肩包里掏出兩包老家產的茶葉塞進對方懷里。
“不害人,能賺錢,怎么活都不為過。”劉哥拉上背包拉鏈,在電梯里對我說,“再努力一把吧,我不想有一天會恨自己。”
再之后,我慢慢聽說,薛胖子將私房菜館辟出一半,建了間微電影工作室,迎來送往一屆屆學弟學妹;北漂同學搬出隔斷房,去了更遠的城中村,但對工作依舊沒有半句怨言;劉哥在朋友圈里日日為他人的電影轉發、點贊,卻對自己接的活兒只字不提,我知道,他對那幾十頁劇本永遠不滿意。
一個人,對一件事到底能有多喜歡?大約就是那種寧可死皮賴臉,也想從它身上嘗一筷頭兒甜的心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