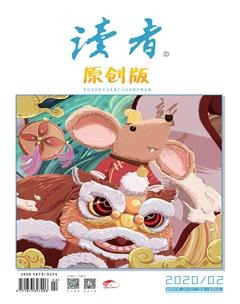芫荽
南在南方
幾個朋友圍著火鍋正吃得酣暢,一位朋友忽然勃然不悅,離席而去,為何?后來才曉得,禍首竟然是一撮倒在湯鍋里的香菜!
香菜這種吃的,有人嗜之如命,有人恨之入骨。恨它的說它有肥皂味,有金屬味,有臭蟲味,因此成立了“世界反香菜聯盟”。
我喜歡吃香菜,總覺得它跟許多食材搭配,恰如一句詞,“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許多作物,在我老家陜南還是舊稱,比如,紫蘇,叫荏;高粱,叫秫;香菜,叫芫荽。都有些古風在。
一般,芫荽秋天種。種子堅硬,得破開。《齊民要術》說:“欲種時布子于堅地,一升子與一掬濕土和之,以腳蹉,令破作兩段。”一般人家種不了那么多,種子放在碗里,用短木棍按住搓開兩半就好了。芫荽可以單獨種,隨便撒點兒在地頭上,一場雨后芽兒就出了地面。許多作物長出地面,都是兩片葉子相對著,有點兒像是鼓掌,只是芫荽的兩片葉子纖細,不似豆子的肥壯。奇怪的是,這兩片葉子邊緣平整,不像長大之后卻是齒輪樣的。
芫荽有兩種,一種矮個子,一種高個子。高個子不香但產量高,如果不是要賣,都喜歡種矮的來吃。
芫荽的吃法,不外乎提味調色。味以入冬最佳,單純清楚,到了春天好像就有點兒含混。大雪落下之前,得用玉米稈苫住芫荽,即便如此,它依然被凍得鼻青臉腫,香味卻還在。祖母常常著我去挖點兒芫荽回來。我掀開玉米稈挖,連紡錘形的根兒一起挖回來,祖母洗了,放在石窩里搗得茸茸的,來一勺羊肉湯自不用說,或者只是就著白餅吃,有沒有它,不可同日而語。
熬好的凍肉將凝未凝時,放幾根芫荽進去,等凍好了,快刀切來裝盤上桌,那點兒綠,真是奪人心魄。
羊肉泡饃是陜西名吃,在我看來,最妙的卻是吃完泡饃之后的那一碗清湯,上頭浮著一些芫荽末兒,一碗下肚,剛剛吞下的肉的肥膩一掃而去,如“歸人有清水可以洗塵”一般。
好久以前看過一篇文章,有一位在南方開蘭州拉面館的師傅,端的好手段,十根手指如同蠶吐絲,一時食客如潮,只是這位師傅堅持給拉面里頭放芫荽末兒,認為這才是正宗。不吃怎么辦?寧可不賣面……結果呢,文章說許多不吃香菜的人慢慢開始吃香菜了。這可能有點兒想當然,科學家研究發現,不吃香菜的人其實是基因作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
知堂先生《五十自壽詩》里頭有一句:“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當時覺得奇怪:為啥羨慕別人吃大蒜呢?后來才曉得好多人不吃大蒜。前幾天又看到他《八十自嘲詩》有一句:“對話有時裝鬼臉,諧談猶喜撒胡荽。”也有疑問,撒胡荽到底是啥意思呢?

就上網查,結果看到一條兀自大樂。文章出自北宋僧人文瑩《湘山野錄》,大意說的是:有位姓李的人種芫荽,當地民俗講究種芫荽得說下流話,不然長不好。可這位李老兄是個讀書人,如何說得出口。正好來客了,他讓兒子繼續種,兒子更說不出口,只念叨:“照我爹說的來。”這般,讀書人說下流話,有了專門的指代:撒芫荽。
古人有許多奇談,比如許多老書里頭說,把鱉剁碎,倒在莧菜下面,說能長出小鱉。這么不可能的事,卻有一個人在書里說:驗之可矣!
這兩天買了幾本二手書,有一本是黃苗子的,又看到一則好玩的,說種芝麻得夫婦同種,方才繁盛,他引了唐人葛鴉兒一首詩:“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不見歸。”
如果不知道這個風俗,這首詩的動人之處好像還差點兒什么。
我從老家帶了點兒芫荽籽兒,種在陽臺上的盆子里,盆子不大,實在不夠一吃。可是每年都要種,來年等它開花,花是傘狀的,細細的白白的,等它老了,收點兒種子。有一回,我把幾顆芫荽籽兒放在手心,三歲小兒湊過來,就讓他聞聞。
“這是啥?”
“香菜!”
他脆生生地回答,不過,他眼里好多疑惑,那些枝枝葉葉怎么變成細微小籽兒?還是香的?實在太可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