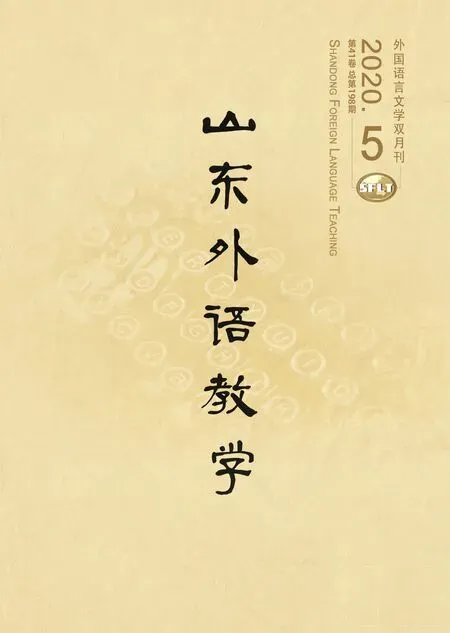晚清翻譯社會功能實現的漸進過程探析
王軍平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語言文學學院, 山東 威海 264209)
1.0 引言
翻譯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鑲嵌在整個人類社會活動的大場景中。對翻譯活動社會性的考察有助于凸顯其復雜性,加深我們對翻譯現象和翻譯過程的認識,同時也符合翻譯研究本身發展的需要。然而,在歷史上長期占據主導的語言學研究范式當中,翻譯的社會屬性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對影響翻譯的社會性因素的探討也一直未能有效展開,就連“翻譯活動是一種社會行為和現象的實踐本質”(胡牧,2006:50)這樣似乎不言自明的認識,也被大多數人忽略掉了。可以說,“長期以來,人們對翻譯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種天真的假設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個假設就是翻譯活動是在真空中從事的;文本創作也是在沒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擾下進行的;語言是透明的、工具性的(而不是主體性的);譯者也是價值中立的、是公允的……”(呂俊,2001:190)。若被這些“天真的”預設前提所遮蔽,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各種社會要素便無法引起重視,人們也就無法“透過符號和符際轉換現象看到活動諸環節的社會本質”(胡牧,2006:50)。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突破了這種相對單純的“假設”,令“人們的眼光從翻譯內部轉向了翻譯外的社會語境”(周領順,2018:98),使翻譯被看成是各種文化因素干涉和控制下的“改寫”(Rewriting)和“操縱”(Manipulation)(Lefevere, 2004)。文化轉向之后,有學者開始倡導翻譯研究的“權力轉向”,關注翻譯實踐背后的權力運作以及意識形態問題,研究的主題涵蓋了后殖民問題、性別問題、對國家身份及認識的操縱、譯者完全中立性的錯覺等(Tymoczko & Gentzler,2002)。面對這些研究,有學者敏銳地指出“這(些研究)里面所涉及的主題,社會(學)方面的至少與文化方面的是一樣多的”(Chesterman,2006:10,筆者譯)。的確,從研究所涉及的要素來看,勒弗菲爾等所提到的贊助人以及相關專業人士等與譯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已經具有典型的社會性特征了。實際上,過去二十多年,翻譯口筆譯研究業已開始經歷“社會(學)轉向”(Wolf,2012;Angelelli,2014)。
近幾年,國內學者也比較集中地開始了對翻譯社會功能的研究。王東風(2019)將翻譯活動與社會演變進程相聯系,對自漢唐以降翻譯之于歷朝國運興衰的影響進行了宏觀的勾勒。此外,作為對“五四運動”百年的紀念活動之一,《中國翻譯》在2019年第三期以“翻譯與五四運動”為專欄刊發了許鈞(2019)、王寧(2019)以及王東風、趙碬(2019)等學者的三篇文章,集中探討了翻譯活動之于五四運動的推動作用、意義和影響,展示出翻譯所具有的社會功能。
就翻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來看,翻譯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是人類社會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緊密相關。翻譯能夠對社會產生影響,而社會需求則是翻譯活動生發的內在驅動力。基于此,我們聚焦于晚清這一特定的背景,考察社會需求如何激發出相應的翻譯需求,嘗試對翻譯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及翻譯社會功能的實現過程進行探索與發掘。
2.0 晚清翻譯的社會功能及其實現
翻譯的最初形式是口譯,其功能是為了滿足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需求。換言之, 翻譯自出現之日起,就是為了服務社會的。《禮記·王制》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轉引自陳福康,2010:2)。由此可見,人們之所以需要翻譯,其根源就是“言語不通”;操不同語言的人彼此無法進行溝通和交流,因此“志無以達,欲無法通”,社會關系的建立也就無從談及了。只有逾越語言的障礙,人們才能進行相應的社會活動,并在社會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西方流傳甚廣的關于翻譯起源的“巴別塔”的故事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翻譯的社會功能:來自四方的民眾,因為被上帝變亂了語言,彼此之間無法溝通,其直接后果就是整個人類再也無法修筑起“通天”的“巴別塔”了。透過這些記載與傳說,我們不難看出翻譯所具有的基本社會功能。當然,前面所言主要針對口譯,而如果將筆譯也納入討論,翻譯的社會功能將進一步得到增強和擴充。
翻譯的目的是為了方便人們進行思想交流,促進彼此的文化互通,從而促進某種社會關系的建立和形成。翻譯所具有的這種社會功能使其獲得了特有的社會價值。許鈞曾對翻譯的社會功能及其價值做了宏觀的概括,他認為“翻譯的社會價值,是由翻譯活動的社會性所決定的,主要體現在它對社會交流與發展的強大推動作用”(許鈞,2004:35)。概而觀之,翻譯的功能可謂林林總總,但晚清時期社會背景的特殊性使得翻譯的某些社會功能(如娛樂功能、審美功能,甚至是商業功能等)因為社會需求強烈程度不夠或社會動員力量不足而退居次席,而翻譯傳遞新知、啟蒙思想和推動社會變革這三個方面的功能得以凸顯。為了便于探究特定背景下社會需求與翻譯活動的互動關系,我們暫且不談那些位居次席的功能,而僅僅以上述三大功能為主進行討論。當然,這三個方面的劃分也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因為知識的傳遞肯定會具有思想啟蒙的作用,思想的啟蒙勢必會帶來社會的變革,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常識。我們之所以這樣區分,主要是為了能更好地呈現翻譯功能實現的具有漸進性的具體過程。
2.1 傳遞新知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通過勞動而建立的生產關系。社會生產讓人們產生了分工合作、互通有無的需求,而這類溝通的媒介便是語言。當只在語言相通的場景下進行的社會活動不再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時,翻譯便應運而生了。如果我們將這看成是翻譯的社會性起源,那么隨著人類社會的高度發展,翻譯也逐漸在不同社會和文化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
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于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生產力提高的前提是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科學技術是人類知識積累的形態之一。由于各種原因,科技發展在不同的社會并不均衡,其外在的表現就是社會生產能力的差異。當生產能力低下的社會不能滿足其成員的生產生活需求時(正所謂“窮則思變”),就有必要向其他的社會學習先進的科技知識,而學習的首選捷徑就是翻譯。通過有選擇的翻譯,先進的源語社會知識、技術和管理思想等得以迅速地被引入目的語社會,給目的語社會注入新的活力,促成其生產力的急劇提高。
跨語言的知識傳遞可以說是翻譯社會功能最直觀的體現。晚清時期,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后,通過翻譯來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知識成為了以洋務派為代表的中國仁人志士的一致選擇。曾經的“老大帝國”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鴉片戰爭讓整個中國陷入了被動挨打、任人宰割的屈辱境地。面對國土淪陷和西方列強在政治經濟上的重重壓迫,“廣大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與此同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開明官紳開始倡導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試圖通過‘師夷長技以制夷’策略,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馮志杰,2011:10)。在統治階級看來,戰爭的失敗,首先歸結于科學技術的落后;而要挽狂瀾于即倒,就要取得軍事力量上的優勢,自強御辱。為達此目的,第一要務就是增強對西方的了解,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于是,翻譯就在這個國家危亡的時刻,承擔起傳遞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知識的社會責任。這也構成“近代早期翻譯活動的主要對象是科學技術著作”(同上:31)這一主要特征。由于特定的社會需求構成的強大的翻譯動力,科技書籍的翻譯活動在晚晴時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翻譯對象包括天文學、數學、博物學、地理學、醫學等各領域的著作。
從翻譯史上來看,國人的科技翻譯活動最早始于明朝萬歷年間。徐光啟與傳教士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科學書籍,可視為科技翻譯之肇始,但這與后來由洋務派推行的翻譯活動,從社會動因上來講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馮志杰通過對比研究后提出,“利瑪竇時期的翻譯活動缺少社會動力。正是由于缺少社會性,因而后繼乏力,未能得到應有的發展而中斷”(同上)。但不管出于何種目的,對科學技術知識的介紹成了此類翻譯的主要任務。明朝的科技翻譯與晚清時期的科技翻譯活動共同構成了中國翻譯史上的“明清科技翻譯”熱潮。以晚清為例,為了滿足對西方科技知識的需求,清政府專門建立了一批翻譯出版機構,如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等,改變了以往只有西方教會翻譯出版西學圖書的局面。翻譯機構的成立極大地提高了翻譯的速度和效率。據不完全統計,自1840年至1898年,共計有569種圖書被翻譯出版(不含收錄的5種宗教圖書)(馮志杰,2011:36)。而僅洋務派直接領導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一家,從成立到解體的短短40多年間(1868-1912)便翻譯了241種圖書;其中得以出版的201種當中,179種都是科技圖書,未出版的40部也幾乎全部都是科技書稿。在器物層面對翻譯的重視是當時的一個突出特點。江南制造局的總辦馮焌光就曾指出,“槍炮火藥與輪船相維系,翻書與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圖,不可偏廢”(陳福康,2010:68)。馮氏所言基本代表了當時洋務派翻譯的指導思想。可以說,在洋務運動時期,翻譯呈現出一邊倒的對于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引進之勢,這無疑是源于當時的時代背景,迎合了人們了解和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社會需求。
翻譯作為不同社會或者國家之間知識傳遞的橋梁,極大地促進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具有傳遞科學技術知識、消減社會發展差異的基本功能。當然,翻譯的社會功能除了具體體現在器物層面的傳遞知識外——比如洋務運動中對科技知識的翻譯旨在利用西方的科技知識發展軍事力量、造船鑄炮、制造兵器,更重要的是對目的語社會的成員進行思想上的啟蒙和引導。所以說,知識傳遞只是翻譯最基礎的社會功能,知識傳遞對目的語社會成員產生的影響和教化,才是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源動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晚清的社會場域中,翻譯的另一個重要社會功能——啟蒙思想也開始顯現了出來。
2.2 啟蒙思想
甲午戰爭的失敗說明,僅依靠引進科學技術知識帶來的器物層面的進步并不能真正實現國家強大。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根基受到了殘酷現實的拷問,引導人們開始反思和總結。洋務運動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和先進的認識,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具有其局限性。馮桂芬是林則徐的弟子,作為最早提出“中體西用”的洋務派思想家和改良派先驅,他的看法頗能代表當時人們對西方的認識。馮氏在《采西學議》中就曾提到:“至西人之擅長者,歷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一二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如能探賾索隱,由粗跡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藍!”(轉引自陳福康,2010:66)從馮氏論斷中可以看出,國人對西人長處的認識僅限于自然科學知識方面,而且即便是這樣的長處,通過一點譯介,以國人的“智巧聰明”也會實現趕超。可以說,正是循著這樣的思想軌跡,洋務運動才會只重視器物層面,翻譯的對象也集中于西方的科技知識。馮志杰(2011:40)分析了洋務運動破產的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洋務派官員自身的近代化修養不足,沒有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建設對其經濟發展所起到的保障作用,在不對落后的政治制度進行變革的情況下單純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最終使洋務運動因缺乏政治保障而步履蹣跚。”
正是基于以上反思,有識之士才開始考慮變法維新,對當時的政治制度進行改良,包括設立議院、推行君主立憲等。而為了維新所做的前期準備,首先就是對西方先進制度和思想的學習。梁啟超在《論譯書》一文中點出“西人之所以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轉引自陳福康,2010:85),藉此呼吁加強對西方除兵書之外的其他重要書籍的翻譯。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開展,晚清翻譯活動開始承擔起啟蒙國人思想的重任。為了迎合這樣的社會需求,翻譯的內容就由“單純的科技翻譯擴展到社會科學翻譯和文學翻譯,開辟了翻譯的新境界”(馮志杰,2011:41)。
晚清翻譯活動啟蒙思想的社會功能,首先集中地體現在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著作的大量譯介,其次是對西方小說的譯介。對西學的譯介,就重要性而言,在近代幾乎無人能與嚴復比肩。當時國內積極反思洋務運動的失敗及教訓的人當中,可以說再沒有比嚴復更加深入和深刻的了。親身參與洋務運動、具有多年西方生活學習經歷的嚴復,準確地透視了中西文明之間存在的區別與差距的根源。在他看來,雖然甲午海戰的表現是在器物層面,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社會制度與國民素質。“國家猶如生物有機體,其優劣強弱與治亂盛衰取決于民力之強弱、民智之高下與民德之好壞。……中國欲圖富強,根本之圖在于從民力、民智、民德措手,收其長效之功”(皮后峰,2003:121)。為達此目的,嚴復提出了三條建議措施:一是禁鴉片,廢陋習;二是廢八股,學西學;三是廢君主,立憲政。而要實現上述目的,須對國人進行思想啟蒙和教育。譯入西方社會科學著作,讓民智得以開化、民德得以改造,嚴復身體力行。他充分發揮自身所學之長,翻譯了一系列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和《穆勒名學》,史稱嚴譯“八大名著”或“嚴譯八經”(王秉欽、王頡,2009),共約200萬字。“嚴譯八經”系統地將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介紹給了國人,在國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給國內民眾的思想啟蒙提供了直接的養分和智力資源。蔡元培評述,“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幾道為第一”(轉引自陳福康,2010:91-92)。此外還必須提及的是,作為維新運動領軍人物的梁啟超,雖然在具體翻譯實踐方面無法與嚴復相提并論,但在觀念層面對翻譯對象選擇的轉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批評了洋務運動中翻譯取向的不足,提出“‘中國官局舊譯之書,兵學幾居其半,’擇譯不當,并建議‘當以盡譯西國章程之書為第一義’,同時要求翻譯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等著作”(馮志杰,2011:44)。以梁氏當時的社會影響力,他這樣的呼吁和倡議無疑會極大地促進翻譯啟蒙思想的社會功能。
另一方面,晚清翻譯活動啟蒙思想的社會功能在小說領域中的發揮亦主要得益于梁啟超,以及其本人所掀起的“小說界革命”。戊戌變法的失敗極大地刺激了維新派人士的神經。梁氏在流亡日本的歲月里,親眼目睹了日本社會明治維新以后的繁榮和富足,試圖借鑒東瀛鄰國以及西方諸強的經驗革新中國社會。他這一階段的思考結果,大約可以從《譯印政治小說序》中窺見一二: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于小說。于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某名儒曰:‘小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陳平原、夏曉虹,1989:21-22)
以上便是梁氏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分析得出的富國強民之道,但這里的“小說”并非中國傳統的古典小說,而是來自泰西的新小說,其中尤以政治小說為代表。政治小說的社會功能被梁氏推到了思想啟蒙的前沿。對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他直言,“于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同上:23)。在這樣的改革思想指引下,他對小說改造社會的功能的論述不斷深化。1902年11月,梁氏創辦了《新小說》雜志,并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說法。文章開篇,他就點明了新小說的革新功能: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同上:33)
作為《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思想的進一步延伸,梁氏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將新小說的“地位抬得更高”,對其改造社會的功能的“論述力度也更大”(趙稀方,2012:76)。小說所具有的無限支配力得到了充分論述之后,就得考慮“新”小說的途徑了。在他看來,“新”小說的唯一途徑,就是翻譯;當時特殊的社會條件下,翻譯應擔當起“新”一國之小說,進而“新”民、“新”社會的重任。為了滿足思想啟蒙的需要,梁氏首先身體力行,翻譯出版了日本的著名政治小說《佳人奇遇》。雖然梁氏一直鐘情于政治小說,但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他所論述的范圍已經不限于政治小說了。事實上,“《新小說》雜志所刊登的既有‘論說’,又有翻譯與創作,既有‘政治小說’、‘歷史小說’,也有‘偵探小說’、‘科學小說’等”(同上)。通過“小說界革命”的輿論鋪墊,小說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其改造國民、改造社會的功能被凸顯出來,成為了整個社會求“新”的主要源泉。而新小說的來源主要是翻譯,此即為,翻譯啟蒙思想的社會功能假借新小說的軀殼,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出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文人輿論烘托下,林紓對西方小說的大規模譯介及其譯作“一時洛陽紙貴”般的受歡迎盛況,將翻譯啟蒙思想這一社會功能落到了實處。在《黑奴吁天錄》跋語中,林氏明確強調了自己的翻譯看重小說啟民智、改良社會的功能:“與魏君同譯是書”并非以“巧與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為目的,而是“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眾一號”,“亦足為振作士氣,愛國保種之一助”(陳平原、夏曉虹,1989:28)。在其后的《塊肉余生述》序言中,他再次強調自己翻譯的目的是“使吾中國人觀之,但實力加以教育,則社會亦足改良”(同上:327)。可以說,正是晚清特殊的時代背景,使得翻譯啟蒙思想的社會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實現。依托精英階層對小說改良社會的輿論渲染,翻譯小說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風尚,翻譯也因此承擔起了啟蒙思想、改良社會的歷史重任。
2.3 推動社會變革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翻譯所具有的“知識傳遞、思想啟蒙”的功能能夠直接在現實的社會運動和變革中發揮作用。民眾思想的革新和進步,無疑本身就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強大推動力。許鈞(2004:36)明確指出“翻譯之于社會的推動力,還在于對社會重大政治運動和變革實踐的直接影響”。我國歷史,特別是近代“西學東漸”以來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每個重要的社會變革時期,翻譯所起的作用都無法回避。甚至于說每一次社會變革都由翻譯始,并直接得益于翻譯的思想啟蒙功能所產生的廣泛社會影響。
近代以來,可以說每一次翻譯運動的勃興都有著明顯的社會目標,都是為了服務當時的社會發展和變革。從洋務派推行的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改革理念的科學技術翻譯,到后來維新派為了給戊戌變法提供思想養料而倡導的社會科學翻譯,都是本著翻譯能夠促進社會革新的明確目的而進行的。晚清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極大地尋求翻譯在社會革新和改造中的功能。外憂內患、強權欺凌之下的中國必須依靠變革和維新走出困境。為此,仁人志士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海外,想要通過翻譯引介、學習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先進經驗促進社會進步、實現國富民強。且不說這些社會運動的最終效果如何,一個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是,通過這樣的譯介,西學開始成為有識之士探尋國家出路、民族自強的智力來源。《天演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揭示了晚清政府“泱泱天國”迷夢背后的虛無與狂妄,為維新變法提供了理論依據。正如馮志杰(2011:236)總結:“只有變法適應潮流,中華民族才能保種、生存,實現救亡圖存,……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正是)在西學的啟迪下,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潮,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件舉世矚目的政治運動。”
戊戌變法雖以失敗告終,但通過譯介而被引入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卻已經春風化雨般地滲透到了國人的內心深處。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譯介,中國的資產階級也慢慢地覺醒和壯大。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戊戌變法的失敗看到了維新派的先天不足,試圖通過對封建制度進行內部改良來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在中國根本無法實現,他們認為徹底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才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改革派行動的思想根源同樣來自于西學,他們“吸收《天演論》中的‘天賦人權’思想,并以此為依據,沖破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君權神賦’的王道思想束縛,從而實行對封建統治階級的徹底革命”(同上)。
二十世紀初,許多反映其他國家革命和變革的著作紛紛被譯介而來,一大批期刊報紙都在從事此類譯介活動。以梁啟超創立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為例,前者相繼刊載了《國家論》《斯片挪莎學案》《盧梭學案》等文章,后者則陸續刊載了《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和《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等介紹西學思想的文章(王秉欽、王頡,2009:46-47)。除此之外,留日學生楊廷棟、楊蔭杭、鄭貫一等也通過創辦《開智錄》和《譯學匯編》等刊物,翻譯刊載了《民權真義》《代議政體》《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革命新論》《法蘭西人權宣言》等革命學說,宣傳革命主張,傳播資產階級社會的政體、法治、民權,使得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為推動社會改革和進步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持和思想依據。憑借西學譯介的助推,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發動了彪炳史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持續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
鑒于翻譯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鄒振環編著了《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1996)一書,通過對譯作的社會影響進行考察,論證翻譯在哪些方面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在鄒振環(1996:V)看來,作為其考察對象的這些譯作“使近代中國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紀、本文化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新的見聞、激動、感悟、靈智與啟迪,使他們開始了從狹窄的地域史走向遼闊的世界史的心路歷程”。就具體的影響而言,這些譯作雖“談不上有主宰中國民族命運的天體之力,但卻如影隨形,如響應聲,……這種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回返影響,也有超越影響”(同上:IV)。其實無論以怎樣的方式,翻譯對于近代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甚至可以說,翻譯是每一次社會革新與進步的先聲。
馮志杰(2011:238)對晚清翻譯的社會功能做了非常扼要準確的概括,認為其“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的近代化轉型,不論是洋務運動期間的科技翻譯,還是甲午戰爭前的社會科學翻譯,甚至是戊戌變法失敗后興起的文學翻譯,都從不同的方面,為中國近代化轉型提供了借鑒與動力,推動中國向近代化邁進”。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也的確符合這樣的論斷。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民主”與“科學”通過翻譯被民眾熟知;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一系列馬克思主義著作經由翻譯進入中國社會后,為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提供了思想武器,指明了前進的道路,進而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潮。
3.0 結語
從傳遞新知、啟蒙思想到推動社會變革,翻譯的社會功能在晚清這樣一個特殊的動蕩年代中得到了充分的實現,是翻譯社會性最顯著直接的體現,其原因在于社會發展的需求。翻譯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本身受到各種各樣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干擾;所有翻譯活動的參與者,首先是具有社會屬性的個體或團體,故而對于翻譯行為與過程的考察,一定不能囿于語言文化層面。服務于當下社會實踐、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翻譯活動的這一重要社會屬性必須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只有這樣,翻譯研究才能夠更好地發揮其社會功能,為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