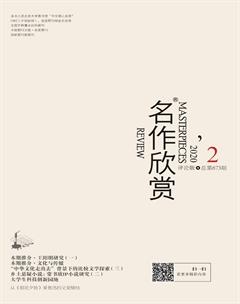迪爾西
摘 要: 美國(guó)近現(xiàn)代黑人的獨(dú)立意識(shí)覺(jué)醒對(duì)南方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迪爾西作為文本最重要的黑人形象,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里通過(guò)探索迪爾西兩方面形象在文本中的體現(xiàn),進(jìn)一步闡釋迪爾西的完美人形象與基督原型的意義。
關(guān)鍵詞:《喧嘩與騷動(dòng)》 迪爾西 人物形象 象征
《喧嘩與騷動(dòng)》不僅僅是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重要作品,還是現(xiàn)代主義意識(shí)流文學(xué)的代表作之一,敘述的是一個(gè)南方家族日益沒(méi)落的現(xiàn)代悲劇。這是一部實(shí)實(shí)在在的意識(shí)流小說(shuō),文本大量采用了隱喻、象征、時(shí)空錯(cuò)位等現(xiàn)代主義手法。其深邃的思想和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模式使普通讀者難以理解,致使各種各樣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方法參與到對(duì)該著作的評(píng)論中來(lái)。福克納把此文本分成了四個(gè)敘述單元,采用多元視角敘述——前三個(gè)內(nèi)視角與最后一個(gè)全知視角。最后一個(gè)全知視角又以迪爾西為主體敘述,對(duì)前三個(gè)內(nèi)視角做補(bǔ)充。意識(shí)流手法的全篇使用加上內(nèi)視角的敘述方式,導(dǎo)致文本透露出的內(nèi)容相當(dāng)缺薄,好在最后一節(jié),作者的全知視角將康普生家族的頹敗表露無(wú)遺。a本文從迪爾西兩種形象的具體體現(xiàn)出發(fā),發(fā)掘其文本作用與深層影響。
一、“完整的人”
迪爾西是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仆,見(jiàn)證了其一家三十多年的衰敗過(guò)程。在殖民擴(kuò)張以后的歐美文學(xué)傳統(tǒng)里,黑人通常是只作為白人家庭的奴隸出現(xiàn),沒(méi)有自己獨(dú)立的人格。由于美國(guó)南部是以大種植園經(jīng)濟(jì)為根基,也使得該地的奴隸程度比其他地方更甚。實(shí)證主義批評(píng)家泰納曾將時(shí)代、環(huán)境、種族作為影響文學(xué)的三要素。南方濃郁的黑奴制風(fēng)氣和歷史傳統(tǒng),使每一個(gè)南方作家都不能躲開(kāi)奴隸制思想的影響。但到了近現(xiàn)代作品里,例如《湯姆叔叔的小屋》,作家塑造的黑人形象卻表現(xiàn)出了比白人更勇敢向上的積極形象。這些作品開(kāi)始意識(shí)到黑人獨(dú)立精神的覺(jué)醒對(duì)南方家族的分崩離析有著深刻影響,而這又不僅僅只作為南方衰落的背景,還參與到南方迅速裂變的歷史進(jìn)程中。高尚的仆人形象在《偽君子》中也有過(guò)先例,這些重視刻畫(huà)底層人的思想,多是吸收了民間文化的結(jié)果。因此,福克納在塑造迪爾西人物形象上,或多或少參照了以往文學(xué)的特點(diǎn)。康普生家族就如同卡拉馬佐夫家族一樣,家族里每個(gè)人都有著明顯的缺點(diǎn):康普生太太只會(huì)抱怨,仿佛所有人都在有意為難她;大兒子昆汀敏感孱弱;二兒子杰森極度自私;小兒子是個(gè)白癡;就連唯一的女兒也是風(fēng)流成性。在這樣一個(gè)家庭里,福克納將視角重點(diǎn)落到了家里的女仆迪爾西身上,賜予了她圣母一般的完美特征。在黑人與白人形象的反差對(duì)比中,探索南方必然衰落的原因。
這樣的完美特征主要是通過(guò)與康普生一家的行為作對(duì)比而體現(xiàn),也正是康普生家族的性格缺陷,使屋子里稍微有些美好品質(zhì)能閃閃發(fā)光。班吉的智力缺陷,弱智兒對(duì)關(guān)愛(ài)的需求,給了作者發(fā)揮迪爾西善良特征的空間。班吉從小就只受到姐姐凱蒂的熱切照顧,最初他叫作毛萊,和舅舅同名,康普生太太甚至嫌棄兒子玷污了她本家的名字,便把毛萊改名為班吉。凱蒂離家后,迪爾西獨(dú)自繼承了其性格里美好的一面,保護(hù)班吉不被杰森送到外地,并時(shí)刻叮囑萊斯特安撫他。丑就在美旁邊,畸形靠近著優(yōu)美,丑惡藏在崇高背后,惡與善共存,黑暗與光明相共。b雨果在克倫威爾序言里提出以描寫(xiě)丑惡來(lái)反襯善,使善良具有更大威力。這里康普生太太和杰森對(duì)班吉的不管不顧,正突出了迪爾西與凱蒂崇高的善。這樣的對(duì)比并不僅是作用于人物塑造,還表現(xiàn)了善惡相對(duì)的人性主題。這種張力在作品的形式和內(nèi)容中融為一體,有著比一般敘述更深的美學(xué)感受。
作為黑人女仆,在主人家庭分崩離析的危難時(shí)刻,她沒(méi)有拋棄康普生一家另謀出路,而是表現(xiàn)出了絕對(duì)的樸實(shí)與忠誠(chéng)。在美國(guó)南北戰(zhàn)爭(zhēng)前后,大量黑人流落各地,而即使是流浪,也比在白人家族遭受奴役更加自由。迪爾西在康普生家服務(wù)了一生,早就把此地當(dāng)作家,一心一意地為夫人付出,從未想過(guò)離開(kāi)。若是把相同情形置換到杰森身上,恐怕在解放第一天便遠(yuǎn)走高飛了。
而且迪爾西仿佛始終沒(méi)有把自己當(dāng)作仆人看待,奴隸面對(duì)主人的暴怒時(shí),通常無(wú)能為力,甚至于任其凌虐。當(dāng)杰森要教訓(xùn)外甥女時(shí),我們可以想象出黑奴仆人縮在角落,任由當(dāng)權(quán)者發(fā)怒的模樣,但迪爾西卻主動(dòng)站出來(lái)化解矛盾,勇于和一家之主杰森作對(duì)抗。在南方白人日益孱弱無(wú)能的節(jié)點(diǎn),黑人迪爾西展現(xiàn)了自己的勇氣。而且與以往刻意丑化黑人形象不同,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刻意將迪爾西的一切美化,表現(xiàn)了作者開(kāi)始自覺(jué)將邊緣人物轉(zhuǎn)移到舞臺(tái)中間來(lái),從千里外響應(yīng)了巴赫金等人對(duì)打破權(quán)威、關(guān)注邊緣話語(yǔ)的要求。
從邏輯上來(lái)說(shuō),迪爾西的完美形象已經(jīng)突破了人類(lèi)范疇,但福克納塑造這一形象并不能說(shuō)沒(méi)有道理,迪爾西在和康普生家族自私無(wú)能的對(duì)比中顯得極度偉大,這種對(duì)比猶如一種補(bǔ)充,填補(bǔ)了這一家族的性格缺失,甚至不只是局限于康普生一家,而是整個(gè)南方社會(huì)。在迪爾西和康普生家族性格的融合下,構(gòu)成了人類(lèi)歷史的一個(gè)“完整的人”。這種反向性藝術(shù)和正向性格的結(jié)合,塑造的是一個(gè)亙古不變的英雄形象。福克納說(shuō)過(guò):“迪爾西是我自己最喜愛(ài)的人物之一,因?yàn)樗赂摇⒋竽憽⒑浪卮妗⒄\(chéng)實(shí)。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c這種永恒的文學(xué)形象會(huì)給人留下很深的記憶,加深作品的文學(xué)性。
二、基督原型象征
除了作為“完整的人”,迪爾西在原型象征上有著更深的內(nèi)涵。福克納從小生活在濃厚的加爾文教文化環(huán)境中,圣經(jīng)文化幾乎在其所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xiàn)。他有自己的宗教觀和神學(xué)觀,只是他的形式不是像哲學(xué)家和神學(xué)家那樣以系統(tǒng)的理論形式闡述出來(lái)。d文本第四節(jié)標(biāo)題,也就是迪爾西的獨(dú)立單元,時(shí)間正是復(fù)活節(jié)當(dāng)天。復(fù)活節(jié)恰好是耶穌復(fù)活的日子,具有很明顯的象征意味。復(fù)活節(jié)的種群原型是死而復(fù)生,原始意象則是耶穌,迪爾西在文本中正是象征著耶穌的形象。
在文本第四節(jié)里,有一處花大篇幅描寫(xiě)了迪爾西協(xié)同家人參加黑人教堂禮拜的場(chǎng)景。在禮拜過(guò)程中,基督教教義被反復(fù)高聲朗誦,迪爾西受洗禮的反應(yīng)也比其他人更強(qiáng)烈,甚至多次流下淚。我們可以看到迪爾西的精神完完全全融入圣潔之中,深受教義指導(dǎo),繼承了基督的意志。也正是在當(dāng)時(shí),迪爾西說(shuō)道:“我看見(jiàn)了初,也看見(jiàn)了終。”而什么人能夠穿越時(shí)空,看見(jiàn)始末呢?在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恰好只有耶穌。迪爾西在這個(gè)南方大家族里生活了一輩子,她能感悟到其他地區(qū)的歷史嗎?不能。因此,迪爾西在禮拜中所感悟到的,或者說(shuō)她所看到的初和終必然是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初和終,放大來(lái)看,也就是美國(guó)南方。在迪爾西的人生暮年,她感受到了死亡的接近,也感受到了南方無(wú)可挽回的衰敗,這二者交織在一起,使得她無(wú)法不深受其觸動(dòng)。
在弗萊的原型理論中,有五個(gè)文學(xué)系統(tǒng)模式,迪爾西的耶穌原型表現(xiàn)為其中第一種,即超人的神。這個(gè)超人的神必然會(huì)由一個(gè)框架環(huán)境所產(chǎn)生,因此生活的環(huán)境也象征著一個(gè)神話框架。迪爾西的基督形象被安置在復(fù)活節(jié)這天,也非常巧妙地暗示了耶穌復(fù)活的場(chǎng)景。耶穌復(fù)活的當(dāng)時(shí),物質(zhì)破碎,人們失去信仰,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和衰敗倒退的南方社會(huì)有很大的共通性。因此,迪爾西的基督象征不僅是表現(xiàn)在個(gè)人自身的象征,這一象征的背后還帶著整個(gè)大環(huán)境的暗示,人物形象必定不能獨(dú)立地出現(xiàn)在文本中,這體現(xiàn)了鮮明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特征。即使這是一部典型的現(xiàn)代主義文本,我們也能從其中的細(xì)節(jié)看到精致的真實(shí)性。
康普生家族道德敗壞、精神薄弱,表現(xiàn)出的是痛苦、荒廢與墮落,是魔幻的意象群。魔幻的意象通常隱喻地表達(dá)了一個(gè)和意愿完全相反的世界,在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與意愿完全相反恰好又反映了作者的理想意愿。因?yàn)楹苌儆形谋緯?huì)無(wú)端地?zé)嶂杂诔蟮拿鑼?xiě),即使是現(xiàn)代主義思潮中的審“丑”傾向,這個(gè)“丑”也是蘊(yùn)含著美的內(nèi)涵,表現(xiàn)著對(duì)美的反映與呼喚。波德萊爾也不會(huì)是因?yàn)閷?duì)丑惡的癖好而把巴黎的破碎展現(xiàn)給人看。可以看出,作者首先是以南部變遷的大環(huán)境構(gòu)造了一個(gè)上古的魔幻意象,再向其中安插了迪爾西的基督形象。通過(guò)這組魔幻意象,福克納塑造了一種反意象來(lái)隱晦地表現(xiàn)自己的理想意愿。
作為橫跨在康普生家族歷史上的女仆,迪爾西見(jiàn)到了其中存在的自私自利、無(wú)為、放縱,最終表現(xiàn)為南方白人家族的脆弱。福克納自小生活在美國(guó)南方,對(duì)南方有著真摯的愛(ài),又深刻地看到了其中必然衰亡的一面。在愛(ài)恨交織的心理下,他希望憑靠迪爾西的耶穌精神和死而復(fù)生的原型象征,向南方家族傳達(dá)扭轉(zhuǎn)衰落的方法。從文本內(nèi)容看來(lái),也正是康普生一家自身的矛盾,導(dǎo)致了家族衰亡的悲劇,也正是南方白人的外強(qiáng)中干,解釋了南方不可避免的衰落。
三、結(jié)語(yǔ)
文本構(gòu)建了一個(gè)日漸式微的南方家族體系,也塑造了許多鮮明的人物形象,在反映美國(guó)南部生活上有著重要意義。福克納使用各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手法塑造的多面迪爾西形象有著很強(qiáng)的文學(xué)性。作為南方人,南方精神的敗壞是福克納不想面對(duì)又無(wú)可奈何的。因此,迪爾西無(wú)論是作為“完整的人”還是象征耶穌的原始意象,都在隱喻性地指示南方的發(fā)展方向,也都表現(xiàn)了他對(duì)南方社會(huì)重獲新生的期望,又無(wú)不流露出歷史進(jìn)程無(wú)法阻擋的哀傷。
a 賈成穎:《論〈喧嘩與騷動(dòng)〉中多元敘事視角》,《海外英語(yǔ)》2014年第23期。
b馬新國(guó):《西方文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c 李文俊:《喧嘩與騷動(dòng)(譯者序)》,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
d 田平、洪增流:《〈喧嘩與騷動(dòng)〉:現(xiàn)代基督的救贖之路》,《山東外語(yǔ)教學(xué)》2008年第5期。
作 者: 劉飛躍,長(zhǎng)江大學(xué)文理學(xué)院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漢語(yǔ)言文學(xué)。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