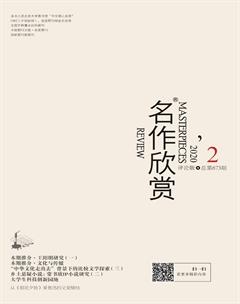在苦難中成就生命甘甜
摘 要:《人世間》 的主要女性人物中,作為受難者的鄭娟,其形象塑造體現的不僅是梁曉聲對底層民眾尤其是作為不幸群體的深切關懷和悲憫,更有對于人在苦難命運面前應當肯定和接納自我,并在直面和承擔責任中走向升華自我、超越苦難的深層思考;作為賢妻良母的鄭娟,則寄托了梁曉聲對于女性美好品格的理想期待,同時傳達出作家挖掘小人物美好心靈,尊重普通人生存邏輯的平民立場。梁曉聲在圍繞鄭娟的苦難敘事中探索生命的深度與價值,并試圖通過苦難的意義找到戰勝苦難的根本出路;在對好女人的書寫中,作家建構理想愛情,呼喚美好人性,以上兩個維度的精神內涵,可以說是鄭娟這一形象最大的意義所在。
關鍵詞:《人世間》 梁曉聲 鄭娟 苦難敘事 好女人
談到自己的小說創作,梁曉聲將其概分為兩類:一類為知青文學,講述特殊歷史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生經歷,諸如《今夜有暴風雪》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這樣的作品不僅承載了曾為知青的老一輩人的精神信仰,也激勵著新時代的知識青年不忘歷史,珍惜當下;另一類為伴隨時代的發展變化而獲得更新的當下題材,或可說現實主義題材,作家更多關注并書寫城市平民中的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的生活境況,在滿懷真情的筆觸中表現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a2018年出版、2019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人世間》 便屬于后者。
就書中的幾名主要女性人物,相比才華橫溢、飽讀詩書的周蓉與出身高干家庭、有著良好教養的郝冬梅,作為家庭婦女的鄭娟不僅出身貧苦、文化程度不高,甚至還遭受過不幸的凌辱且成了有孩子的寡婦,加之前后幾次歷經不幸,除去命運曲折坎坷這一點以外,鄭娟似乎可以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正是在這個并無很高學識和社會地位的女性身上,作者賦予了其作為一名普通女性的種種美德。通過對鄭娟幾次受難的書寫及其內在心靈的刻畫,作品不僅傳遞出尊重普通人生命邏輯的道德立場和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更有對于人在苦難命運面前應持何種生存姿態的終極思考,作者肯定苦難對人的意義并接納苦難,同時挖掘人性本真的美好與高貴;毫無疑問,這是梁曉聲通過塑造這個受難的好女人形象試圖探尋人的生命價值的一次有益實踐。
一、作為受難者:接納自我、承擔苦難
梁曉聲筆下的鄭娟,是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苦命女人,從作為棄嬰被收養,到成年后正值花季被暴徒侵害,接著懷孕生子成為寡婦,迎來新的生活之后又遭遇丈夫獲罪入獄十二年,繼而人生中年痛失長子,可以說接連不斷的坎坷經歷,讓鄭娟的一生都充滿了悲劇性意味。面對看起來似乎是破碎不堪的人生,鄭娟的反應和態度始終是從容而坦然的,幾次受難,盡管經受著心靈上的巨大痛苦,鄭娟都選擇了面對和默默承受,在整個命途多舛的人生面前,她表現出的是直面人生的勇氣和在苦難中肯定自我、承擔苦難的精神向度。顯然,對于這樣一個仿佛是以“受難”為標簽的女人,作者并沒有止于純粹地展示苦難,而是聚焦于人物的心靈特質,挖掘人物身上自我珍視、敢于承擔并超越苦難的內在品格,并試圖以人物的忍耐、堅韌和寬厚消解苦難帶來的對生命的極端壓迫。
按照周保欣對受難類型的劃分b,鄭娟的受難屬于弱者的受難,也屬于無辜者受難。根據文本的敘述我們知道,被遺棄和肉體上被侮辱的經歷源于他者的人性惡,成為寡婦是由于前夫涂志強卷入殺人案件當了替罪羊,與周秉昆結婚后再經歷丈夫入獄,雖是由于早年的感情糾葛產生的遺留問題,但最終意外的發生更多是與丈夫周秉昆的性格直接相關,其中也不乏偶然因素的參與;兒子的犧牲則完全是超乎可控范圍的絕對意外。可見,鄭娟的受難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無辜的與被迫的,而梁曉聲敘述這個無辜者遭受苦難故事的重點并非是要對其中涉及的人性惡以及不合理不公正的社會現象進行批駁,當然這并不是說作家完全忽視了這一點,而在于力圖通過塑造鄭娟的直面苦難和承擔呼喚美好的人性,并在對苦難的接納和認同中探索生命的深度與價值。
首先,作品肯定女性歷經苦難而能接納并認同自我的存在勇氣。人生伊始遭受身體的凌辱、成為孀居的單身母親,對于一名正值芳華的年輕女性來說,這背后需要承受的心理傷痛和打擊幾乎可以說是毀滅性的,對此,鄭娟自己也不是沒有產生過極端的想法;盡管如此,最終她依然接納了這一令人痛心的現實命運,接納了曾經遭受創傷的自我。“從邏輯上說,自我保存與自我肯定所指的是對某種(至少是潛在的)威脅或否定自我的東西的克服”c,青春年華遭遇的不幸并沒有威脅到鄭娟的自我認同和自我保存權利;相反,她對痛苦清醒的自我克制與自我肯定幫助她度過了這一次的生存危機。也正是基于此,在后來為照顧周母住到周家時,面對周圍人對她的議論,鄭娟才可以做到鎮定自若。眾人目光之下作為被看者的鄭娟,沒有半分恓惶和自我猶疑,而是在不言不語之間充分表露了自己該有的尊嚴,作者肯定她心態的磊落和對自我的珍視,甚至用“上帝差遣到民間的天使”這樣的辭藻來譬喻鄭娟對于秉昆的意義,這也成了她后來開啟新的愛情和婚姻的關鍵因素。在面對自己的情感問題時,鄭娟的態度坦誠且坦蕩,她不僅尊重自己,同時也充分尊重周秉昆的選擇自由。她首先接納了自己滿含創痛的過去,并在與周秉昆確立關系前平靜從容地據實以告,未加絲毫的遮掩和粉飾。在對所愛之人講述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去時,她并無半點妄自菲薄的意味,她的敘述語調也是極為平靜的,似乎只是在客觀冷靜地陳述過去發生的某件事情。隱含作者的立場則在哥哥周秉義與周秉昆的談話中流露了出來:“好青年正確對待個人問題的三原則是,要對自己負責,對對方負責……對自己負責就是不勉強自己,凡當初勉強,婚后生活必有裂痕。對對方負責就是要真誠坦白,不能為了與對方實現婚姻目的就隱瞞自己的實際情況。要明明白白地講清自己是怎樣一個人,自己家庭是怎樣的家庭,讓對方一清二楚,要讓對方做出感情和理智的決定。”d這里,敘述者的聲音與隱含作者的聲音合為一體,敘述者的立場顯然也代表了隱含作者的立場,對于鄭娟在周秉昆面前那一番真誠的自我剖白,隱含作者是給予了充分肯定的。應當看到,不管是鄭娟的自我接納還是后來周秉昆直面并承擔起內心對鄭娟真誠的愛、對鄭娟的最終接納,背后都意味著作者對傳統貞操觀的拒斥,同時也是對“失貞”女性爭取愛情和婚姻自主權的捍衛,梁曉聲想傳達的無非是這樣一種現代文明觀念,女性的生命價值并不因為貞潔的失去而有所貶損,真正影響女性個體幸福與否的,是其自身的內在品格。這一思想旨趣,在女性遭受性侵害案件頻發的今天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觀照意義。
其次,作品高揚女性在苦難中直面和承擔責任的內在精神。按照小說情節的發展,婚后的鄭娟在面對周秉昆因誤傷駱士賓獲罪入獄一事時,其表現出的從容和擔當十分令人敬佩。在周秉昆入獄的十二年里,鄭娟獨自面對人生,一人承擔起了照顧周母和養育兩個孩子的責任(第五年周母去世);周秉昆出獄時,大兒子周楠已考上了哈佛的公派留學生,小兒子周聰也順利從大學畢業。作者并沒有深入細致地展開去寫鄭娟十二年里是如何含辛茹苦,甚至都沒有去寫丈夫入獄對鄭娟造成的心理沖擊,而只在展開小說情節的必要之時以寥寥數語提到鄭娟在周秉昆入獄后出去工作并對丈夫探視得勤,這種創作手法上的盲處理恰恰凸顯了鄭娟超乎常人的強大心理素質,似乎這對鄭娟來說并非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她需要做的只是想辦法去迎頭面對,隱含作者對她的所有憐惜則以周秉昆的視角傳達了出來:“1989年后的十二年間,她每一次去探望他,他都能發現她比上一次更憔悴了。如同一朵大麗花,秋天里隔幾天便掉落一片花瓣……十二年,四千三百多天,在沒有他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之花無可奈何、無可救藥地凋零了。”e大麗花凋零的比喻美麗而又殘忍,蒼涼無奈的語調中飽含著作者對筆下人物深切的同情和關懷,也飽含著對她的無限敬意。面對突如其來的由非己因素造成的意外,作者在敘事中讓鄭娟選擇接受與承擔,并在這樣看似無聲的接受與承擔中形成一種靜默的反抗;換句話說,不被厄運打倒,也并非走向墮落或者虛無,而是在細水長流的日子里完成生命的正向延續,這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性的反抗。我們可以將梁曉聲賦予鄭娟的此種特質看作是其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與揭示,這與他一貫堅持的“人生的意義在于承擔責任”f 這一價值理念是并行不悖的。
最后,作品不遺余力地展現并謳歌女性在苦難中造就和升華自我的高尚品格。如果說在此前幾次經歷命運的坎坷時,對自我存在的肯定和直面人生的勇氣是鄭娟面對苦難最好的良藥,那么中年以后大兒子周楠的死則讓鄭娟的人格形象呈現出了新的高度。在美國參加兒子的追思儀式時,作為一位普通的中國母親,鄭娟盡管悲痛不已,但她在眾人面前的鎮定和從容不迫,以及拒絕用周楠的死向慈善機構申請救濟金的高大形象,贏得了所有人的敬意。梁曉聲在敘述中認同了鄭娟的價值選擇,并對鄭娟的這一行為給予高度評價。透過這樣的書寫,作家讓我們知道,人的真正高貴無關乎財富或社會地位,而在于心靈的寬厚和廣博的愛。對于鄭娟的這一舉動,也有的觀點著眼于正義與公平二者的關系,認為鄭娟是將自己放在了一種不自覺的不平等的狀態之中,只看到金錢可能有損正義作為一種崇高的榮耀而忽視了美國人的捐款其實也是一種愛的表示,因而鄭娟的舉動是一種為得到外在的尊重而有意放棄公平的行為。事實上,在美國最高學府的各位文化精英和政府官員面前,鄭娟作為一個“粗服亂頭、笨拙淳樸”的底層中國母親出現,所處的社會地位本就是不平等的,擔心自己會因身份的緣故被對方看低也不無道理,正是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鄭娟才要用精神上的高大來為自己爭取人格上的平等,這恰恰是對自己作為底層貧苦百姓身份的反撥。美國人對于周楠舍身保護師生的賠償也并非來自校方的官方補償,而是另有民間慈善基金提供的救濟,鄭娟拒絕的理由一是:“咱們不是來祈求同情和憐憫的,是不是?”g同情和憐憫有時是屬于愛的情感,但在作品的情境預設中顯然不是基于平等的愛(如果是,那么校方就有義務主動提供賠償款項)。二則是鄭娟對兒子的愛和疼惜,“楠楠這孩子的死,不能和錢沾一丁點兒關系……我們當父母的,如果花兒子用命換來的錢,那是種什么心情?”h兒子的死讓鄭娟感到無比悲傷,同時也感到無比的欣慰和自豪,正是這樣雙重交織的情感讓她無法接受因為兒子的死而得來的金錢,在她看來,那會玷污了兒子的崇高,也將陷自己于卑微的境地。如此一來,鄭娟在面對大兒子周楠的死一事上完成了道德的進一步完善和升華,其行為是出于主體的心靈自由做出的抉擇,因此,這種對他者的寬厚本質上源于單純的善與愛 。i
不難發現,鄭娟的高尚品格消解了失去兒子的悲劇感,苦難于她固然是沉痛的精神打擊,同時也是精神領域的鍛造和磨礪;由苦難走向崇高,作者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超脫了物欲、追求道德與精神上的雙重自足的悲苦女性。梁曉聲用他的書寫告訴我們,苦難之中的人并非只是被同情和被憐憫的對象,一如鄭娟,以心靈的柔韌和深厚戰勝苦難,在苦難中實現精神的內在超越和道德層面的質的升華,無疑這樣的人將對社會的思想文化形態產生正向的精神鼓舞。
“勇氣是這樣一種狀態:它欣然承擔起由恐懼所預感到的否定性,以達到更充分的肯定性,生物學上的自我肯定,是指對匱乏、辛勞、不安全、痛苦、可能招致的毀滅等的接受。沒有這樣的自我肯定,生命就不可能得到保存和發展”j。從接納、肯定自我,到直面、承擔責任,再到道德上的升華自我,可以說,在受難者鄭娟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作為存在者的勇氣。隱含作者在敘述中一面對命途多舛的鄭娟心懷憐惜,為她的不幸命運感到難過;一面毫不吝惜贊譽之詞,肯定和贊揚她在人生苦難面前表現出的珍惜自我存在、直面人生的勇氣和品質。我們不妨將這看作是作家對于人與苦難關系的另一種思考——即面對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苦難,人究竟應該怎樣?文學又如何關懷身處苦難中的弱者?這是梁曉聲試圖回答的問題。
舍勒在《受苦的意義》一文中論述了人類對待受苦的許多種方式,主要有使受苦對象化和聽天由命(或主動忍受)、享樂主義地逃避痛苦、漠化痛苦直至麻木、英勇地抗爭并戰勝受苦;抑制受苦感并以幻覺論否認受苦等。! 1通過鄭娟這一人物的命運想象,我們發現,梁曉聲傳達出的精神指向更接近于主動忍受與英勇抗爭二者的結合,在極端的境遇中,人需要保存自身,同時在忍受苦難的過程中積蓄力量,最終超越苦難,在苦難中完成自我升華。如此看來,梁曉聲其實是借鄭娟的人生遭遇傳達出了苦難的意義所在,也由此在小說的敘事中形成了一種與苦難對抗并超乎其上的生命深度和力量感。
“真正的人道主義,首先就應該是一種苦難哲學,沒有對人類苦難的深層理解、體認和同情,沒有對人類苦難的疼痛觸摸,就沒有真正的人類關懷,更不可能提出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救贖之道”! 2。通過鄭娟的受難書寫,我們感到作者對人物的無限悲憫和體諒,這是作家對人、對他者深厚寬廣的人道情懷的體現,同時也借著鄭娟的不幸,作者照亮了那些受難者的人生,完成了對苦難的精神超越。“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3,盡管人生有苦難,有折磨,有悲劇,但這些掩蓋不了人性本身的真、善、美,身處苦難之中的人依然有希望探尋一種合乎人性的理想生活;可以說,這是梁曉聲的苦難敘事最打動人心的一面。
二、作為賢妻良母:在愛和奉獻中存在
前面我們分析的是作為受難者形象的鄭娟,而在小說里作為家庭婦女的鄭娟,其形象設置也同樣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如果說書寫受難者鄭娟傳達出的是作者對人物的悲憫和對生命苦難的深沉思考,那么敘寫鄭娟作為賢妻良母的種種特質,充分展現人物本身所具有的美好品格,則在某種程度上寄予了作家對于理想女性的期待,同時傳達出尊重普通百姓的生命邏輯、挖掘和頌揚平凡人美好心靈的價值立場。在“受難”這一標簽之外,作家賦予鄭娟種種美好品格,擺脫了居高臨下的同情和垂憐的敘事嫌疑,這體現出作者對于受難者本身深厚的心靈關懷,也是作家對美好人性的期待和召喚。
埃里希·弗洛姆在《占有還是存在》一書中論述了人本身具有的兩種生存傾向,一種是占有傾向,即我同世界的關系是一種占有和被占有的關系;一種是存在傾向,主要是愛、分享和奉獻,人也通過這種生存方式指向真正意義的幸福。! 4那么,在鄭娟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后一種生存傾向,即重存在的傾向。無論是之于周家、之于周秉昆,還是之于鄰里和朋友,愛、分享和奉獻始終都是鄭娟付諸實踐的人生信條。
對于周家,毫無疑問,鄭娟付出的是真誠的愛和奉獻,這一點也在小說的敘事中得到了作者的充分認可。從本質上講,對周家的付出其實是鄭娟為愛的無怨無悔和心甘情愿,婚后對一家老幼的照拂則是在盡妻子的本分,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對美好品質的恪守呢?在周秉昆被捕的日子里,鄭娟以自己的堅韌和辛勞一面無微不至地照料周母和周秉昆的外甥女,一面又盡姐姐和母親的責任,并且用長年如一日的按摩拯救了已經成為植物人的周母。盡管鄭娟對周家的幫助含有與周秉昆直接相關的情感成分,但這與她性情中原有的善意也是分不開的。鄭娟對周秉昆談起母親時說:“興許她媽才是什么神明的化身,要不她媽為什么樣子那么丑而心地又那么好呢?媽即使在外邊看到了只小野貓或小野狗,都會顛顛地跑回家拿些吃的東西給它們。”! 5鄭娟和弟弟光明都是母親撿來的孩子,對于這位母親對兩個孩子人格的影響,劉軍茹有貼切入理的分析:“承認并撫摸個體的差異和脆弱,這是一種給予希望的善與愛,并指向信仰的無限、愛的無限。鄭母不僅給予被摒棄被侮辱者以生命,還如一道微弱的本能之光,溫暖并引領著兩個柔弱之軀幾經磨難而仍然心懷善意。”! 6鄭娟的付出和奉獻對于后來鄭娟與周秉昆婚姻的結合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關系就不再停留于鄭娟作為單向的弱者和被拯救者,而是走向了互相扶持、共同面對人生的新境界,兩者之間精神與人格上的平等也就有了可能,這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對于理想婚姻關系的一種投射。觀察鄭娟與秉昆從初識到走入婚姻的始末,不難發現,梁曉聲既看重女性的美貌,也看重女性美德,某種意義上,這其實寄托了作家本身的愛情理想。周秉昆最初愛上鄭娟是因為她外在的美麗氣質,而最終促成他們婚姻結合的則是鄭娟接納自我和關懷他者的內在品格,這種對他者的關愛和奉獻深深地延續到了丈夫周秉昆的身上。盡管周秉昆在知道鄭娟曾被棉猴奸污的過往時有過心理上短暫的不適,但這種不適很快被他對鄭娟熾熱而真誠的愛所沖淡,他最終依然選擇的是對自己內心感情的接納和擁抱,婚后鄭娟小寡婦的身份也并沒有對他們的夫妻感情產生任何不良影響,反而因為與鄭娟的結合,讓周秉昆覺得自己是共樂區最幸福的丈夫,讓偶感人生愁煩和憂悶的他覺得“世界終歸是美好的,覺得人生畢竟值得眷戀”! 7。作者如此安排和構置人物的人生,顯然摒棄了中國傳統的貞節觀念和所謂處女情結的桎梏,而是承繼了“五四”以來“人的發現” 的精神指歸,意在從人真正的內在情感需求出發,探尋并呼吁一種更合乎人情的婚戀價值觀。
婚后的鄭娟,對于自己在家庭中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她也是甘于奉獻和付出愛的。疏離時代政治話語,單純地享受并盡最大的努力去做妻子和做母親,隱含作者并未輕看鄭娟甘心作為一名普通家庭婦女的心理,而是首先對鄭娟的價值選擇自由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同時在敘述中也有對其努力承擔家庭責任的肯定和贊賞。“五四”以來,女性主義思潮的主流話語是女性為爭取男女平等渴望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然而是否女性作為賢妻良母就意味著男女不平等?劉慧英認為,理想的男女兩性關系是建立和發展一種雙性文化特征,即“在充分尊重男女獨立人格的同時,完善和發展健康的人性與人的自由”! 8。梁曉聲在這里通過鄭娟的自白也做了思考與回答——即肯定作為家庭婦女與作為職場女性同樣具有意義和價值,這不妨看作是對劉慧英所提理論的回應和對照,也是對五四以來“男女平等”觀念的再反思,由此,作品也具有了更為豐富的現代性意蘊。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鄭娟甘心做一名家庭婦女,但其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并非完全是丈夫的附屬物,在周秉昆入獄的十二年里,我們看到了鄭娟的獨立和對家庭責任的承擔,那種一味強調鄭娟在婚姻中具有依附性的觀點其實是有失偏頗的。梁曉聲也沒有忽視在敘事中建構鄭娟作為女性人物的主體性,比如,在夫妻關系中,作者就讓鄭娟發出“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 9這樣的抗議,我們明顯看到鄭娟朦朧的自我意識,也看到梁曉聲在刻畫女性形象時為警惕物化女性所做的一番努力。除去對鄭娟坦蕩胸懷和奉獻精神的贊美,作品還充分肯定了鄭娟在婚姻中對物質生活的淡泊和知足喜樂的性情。不同于吳倩和于虹對丈夫的種種期待和要求,也不同于春燕的精明和懂得算計,梁曉聲筆下的鄭娟是簡單而容易知足的,她不會過多地苛責丈夫必須要為自己提供更好的生活,創傷之后重獲幸福的經歷讓鄭娟對于人生有了一種全新的懂得知足和珍惜的眼光,她懷著近乎感恩的心在經營著自己與周秉昆共同的家,如文中所言:“她總是自覺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她在太平胡同的生活,絲毫也沒有不幸福的理由。”@ 0她的淡泊、知足極大地祝福了她與周秉昆的婚姻,即使居住環境一波三折忽而變好忽而變壞,她也并未隨之產生過于強烈的心理波動,而是一如既往、高高興興地熱愛生活。作者在敘述中肯定鄭娟這樣的女性,她們在人生陷入困境時不卑不亢,當生活發生新的轉向時又能不驕不躁,而是持續地生發出生命韌勁,以從容不迫的姿態去迎接人生更長更多的日子。換句話說,這是作者試圖通過塑造鄭娟這一形象所倡導的人生態度。更進一步,在這種理想的婚姻關系中,男性主要承擔家庭的經濟責任,并且需要女性對男性的諒解和體貼,與此同時,女性為家庭的付出同樣也是一種承擔,也值得被認可和被肯定。梁曉聲在鄭娟和秉昆的婚姻關系中所流露出的這種價值傾向充分尊重了男性與女性的主體間性,是其作品文明尺度的體現。
鄭娟的美德不僅體現在婚姻家庭當中,還體現在對與己有關的他者的關懷之中。但凡自己的境況稍好一些,她想到的便是盡力讓身邊的朋友們也脫離貧苦,同她一樣過上“好日子”。在聽說趕超和國慶掙錢不易以及趕超妹妹投江自盡的事以后,鄭娟立刻讓秉昆把周聰帶回家的年貨全部給他們,當借住在鄭娟太平胡同房子里的趕超和于虹面臨沒有房產的危機,鄭娟便毫不猶豫地把太平胡同的房屋產權無償贈送給趕超和于虹。因為切身體驗到極端的境遇有多么令人痛苦,鄭娟對周圍人的生存困境生發出巨大的共情能力和寬厚的同理心,這就驅使著她以廣博的愛心去幫助和關懷他者,這是梁曉聲再度展現的人性美好與溫暖的一面。文學應當書寫真善美,教化人心,七十歲的梁曉聲依然在身體力行。盡管作者在小說中透過周蓉知識分子的形象表達過對于思想修養的看重和追求,也明確地通過周秉昆之口表達過此種立場。@ 1但對知識的信仰和追求并不意味著作家對知識匱乏之人的鄙夷;恰恰相反,尊重尋常百姓的生活邏輯,肯定平凡的價值才是作家一貫堅持的立場,“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 2。那么在小說中,作者如此塑造鄭娟這位笨拙淳樸、學識無多的家庭婦女的不普通之處,既不是從財富和社會地位出發,也不是以學識和思想水平為唯一評價標準,而是挖掘和頌揚普通人的美好心靈,這樣一來,作家就跳出了知識分子的固有立場,在尊重和關懷普通眾生的視野下進行創作,使得作品同時具有追求知識與文明和尊重普通民眾的生命邏輯,并于其中發覺他們人格珍貴之處的多重價值尺度意味。
“好女人是一切美好品德的總和”@ 3,如果說塑造周蓉那樣的女性寄托的是作家對于女性富有學識和思想的期待,那么塑造鄭娟這樣的女性,我們看到的是梁曉聲對女性美好品行的期待。如果再將眼光投放到小說中的男性人物身上,我們會發現,對于男性,作家有著同樣的期待。顯然作者讓小說里的女性追求文化和思想深度,女性需要美好品德,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周秉義那樣的政府官員,一直都對自己有著嚴格的道德約束,工作之余始終堅持讀書思考的習慣;周秉昆也是心胸坦蕩、正直善良的好人,盡管沒能上大學也認識到思想對于個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梁曉聲眼中,不管是學識還是美德,男性同樣也是需要不斷探索和努力追尋的,這其實是作家努力跳出性別局限的體現。
三、結語
“從21世紀初,梁曉聲作品的主題趨向展現人性光輝,展現在通透知曉了命運的殘酷和悲劇的不可回避之后重視人、人性、人在生存困境下的價值,拒斥荒謬,反抗絕望,直面現實,積極樂觀地面對困境”@ 4。《人世間》 里鄭娟的人物想象很好地詮釋了這一創作思想,作者也讓我們看到真正有力量感的、能為他人帶來福祉的女性應該是怎樣。苦難命運并沒有摧毀鄭娟,而是鍛造了她珍惜自我存在、懂得愛與奉獻的內在修為,即使中年以后因喪子之悲一度陷入抑郁,但她最終在佛法里找到了自我療愈的精神出口,重拾對生活的盼望和信念。小說結尾和周秉昆牽手軋馬路的溫馨場景,則更有了渡盡劫難、人生歸寧的哲學況味。
從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來看,不管是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還是在當下及可預見的未來,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始終都是人類要面對的人生問題,由此帶來的不幸與苦難一直伴隨著人類而存在,苦難記憶與創傷書寫也成了文學作品中被反復書寫的命題。“苦難正是催生崇高的力量,經由苦難我們獲得的是命運的恩惠。苦難亦是愛的召喚,是對自由意志的考驗,它令受難的主體以承擔或反抗的方式消化著生命的重量”@ 5。在鄭娟的苦難敘事中,梁曉聲既沒有消費苦難,也沒有美化苦難,而是讓主人公直面并完成對苦難的超越,最終透過苦難敘事探尋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既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也寫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通過‘應該怎樣,體現現實主義亦應具有的溫度,寄托我對人本身的理想”@ 6。在無端發生的、令人無能為力的苦難面前,并非只有走向虛無和自我毀滅,而是也能在另一種承擔和奉獻的姿態中確立并合理安放自我,鍛造美好品德和內在修為,并在對他人的愛和奉獻中實現人生的意義。通過這一人生命題的探索,梁曉聲不僅為鄭娟開創了幸福安寧的人生,同時也寄予了自身對美好人性的期待與呼喚——他讓人物以自己的道德修為和美好的內在品格為戟,開拓了一種充滿希望和力量的人生境界,激勵和鼓舞著現實世界中的人們:敢于承受生命與心靈的痛苦,并不斷向真、向善、向美。
a 梁曉聲:《書寫城市的平民子弟》,載《文藝報》2018年2月23日。
bl 周保欣:《沉默的風景——后當代中國小說苦難敘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頁,第164頁。
cj 〔美〕蒂利希:《存在的勇氣》,成窮、王作虹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頁,第70頁。
doq@ 1梁曉聲:《人世間》上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97頁,第390頁,第77頁,第283頁。
egh梁曉聲:《人世間》下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頁,第208頁,第209頁。
f 梁曉聲:《梁曉聲散文精選·人生的意義在于承擔》,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頁。
ip劉軍茹:《〈人世間〉:承擔自我與他者的責任》,《棗莊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k 〔德〕舍勒:《舍勒選集·第二編:受苦的意義》,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650頁。
m 《羅馬書》5:4,《圣經》和合本,中國基督教兩會2001年版,第264頁。
n 〔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還是存在》,李穆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7頁。
! 8 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15頁。
st梁曉聲:《人世間》中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頁,第231頁。
@ 2 梁曉聲:《為什么我們對“平凡的人生”深懷恐懼》,《教師博覽》2012年第6期。
@ 3 侯志明、王津津:《好女人是一所學校——訪青年作家梁曉聲》,《名人談女人》,中國社會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x 華祺蓉:《生存困境敘事——論90年代以來梁曉聲的小說創作》,《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y 路文彬:《中西文學倫理之辨》,中國文化戰略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頁。
z 叢子鈺:《梁曉聲:現實主義亦應寄托對人的理想》,《文藝報》2019年1月16日。
作 者: 肖瑛,北京語言大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 張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