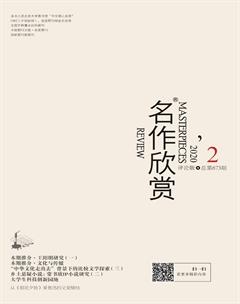論波德萊爾《惡之花》中選擇“惡”的緣由及其延伸方向
摘 要: 法國著名詩人波德萊爾被尊為現代派的鼻祖,其著作《惡之花》影響深遠,他在詩中選用了大量的丑的意象,為我們呈現了博大而真實的內心世界。本文之所以將《惡之花》中選擇“惡”作為核心的緣由及其延伸方向作為文章的核心論題,旨在前人研究“惡”的內容和價值基礎上去探究為何波德萊爾會選擇“惡”這一道德倫理意象作為評價社會、反觀社會的焦點和著力點,作為詩集的核心,為何不選擇“猥褻”“丑”等角度,即意在從文化流傳及其自身意義的角度探究其選擇惡的原因和“惡”在被詩人所賦予內涵之上的本身價值。
關鍵詞:惡 丑 波德萊爾 《惡之花》
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丑美學”理論打破了傳統的美學觀,極大地拓展了文學藝術審美領域,在19世紀中期和末期歐洲的思想潮流中樹立了一個獨特的新的航標。那么波德萊爾為何最終會選擇這樣的角度,而“丑惡”最終為何又能對于現實形成如此直觀的反映和影響?這是否是由“惡”本身的性質所決定?這些問題是本文思考并試圖解答的核心。
一、“惡”具有相對純粹性
(一) 從道德意象和審美意象,即丑惡與美善的相對關系而論
我們所說,《惡之花》中的“惡”最終可分為“人性之惡”和“社會之惡”,而對于“惡”所描繪表達的是一種近于病態于更加真實的美。但我們應當知道,“惡”這個道理倫理意象在我們的傳統觀念意識中所對應的,應是同為道德倫理意象的“善”,而不是“美”這個審美意象。所以在開始探索前,我們應當現理清“美”“惡”對立的前提,也就是美善融合,以及與丑惡相對立的必要性。
西方文化中的美善結合思想由來已久,在古希臘文化的形成時期,對美的認知就呈現出了被劃分為形式之美和靈魂之美——兩個相對的內在和外在部分的趨勢。其中,形式之美更多指向肉體之美和物質規則之美,而靈魂之美則提升至了精神層次,不可避免地與道德觀念相融合,并且哲學家們認為靈魂之美遠勝于形式之美,并對于形式之美起到了主導作用。而善這個道德倫理意象,無論從其外在行為表現形式,還是內在核心的道德倫理內涵,都無比契合于美的要求,隨著人對于自我本性的逐漸探索和社會觀念的成熟,這種融合似乎也成為一種必然。
但同時,觀念演變中的時人,其思想中的美丑觀念所承載的美丑模型,雖已是一個固定的可解釋的“特定”模型,但并不是一個完全對立構造的模型,即美的相反就是惡,這一點從宗教中的宇宙至美論的觀點即可見一斑:其人認為美就如同上帝創世所發出的光一般籠罩大地,丑無所容身甚至不必存在,意為世界上只存在美,而丑是美所照不到的地方的影子。在丑的概念中,形式上的丑是一個整體的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缺乏均衡,即丑是對于整體物質規則的不連貫,不完整。同時柏拉圖認為,丑即物質世界。但幾乎所有美學理論中又講到任何一種形式上的丑都能最終經由藝術上忠實、效果充分的呈現而化為神奇,即任何物質形式上的丑都可經過藝術加工而變成美。這兩點的結合,就意味著決定丑的并不是美的標準,而是物質的標準,隨之帶來對美界定標準的界定泛化和模糊。另一方面,正如尼采所說的“人以自己為完美標準,任何反映它的事物都是美的”,就又在界定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問題,即美的標準是由當時社會的整體審美而決定,會隨個人思想和社會發展而改變,而善又作為一種道德倫理處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頂端,即人性的部分,也會隨著社會和個人的思想的改變而發生部分的變化,兩者都不具備恒定標準,并且僅存在于人的意識形態中,意象之間的融合關系并不穩固,雖因其根本特性和人最終本性的穩定性的綁定而使兩者之間難以徹底分離,但在碰撞消化后,常會帶來一者對另一者,或二者之間的蒙蔽。當美這個審美意象和善這個道德倫理意象相融合的時候,善成了美,美成了虛偽的善,甚至說美成為波德萊爾當時所生活的、詩中所描述的社會中裹著善外表的裹尸布,這樣的美,很明顯,不是真正的美。由此可見,單從美的角度已無法全然地向世人展示闡述美的存在,這時勢必尋求一種與之對應的、可相對而論的事物去進行反映。
(二) 惡最終是丑的道德之丑
上文中我們已提到過美的泛化,而要通過一種A事物去論述一個泛化而無明顯界限的B事物,如果繼續選擇一個泛化的即使與之對立的A事物,這明顯也是無法得到一個確切的結論的,這樣做最終很可能非但無法做到有效的對應、闡述,甚至會使得作品趨于混亂,所以其選擇以A事物的具體性或相對純粹性的一個方面去對應是很好的選擇。波德萊爾選擇了丑惡作為其唯一描寫對象,認為美可以從天而降,也可以從深淵里上升,這是否可設想為其認為在其詩中所描繪的世界里,惡是擁有類似相關特性的物質。
在《丑的歷史》一書中,將丑分為三類,即丑的本身、形式上的丑和藝術對著二者的刻畫。這樣看似乎丑即流于形式和外在物質的表現或藝術品的客觀反映,但如果僅這樣認為,無疑是忘記了丑和美同樣來自于思想感官判斷,即使是丑的存在沒有像美一樣被哲學家、世人所認同,但其精神層面存在的地位不可被否定。固可認為,若先除去丑的本身不論,在美丑能夠對立并其核心質量對等的情況下,其本質是否也可像美一樣劃分出形式之丑和靈魂之丑二類,而靈魂之丑相對于靈魂之美,更加需要并也在現實判斷上大量填充了惡這一道德倫理意象的力量。但就如同前文中所提到的,在現今及以往的美學觀念中,任何形式之丑都是可經過藝術加工而轉化為美的,這就使得對于形式之丑的討論已失去了其存在價值和意義,使得原本分為兩個部分的丑的質量全歸于靈魂之丑之上,雖不可直接說靈魂之丑就是丑,即對于一個整體的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缺乏均衡和不連貫、不完整的丑,但可認為靈魂之丑代表了大部分我們面對丑時所形成的判斷和觀念依據。即使我們知道經過藝術加工或觀念填充,我們可將其轉化為美或認為其美,但我們對其仍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丑的感覺。因為我們對于一個事物的直觀判斷是與自身美的標準和符合規則的連貫性感受直接連接的,而像上述所說的丑轉化為美的過程是一種后期加工過程。但我們仍然可說靈魂之丑代表了丑的大部分本質意義,固也可說此時惡就是靈魂之丑,丑也就像羅森克蘭茨在《丑的美學》中所說的那樣:“丑即道德之丑。”
在此,惡與美的對立關系逐漸形成,而美是駁雜的,萬物皆可為美,而美相對的就是惡,那么惡也是駁雜的嗎?我們可以認為,其之間的映照關系就如同白天(美)和黑夜(惡),暗示了一個會形成變幻的全然光亮(或美)對立面,存在一個相對即穩定的黑暗(或惡)。惡或許會因其靈魂之丑的限定使其在內部相對于美來說更具統一性和一貫性,相對于美或其他意象來說更具有可衡量、可融合、可劃分的純粹性的反映。而如果將其放在人性之中來看更是如此。
(三) 在真實的人性中惡比美更具明顯的刺激性和純粹性表現
在現實中,我們對于善惡的處理和劃分因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或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但無論西方文化中思想觀念的差異如何,其人性部分中道德判斷標準即人性底線在人類意義上來說應是相同的。若我們將這一條處于人性中的線好好觀察,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似乎恒定的現象:在外部條件穩定的情況下,如果將這條線上移,別人不會說此人是一個善人,而只會做出是好人的評價,而若是將這條線下移,那么與之標準不符的人一定會說此人是一個惡人。這個現象也意味著人們對于惡的接受程度遠低于善(美),對于惡遠嚴格于善(美),換句話說,在真實的人性中惡比美對于人更具明顯的刺激性感受。波德萊爾在詩中頻頻使用內部丑陋不堪的意象,比如妓女、蛆蟲、腐尸、憂郁、孤獨等,未必無處于此方面的考慮。
而從另一個設例中,我們似乎也能得出在前文中所提及的惡內部統一性的觀點:若一個善人做過一千件善事,但他只要做了一件惡事,即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名偽君子,繼而在他人觀念中向惡人的形態轉變,而一個人做過一千件惡事,即使做了一件具有十足價值的好事,在眾人的觀念中似乎也無法成為一個全然意義上的善人。其中,他人對于善惡的判斷也許會帶有以往的思維慣性傾向,但其最終的判斷顯現出在人性條件下,即使美中包括可轉化的形式之丑,其巨大的包容性和寬廣的范疇也使其內部的穩固性、統一性和純粹性相比于惡來說顯得不足。而可能正是因為這一種人性中的差異性的表現,波德萊爾才會選擇以一種對照的方式去探索真實的美。
(四) 《惡之花》 中所體現出惡的純粹性及其呈現方式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惡的純粹性不僅表現在其內部的統一性和人主觀判斷的統一性上,還在于惡的本身。
在泛化的現實客觀環境中,可能會呈現出無限美而只對應一惡的情況,這也可以看出惡的濃縮和內在內容的豐富。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若不將美惡對立的環境設定在特定的條件下,是無法明顯看出惡對于美的觀照作用的,即也無法看出惡在此條件下的純粹部分。而《惡之花》則充分利用了這一點。
詩歌本身的文本屬性代表著一種天然的論域屬性。波德萊爾通過不斷的論域條件的轉換,以一個穩定的麻木不仁的哀傷世界作為論域,將個人理想、精神世界、繁華的巴黎社會作為條件,從一個完整的社會背面的角度去描繪真實的現實的惡,不僅除了其中的惡的形式上是純粹的,其本身也是純粹的。但這兩點我們只能通過詩人的詩句文本語言來體驗。此外,無論是追尋一種“死亡的勝利”,還是“想要在女巨人身上縱情狂歡”,這對于邪惡事物的道德化理解,都體現了其以一種純粹的態度來追尋物質和人類存在的本質意義,以打破真善美的一致性的決絕態度,來揭示一種社會應有的真實之美。其將惡的無形存在狀態轉變為具象化的存在象征,從而去揭露其真面目,豐富其本質,最終達到對丑惡、病態意象做出描繪,再現個人豐富的內心情感世界,抒發對陰暗社會的仇恨,揭示社會、人生的本質的最終目的和展露出藏在惡背后,或者在惡之上開出的真實之花的花朵。
二、惡最接近于“存在”
(一) 惡最接近于經驗世界中的道德本體
在經驗世界中,人對于惡的判斷多來自于主體的經驗所累積的道德標準,這種經驗可看為對傳統原始經驗累積的繼承和自身對于物質世界的認知。而道德本體在現實生活中呈現的形態或者說載體就是人,或者說是人的自由意志和思維模式。
我們通過自我的感官認識世界,再在意識中從認識再現現象和事實,并在這一過程中加上自己對于經驗世界傳遞過來的經驗的理解和繼承而合一形成自己的世界。透過這樣的模式,我們于是似乎可以這樣認為,每個人所認知的世界都是在共同的大的經驗世界和物質世界里嵌套入自我獨屬世界(也可認為是自我的自由意志和思維模式)而最終形成的世界。而每個人都是各自世界中的道德本體,即該世界中個人的道德標準就是個人的善惡;而社會是由無數人組成的組合世界,其看上去主要以大的物質世界為基礎,不斷地接受容納入個人的個體世界,從而形成最終個人眼中客觀大世界的主體。社會與人之間的紐帶聯系,代表著每個社會中的大的物質世界都會存在經驗、道德標準等能在每個個體世界中達成共識的精神共通認知的部分,也可以說是一種得到普遍承認的道德標準或思維模式,成為個人世界道德本體形成的先天約束條件,并伴生這康德所說的“先驗直覺理解模式”等由意識支配的行為模式和對于主觀和客觀世界的認知模式以及價值判斷。正因為有著這類條件的存在,大的物質世界才能夠接納不以具體數量來衡量的“無數”的小世界,并且這些小世界才能夠在所處的大世界中共存而和諧。但這樣的大小融合并不意味著大的物質世界對于小的個體世界的吞并。如果我們的客觀物質世界完全同化、吞并所有的小世界,那么只存在著一個社會,一個機體,即此時的“人”的概念不再代表著一個生物。而成為所有相同的此前被稱之為“人”的個體的總和稱呼,這于現實來說,明顯是不合理的。
同時,人時刻尋求著于大的客觀物質環境中的具有普遍性的在每一個時間和空間內達到的共同的認知基礎,并將其作為在自我的個體世界中的價值判斷的基礎,隨著外界的認知或者說物質世界中群體意識的變化而調整。比如說,一百年前我們認為為惡的事,此時的我們看待時并不一定覺得為惡,反之亦然。如果我們再將時間條件移除,在同一個空間內,殺一人、殺十人者我們認為罪大惡極,而殺千人乃至萬人者我們卻視之為梟雄霸主。其間的認知轉變在除去時間的隔斷后更加明顯。這一切的判斷都是來自于外界經驗對人的影響或者說促使人認知變化的影響因素來自于外界的社會,來自于物質世界和經驗世界之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對于人的意識、價值判斷,善惡取向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發生的,并且必有一定的限制條件,沒有無約束的絕對的善惡判斷。所謂無約束的,也就是指在時間和空間條件外,還應有一定的主觀或客觀的限制條件,不能無緣無故地去評定惡和善。這個“緣故”通常來說是指個人或當時社會所形成的道德標準,在與事實、現象對比之后發現的惡的不完善或者完善的善。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地對一個獨立個體做出善惡判斷,而當我們做出判斷時,一般是在確切地相信著得出結論所對照的客觀物質世界的現象,在社會或個人的道德判斷的情況之下。而所謂的不存在絕對的善惡判斷,簡單來說就是對于同一種行為,相同條件下的人看待時也會有不同的判斷結果,而自我的他人也可能是自己,不論是否是在相同的時間段內,一個人對于同一種認知的行為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并且,現象與人的善惡判斷之間交互也是雙向的,現象反映人,人判斷現象。第二,人的意識和價值判斷不能獨立,不能完全地脫離經驗世界和物質世界。誠然,我們不應該只相信、僅局限于經驗世界,但當我們完全脫離經驗世界變化而帶來的認知模式變化后,人在認識善惡行為時,無法從過往中汲取依據或憑借經驗上賦予行為價值判斷,而只能憑借直覺呈現出未知的狀態。此時,人真正成為完全意義上的道德本體和善惡依據。如果我們設定存在第三種格局,即道德的最高處是無善無惡的(但我們應當明白,這里的高度是通過消除來得到的,而不是疊加),因為經驗世界的消失,人也就成為個體世界的道德最高點,當人被限制于自己的本質時,不但惡失去了直接感受的事實合理性,而且善也失去了這一根據,于是便有可能出現萬物皆惡或萬物皆善的極端,而當道德經由增加累計到達最高點時,也往往是無善無惡的。在宗教中,人不能超越世俗而被限制于自己的本質中,所有的解釋權和原因都歸于造物者的意志、選擇和行為,而在這類情況中,這一切都歸于個人。
惡的存在在經驗世界中來說是合理的。在經驗世界中,我們的思維運轉往往依照邏輯,而邏輯思維所帶來的便是附加在事物或者現象上的因果關系。客觀物質世界因為因果關系的存在而形成了認知上的閉環而得以顯示出存在,即使因果關系最終來說也只是我們附加在物質之上的直覺。因果關系的存在使得現象的產生,現象的產生向我們彰顯出物質的存在。而“惡”對于我們來說也是如此,行惡是“利”的驅使,惡是“欲念”的轉化,因為“想”的意志,所以有了“要”的行為。不會存在無緣故的行惡,即使是最窮兇極惡的、以殺人為快感的人,對于自我的行為,也存在著淺顯的因和最根本的因,童年陰影、精神病征等都是因。那么既然惡的存在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中存在著合理的因果關系,那么惡對于我們的經驗世界來說就是合理的。
惡具有主觀性,這一點其實很好理解,每個人的惡人只是一個人的惡人,所謂的惡人必然是某人的惡人,離開了主體,惡是不存在的。同時,惡也存在著某種普遍性質——行惡相較于行善,無論是在心理還是行為上的所需克服的門檻都要低得多。我們的意識可分為意志和自由意志,意志指本性,自由意志指人心,但相對于衡定的本性來說,自由意志往往顯得極不可控、非常不穩定。外界的刺激對于自由意志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可以將本體行善或行惡的行為選擇看為二者之間于經驗世界和物質世界之中的矛盾,當意志的控制力大于自由意志時,我們的行為是可控的,符合我們所謂善的概念的,而當自由意志的控制大于意志時,我們的行為是不可控的,符合我們所謂的惡的標準的。于是我們可以開始思考,在客觀物質世界中,我們的意識和行為大多數時間內是由何種意識支配的,結果十分明顯,墮落總比向上容易,下墜總比攀登容易,行惡總比行善容易。對于人來說,惡是從心底的細微處緩慢而廣大地滋生的,善是在大處快速而狹小地宣揚的。
(二) 從惡的行為反映出人的實際欲望,接近于人于社會中的真實行為
在現實生活中,善惡是并存的,“善象”不斷發展,“惡象”也不斷發展。而惡的產生與我們的欲望跟我們所獲得的之間的距離非常有關。其二者之間的距離越大,個人的趨利心理越強,行惡意識的誘惑越大,就現在《毀滅》 一詩中所說的:“魔鬼在我的身旁激動不已,在我的周圍/ 仿佛摸不著的空氣一樣飄蕩/我一口把他吞下去,卻感到他給我的肺/燃起火來,使它充滿有罪而永不消失的欲望。”a
人不僅會在對善產生失望時才會去行惡。當這個距離大到打破了自由意志和意志矛盾的臨界點時,欲望戰勝理智,需求大于規范,于是人做出了惡的行為。我們可以僅就單個的距離問題來說,就比如人對糖果和對金子的欲望是不一樣的,人、糖果、金子處于同一時空內,此時的人想要吃糖,想要金子,設定人對于糖和金子的概念與現實生活相同,吃糖的欲望會逐漸變小,因為人與糖之間的距離即欲望和獲得之間的距離是小的,還不足以打破自由意志和意志之間的平衡。但我們對于金子的渴求卻會逐漸放大,直至打破道德規范與惡的平衡,產生惡的行為。當然在這個論域中還缺少很多必要的設定和約束來保證設想完整而有據地進行,但這些因素如果放置在現實社會中的人的身上便很難進行把控,因為客觀物質條件在時刻的變化中,總是運動的狀態,個人心理和對于道德規范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我們不可能在現實中找到一組完美對立的標本或現象進行論述。此番所講,只為說明我們的欲望與獲得距離的存在,在社會道德約束下的人心中對行為的善惡衡量的存在,惡念的滋生是因為利、欲望的存在。而從事實上講,我們無法可知一個人惡的心理的成長過程,而最終只能通過打破善惡心理平衡后人的行為來看出是否具有惡的性質。
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欲望與我們所獲得的之間距離的存在是必然的,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是必然存在的,因為物質世界是有限的。我們所得的是有限的,因為獲得的有限而必然產生對于更多的無限的追求。如果世界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的,就不存在多和少的意義,也不再需要金錢和權力等用于爭求利的輔助工具。我們的欲望與我們所獲得的之間的距離在物質方面即為零,惡逐漸消失,與之對立的善也逐漸消失,此時的矛盾反歸于對于我們自我生命的本身。但現實不可能如此,其注定有限的條件,明確了“利”的必定存在,顯示出欲望的存在,也即惡的行為的必然發生。于是,從人的行為我們可以看出其具有惡的性質,我們可以換而言之,即人的惡的行為可以看出人的欲望,不論這欲望是否真實。
但同時,人善于通過偽善來掩飾自己的欲望。《毀滅》:“他往往化為最富有魅力的嬌娃/因為他了解我對藝術強烈的愛好/他又在偽君子似是而非的借口下/使我的嘴唇習慣于不光彩的媚藥”。因為自身利益需求而去追尋“利”,往往會通過偽善的形式掩飾,從而達到最終惡的目的,這使得從善的角度來評判帶來困難。道德惡的含義從唯物論的觀點上看,一般意義上來說,凡是符合某一群體或階級的道德原則和規范所要求的道德現象和道德行為,就會認為是善的,反之就是惡,也就是說,善就是利人,惡就是損人。但就個體來說,其間的劃分絕無如此干脆明了。在人的意識中存在著善的概念和惡的概念,但何為真善,何為偽善,偽善是否為惡?
這方是我們所考慮的重點。每個人的本性不同,本心也不同,后天教育不同,教化所產生的影響不同,生存環境的不同等個人、物質環境因素的不同,使得其對于普通個人的道德約束的結束程度和貫徹程度不同:有的人真心行善,有的人為善而善,有的人假善而惡。當然此時的善惡標準是以客觀現實生活中的善惡概念為準,因為我們不可能去討論無邊際的善惡問題,如果一個人的善實為社會的惡,那我們也無法展開實際有效的討論。真心為善如果確定為真善的標準,即“自身為善”,那么“為善而善”與“假善為惡”便可看作為偽善,即為符合他人眼中善而行的善,無論是“為善而善”的心理狀態,還是“假善而惡”的行為狀態,都帶有虛偽的成分。但可認為,“為善而善”的狀態在偽善中無論真實的心理出發點是否為善,其最終所呈現的,是偽善積極的一面,而“假善而善”的狀態,雖無法將其明確歸于偽善還是惡,其意為做著一個表面為好事的壞事,比如借助公益的名義洗錢,其公益的一面為善,其真實的一面為惡,其間是無視善的一面根據最終的目的來劃分為惡,還是兩者兼顧劃分為偽善,難以抉擇,但就其于偽善相關的一方來說,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偽善惡的消極的一面。偽善的特征是內在的自然德性與人為德性之間的矛盾,外在的思想與言語的矛盾,言語與行為上的矛盾。但問題是,我們最終對行為所做出的善惡判斷,最終只能從其言語、行為等實際表現和所引起的反應是否是積極正面的,。這不僅是因為單純以人的善惡概念來評斷是不客觀的,而是最終也因為我們無法得到他人的思維。因此我們只能從其行為外顯的最終效果來評判善惡,只能從最終惡的行為的判斷上也推測出其真實的欲望。因為無論如何做出善的意圖,也掩飾欲望,其行為最終顯現的惡是無法改變的,就是說惡接近于人的真實欲望。
一切惡的行為都是可以被修飾的,無論是文本中的還是現實生活中的,我們都可以通過語言對行為的扭曲,或下一行為對上一行為的疊加來模糊、修飾人的真實的行為。善可以修飾惡,可以改變惡的形態,隱藏惡的行為的真實性,這使得惡的行為本身就代表著人的行為的真實。人似乎擅長對善的夸揚和對惡的隱藏。《異教徒的祈禱》:“啊,肉體的享樂,請永遠做我的王后!/請戴起由天鵝絨與情欲/構成的美人魚的假面具。”b其以詩的語言在擁有善的道德標的同時,又對于惡的事物有著先天的著迷和趨向,惡不僅包含了丑的最終源頭和歸宿的意義,一切未知的事物也類似的屬于惡的范疇。人類向來愛看殘忍場面。這類隱藏在本性中的未可定性的心理,類似于精神病癥群一般,努力尋找著一切善的表象,成為集體狂歡或無節制的性行為的借口。
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因為物質層面基礎生活的需求,我們大部分的行為都是趨利。而以趨利為目的,在有限的世界中,這樣的行為就必然會帶有惡的潛質,只是在于是否最終被觸發,形成行為,造成影響而被視為惡的行為。在善惡對立的狀態下,善對于人來說更像是一種道德要求,而惡則更像是人的自由意志而轉化而成的真實行為,但不是說行善是困難的,而行惡便是有理由的、合理的,因為人性在其現實上具有多樣化,所以道德教化、規范約束和道德他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波德萊爾選取惡作為方向也體現出反映人的真實的行為和顯示現實的虛偽。
三、從詩的大觀來說
波德萊爾在《七個老頭》中展現了在美麗的巴黎清晨,詩人看到的確實骯臟的黃霧、陰沉的街道、眼前穿著破爛的黃衣服。其深入邪惡中體驗美,在性和毒品的刺激中尋求精神的慰藉,企圖創造一個自我的“人工天堂”。
波德萊爾思想上的二重性趨向于一個不可得的純粹精神世界,而面對這個世界,波德萊爾將悲哀看作一種榮耀,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理想世界的幻滅中蘊含的孤獨絕望的情緒。在波德萊爾的詩境中,惡是大美的背景和映照,惡最接近于“存在”。其選擇丑惡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必然。對于《惡之花》來說,將社會底層被遮蔽的統一的惡的表現作為美歌頌的載體,以一種最刺激、直觀的方式向讀者講述人和社會的存在和價值。行惡是人最真實也是最習慣的行為不必再加以掩飾,對于善良的天性來說,無論給予他人多少純粹的善良,都無法掩飾惡的存在。其想要于當時的社會中尋找到精神的歸宿——既然向上已不可得,那么不如直面社會中的偽善和其中的丑惡,在一種真實之中找到意義和美。
ab 〔法〕波德萊爾:《惡之花》,張秋紅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頁, 第362頁。
參考文獻:
[1] 宋敏.波德萊爾《惡之花》 中“惡”的體現及其內涵探究[J].淮海工學院學報,2018 (12).
[2] 〔意大利〕翁貝托·艾柯《丑的歷史》[M]. 彭淮棟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3]沈順福.論惡的本質[J].中山大學學報,2010 (6).
[4] 石永之.陽明子的至善論及其當代意義[D].四川大學.2005.
[5] 李培,曹薇.道德惡的本質研究[J].現代交際,2010 (10).
[6] 鐘海北.淺談波德萊爾《惡之花》丑的審美意象[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4(8).
作 者: 朱濠煴,湖州師范學院求真學院2017級本科生。
編 輯: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