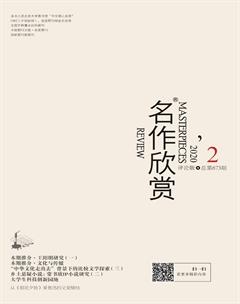超現實小說的“平衡—失衡”敘事結構
摘 要: 沈大成的短篇小說集《屢次想起的人》中收錄了大量超現實小說,在情節設置與敘事結構上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本文從托多羅夫的敘事語法理論入手,以《屢次想起的人》為例分析超現實小說的“平衡— 失衡”敘事結構,詳細論述初始平衡態、失衡態、再平衡態三種基本狀態,并在文末提出一個運用本文所述結構構建敘事情節的小說范例,以期增強敘事結構的應用價值,協助寫作者跳出固有寫作模式,開創全新的故事類型。
關鍵詞:超現實主義文學 敘事結構 敘事語法 《屢次想起的人》
沈大成創作的超現實小說主要見于《萌芽》 雜志“奇怪的人”專欄和短篇小說集《屢次想起的人》。《屢次想起的人》收錄了十五篇小說,塑造了各異的人物,如殺死了無數個自己的小說家、胸口長著口袋的少年等。這些小說相互獨立,但其敘事卻具有高度一致性,總體上呈現出顯著的“由平衡轉向失衡、再從失衡回到平衡”的轉變,并通過這樣的方式推動情節的自然發展。
托多羅夫曾借《十日談》 系統地闡發了敘事語法理論:“一篇敘事中會有兩個序列,一個描寫某種狀態,一個描寫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a在沈大成創作的超現實小說中,由于對情節虛構性的更高要求,這一結構更為顯著。因此綜合敘事語法理論與《屢次想起的人》 具體內容歸納出“初始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基本敘事結構,由此解讀沈大成向讀者展示的富有魅力的幻想世界。
一、初始平衡態:偽裝的藝術
超現實小說的敘事是在現實之上展開的,沈大成在《屢次想起的人》 中為主人公賦予了真實的職業,有小說家、玻璃清潔工、瑜伽教練等。除了職業,還有部分主人公的故事來源于一些常見的生活現象,例如失眠、搬家甚至情緒失控。以上兩類之外,個別主人公被和一些相對特殊但是又不超出現實的身份相聯系,有智力障礙、肥胖人群、殺人逃犯等。一言概之,超現實小說的主人公最初都處于一種具有現實性的平衡態,筆者將其命名為初始平衡態。
在《閣樓小說家》 中,開篇一個小節即描述了小說家的日常生活——在出版社的編輯們下班后,小說家外出散步,路遇保安并向對方問好。在小節結尾以一句“小說家定居在出版社”作補充,直敘小說家與保安等人保持有穩定而融洽關系的原因,完整地補充了小說家生活的邏輯鏈,交代了小說的初始平衡態。《閣樓小說家》 的平衡態以“小說家”的職業為核心,在作者的敘事中又添加了長期生活在出版社、人際關系良好、生活規律、完美主義等諸多要素。
事實上,小說的初始平衡態無非是背景介紹與初步的人物塑造,但由于超現實的特性,初始平衡態在實質上成為“暴風雨前的寧靜”。沈大成在跋中自述超現實小說的特征是“假”,而初始平衡態卻是“假”前的“真”,是對后續超現實情節的偽裝。這種在平凡中隱匿不平凡的技巧,正是沈大成處理超現實帶來的真實性缺乏的高超之處。
二、失衡態:初始狀態的異化
異化是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常見的現象,諸如卡夫卡《變形記》中格里高利化作甲蟲等。異化往往緣于某些外在壓力或客觀變動,又進一步推動情節繼續變化,為后文的不合常理創造合理性,有著承前啟后的功能,是超現實小說的靈魂所在。
布勒東認為:“超現實主義的基礎是信仰超級現實,這種現實即迄今遭到忽略的某些聯想的形式,同時也是信仰夢境的無窮威力和思想能夠不以利害關系為轉移的種種變幻”b,他將現實“超現實化”,即“異化”的方法歸結為聯想與無意識的夢境。在《理發師阿德》中,作者為阿德設計的異化就出于聯想,理發師的職業很容易與頭發發生關聯,作者基于這種聯想將理發師阿德異化成以頭發為食的特殊人類;而在《口袋人》中作者則將主人公坡置入夢幻般的無意識,創造了擁有皮膚夾層的口袋人形象。
異化是誘發失衡態的途徑,其方式多種多樣,一部分是通過主人公自身的改變實現的,如癡迷于擦玻璃、在四十歲時可以分裂成兩個人;另一部分是通過外部環境的改變而對主人公產生間接影響,如遇到了死而復生的偶像、發現隔壁房間每天生產不同的人。為達到失衡狀態而必需的異化,在敘事語法中對應體詞的描述面,與傳統小說不同,超現實小說的異化與失衡態是超現實的,這也是其與現實主義小說的主要區別。
在《理發師阿德》中,鋪墊了阿德在小鎮里悠然的生活后,筆鋒一轉阿德被異化成以吃頭發維持生命的特殊人類。在此需要說明雖然阿德在被作者異化之前就已經處于“吃頭發維生”的狀態,但是由于這個狀態不被讀者了解,出于敘事的考慮,筆者僅將讀者認知到的阿德形象改變之后的狀態視為失衡態。
失衡態作為引發矛盾的導火索是超現實小說的核心。沈大成對于失衡態的認識是“調動現實世界的某個數值,使社會的方程式錯亂”c。但是需要認識到的是沈大成筆下的異化并不是隨意的,而是具有目的性的,其目的也正是小說要表現的主題,經過超現實的失衡后,小說的表現力得到了大幅增強。
三、再平衡態:潛伏態與轉化態
當敘事處于失衡態時,主人公正身陷不利的僵局,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延續下去,主人公會做出努力,推動情節走向下一個平衡態,筆者將其稱為再平衡態。事實上,在真正過渡到再平衡態之前,還存在著兩種潛在的二級狀態,即潛伏態和轉化態。潛伏態和轉化態是對立的,潛伏態是失衡態自行發展所帶來的新平衡態,這種狀態往往是主人公要盡力避免的,而轉化態則是主人公為了避免潛伏態發生而做出的選擇或改變。
在《脫逃者》中,病人因調節理性與感性的旋鈕失控而被送入醫院,此時他面臨兩種發展方向:潛伏態是留在醫院度過缺乏情感的余生;轉化態是選擇脫逃,享受自由的情緒變化。主人公最終選擇了出逃即轉化態,開始了在人們庇護下自由的流亡生活——進入了一種再平衡態。
然而有時轉化態會因某些原因而顯得不合情理,產生古希臘戲劇中“機械降神”的效果,即安排一些特殊人物的出現扭轉或者終結情節,這里也引申為主人公自己做出某種超乎尋常的舉動給情節帶來改變。在《分段人》文末出現的更高級的分段人給予主人公的人生以新的轉折,《閣樓小說家》中小說家最終殺死了過去的全部自己,都呈現生硬的特點。
當敘事由初始平衡走到失衡,再由失衡轉向再平衡,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才告一段落。兩至三個結構首尾相連,便能構成一篇超現實小說。若說初始平衡態是在將假偽裝成現實,失衡態是在造假,那么再平衡態則是在圓謊。超現實小說的再平衡態令小說情節再次回到現實的正軌,為讀者營造了一種精巧的回歸感,如《口袋人》結尾“此后靜靜地陪伴我,等待飛機從雪空降落”d般自然收束,不失余韻。
四、一場寫作實驗:《電梯里的人》
在全面分析了《屢次想起的人》一書中的敘事結構后,運用這一結構進行超現實小說的創作便產生了新的可能性。
首先,選取主人公的身份與一個常見生活現象來構成該篇小說的初始平衡態。因此賦予主人公以上班族的職業,構建了乘坐電梯為背景現象的世界,并令主人公以“我”的第一人稱視角敘事。在“上班族”的設定中,隱藏著家庭矛盾、工作壓力大、生活不順利等隱藏的條件,支持著異化的發生。其次,將“同‘我一起乘坐電梯的人看不見‘我”作為“我”的異化條件,并由此引導“我”的生活轉向失衡態,“我”開始沉迷于別人看不見“我”的生活。最后,為“我”恢復到再平衡態構造潛伏態——“我”終究會走出電梯被人看見和轉化態——“我”從此不再離開電梯,在電梯中生活,為“我”選擇了轉化態的生活,使之回到再平衡態并以此表現現代人困苦的生存狀態與逃避現實的潛意識心理。
《電梯里的人》情節概括:我是一個每天乘電梯上下樓的普通公司職員,在公司工作堆積如山并被上司同事冷眼相待,回家后被妻子呵斥、也得不到孩子的尊重,在人際關系上一竅不通、缺乏友人。有一天我發現和我一起乘電梯的人看不見我,在電梯里我可以扮鬼臉、咒罵老板,隨心所欲而不受打擾。但是我一旦離開電梯又會變成可視的普通人,于是我在經歷了電梯中的生活與普通生活的多次強烈對照后,決定不再離開電梯,將食物、家具和生活用品等搬進電梯間,選擇留在電梯里度過隱形而輕松的余生。從此這個世界與我無關,我成了游離于現實世界之外的“超現實人”。
五、結語
閱讀沈大成《屢次想起的人》,不僅是在閱讀一本超現實小說集,還是在閱讀一位作家的敘事理念。從《屢次想起的人》中筆者分析出了小說創作的“平衡—失衡”結構,并且能借此初步構建一篇小說的敘事框架,給予超現實小說寫作以啟迪,但這并不能說明小說創作能夠套路化、公式化。敘事結構為文學作品提供的只是作者向讀者傳達思想的手段與工具,一部缺乏作者的人文關懷與讀者的心靈共鳴的小說,即使運用了華麗花哨的敘事結構,也是沒有靈魂的。文學即人學,學會敘事只是文學創作的第一步。
a 〔法〕茨維坦·托多羅夫;《散文詩學:敘事研究論文選》,侯應花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頁。
b 高建平、丁國旗:《西方文論經典(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頁。
cd沈大成:《屢次想起的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頁,第65頁。
參考文獻:
[1] 茨維坦·托多羅夫.詩學[M].懷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2] 沈大成.屢次想起的人[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作 者: 劉天宇,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