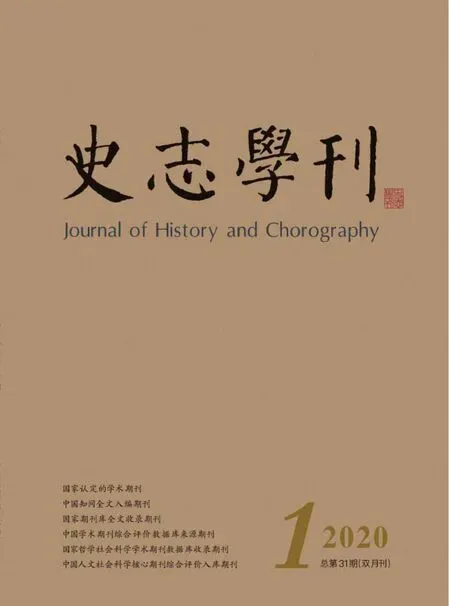先秦史官與上古神話的口頭傳播
葉慶兵
(山東大學文學院,濟南 250100)
一、史官與上古神話的傳承
《國語·楚語》載: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1]徐元誥.國語集解[M].中華書局,2002.(P525-526)
王孫圉以觀射父、左史倚相為“楚之所寶”,并評價左史倚相“能道訓典”“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這一評價也適用于其他史官。所謂“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可見史官對鬼神之事非常熟悉,這其中應該包含了不少上古神話。
《左傳》昭公元年載: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2]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P705)
從后文子產的回答可知,實沈、臺駘均為神話中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叔向向子產提問時特意提到“史莫之知”,言下之意,史官本應知道。由此也可見史官是上古神話的保存者與傳承人。
史官之所以保存上古神話,與其身份職能有密切關系。
首先,史官身份特殊,他們與巫有密切的關系。古書中巫、史常常聯稱,如《周易·巽》“用史巫紛若”[1]孔穎達.周易正義[M].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P129),《國語·楚語》“及少皞之衰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2]徐元誥.國語集解[M].中華書局,2002.(P514-515),《禮記·禮運》“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3]孔穎達.禮記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P421)。這些記載表明,史與巫有密切關聯。陳夢家先生在《商代的神話與巫術》一文中即指出“‘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4]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J].燕京學報,1936,(20).(P488-579);李澤厚先生《說巫史傳統》一文在此基礎上又有補充,認為史是巫的“理性化的新形態和新階段”[5]李澤厚.說巫史傳統[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P23)。
史源于巫可在文獻中找到依據,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回顧其家世云: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6]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1982.(P3285)。
重、黎是神話中“絕地天通”的神巫,追溯史官的源頭而至神巫,這也表明“史亦巫也”。史官不僅源于巫,直至春秋時期還保留了部分巫的職能。如《左傳》哀公九年載: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沉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后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7]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P1014)
占卜一般由巫承擔,而此處記載史趙、史墨、史龜均行占卜之事,可見,史官亦兼有巫職。
巫是溝通人神的特殊職業,《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8]袁珂.山海經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396)這是對巫溝通人神的神話化表達。巫要溝通人神,那自然要熟悉相關的神話故事。史源于巫,也繼承了巫的這一特性。
另一方面,就史官的職能而言,史官是文獻典籍的管理者。王孫圉評價左史倚相的另一特點就是“能道訓典”,所謂訓典,就是先王典籍。史官對于文獻的掌管,在歷史上有明確記載。《周禮》載: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掌贊書[9]賈公彥.周禮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P401-413)。
在這些豐富的文獻資料中,就包含了“三皇五帝之書”,其中必然也包括了不少的神話故事。
正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職能,史官成為上古神話的保存者,也因此,他們才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
二、史官與上古神話的口頭傳播
作為上古神話的保存者,史官又會將這些神話內容傳播開去,從而成為上古神話的傳播者。關于史官對上古神話的傳播,過去關注的主要是書面傳播的形式,如劉城淮先生在《中國上古神話通論》中認為“史官等的傳播為書面傳播,而酋長等的傳播為口頭傳播”[1]劉城淮.中國上古神話通論[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P229)。但實際上,史官傳播上古神話,也常以口頭的形式。
史官對上古神話的口頭傳播,常常體現在對別人提問的回答中,尤其是王侯的提問,如《國語·周語上》載: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得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耹隧。商之興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一,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貍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滅虢[2]徐元誥.國語集解[M].中華書局,2002.(P28-31)。
在這一段對話中,內史過講述了夏、商、周各自興亡的神話,還提到丹朱、堯等神話人物,而其對這些神話的介紹,源于周王的咨詢。又如《國語·鄭語》:
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
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且重、黎之后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2](P460-466)
鄭桓公詢問史伯,南方是否可以“逃死”,引起史伯講述了一大段神話,既包含南方的重、黎、祝融等神話,又涉及虞、夏、商、周的神話。
復如《左傳》昭公八年: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置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绖于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后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胡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1]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2001.(P770-771)
晉侯詢問史趙“陳其遂亡乎”?史趙作出回答,并從陳國的歷史進行分析,其中涉及顓頊、虞舜等神話人物。
史官在諫言時,有時也會主動講述上古神話。如《左傳》文公十八年載:
莒紀公生大子仆,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仆,且多行無禮于國。仆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大史克代季文子應對國君,雖然也是回答,但其性質與前幾處所舉應答不同,實際上是諫阻文公,在諫言中大史克講述了一大段神話內容: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梼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圣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德,丑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兇,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云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兇族渾敦、窮奇、梼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兇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兇人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兇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1](P352-355)!
高陽氏、高辛氏、帝鴻氏、少皞氏、縉云氏以及堯、舜等均為神話中人物。中國上古神話流失嚴重,而這段對話同時講述了有關這些神話人物的諸多故事,尤為可貴。
三、從神話的運用看先秦史官的現實關懷
從上文來看,史官在上古神話口頭傳播的過程中確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一些神話得以流傳下來,正依賴著史官。同時,從史官對這些神話的講述來看,其對上古神話的傳播是與現實密切關聯的,其中體現了史官的現實關懷。
首先,這些神話內容多因現實問題而被提及,史官講述這些神話是為了給現實問題提供借鑒。如《左傳》文公十八年所載大史克代季文子應對魯文公所講述的神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莒國太子仆弒君之后逃到魯國,魯文公因接受其饋贈而欲接納他,而季文子因其為弒君之人而將之驅逐出境。事后,季文子委托大史克應對文公的責難,大史克在應對中講述了高陽氏、高辛氏、帝鴻氏、少皞氏、縉云氏等神話人物之“不才子”的傳說,這些不才子被百姓視為兇族,而舜的功勞就是驅逐他們。最后,大史克將季文子驅逐太子仆與此照應,認為“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兇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顯然,大史克講述神話的目的是為了證明季文子的做法是正確的,是以神話故事為前車之鑒。
其次,從史官所講述的神話內容來看,其關注的重點并非神話故事的情節,而是神話中與治國理政相關的內容。如《國語·周語上》載內史過論神云:
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1]徐元誥.國語集解[M].中華書局,2002.(P28-29)。
國家興亡將有神靈預兆,而神靈之所以降臨又決定于國君的德行操守,國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則神靈降之以福;反之,國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則神靈降之以禍。又如《左傳》昭公八年,史趙論陳之不亡云“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胡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陳之不亡,由虞舜之德已經奠定了,可見君主之德的重要性。從中不難看出,史官講述神話時有意地作了價值引導,其目的在于通過神話故事說明國君修德在國家治理上的重要性。因此,雖然講述的是神的故事,其著眼點卻時時不離當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