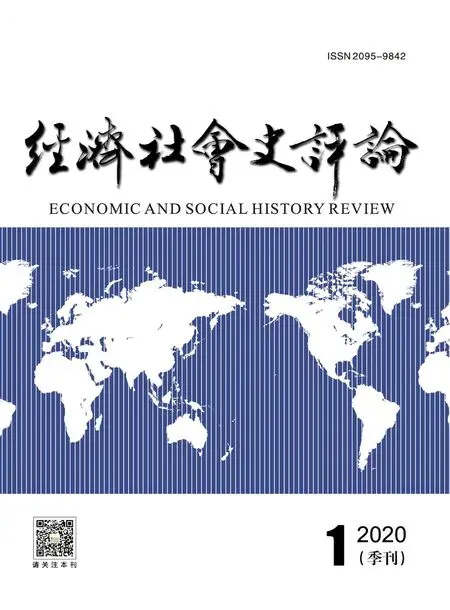卡爾馬聯盟:北歐向現代國家轉型的起點
劉俊豪
卡爾馬聯盟(the Kalmar Union)是中世紀晚期丹麥、瑞典、挪威在丹麥王室統治下結成的聯盟,涉及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聯合。①當時芬蘭從屬于瑞典,冰島被挪威征服,所以這一聯盟具有地區整體性。卡爾馬聯盟的建立保障了北歐國家的整體利益,有效地遏制了德意志漢薩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勢力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擴張。其后,聯盟共主埃里克七世(Erik VII)又分別與英、德兩國聯姻結成了兩個重要同盟,增強了卡爾馬聯盟在歐洲的影響力。但是,聯盟隱含的離心傾向和丹麥王室的一些政策性失誤導致其他王國的強烈不滿,最終在漢薩同盟的挑唆下,瑞典單獨擁立貴族古斯塔夫·瓦薩(Gustavus I Vasa)為國王,宣告了聯盟的解體。卡爾馬聯盟作為一個北歐國家聯合體的嘗試,其歷史意義不容小覷。
北歐國家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在《拉丁與條頓民族史》中就把斯堪的納維亞民族視為歐洲六大民族之一②利奧波德·馮·蘭克:《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付欣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頁。,而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也說,“斯堪的納維亞民族雖然加入較晚,然而這一方面完全無關緊要”③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p. 50.。湯普遜(J. W. Thompson)曾指出卡爾馬聯盟成立后很大程度上排擠了漢薩同盟在北海、波羅的海的勢力。④詹姆斯·W. 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徐家玲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近年國外學者更有一些新的認識,如斯韋勒·巴奇(S. Bagge)認為卡爾馬聯盟的成立并非是國家形成的倒退,因為它推動了一種新型國家形態——現代國家的出現,是一個歷史進步;他還提出現代國家是君主制的衍生品,也是教會的衍生品,這一點在斯堪的納維亞尤為明顯。①Sverre Bagge, Cross and Scepter: The Rise of the Scandinavian Kingdoms from the Vikings to the Reformation,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Introduction.《新編劍橋中世紀史》認為卡爾馬聯盟是北歐國家為了對抗漢薩同盟在北歐的商業貿易壟斷和政治干涉而成立的。②Christopher Allmand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I, c.1415-c.15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71-706.《劍橋斯堪的納維亞史》論述了14世紀末北歐地區局勢的急劇變化使得三個北歐王國走向聯合,而隨著1523年瑞典的獨立,中世紀晚期北歐三國聯合的卡爾馬聯盟時代最終結束。③Knut Hel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83-770.國內也偶爾有學者關注卡爾馬聯盟問題。④敬東主編:《北歐五國簡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75—79頁;孫培培:《卡爾馬聯盟的歷史演進——從14到16世紀》,碩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7年。本文聚焦于卡爾馬聯盟的歷史發展脈絡,以瑞典和丹麥為主要考察對象,因為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幾個國家中,只有瑞典和丹麥在幾個世紀里歷經了建構獨立國家的過程⑤Tim Knudsen and Bo Rothstein, “State Building in Scandinav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6, No. 2 (January 1994), p. 204.,重點則論述卡爾馬聯盟對北歐王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影響。
一、“前卡爾馬聯盟時代”的斯堪的納維亞
1.漢薩同盟與瑞典的混亂政局
早在呂貝克(Lübeck)建城起,德意志商人就與瑞典建立了商業聯系。13世紀中期,漢薩商人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經營手段盤活了瑞典經濟。如呂貝克人通過提供技術和資金控制了貝格斯拉根(Bergslagen)⑥貝格斯拉根位于瑞典中部地區,當地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的采礦業。德意志移民逐漸在瑞典商業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瑞典經濟隨之對漢薩同盟產生了依賴。到13世紀末,瑞典國王不得不通過給予特權、免除義務等優惠條件迎合德意志商人。德意志人“相對充足的資本和使用的大商船,使他們比瑞典商人更具優勢;不僅在哥特蘭地區,在瑞典的其他地區也是如此”。⑦尼爾·肯特:《瑞典史》,吳英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第33頁。1250年以降,哥特蘭(Gotland)島上的主要城市維斯比(Visby)已由德意志商人控制。14世紀初,呂貝克完全控制了哥特蘭島,主導著斯德哥爾摩一線的貿易。這種局面主要是由于瑞典國內政局混亂,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君主政權,大貴族相互傾軋,無法全力應對來自外部的威脅。
中世紀瑞典政治的特點是缺乏一種穩定的王位繼承秩序,導致貴族輪番把控政權。1317年,瑞典貴族利用國內爆發的大規模反國王浪潮攫取了政權,兩年后在烏普薩拉(Uppsala)推舉年幼的馬格努斯·埃里克松(Magnus Eriksson)為瑞典國王。他們“選擇馬格努斯·埃里克松的一個因素是,國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親政,這將給顯貴們提供鞏固自己特權的機會”。①Birgit and Peter Sawyer, Medieval Scandinavia: From Conversion to Reformation, circa 800-1500,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81.他們的利益在隨后起草的一份具有憲章性質的法律文件中得到保證。條文確認了貴族和教會的特權,提出君主征收新稅必須得到政務會(Council of realm)的同意,強調瑞典國王要由選舉產生。成年后的馬格努斯努力擴大王權,與貴族矛盾激化,1363年貴族們合力將國王驅逐。但是,國王在位時將幼子哈康(Hakan Magnusson)與丹麥公主瑪格麗特(Margrete I)聯姻,“這一舉措為長期的王朝沖突提供了解決辦法,并有利于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未來都聯合在一個王朝的統治下”②尼爾·肯特:《瑞典史》,吳英譯,第29頁。。這為卡爾馬聯盟的建立埋下一支伏筆。
2.丹麥與德意志在波羅的海的較量
丹麥與德意志對波羅的海的爭奪由來已久。斯堪尼亞(Scania)在13世紀后期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性貿易區域,呂貝克人利用對鹽準入市場的壟斷逐漸控制了此地的貿易。“奇怪的是,斯堪的納維亞王國中最強的丹麥,卻是最后一個針對日耳曼貿易采取保護性立法的國家——之所以奇怪是因為,丹麥比挪威更早感覺到日耳曼商業特權的影響。”③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庫克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3卷,王春法主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37頁。
到13世紀后半期,丹麥王權衰弱,“不能應對貴族和高級教士日益膨脹的野心”④Michael Jones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 c.1300-c.14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21.。在1282年召開的尼堡(Nyborg)會議上,國王埃里克(Erik V)被迫與貴族簽署了一份法令,宣布貴族可以組成政務會為王室提供政策性建議。從此,丹麥貴族就可以合法地限制君權,其勢力更加膨脹。直到丹麥歷史上偉大的瓦爾德瑪四世(Valdemar IV)在位時,國王才通過教會的支持、收回王室領地和給予部分城市特權的方式逐漸增強了王權。瓦爾德瑪四世為恢復昔日丹麥在波羅的海上的強盛地位,從14世紀60年代起,他收回斯堪尼亞、攻占維斯比,這威脅到了漢薩同盟在波羅的海的利益。漢薩城市為繼續其壟斷地位,在1367年組織了科隆軍事政治同盟(the Confederation of Cologne),于1370年徹底擊敗丹麥,并與之簽訂了《斯特拉爾松和約》(Peace of Stralsund),規定丹麥將斯堪尼亞租給漢薩同盟15年,允許同盟船只在松德海峽自由航行,漢薩同盟有權干預丹麥的王位繼承。此和約使漢薩同盟完全控制了這一區域的貿易,主導了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的貿易集市。“其實漢薩同盟城市對整個波羅的海地區保持一種嚴格的政治、經濟霸主地位,實際上將波羅的海地區當作它們的‘后花園’,只能接觸漢薩同盟的商人。”①克努特·耶斯佩森:《丹麥史》,李明、張曉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3頁。出于對呂貝克及德意志勢力的恐懼,三個王國均有了結盟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君主(指瑪格麗特——引者注)想把這三個王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權存在。”②Knut Hel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20, p. 686.
3.北歐聯盟的建立
1363年,瑞典貴族操縱政務會選舉梅克倫堡公爵的次子小阿爾布萊希特(Albrecht the younger of Mecklenburg)③他是梅克倫堡的阿爾布萊希特(Albrecht of Mecklenburg)與馬格努斯的妹妹之子。為國王,在漢薩同盟的支持下,小阿爾布萊希特隨之順利入主斯德哥爾摩。“阿爾布萊希特國王向他的德意志同胞授予了重要封地和職位,這讓瑞典貴族無法容忍,并逐漸出現了強大的反對派。”④Vivian Etting, Queen Margrethe I (1353-1412)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dic Un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04, p. 52.而且小阿爾布萊希特還要求貴族歸還他們之前從王室手中非法奪走的財產,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在這種危急情況下,瑞典貴族轉而向丹麥的瑪格麗特女王求助,他們認為三個王國在一個共同的君主統治之下會有利于保持自身特權。1389年,丹麥女王瑪格麗特在阿斯勒戰役(the battle of ?sle)中擊敗了小阿爾布萊希特,她被三個北歐王國擁戴,斯堪的納維亞在中世紀晚期達成聯合的基礎由此奠定。
卡爾馬聯盟是以王朝聯姻、五國⑤這一聯盟在地域上涵蓋了今天的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和冰島等國家,當時是丹麥、瑞典和挪威三個主要王國的聯合。共主的方式建立的。1389年,丹麥和挪威的貴族們選擇瑪格麗特作為兩國女王后,瑞典也如法炮制,授權瑪格麗特提名未來的國王,瑪格麗特選擇其養子——波美拉尼亞的埃里克(Erik of Pomerania)作為繼承人。1397年,埃里克作為三個王國共同的統治者在瑞典小城卡爾馬(Kalmar)加冕,即埃里克七世(Erik VII)⑥丹麥世系為埃里克七世,在瑞典則稱埃里克十三世。。“6月17日,包括隆德和烏普薩拉大主教在內的三個王國的貴族以及教士,都目睹了埃里克的加冕。”⑦Michael Jones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 c.1300-c.1415, p. 722.至此,北歐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政治聯合體——卡爾馬聯盟正式誕生。盟約規定:各王國應保持各自主權;各國按照本國原有法律統治,在任何一個國家被判處犯罪的人,在其他國家也被視為罪犯;如果其中一個王國與別國處于戰爭狀態,其他盟國也必須全力援助。另外,盟約還提出“每個王國都應保留自己的法律、習俗、參議會和各種特權;最高官員應從當地人中挑選”⑧Paul C. Sinding, History of Scandinavia: From the Early Times of the Norsemen and Viking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udney and Russell Publishers, 1859, p. 148.。
二、卡爾馬聯盟的歷史演變
1. 聯盟成立初期的成就
“聯合起來的北歐王國已成為改變歐洲政治格局的因素之一。”①Knut Hel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20, p. 728.卡爾馬聯盟的版圖覆蓋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還有無數個島嶼,如冰島、格陵蘭島等。瑪格麗特成為斯堪的納維亞的無冕之王,實際上在其有生之年都對整個聯盟有著行之有效的控制。瑪格麗特致力于中央集權,建立了高效的中央財政管理體系,聚斂了大量的財力,1408年從條頓騎士團手中贖回了哥特蘭島。同時,她限制貴族力量,增強王權,“在丹麥,她禁止興建私人城堡。……她盡量減少對教士和貴族的免稅地產,當然這一做法受到反對。在地契被徹查后,大量的土地被劃歸王室所有”②Christopher Allmand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VII, c.1415-c.1500, p. 676.。這顯示了聯盟成立初期君權得到強化,1398年梅克倫堡人歸還了斯德哥爾摩,諾爾蘭和芬蘭也不再反抗,而一直抵抗的哥特蘭人也于1408年最終屈服,整個北海和波羅的海地區似乎安靜了。更重要的是,它的成立嚴重地削弱了漢薩同盟的勢力。“女王強迫同盟放棄對丹麥的直接政治控制,交出同盟占據的堡壘,廢除同盟實行的稅收。同盟不得不接受其在丹麥水域的巨大損失。當同盟向她找麻煩時,女王便暗中支持海盜襲擊他們,報以雙倍的騷擾。”③詹姆斯·W. 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249頁。這個被丹麥人世代崇敬的女王以勇敢對抗外敵著稱,直到臨終她也沒有放松對漢薩同盟的打擊。
為了鞏固卡爾馬聯盟的政治影響力,埃里克親政后,通過聯姻結成了兩個重要的同盟,一是他本人迎娶英國公主菲利帕(Philippa),再是其妹妹卡特里娜(Katerina)嫁給神圣羅馬帝國王子巴伐利亞的約翰(Johann of Babaria),“這些行動有助于更牢固地強化他的地位,使他躋身歐洲勢力最強的統治者之列”④尼爾·肯特:《瑞典史》,第31頁。。卡爾馬聯盟及政治聯姻無疑對中世紀晚期歐洲地緣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
2.丹麥霸權的出現
北歐大聯盟建立起來后,由于丹麥國力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最為強大,更兼女王瑪格麗特精明強干,在她實際統治的十幾年里,政權向中央集權方向發展的趨勢愈發明顯,她派遣直接聽命于君主的行政官員負責推行國家行政管理,王室權威逐漸增強。在15世紀初,瑪格麗特和其繼任者波美拉尼亞的埃里克都時常把丹麥利益凌駕于其他王國之上,丹麥王權壓制了各地貴族,“在這個世紀剩下的時間里,一連串的統治者都努力在丹麥建立控制權,并說服挪威和瑞典的大貴族接受他們的統治”⑤David Kirby,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arly Modern: The Baltic World 1492-1772, New York and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3, p. 42.。“她在瑞典建立了強大的財政管理:稅收被簡化、永久化,估價都采用貨幣而非實物。在那里,國王地區代表通常從丹麥更低層的貴族中選拔。最后,大約在1400年,她完成了對地產的大規模回收——這些地產都是皇室在14世紀下半葉晚期在丹麥和瑞典失去的。”①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庫克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3卷,第326頁。顯然,這傷害了瑞典王國的利益。
埃里克國王繼承了女王瑪格麗特的貨幣稅改革政策,這固然有助于加強中央集權,但與實物稅相比,貨幣稅收卻給瑞典民眾增加了實際的負擔,同時埃里克國王實施的貨幣貶值政策大大損害了瑞典的對外貿易,這是后來瑞典爆發起義的重要原因。另外,石勒蘇益格ˉ荷爾施坦因問題也成為丹麥與各方爭端的焦點。石勒蘇益格原屬丹麥,但是由于與德意志互相通婚以及封建采邑制的影響,兩者關系非常密切。埃里克親政后意圖強制回收該地,召開政務會討論石勒蘇益格問題,并作出決議,“石勒蘇益格公爵由于反抗過埃里克國王,他的屬地被沒收,重新歸屬丹麥”②Christopher Allmand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I, c.1415-c.1500, p. 679.。石勒蘇益格領地歸屬丹麥使得后者實力大大增強,引起了漢薩同盟的恐慌,雙方發生戰爭。漢薩同盟封閉了斯堪的納維亞各港口,戰爭不可避免地連累了瑞典,給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人員損失,同時也阻礙了該地原材料與生活必需品的進口,瑞典民眾苦不堪言,反抗已不可避免。
從深層次來說,卡爾馬聯盟初期實行的中央集權是由政治上的獨裁體制導致的,不是經濟以及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所以這種中央集權或者王權膨脹只能靠強有力的君主來維持,一旦出現王位變更或者政策失當就容易出現動亂,1434年瑞典王國大起義便是例證。
3.卡爾馬聯盟后期的動蕩局勢
1434年6月,在小貴族恩格爾布萊克特松(Engelbrektsson)領導下,瑞典各階層聯合發動了一場反丹麥大起義。起義有礦工、商人和大量平民參與,同時得到本地教會和許多政府官員的支持,后來瑞典政務會也聯名響應。1436年,起義軍領導權轉移到卡爾·克努特松(Karl Knutsson)手中,1438年他在政務會得到廣泛支持。“在猶豫了一段時間后,貴族加入了叛軍,他們一起推翻了埃里克國王,先是丹麥和瑞典(1439年),最后是挪威(1442年)。”③Sverre Bagge, Cross and Scepter: The Rise of the Scandinavian Kingdoms from the Vikings to the Reformation, p. 251.隨后丹麥政務會支持了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III),1440年克里斯托弗即丹麥王位,次年也于瑞典加冕,1442年在挪威他也得到了擁護,聯盟得到恢復,而卡爾·克努特松則以補償芬蘭土地的方式被強制流放。1434—1439年瑞典大起義是一場瑞典各階層參與的反丹麥、反壓迫斗爭,各個階級不同程度地團結起來推翻了埃里克的專制統治,給瑞典的發展創造了新機遇,起義中瑞典民族意識開始萌發。
1442年,克里斯托弗頒布法典規定,瑞典城堡的土地應該授予政務會及其支持者,不應給予德意志人,這有助于瑞典國土的完整。1448年克里斯托弗逝世,丹麥政務會推舉奧爾登堡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I)為國王,1449年在挪威政務會也承認了他,而之前被流放的卡爾·克努特松卻謀取了瑞典國王(盡管他仍想做北歐國王),聯盟再次出現二主。到1471年,克里斯蒂安一世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戰爭準備徹底收服瑞典,但不幸在布倫克貝格戰役(the battle of Brunkeberg)中被擊敗。這次戰爭使丹麥再也無力對瑞典進行實質性控制,瑞典進入了斯圖雷(Sture)家族掌權時期。到1515年,時任瑞典攝政(regent)的小斯圖雷(Sten Sture the Younger)與烏普魯薩大主教發生嚴重沖突,1517年小斯圖雷及其盟友被開除教藉。這時丹麥王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 II)趁機出兵瑞典,經過幾次苦戰,到1520年才擊敗小斯圖雷的軍隊,得以重新入主斯德哥爾摩,并于當年11月加冕為瑞典國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為徹底根除瑞典貴族的分裂勢力,制造了“斯德哥爾摩慘案”(Bloodbath of Stockholm),“他在加冕盛宴那天,殺死了所有他懷疑反對自己的那一派貴族”。①Anders Bure, A Short Survey of the Kingdome of Sweden, London, 1632, p. 71.斯德哥爾摩事件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慘案消滅了大批實力派貴族,導致瑞典貴族力量受到很大損害,再也沒有恢復過來,這為后來瓦薩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打下基礎;另一方面瑞典民眾對丹麥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瑞典人再也無法融入聯盟之中。三年后的1523年,古斯塔夫·瓦薩被擁立為瑞典國王,聯盟解體。
三、卡爾馬聯盟與北歐王國的轉型
卡爾馬聯盟于1397年正式成立,其間分分合合,終于以1523年瑞典獨立為標志,宣告壽終正寢。雖然挪威還繼續留在聯盟內,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丹麥的屬地,而芬蘭則跟隨它的宗主國瑞典脫離了聯盟,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卡爾馬聯盟此時已經解體了。
卡爾馬聯盟對北歐現代國家轉型的影響至少有以下幾點:
其一,民族貿易得到關注,本土商人階層崛起。以往漢薩同盟能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暢行無阻,從側面反映出斯堪的納維亞本地商人的弱小。卡爾馬聯盟存續期間,總體上比較注意保護本地商人的利益,商人團體的力量漸趨壯大,這使得聯盟政府能夠制定積極的財政貿易政策,以對抗漢薩同盟的斯堪的納維亞政策,體現了北歐國家對民族貿易的關注。聯盟出臺了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立法,直接針對外國(主要是德意志)商人的商業壟斷,“保護主義立法可以追溯到13世紀末的挪威和瑞典以及14世紀中葉的丹麥,然而直到大約1400年聯盟形成后,這項立法才得到認真落實”②Anders Andrén, “State and town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8,No. 5 (September 1989), p. 600.。正是卡爾馬聯盟增強了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整體力量,才使得保護民族貿易的立法得以落實。在挪威,卡爾馬聯盟把它從中世紀虛弱的政體中解脫出來,盡管后來它仍長期處于丹麥的統治下,但在歷次反丹麥斗爭中,挪威人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同時挪威本地商人逐漸壯大,開始往返于國際貿易,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避免了外敵利用經濟封鎖達成窒息挪威本土生活的目的,這是一個歷史進步。在丹麥的支持下,早已淪為漢薩同盟據點的卑爾根也伺機收回一些漢薩商站占有的特權。1423年,聯盟國王埃里克下令在松德海峽兩岸設點向過往船只征收通行稅,并不惜為此與漢薩同盟開戰,這項政策主要是針對漢薩同盟在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壟斷出臺的,反映出聯盟自成立以來表現出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傾向及整體實力的增強。丹麥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在位時期,曾利用市民和中小貴族的力量來牽制大貴族以建立集權統治,“他鼓勵市民從事對外貿易,改善手工業作坊的生產條件,甚至還擢用市民出身的人到各級行政部門直至中央機關做官”①敬東主編:《北歐五國簡史》,第31頁。。“除此之外,他的計劃中還包括設立一個斯堪的納維亞商業同盟,希望在荷蘭人的協助下把漢薩同盟商人排擠出去。”②安德生:《瑞典史》,蘇公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73—174頁。這些措施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即使到卡爾馬聯盟解體之后,保護地區工商業的做法在近代早期瑞典和丹麥也被保留了下來。
其二,斯堪的納維亞民族意識逐漸覺醒。15—16世紀以降,西班牙、英法等國王權得到加強,這種情況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北歐國家的政治走向。“直到15世紀,歐洲鞏固王權的發展趨勢才導致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經濟政策的出現——它們受到一些模糊的社會目的的影響。但是,當這些真的發生時,漢薩對國家貿易的壟斷就成了引起政治爭端的主題。”③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庫克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3卷,第336頁。北歐整體民族意識躁動,驅使它們走向聯合去應對漢薩同盟的貿易壟斷和政治經濟控制。另外,聯盟盟主埃里克國王對城市貿易實行保護性政策也并沒有隨他之后被驅逐而中斷,而是在后來的貴族統治中得到延續,丹麥城市市民力量的不斷增強,當然這一政策也有利于下層群眾。15世紀70年代,丹麥王克里斯蒂安一世下令禁止德意志人在丹麥永久居住,并取消了丹麥行會,這些情況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丹麥民族意識的萌動。更為關鍵的是,當卡爾馬聯盟解體過程中,具體說在其他民族反抗丹麥王室控制的過程中,“丹麥人”也和其他國家的民眾一樣,民族意識開始覺醒,開始了向現代國家的轉變。“正像近代瑞典史正常情況下是從1523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瓦薩與卡爾馬聯盟決裂開始,近代丹麥史也可以從這個時刻開始。”④克努特·耶斯佩森:《丹麥史》,第10頁。丹麥能從一個北歐混合體轉變成現代單一的民族國家,卡爾馬聯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催生了丹麥的民族意識,使丹麥開始了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漫長歷程。卡爾馬聯盟的解體、漢薩同盟的衰落以及新航線的轉移,使得波羅的海的位置越來越重要。1523年北歐王國分家后,位于丹麥境內的厄勒海峽成為波羅的海主要貿易航道,這一地理位置使丹麥成為波羅的海守門人,對它未來的發展起著重大影響。當然,聯盟的最終瓦解還是要直接歸結于瑞典民族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的后一階段,瑞典人對聯盟統治者的不斷反抗逐漸發展為一種瑞典民族認同意識”①Tracey R. Sands, “Saint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Kalmar Union Period: The Case of Saint Margaret in Tensta”, Scandinavian Studies, Vol. 80, No. 2, (Summer 2008), p. 141.,“聯盟主義已被瑞典的國家主義所擊敗”②Michael Roberts, The Early Vasas: A History of Sweden 1523-16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p. 23.。北歐聯盟解體后,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一世為增強王權以應對丹麥王室和其他外部威脅,在北歐率先進行了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這相應地推動了民族語言的復興。1526年,《新約》的瑞典文本首次發行。“無論是從宗教還是文化的角度來看,瑞典語的《新約》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③N. K. Andersen, “The Reformation in Scandinavia and the Baltic”, in G. R. Elton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I, 1520-15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8.在烏普薩拉大主教勞倫提·彼特里(Laurentius Petri)的組織下,瑞典文的《新舊約全書》在1541年正式出版。“上帝的話語必須用母語向人們宣講以及應該讓其有機會用方言閱讀圣經的原則,有助于在歐洲偏遠和隱秘的地區創造和培育新的書面語言。”④E. I. Kouri, “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Sweden and Finland c. 1520-1560”, in Ole Peter Grell (ed.), The Scandinavia Reformation: From Evangelical Movement to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7.此后,各階層的識字者都可以通過本地語文去閱讀圣經了,這是推動瑞典民族語言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瑞典語在民族政治、宗教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本民族語言的普及是瑞典民族意識充分覺醒的生動寫照。
其三,絕對主義王權在夾縫中生長,并逐漸獲得本國民眾的認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幾個國家和波蘭,中世紀中期的幾個世紀幾乎沒有帶來王權的鞏固,反而發生了許多政治上的混亂。”⑤朱迪斯·M. 本內特、C. 沃倫·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第10版),楊寧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310頁。實際上,即使是到卡爾馬聯盟成立之時,也沒有確立起世襲的王位繼承制度,瑪格麗特女王和埃里克國王都沒有取得對貴族的絕對優勢。“雖然繼承人是從王室中選出的,但是由三個王國的政務會任命,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著他的政府;瑪格麗特女王可能對這一決定并不完全滿意,但是傳統上確實只有挪威擁有世襲君主制。”⑥Vivian Etting, Queen Margrethe I (1353-1412)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dic Union, p. 99.1523年,古斯塔夫·瓦薩帶領瑞典徹底脫離聯盟,并于1528年在烏普薩拉大教堂加冕,成為瑞典第一位世襲君主,隨后他正式確立了世襲制度。“古斯塔夫在這一領域中最大的成功就是使1544年在韋斯特羅斯(V?ster?s)召開的國會接受了以下原則:從此以后,君主將不再由選舉產生,而由瓦薩家族世代相襲。”⑦佩里·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劉北成、龔曉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頁。王位世襲制的現實意義是能夠鞏固主權國家自身的穩定,因為以往推舉制下的王位繼承很容易造成國家政治的混亂無序。對外方面,瓦薩能夠在對丹麥的反抗中獲勝,跟漢薩同盟的援助是分不開的。“但是,一當古斯塔夫·瓦沙登上王位,便與曾經幫助過他的呂貝克人斷絕關系,宣稱‘瑞典王權作為漢薩人經商對象的時間太久了’。”①詹姆斯·W. 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250頁。到16世紀30年代,隨著瓦薩地位的鞏固與瑞典國力的增強,他徹底放棄了呂貝克的支持,轉而發展瑞典自身的力量,迅速將中央集權管理體制建立起來。在瑞典歷史上,瓦薩君主政府是第一個足夠強大、能夠有效抵抗呂貝克的政權,這正是卡爾馬聯盟留下的歷史遺產。瑞典成功脫離卡爾馬聯盟為瓦薩建立絕對君主制度提供了條件,推動瑞典向一個獨立的現代國家轉型,其后進行的新教改革則進一步鞏固了它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16世紀以后,北歐民眾對各自的共同體產生了極大的民族認同,擁有了“歸屬感”。國王已經享有本國民眾一定程度的自發效忠,這種“自發效忠”就是已經覺醒的民族意識,就是14—15世紀開始出現的民族向心力。實際上,王權走向集中的過程就是民族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
四、余 論
從歷史縱向發展來看,卡爾馬聯盟成立前夕,斯堪的納維亞整體的民族意識已處于朦朧之中,而在聯盟前期共同反抗漢薩聯盟的控制、以及聯盟后期各地反抗丹麥的專制統治時,北歐諸王國的民族意識已逐漸顯現,由此推動了各王國向現代國家轉變。從歷史的橫向發展來看,卡爾馬聯盟延續期間,正是歐洲許多地區民族意識逐步覺醒的時代,以專制君主為核心的現代國家正在形成,特別是西班牙、英國、法國等相繼轉型為強大的民族國家。北歐各國在經濟、軍事實力方面與之相比則相對弱小,因此卡爾馬聯盟作為一個整體可以有力地維護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共同利益,為各王國的發展提供相對穩定安全的環境,同時促進各國內部結構的轉型。
卡爾馬聯盟的成立是斯堪的納維亞君主國在與德意志商人的斗爭中,通過王朝間的聯合贏得的政治勝利。從歐洲的大環境看,進入近代早期,舊的中世紀歐洲標準和價值觀已經開始崩潰,中世紀普世天主國,即一個由羅馬教皇和神圣羅馬皇帝領導的普世理想破滅了,整個歐洲的封建制度搖搖欲墜,領土邊界相鄰的以單一民族為基礎的國家(state)逐漸取而代之。卡爾馬聯盟的終結并非孤立現象,和它具有相似性質、淵源頗深的漢薩同盟、條頓騎士團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甚至在德意志強大一時的天主教會也大約于同時代轟然坍塌,這一切并非偶然。從這個意義上講,卡爾馬聯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成立于斯堪的納維亞各王國孱弱之時,面對漢薩同盟的威脅,各王國貴族通過妥協共同成立了一個聯盟國家,抵制了外來勢力的侵擾,維持了本地區國家的獨立。“這三個大國的緊密聯合成為維護它們安全的有力堡壘,并使它們在一個多世紀內成為歐洲體系的仲裁者;北方半島的三個民族呈現出一條密切而統一的陣線,這使得他們能夠蔑視任何外來國家的侵略。”②Paul C. Sinding, History of Scandinavia: From the Early Times of the Norsemen and Vikings to the Present Day, p. 149.
16世紀20年代,瑞典、丹麥已成長為可以單獨應對外來干涉的君主制國家,商人階層也陡然崛起,這一切都增強了北歐地區的綜合實力。聯盟成立之前,總的來說各國貴族勢力相對強大,君權虛弱,中央政策無法得到有效推行,無法采取一致措施應對外來威脅。而在北歐聯盟時期,君主在夾縫中伺機壯大自己的勢力,為建立中央集權而盤旋于貴族之間,“這個聯盟主要是為了對抗德意志商人和漢薩同盟的商業統治而宣揚王室權力的一種策略”①Tim Knudsen and Bo Rothstein, “State Building in Scandinavia”, Comparative Politics, p. 205.。聯盟解體后,各國已經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政體,這一點在瑞典表現得最為明顯,有序的王位繼承制度、君主治下的中央集權體制推動瑞典向現代國家大步邁進。“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個大北歐王國的迷夢已被粉碎;另一方面,卡爾·克奴特遜和幾個斯圖雷所懷抱的理想——在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手下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卻實現了。”②安德生:《瑞典史》,蘇公雋譯,第178頁。卡爾馬聯盟起著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它是將北歐各國從漢薩同盟的后院改造為具有現代特色的新型歐洲國家的搖籃,繼而深刻地影響了北歐各國歷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