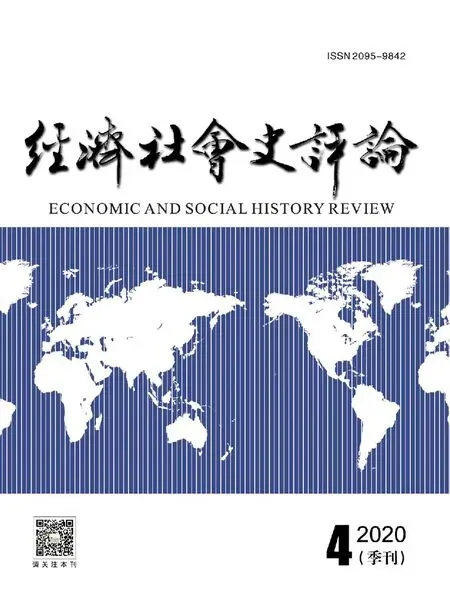中共早期黨員生活費制度*
楊 陽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產業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建黨初期,中共主張的革命道路是以城市為中心、組織工人階級開展革命斗爭,待時機成熟后發動工人暴動,占領中心城市。由于黨員群體長期活躍并生活在大城市,中共中央在1921年即建立起生活費制度。該制度對保障黨員日常生活,實踐列寧提出的“職業革命家的組織”,起到一定作用。以往學界主要關注早期中共組織經費的整體收支狀況,(1)學界對中共早期組織經費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主要論文參見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4期;何益忠:《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活動經費研究》,《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年第7期;劉小花:《中共創建時期的經費來源情況考察》,《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1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徐元宮:《關于中共誕生初期活動經費來源的歷史考察》,《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3年第4期。未將黨員生活費作為專題探討,甚至籠統地將生活費等同于黨的組織經費,對生活費制度的由來、擴大與調整,缺乏系統研究。(2)目前學界對中共組織經費中具體類別經費的專門研究相對較少,尤其缺乏對生活費制度的專題論述,僅在整體研究中偶有提及生活費問題,參見陳彩琴:《中共地方組織早期經費情況考察——以上海地方黨組織為中心》,《上海黨史與黨建》2016年第9期。筆者綜合利用多方檔案文獻,試圖解答:中共因何且如何確立生活費制度?生活費制度對革命職業化和中共早期組織發展起到什么作用?對生活費制度衍生出的消極現象中共中央如何應對?由此,進一步探析革命者的日常生活、政黨制度建設和革命職業化三者間的互動關系。
一、生活費制度的初步建立
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黨的經費來源不穩定,一是依靠蘇俄(共產國際),二是黨員自籌。經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與共產國際駐遠東代表舒米亞茨基等人之手,蘇俄向中共提供過幾筆經費,(1)《舒米亞茨基致柯別茨基的信摘錄》(1921年1月21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2頁;《施存統在警視廳的供述概要》(1922年2月),《中共建黨前后革命活動留日檔案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5頁。數目不等且不固定。中共早期尚未建立黨費制度,組織籌款方式有三:一是黨員捐獻稿酬。據早期黨員李達回憶,1920年12月維經斯基離滬后,組織經費主要來源于“在上海的黨員賣文章”。(2)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頁。早期黨員陳望道也提到,他與李達、李漢俊等人合力翻譯稿件,“一夜之間可譯萬把字”,每千字售得四或五元,憑借稿費收入支持建黨活動。(3)寧樹藩、丁凎林:《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志生前談話紀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李漢俊主持的上海《新青年》社“營業贏利計4 000元”也用于建黨工作。(4)K·B·舍維廖夫:《張國燾關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7頁。二是職業薪酬較高的黨員貢獻部分月薪。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是“每月從黨員的收入中抽百分之十”。(5)《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年7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7頁。李大釗從月薪中拿出八十元作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經費。(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06頁。三是個別家庭富裕的黨員奉獻。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金家鳳說,因見到陳獨秀“生活無著,貧苦之至,活動費、招待費都沒有”,于是他捐助了個人六千銀元的留學費用。(7)金家鳳:《我的歷史上的思想情況摘錄》(1956年10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編:《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史料選輯》下,第1339頁。中共領導的上海外國語學社成立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捐款建立學社圖書室,并捐獻稿費定期支付該室管理員的月薪。(8)《周伯棣回憶外國語學社的情況》(1961年6月19日),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299頁。
隨著建黨工作日趨繁雜、支出增加,自籌經費難以滿足組織發展的需要,黨的活動被迫停頓,黨員生活貧困等問題日益突出。自1921年1月起,中共早期組織因經費支絀導致“工作出現停滯”,(9)《舒米亞茨基致柯別茨基的信摘錄》(1921年1月2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 檔案資料集》,第92頁。在上海開辦的工人學校停辦,(1 0)《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1年7月1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 檔案資料集》,第397頁。《共產黨》月刊僅出版兩期后也被迫中止。老漁陽里2號的《新青年》社與新漁陽里6號的外國語學社均無力支付房租,“有的青年離開了”。(1)徐承武訪問整理:《李達談1920年—1923年的社會主義青年團》(1957年1月),《覺悟漁陽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史料選輯》下,第1343頁。與此同時,黨員生活貧困化現象突顯。李達說,中共早期組織每月經費“僅需大洋二百元”,但黨員群體“卻無力負擔”,原因是黨員忙于建黨而“不能掙錢”。(2)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9頁。據青年團成員袁同疇回憶,當時上海黨員的生活“都很苦”,黨組織代理書記李漢俊長期“苦撐外國語學社非常吃力”,生活“很簡樸”;(3)張朋園、馬天綱、陳三井訪問:《袁同疇先生口述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7頁。在經濟壓力下,李漢俊不得不“暫時把機關部停止活動”。無獨有偶,其他地方黨組織也陷入窘境。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負責人包惠僧“在武昌幾乎無錢舉火”,只好帶人到上海,但上海黨員也正“打饑荒”,心有余而力不足,包惠僧又轉赴廣州,請陳獨秀商籌解決辦法。(4)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21頁。而陳獨秀親自指導的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也面臨經費困難,已被迫將《勞動界》停刊,“兩個工人工會也得停辦”。(5)《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年7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7頁。可見,經費問題和黨員貧困化現象已經嚴重影響到黨組織的正常運作。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抵達上海。他針對中共組織發展停滯與黨員生活貧困化問題,提出由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常性的經費援助,并發放黨員薪資。在馬林看來,共產國際向各國共產黨的黨務人員提供薪資屬于工作慣例且合乎情理。當時,活躍于上海的朝鮮革命者每月可從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領取200元;(6)此款項原檔標注幣種為“上海元”。《馬林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信》(1921年7月7—9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 檔案資料集》,第144頁。中共黨員張太雷出任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書記后,也依照三級政治工作人員的標準領取月薪。(7)《第41號命令》(1921年3月23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 檔案資料集》,第103頁。但是,馬林的提議并要求李漢俊提供中共經費預算方案時,卻遭到后者的拒絕。李漢俊對中共接受共產國際定期提供的組織經費,和給黨員發放薪資的提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中共正式宣告成立以前,向共產國際提交經費預算方案為時尚早,況且中共黨員應當義務為黨工作而不應領取報酬,“反對吃革命飯、領薪水”。(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33頁;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14頁。李漢俊的回絕使該問題被暫時擱置下來。
中共一大閉幕后,馬林再次向新成立的中央局提出經費與黨員薪資問題。馬林指出,中共正式建立后“工作愈開展所需經費愈多”,僅憑自籌“以后將何以為繼”?既然“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中共也應當坦然接受”國際的資助,同時,馬林還提出了黨員“按月支領薪金”的計劃。新當選的中央局成員對此意見不一。組織委員張國燾認為馬林的提議合乎現實,應當予以采納,并率先以“贊成的口吻”向中央局作了報告。代理書記周佛海也認同向馬林提交經費預算是黨成立后“應有的舉措”,以“迅速展開工作起見,不必等待”。宣傳委員李達則持“從長考慮”的保留意見,認為黨員領取薪資“可能發生雇傭觀念的流弊”,他建議該問題留待書記陳獨秀決定。陳獨秀抵達上海后,對張國燾率先向馬林送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計劃草案與經費預算一事表示不滿,認為“對于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等于雇傭革命”,中共應當堅持“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的立場。(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 150—152,159頁。其間,陳獨秀還數次拒絕與馬林見面,認為“沒有共產國際的幫助,我們也能夠干”,最終“在擬定預算時也沒有找他商量”。(2)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212,216頁。
1921年以前,陳獨秀、李漢俊并未拒絕共產國際給予的經濟援助,但何以此時產生激烈的反對意見呢?他們前后態度的差異反映出黨的主要成員在若干問題上的觀點分歧,首先是對共產國際與中共關系的認知。在陳、李二人看來,中共是否加入共產國際“還待研究”,二者之間并無組織關系,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是支援中國革命的臨時協助,但如果這種臨時性的支持變為常態型的制度,尤其是建立黨員薪資制度,將會改變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與地位,限制中共獨立自主的活動空間。陳獨秀明確說:“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中共應當“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黨員也“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否則“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3)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84頁。李漢俊在與馬林接洽時也表達了相同看法:中共“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因此唯有在經費“感到不足時才接受(共產國際)補助”,但“并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即便接受了經費,也須根據自身“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33頁。李漢俊始終認為,共產國際應只作中共的協助者,后者接受前者的理論指導而非組織領導,這種觀點與馬林的預期相距甚遠。(5)楊陽:《中共一大代表與共產國際代表關系之研究——以張國燾、李漢俊與馬林的三者互動為對象》,《蘇區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6頁。陳獨秀、李漢俊所代表的主張,是在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系形態尚未確定以前,原則是組織領導不應構成經濟援助的前提條件。
關于建立黨員薪資制度的爭論還反映出“革命職業化”觀念尚未在黨內形成共識。根據列寧提出的共產黨是“職業革命家的組織”的建設原則,黨員干部應作職業革命家。列寧認為,“職業革命家的組織”是一種“聯系的酵母的組織”,(6)《我們是否應當組織革命?》,《列寧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5頁。參加這種組織的“主要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7)《怎么辦?》,《列寧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34—435頁。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沒有職業革命家,事情總是寸步難行”。(1)《給葉·德·斯塔索娃》,《列寧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25頁。中共是根據列寧主義建黨原則成立的無產階級政黨,造就全身心為黨工作的職業革命家隊伍是政黨組織建設的基礎。何謂“職業革命家”?留俄歸國的黨員羅亦農曾作出闡釋,即“將所有的精神對付革命,沒有一切非革命的牽掛,無論在什么時候都絕對自由,可以隨時遷徙,可以在一定的時候變更他自己的私人生活”的人,“總而言之,革命是這種人唯一的職業。”(2)羅亦農:《關于〈無產階級政黨之建設〉的序言》(1926年7月),檔號:D4-0-75,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檔案。既然革命是職業革命家“唯一的職業”,他們便無余暇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以謀取經濟收益,需要組織提供最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基于上述原則,革命者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需要摒除一切非革命的營利工作,專心一意為黨工作,結成職業革命家的組織。陳獨秀等人持有的“反對職業革命論”顯然不符合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建設方向,因此被黨內成員指為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張國燾進而提出:“黨的工作人員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須無顧慮,才能專心致力于工作”,“黨員向黨拿了少數的生活費用”不能稱之為雇傭。(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59頁。中共早期重要理論家蔡和森后來也批評李漢俊“反對領薪水”的觀點,是“根本不了解職業革命家的意義,以為每個黨員應另有職業”。(4)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蔡和森文集》下,第814頁。經過此次爭論,陳獨秀放棄了“反對職業革命論”,接受了黨的主要干部應當是職業革命家的主張。
在中央局會議上,陳獨秀最終接受了馬林的提議,決定首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確立生活費制度,為從事工人運動的黨員、團員提供一定數額的生活津貼。不過,該津貼名義上不稱“薪給”或“工資”,“統稱之為生活費”。(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 159,165頁。陳獨秀本人的生活費也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6)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308頁。由于中共建立生活費制度之初便含有對黨員艱苦奮斗的期許,因此最初提出的生活費標準是每人每月20至35元,實施范圍限制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內,保障范圍是針對“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志”。中共中央在審議該標準時,將原定的最高標準再次降低至每月20至25元,決定超越自巴黎公社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國共產黨“薪給數額任何最低規定的前例”。這個數額較之黨員干部原先的社會職業收入要“低得很多”,“大致約為一與十之比”。(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52—153,166頁。自此,生活費制度開始在較小范圍內有限施行,開啟了黨員干部的革命職業化進程。
二、生活費制度的擴大
生活費制度正式建立后,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實施范圍的變化。該制度在創設之初,主要針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員,覆蓋人數較少。1922年中共二大后,黨的經費由中央統一開支,生活費一項從原先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勞工運動名義下支出”改為由中共中央開支。(1)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后》,本社編:《一大回憶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43頁。其覆蓋范圍也溢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向各組織機構傾斜,但涉及對象仍然有限,沒有普及到所有黨的工作者。比如,1926年在北方區委工作的王凡西稱,當他“開始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后,仍“必須自籌生活費用”,區委其他成員也“都不是靠此吃飯的”,“由組織維持生活的大概只有地委的工作人員”。(2)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30頁。生活費制度在青年團內也僅涉及少數專職從事工運的團員。1922年時任團中央書記的施存統說自己“起初是不拿薪金”,后來團中央也僅他一人“每月領取30元生活費”。(3)施復亮:《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前后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第73頁。
1922年以后生活費覆蓋范圍逐步擴大,主要是以下幾個因素促成的,首先是黨員干部的革命職業化進程。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后,除中央局成員以外,黨內“并沒有專任事務工作的人員”,中央機關也無集中的辦公場所。(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50頁。隨著組織發展與黨務增多,黨對專職人員的需求增加,一些黨員開始辭去社會職業,轉變為職業革命者。對專職人員給予生活費是必然趨勢,否則黨員既從事黨務又擔任社會職業,其間難免有抵牾之處。以上海工人黨員徐梅坤為例,1923年6月后,他既擔任上海區委代理委員長兼任勞動運動專職委員,又在印刷廠作排字工。由于“工作太忙,兼顧不過來”,中央責令徐梅坤“脫產工作,生活費由黨組織補貼”。(5)徐梅坤:《九旬憶舊——徐梅坤生平自述》,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31頁。不僅城市黨員如此,受黨組織委派到鄉村領導農運的黨員也面臨無法兼顧物質生活的困境。1927年,四川臨時省委農民部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總結,黨員領導農運時面對的“第一困難就是他的生活問題”,因本人需要吃飯,其家庭也“需要他們拿錢回去養家口”;他們受“生活逼迫而去另謀職業”,地方上“不易得到”從事農運的黨員。黨組織如欲解決,就“非給生活費不可”。(6)《四川臨時省委農民部致中央報告》(1927年10月31日),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6年—1927年)》甲1,1984年,第257—258頁。面對上述情況,為避免削弱黨在基層的組織效能、保障黨員專心為黨工作,向專職人員提供一定的生活費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建立生活費制度的另一個初衷是為遭遇特殊困難、失去經濟自立能力的黨員提供一種生活保障。如黨員被捕入獄、疾病損傷等,“黨應予以積極的照顧”。(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66頁。上海是中共中央長期駐扎地,也是早期革命斗爭的橋頭堡,(8)張仰亮:《中國共產黨早期支部制度及其實踐——以大革命時期上海黨組織支部建設為例》,《黨的文獻》2019年第4期,第85頁。因此常有革命者被捕事件發生。黨員陷獄后,黨組織如何營救并接濟日常飲食、安撫家屬,此類問題需要制度性的解決方案。1923年9月,上海地委兼區委會議專門討論了“接濟在獄同志”問題,決定接濟陷獄黨員的生活,“每月應送食物及衣服”。由于接濟“需款約在二十元左右”,不僅陷獄者個人無力支付,地方組織亦感乏力,唯有“決請中央任之”。(1)《上海地委兼區委第十五次會議記錄——國民運動問題、改編小組及整頓紀律等問題》(1923年9月27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1989年,第31頁。11月,上海地委兼區委會議再次討論了營救陷獄黨員方案,決定除“每星期送食物(約一二元)”外,還需要籌劃“從根本的救援在獄同志”的辦法,比如“用家屬打稟”(2)動員家屬向監獄方送報告。“說項”等。為盡力保障被捕黨員的人身安全及生活,黨組織需要設法募集資金。地委兼區委候補委員瞿秋白提議,由上海地委“酌定派捐一次”款項以營救之。(3)《上海地委兼區委會議記錄——審討論地委經濟獨立和組織國民外交委員會等問題》(1923年11月23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54—55頁。黨員在嚴酷的斗爭中還可能因革命而失業,比如有的因組織工人罷工而被廠方開除,有的革命者“因宣傳主義”而“被撤差”,(4)《仲毅關于個人情況致國昌的信》(1922年4月),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第1冊(1922年3月—1926年7月)》甲,1983年,第31頁。由此陷入生活困境的失業黨員,向組織提出生活補助的請求。不過,中共設立生活費制度的目的不是為失業黨員提供救濟,失業造成的經濟壓力并非領取生活費的前提條件。例如,1923年11月上海地委勞動運動委員會委員曾憲明因華豐停工而失業,他向地委表達“要求團體補助意”。為此,上海地委兼區委會議討論了“曾憲明問題”,會議決定“資助其最近一月內之生活,給洋五元”,但給予的原因是“留吳淞幫辦組織工會”而“非因他失業”。黨組織“對于失業同志,勢不能給以津貼”。(5)《上海地委兼區委第二十三次會議記錄——審查批準候補黨員及曾憲明、林伯渠問題》(1923年11月22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50頁。可見,黨組織對失業黨員提供生活費仍是根據所事工作發放,而不是作為一種救濟手段。
生活費制度提供的物質保障作用也促使一些黨員在遭遇生活困難時,派生出依賴組織維持生活的心理,這在青年學生中表現尤為明顯。由于早期黨員中有大量學生,青年團更“可說完全是‘學生團’”,(6)《對于青年團的意見》,《先驅》第6號,1922年4月15日。學生無社會職業,其生活多數需要仰賴家庭或學校提供支持。他們離開家庭與學校后,如果未能及時就業或進一步入學深造,經濟上難以為繼,時常“因為生活不能遂意而陷于煩悶”。中共試圖“將此感覺生活困難的人聯合起來,各就力之所及,共同促進革命,以謀社會經濟之根本改正”。(7)《答問》,《中國青年》(第76—100期),第2頁,檔號:D2-0-14-196,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檔案。當大量貧苦學生響應中共號召參加革命,并轉變為職業革命者后,他們的生活問題便發展成為需要組織解決的經濟問題。同時,一些脫離鄉土社會農業生產的革命者,在物價高昂的城市維持生活殊屬不易,陷入經濟困境后也會向黨組織求助,因此上海中央時常接到各地方的求援信件。1922年4月,唐山青年團員梁鵬萬因處“在窮困煩惱中”,急需“找工作賺錢養家”,(1)《舒關于唐山情況及不同意梁鵬萬出席會議致國昌的信》(1922年4月14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第1冊(1922年3月—1926年7月)》甲,1983年,第22—23頁。于是“動身去滬謀生”,請求中央提供幫助。(2)《彝關于赴廣旅費及唐山青年團成員情況致國昌的信》(1922年4月10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第1冊(1922年3月—1926年7月)》甲,第19—20頁。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也接到革命青年的經濟求助,編輯部因之感慨說:“我們既投身革命,自己的生活都是漂泊艱苦,安有余力為感生活困難的青年解決生活問題呢?”(3)《答問》,《中國青年》(第76—100期),第2頁,檔號:D2-0-14-196,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檔案。1924年12月,江西安源黨組織負責人賀昌向上海中央發信,稱黨員胡士廉因黨務繁忙無暇從事社會職業,導致“生活尚無著落”,而地方黨組織“又無錢開支一人生活費”,請中央設法提供“最低限制之生活費”。(4)《致鐘英的信——關于安源地方取消小組,請津貼胡士廉生活費及增發〈中國青年〉等》(1924年12月3日),穆生高主編:《賀昌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89—90頁。同月,安徽蕪湖團地委負責人專門致信上海,提出因“生活困難關系,致不能用全副精神來活動”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地方工作。他建議,團地委書記的“生活費由中央供給”,使之“能用全副精神來工作,無生活壓迫之憂慮”,盡量減輕地方組織的經濟壓力。(5)《劉一清致惲代英并團中央的信——關于蕪湖團的狀況及建議(1924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安徽省檔案館編:《安徽早期黨團組織史料選》,1987年,第89頁。這個時期,大批投身革命的青年團員、黨員在面對現實困境時向組織求助,也促使中共中央考慮增加生活費的部分實施對象。
綜上三種因素的推動,生活費的實施范圍逐步擴大。1925年中共四大和“五卅”運動以后,黨的經費有所增加,為生活費范圍的擴大并標準提高提供了客觀條件。以中共中央為例,1925年以前“包括中央委員在內”的黨員干部,每月生活費標準大體為“約20元至30元”。(6)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第167頁。1925年以后,在中央工作的陳獨秀、蔡和森、彭述之“每月領40元”,張伯簡、向警予、鄭超麟“每月領30元”。(7)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13頁。又如上海地方組織,根據1923年7月《中央核準上海區預算案》顯示,區委每月生活費合計68元;(8)《上海地委兼區委第一次會議記錄——委員分工及黨內教育、訓練等問題》(1923.7.9),《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6頁。至1925年10月,區委生活費預算已增至415元。此外,區委下轄七個部委生活費合計為320元,外埠生活費為90元。(9)《上海區委組織系統、組織關系、經費預算表及黨內負責人名單》(1925年10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乙3,1989年,第50頁。可見,黨員數量的急劇增加和生活費覆蓋范圍的持續擴大,生活費總量和個體標準均有所提高。
再將生活費置于黨組織的財政結構中觀察,可見其在整體經費開支中占據了較高比例。1923年7月,上海區委每月經費總預算為140元,其中生活費68元,占比接近1/2。1925年10月,上海區委經費總預算已增至1 374元,其中區委及轄下各部委與外埠黨員生活費預算合計825元,占經費總數的60%。1927年10月,四川省委經費總開支為641.77元,11月經費總預算為830元,其中生活費分別為170元和200元,約占經費總數的1/4,為各項開支中最大一筆。由于生活費直接關系到黨員的日常生活,地方組織在壓縮各項經費開支時,將生活費列入“萬難減少”的行列,“否則當有絕食曠工之虞”。(1)《四川臨時省委給中央報告——關于十月份政治及校務工作概況》(1927年11月),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6年—1927年)》甲2,第335頁。因此,生活費一項在黨組織經費中始終占有較高比例。
生活費制度在實踐過程中,盡管其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涉及人數增多,但對個人的發放標準長期仍處于較低數額。黨員干部領取“每月約20元至30元”的生活費僅相當“一個工作的薪金”,甚至有的黨員每月僅支數元,遠低于技術熟練工人的收入。而且,在組織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減少或遲發黨員生活費的現象亦不鮮見。例如,1923年9月,上海地委由于收繳黨費不足,唯有根據中央撥款重擬預算,發給3名黨員的生活費分別縮減至5元、9元和10元。(2)《上海地委兼區委第十三次會議記錄——地方預算、批準黨員和決定演講人名單(1923年9月17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24頁。因支付機關房租,發給周啟邦的10元生活費再次縮減至5元。(3)《上海地委兼區委第十五次會議記錄——浦東工人請求援助與國民運動委員會工作(1923年9月20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31頁。杭州支部原定自1925年9月起每月額定經費50元,其中生活費30元,但當月即欠發20元,遲至10月補齊。(4)《杭州支部黃綸關于民校工作報告(1925年11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杭州、紹興、嘉興、溫州地區(1925年—1927年)》甲6,1988年,第17頁。可見,由于客觀條件限制,黨員實際獲取的生活費可能低于額定標準,且時間并不穩定。
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薪資要比中共黨員的生活費“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5)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第167頁。例如,周佛海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戴季陶的秘書,“每月薪水大洋二百元”,同時他受聘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每月“送大洋二百四十元”。收入之多,周佛海本人亦感嘆“實在是始料所不及”。(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4年,第34頁。二者比較,更見共產黨員生活費的微薄。為照顧情況特殊的黨員,中共也會安排他們到國民黨控制下的廣東工作,借此改善生活狀況。如留蘇黨員袁慶云回國后,原擬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任職,中央考慮“在黨內工作生活費甚少,最高的每月不過三十元”,“其次的二十五元或二十元不等”,因此委派他到廣東擔任俄國顧問的翻譯,薪資遠高于黨員生活費。盡管一些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身居要職,但他們并未改變艱苦奮斗的作風,“仍舊保持克已、樸素的生活”。據早期黨員陳碧蘭回憶,當時的共產黨人“有一種普遍的傾向,就是只顧革命工作,而不顧自己的生活和健康”,“自覺地吃苦、近乎清教徒式的”生活習慣是共同標準。黨員在日常飲食上異常簡單,尤其是干部“吃苦耐勞和極端樸素的生活態度”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惲代英、蘇兆征、董必武和譚平山等人率先垂范,彰顯了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7)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第129—131,167頁。
三、生活費制度實踐中的問題及應對
生活費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職業革命者的后顧之憂,有利于黨員專心一意為黨工作。不過,這一制度在實踐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問題與困難。大體而論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黨員滋生依賴黨組織維持生活的觀念,出現雇傭勞動化和貪污腐化現象;二是地方組織過度依賴中央撥款,獨立籌款能力降低。
生活費制度保障了黨員干部的基本生活,但在城市生活壓力下,少數地方黨組織借生活費吸引失業群眾入黨,宣稱“全世界都有組織,走到任何地方具不至無飯”,(1)《四川臨時省委給中央報告》,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8年—1929年2月)》甲3,第344頁。由此“因失業窮無所歸”的人,便“專門找黨來解決生活問題”。(2)《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黨史史研究室,中央黨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第1003頁。依靠黨組織維持生活的觀念,使一些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同時,隨著“五卅”運動后各級黨組織經費的增加和生活費制度的擴大,一些黨員干部在金錢誘惑下出現雇傭勞動化和貪污腐化現象。比如,上海法租界部委會議指出,某些組織中“有支干薪而絲毫不管事的同志”,認為此類作風與“軍閥官僚的位置私人是如出一轍”。(3)《上海法界部委對中央擴大會議案的意見書》(1926年8月29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甲3,1986年,第363—366頁。有的地方還出現多拿多占現象。中共中央收到外地黨組織的檢舉信,彈劾個別黨員“領P生活費又在Y支錢用”,即同時領取黨和團的生活費。(4)《關向應關于王辯問題致鄭容信》(1925年10月),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4—1933)》乙,1996年,第7頁。
生活費制度經過數年實踐后,黨內對雇傭化、腐化現象及其影響已有較清晰的認識。中共中央認為,在“黨的發展和工作中”出現“雇傭勞動化和貪官污吏化的缺憾”這樣“很嚴重的問題”,將會導致“黨的質量的惡化”,因此亟待矯正。(5)《上海法界部委對中央擴大會議案的意見書》(1926年8月29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甲3,1986年,第363—366頁。對此,1926年8月4日中央擴大會議發布通告,指出大革命高潮興起后,“在比較接近政權”或在軍事、政治工作較快發展的地方,有一些投機與腐敗分子趁勢混入黨內,其“個人生活上表現極壞的傾向”,“在經濟問題上發生吞款、揩油的情弊”,對黨的形象造成惡劣影響。(6)《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1926年8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48頁。遵照中央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開始審查黨員的不良傾向、清洗腐化分子。8日,上海區委通告指出,地方組織中“雇傭勞動化”“貪官污吏化”現象是“應有盡有”,中央擴大會議通告是針對“本黨黨員過去以及目前所犯弊病的一個重要針砭”,這一警示“純關系于黨的整個的存亡問題”。(1)《上海區委通告 樞字第七十號——關于執行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嚴格審查同志的不良傾向》(1926年8月8日),中央檔案館、上海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1986年,第313—315頁。在一些黨員看來,雇傭化、腐化現象的出現與生活費帶來的消極影響有關。9月,施存統在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上將生活費問題與“雇傭化現象”聯系起來,批評上海的黨員應當糾正的一大“毛病”是“雇傭性質”,所謂“雇傭性質”即“是指拿生活費的”。不過,施存統的意見并不是針對生活費制度,而是反對少數黨員將為黨工作獲取生活費看作個人的謀生手段。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兼上海區委職工部主任汪壽華也指出,基層組織的黨員“雇傭性質格外厲害,你罵他也好,打他也好,只要不裁他生活費,此種人永遠不會提起精神,到了裁掉生活費,他就發現各種不好的景象”。(2)《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關于政治工作、干部狀況、人員分配和小沙渡工潮問題的討論》(1926年9月10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6年7月—1926年9月)》乙3,1989年,第387—389頁。
生活費制度實踐中產生的雇傭化、腐化現象是需要防止的主要問題,然而在促進黨員干部“革命職業化”過程中如何杜絕“雇傭勞動化”現象?黨內認為,黨員的主觀因素較為重要。據浙江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的分析,“黨的工作人員有腐化的傾向”是因為有投機分子混入黨內,“在工作人員中發現雇傭勞動化、揩油化、欺騙化的不是為革命而加入隊伍的惡劣分子”。(3)《中共江浙區第一次代表大會趙世炎關于黨務報告》(1927年2月12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江浙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有關文件(1927年2月)》乙7,1990年,第107頁。意即消極現象的出現是由于吸納了動機不純者。為嚴肅黨紀起見,中共采取的主要懲戒措施是將投機腐化分子剔除出黨,維持肌體的健康與純潔性。如汪壽華提出,建黨初期“黨的權威尚未建立,對同志不好的沒有加以嚴重的懲戒”,如欲維護黨的權威,中央和地方黨組織應“下決心整頓紀律”、淘汰腐化墮落分子,“從辦事人做起,以三個月的功夫,做完此洗刷工作”。(4)《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關于政治工作、干部狀況、人員分配和小沙渡工潮問題的討論》(1926年9月10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6年7月—1926年9月)》乙3,1989年,第388頁。根據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各級黨組織開始“迅速審查所屬同志”,對雇傭勞動化、貪污腐化分子“不容情地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5)《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1926年8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348頁。就此,全黨開始了一場清洗落后分子的運動,各區委、地委、部委、獨支、支部對具有雇傭勞動化、貪污腐化現象的黨員,“絕對不客氣地無條件開除”。(6)《上海區委通告 樞字第七十號——關于執行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嚴格審查同志的不良傾向》(1926年8月8日),中央檔案館、上海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1986年,第313—315頁。各級黨組織對涉及多拿多占問題的黨員也出臺了堅決的清除措施。如上海區委提出:“揩油的開除”,“一面發展,一面開除”。(7)《上海區委召開黨的部委和團的部委書記聯席會議記錄——關于準備“九七”紀念活動》(1926年9月1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6年7月—1926年9月)》乙3,1989年,第336頁。
生活費制度實踐中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地方組織過度依賴中央撥款,獨立籌款能力降低。黨員生活費包含在黨組織經費之內,而經費主要有兩大來源:一是中央撥發,二是黨員繳納黨費。不過,各地黨費往往繳納不足。1923年6月,馬林在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稱,全黨“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1)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2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77頁。實際上有時地方組織的黨費“繳來者不過百分之一”。(2)《上海區委組織部通知第十號——關于征收黨費問題》(1926年2月4日),中央檔案館、上海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甲3,1986年,第129頁。一旦中央停止撥款,地方組織便缺乏資金開展日常工作,甚至需要舉債度日。以上海區委為例,1923年原定由中央每月津貼75元,由地方自收黨費每月約30元,但地方黨費“能否照數收齊,實一問題”,唯有依賴中央撥發的經費酌情作分配。(3)《上海地委兼區委第十三次會議記錄——地方預算、批準黨員和決定演講人名單(1923年9月17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24頁。7月,“中央停止津貼一個月”,上海區委便不得不向外借錢。通過地委兼區執委會委員長鄧中夏“借到墊款五十元”,又經執行委員沈雁冰“借到墊款三十元”,此兩筆借款計劃是“由地方陸續籌還”。(4)《上海地委兼區委第十次會議記錄——鄧中夏離職前移交工作(1923年9月5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3年7月—1926年3月)》乙1,第20頁。中央未及時撥發經費,黨員便無從支領生活費,陷于無米入炊的困境,唯有頻頻向上級機關討要。1924年8月,山東黨組織向中央發信,催促匯款“以濟燃眉之急,否則受困矣”;(5)《鄧恩銘關于速寄八月份津貼事致宗兄信》(1924年8月14日),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4—1933)》乙,1996年,第2頁。同月,濟南團地委因“借下了好多的賬”,請中央速寄生活費“以救急需”。(6)《團濟南地委關于速寄津貼事致愛英信》(1924年8月),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4—1933)》乙,1996年,第3頁。1925年11月,杭州支部黨員黃綸發信給上海地委,述其“在杭有妻子、女兒、房租等”支出壓力,無奈已將個人“衣服付質庫”典當,催促匯寄生活費。(7)《杭州支部黃綸關于民校工作報告(1925年11月1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杭州、紹興、嘉興、溫州地區(1925年—1927年)》甲6,1988年,第16頁。同月,南京團地委也向團中央發信,稱地委辦公費、交通費及書記華少鋒的生活費全靠“東挪西借”維持,“已至一錢莫名之境”,尚“負債至二十元之譜”,請求上海方面“先匯寄若干,以應急需”。(8)《團南京地委給曾延的信》(1925年11月13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年—1926年)》甲9,1986年,第79頁。地方組織在經濟上對中央的過度依賴,不僅降低了自籌經費的能力,且令大量脫產的黨員干部完全仰賴中央提供的經費維持生活,喪失靈活應對能力。徐州團地委在報告中感慨:“我們總在謀生活,不過能夠自活的很少”,待中央撥款用畢,地委成員領不到生活費,連“吃飯和租房子都未付錢”。(9)《團徐州地委關于經費及委員情況的報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年—1926年)》甲9,1986年,第215頁。
為矯正地方組織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央的觀念,中共試圖降低生活費標準并收縮生活費的覆蓋范圍。1926年8月中央擴大會議后不久,上海法租界部委就中央決議案致區委意見書中提出建議:“訓令同志們盡可能的降低生活單位”,“各地黨部,不得特殊待遇少數同志,供其高生活單位的揮霍”,“訓令同志減低生活單位,黨部應采取不遷就妥協的態度處理之”。(1)《上海法界部委對中央擴大會議案的意見書》(1926年8月29日),《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4月)》甲3,1986年,第363—366頁。上海區委贊成此看法,并首先嘗試削減了上海總工會和各部委的經費預算,提出:“現在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如果我們不苦就不會革命,決不是革命黨員的態度。”(2)《上海區委特別會議記錄——全國及上海政治狀況與黨的工作方針、策略》(1926年9月14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6年7月—1926年9月)》乙3,1989年,第422頁。1927年,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訓令,要求“黨內最高生活費不得超過三十元”。各地方黨組織遂遵照此標準執行。如,湖北省委第七次常會根據中央命令重新規范黨員生活費標準,自省委常委、秘書長以至各科主任、干事、秘書、交通員等職務的生活費均限制在30至20元的范圍內。(3)《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十號)——關于省、市,區,縣各級干部生活費的規定》(1927年12月31日),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省委文件(1926—1927)》,1983年,第466頁。四川臨時省委也遵示降低標準,省委至縣委或市委委員每月生活費壓縮為20至10元不等。(4)《四川臨時省委通告(第九號)》(1927年8月30日),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6年—1927年)》甲1,1984年,第69頁。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和黨組織恢復重建工作后,向全黨發出通告,進一步收縮生活費的領取人數。中央申明,“黨只需要少數的革命職業家擔負日常的黨務”,“在群眾中工作的黨員”不應放棄社會職業,防止“人人都派作一黨部工作”,糾正“支部干事也要津貼”的錯誤傾向。(5)《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1928年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下,第1003頁。在重建黨員組織關系時,有的地方組織還明確規定黨員必須“有一定的職業”。(6)《中共廣濟縣代表大會組織問題決議案》(1929年6月),《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0,第84頁。諸如此類的設定,即是針對中央指出的某些“因失業窮無所歸”者“專門找黨來解決生活”的問題。中央鼓勵黨員深入群眾而非留在黨部工作,這樣既能進一步縮減生活費的覆蓋范圍,又能保持一般黨員與群眾的緊密聯系,有效杜絕黨員過度依賴黨組織維持日常生活的觀念,防止雇傭勞動化傾向的發生。
結 論
革命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中,生活費制度之于職業革命家具有重要實際意義。正如有學者提出,革命活動“是以金錢為基礎”,缺乏資金支持會導致“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政治活動都寸步難行”。(7)何益忠:《論土地革命時期中共活動經費來源及影響》,《史林》2010年第6期,第155頁。相較于普羅大眾而言,盡管革命者更為關注精神層面的理想追求,但他們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生活,開展革命活動是建立在必要的物質生活基礎之上。中共一大召開前夕,革命者專注于建黨工作,面對大城市經濟壓力卻無法兼顧社會職業,生活貧困問題趨于嚴峻,客觀上降低了組織工作效能。根據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向黨務人員發給薪給的慣例,與列寧強調的“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建設要求,中共中央采納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建議,在黨內初步確立了黨員生活費制度。該制度的有效實施,不僅有助于黨員克服物質生活困難,也促進了職業革命家群體形成,保障了中共早期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因此,這項制度得以長期延續,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仍發揮了積極作用。
曾做過碼頭工人的美國學者埃里克·霍弗認為,許多人參加革命的最初期待是“革命可以急速而大幅地改變他們的生活處境”,革命于是成為“一種追求改變的工具”,但在真誠的革命者看來,革命運動中任何的自利心理都是“墮落邪惡的”,“任何出于為己謀的行為”都是不足取的。(1)埃里克·霍弗:《狂熱分子》,梁永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5、39頁。革命是一件神圣的事業,共產黨員的人生因共產主義革命事業而崇高,為解放全人類而奮斗所帶來的自信、自豪、使命感和價值感,是超越物欲和利益需求的。中共中央在確立生活費制度之初,便積極主張共產黨員原則上應不計報酬地為黨工作,非黨務工作者不領取生活費、黨務工作者只領取極少量的生活費,主動降低個人生活消耗,“盡量發揮刻苦的精神”,使“一般黨員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第166頁。一些經濟上寬裕的黨員甚至時常捐獻個人財物,以補貼同志生活和支持黨組織的發展,如建黨初期的李大釗、沈雁冰等人,體現了共產黨員的革命意志與奉獻品質。
作為一個在政治上代表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革命政黨,共產黨員應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表率,“當然要十分刻苦,以防止有腐化之傾向”。(3)《四川臨時省委通告(第九號)》(1927年8月30日),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6年—1927年)》甲1,1984年,第69頁。艱苦樸素、無私奉獻、“用錢少而工作好”成為黨員對自身的期許。(4)《小沙渡日廠罷工的經過和教訓》(1926年9月20日),中央檔案館、上海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1986年,第363頁。自中共宣告成立后,革命者對共產黨員這一光榮身份的認同不僅是政治身份的界定,而且形成一種基本群體的歸屬感。在面對“自己如何被別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時,身份代表了一種行為標準和價值理念,(5)哈羅德·伊羅生:《群氓之族: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鄧伯宸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7頁。促使共產黨員在日常生活中自覺使用艱苦奮斗、深入勞苦大眾等革命的標準來塑造自身的行為模式。同時,黨組織也通過對生活費制度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加以省思與調適,摒除雇傭化現象、清洗腐化分子,不斷加強對黨員的觀念引導,維護組織體系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