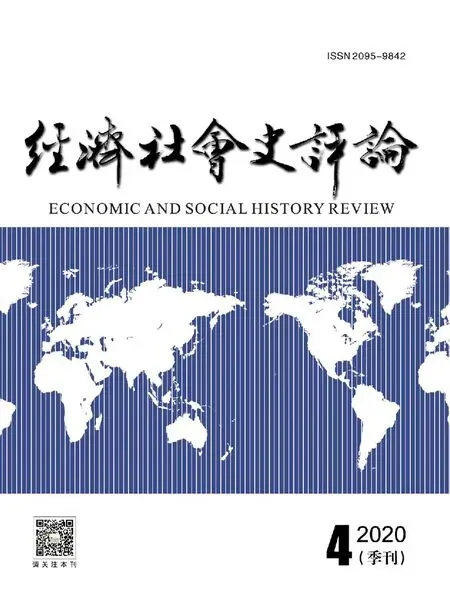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路徑與邏輯*
——以《法律選編》為中心
李繼榮 徐家玲
一、引 言
早期拜占庭(東羅馬帝國)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歷史時期,處于羅馬帝國轉型與變革階段,基督教思想不斷融入帝國社會,開啟了基督教觀念和羅馬法制傳統相結合的新時期,至8世紀伊蘇里亞王朝最終實現了帝國立法基督教化,此時頒布的《法律選編》以基督教法典的模式成文,成為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過程中的重要案例,為后世立法奠定了基礎。《法律選編》是繼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后,拜占庭伊蘇里亞王朝皇帝利奧三世與君士坦丁五世因時代變遷之需于740年共同頒布的一部新型簡明法典,共18章,以民法為主、刑罰為輔,體現了基督教圣典的立法精神,以及家庭和睦、社會公平和刑罰“仁愛”的立法原則。與《民法大全》僅在形式上包含了基督教的內容相異,《法律選編》真正將基督教的思想融入到了法典的具體條款之中,成為利奧三世皇帝時期流傳下來的彌足珍貴的官方文獻之一,歷來備受學界珍視。自該法典的稿本發現之日起,“諸多學者就開始對其進行校勘、整理和翻譯,其希臘文本、英文本、法文本及德文本均先后問世”(1)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ix.;20世紀30年代后,各國學者展開了對該法典的深入研究,如著名拜占庭史家瓦西列夫注意到,該法典雖然充斥著使獲罪者肢體致殘的懲處規定,但因其多數情況下是用致殘來代替死刑,故不能認為這是一部野蠻的法典(2)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2, p. 242.;奧斯特洛格爾斯基和伯里則認為該法典受到教會的影響較大,使羅馬法的精神開始在基督教的宗教氣氛中發生變化;奧爾頓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該法典是一部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基礎上被簡化、基督教化的法典(3)李繼榮:《拜占庭〈法律選編〉“仁愛”化原因探微》,《歷史教學問題》2017年第4期,第86頁。。國內學者如陳志強教授等在其論著中都談及該法典,但研究多是將其置于歷史的總的進程中加以闡釋,并沒有對之進行深入的個案分析。鑒于此,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法律選編》文本出發,由點及面,對早期拜占庭立法基督教化的成因進行初步探析,以期能對學界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二、君權神授理論與皇權強化趨勢的契合
在古代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政權的穩固都與其所依仗的宗教系統密不可分,羅馬ˉ拜占庭帝國皇權的強化亦是在與基督教信仰的博弈、認可與利用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共和時期,雖然羅馬宗教與希臘的多神教體系有諸多共同之處,但它畢竟產生于羅馬歷史與文化的基因之中,其神名、神性與神的功能等諸多方面亦擁有自己的特性,“宗教的風貌大相徑庭”(4)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歷史上的宗教》,魏慶征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473頁。。它源起于羅馬家庭—氏族守護神崇拜,融合了意大利本土的諸種自然神的崇拜,加上一些人們想象中的抽象概念(如和平之神、希望之神、勇武之神)形成一個神族系統,并以實物(牲畜、家禽或其他)(5)瓦西列夫在論及背教者朱利安恢復羅馬傳統宗教的舉措時,特別提到他親自操刀參與宰殺牲畜,于是,一首民謠廣泛傳播:“小白牛向馬可愷撒問候!如果你取勝,那將是我們的末日。”參見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國史》,徐家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17頁。獻祭方式展示人們對神的敬仰。但是隨著羅馬由共和向帝制的轉變,利用宗教意識加強和神化皇權逐漸成為帝王不斷獲得權力和鞏固統治的有效手段,并通過思想或道德的灌輸方式“溫和”滲入,利用道德和倫理掌控和管理帝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早在公元前27年,屋大維創立元首制時,帝國就逐漸開始了皇權神化、君主崇拜的歷程。但因帝制創建初期,傳統元老貴族實力依舊較大,故皇帝只能借著“元首制”的共和外衣,隱秘地利用宗教來加強帝制統治。故而屋大維為了使自己的稱呼在避開獨裁者身份的同時,還能彰顯其至高無上的神圣性,一方面,他賦予自己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新名字“奧古斯都(Augustus)”,該詞源自于古羅馬的一個古老職業“占卜者(augurium)”,意為“神圣”;另一方面他還兼領羅馬宗教中的“大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的頭銜,意在表明其與神明之間的密切聯系。屋大維以帶有宗教色彩的稱號和頭銜神化王權的手段被后世皇帝繼承,如馬可皇帝開始自稱為全體臣民的“君主和神”(dominus et deus),戴克里先皇帝則自詡為“大神朱庇特的助手和代理人”(1)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9—330頁。,羅馬皇帝日益成為帝國宗教信仰和道德價值方面的最高權威,任何可能威脅其權威者都可能遭受皇帝的殘酷鎮壓。
屋大維建立起來的以羅馬諸神為核心的神化皇權的體系雖然被之后的皇帝所繼承,但基督教在帝國境內的發展卻開始對其造成新的沖擊。公元1世紀,基督教發源于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區,因其早期的活動受到外界壓力,各地區社團之間也沒有建立起經常性的聯系,加之多在猶太會堂中以隱秘的方式進行活動,故其被認為是猶太教的分支,在帝國享有合法權利。但是“當人們對耶穌基督的認識趨于統一時,便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統一的團體,安條克主教伊格納修斯稱這個團體為普世教會”,(2)G. F. 穆爾:《基督教簡史》,郭舜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50頁。其組織形式日益完善,傳播范圍與日俱增,與帝國傳統多神崇拜的宗教(基督教化時代被稱為“異教”)的矛盾和斗爭也日益激烈,特別是基督教的“天國”概念,使作為“異教”的最高代表者的皇帝們總感到自己的統治會被顛覆。于是,剪除可能會引起帝國混亂和王位不穩的基督教力量,成為“異教”統治者的根本職責。
因此,自公元64年尼祿皇帝借羅馬城大火,以“縱火罪”對基督徒進行捕殺,到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連發數道敕令對基督徒進行最后一次大規模判罪,掀起了對基督教斷斷續續200余年的迫害運動。但是歷史地看,皇帝對基督教的積極迫害,并非因為其認為基督教十惡不赦,而是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引起的皇帝自我危機意識和內心不安所致,正如塔西佗所言:“他把那些自己承認是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來,繼而根據他們的揭發,又有大量的人判了罪,這與其說是因為他們放火,不如說是由于他們對人類的憎恨。”(3)塔西佗:《編年史》(下冊),王以鑄、崔妙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99頁。在皇帝看來,基督教是一個離經叛道、有違祖訓的秘密團體,對帝國穩定和皇權鞏固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應是帝王對其進行迫害的主要原因。
但是1—4世紀帝國的基督教迫害政策,不但沒有消滅這一團體,相反卻使其獲得巨大發展。一些基督教“護教者”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孜孜不倦地向帝國民眾宣傳基督教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信條,消除了一些人對基督教的誤解,皇帝也開始改變了對基督教的態度。起初只是個別皇帝對基督教相關政策的臨時性改變,以尤西比烏斯所記載的圖拉真與兩個基督教農民的故事最具戲劇色彩,“當皇帝得知他所審問的這兩個被視為帝國危險分子的人只擁有2.5英畝土地(約合15畝),而且他們所追求的‘將來的國度’,并不是在地上,而是在來世的天上時,輕蔑地嘲笑了這兄弟二人,并把他們釋放了,然后皇帝下令停止迫害基督徒”。(1)徐家玲、李繼榮:《“米蘭敕令”新探》,《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第70頁。4世紀后,基督教的不斷發展最終使帝國皇帝也逐漸落實在整體政策的考量上,代表性的文件是311年伽勒里烏斯皇帝頒布的《寬容敕令》:
朕認為應將最及時的寬容亦給予他們,以便于他們可以再次成為基督徒,且組織集會——只要他們不做違法亂紀之事……對于朕的寬容,他們要在上帝面前為朕之健康,吾邦之安全,亦為他們自己之健康祈福,以使吾國四面八方安寧無憂,他們亦能安居樂業。(2)李繼榮、徐家玲:《“伽勒里烏斯寬容敕令”文本考——兼論“伽氏敕令”的歷史地位》,《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171頁。
起初對基督徒的迫害是帝國統治者擔心基督教的發展將會有害于帝國統治,現在承認其合法性則是皇帝發現其于自身統治無害。加之,其時皇帝伽勒里烏斯本人已感染疫病數月,原先崇尚的異教神明并沒能使其擺脫病魔的“糾纏”,故其竊以為是自己得罪了基督徒的上神,遂改變態度,希望自己對基督教的承認能換來基督教上帝之寬恕與庇護,助其恢復健康,護佑帝國安寧。但是他態度的改變終究晚了些,未及該法令實施,便與世長辭,帝國復又陷入混亂。313年君士坦丁與李錫尼烏斯頒布“米蘭敕令”重新確認了“伽氏敕令”中的原則,使基督教正式在帝國境內獲得合法地位。(3)傳統觀點認為,“米蘭敕令”的頒布標志著基督教合法化的開始,近年有些學者則認為早在“伽勒里烏斯寬容敕令”中就已經認可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蘭敕令”只是將其重申。參見李繼榮、徐家玲:《“伽勒里烏斯寬容敕令”文本考——兼論“伽氏敕令”的歷史地位》,《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徐家玲、李繼榮:《“米蘭敕令”新探》,《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當然,就在皇帝對基督教從堅決鎮壓到逐漸認可最后完全接受的全過程中,基督教也在不斷調適著自身的理論精要,期望能與帝國的皇權達成一致,以獲得帝王的支持。事實上,早在耶穌赴難后,基督教徒為了迎合羅馬皇帝,就已經開始試圖與羅馬皇權合作,保羅的著名論斷“那在上有權柄的、人人應當順從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由于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4)《新舊約全書·新約·羅馬書》(中文版),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2012年,第180頁。已經明確地向基督教眾說明皇權受之于上帝的理念,坦言了基督教是支持“君權神授”原則的,這成為皇權與教權合作的根基。
皇帝需要新的宗教理論使皇權合法化,基督教則需要皇權對自身進行保護,在這一“需要—契合”的相互支撐下,君士坦丁重新恢復帝國大統之后,決定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積極以上帝代理人的身份,打著“維護神的和平”之旗號,敦促人們遵守上帝的誡命,并在干預和主宰教會事務方面親力親為,積極主動地依靠基督教實現君權的神化。從此,教權與皇權的依存與斗爭貫穿于整個拜占庭帝國,325年君士坦丁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基督教全體主教公會議,親自參與“正統基督教義”的制訂,晚年接受基督教洗禮,并促使他的諸子成為基督徒。當然,皇帝積極干預宗教事務,完全是從帝國社會穩定出發的,從他以下的一段話可見端倪:“如果上帝的人民——我指的是我那些上帝的仆人弟兄們——因他們當中邪惡和損害性的爭吵而分裂成如此狀況,我的思緒如何能夠平靜下來呢?你們要知道,這給我帶來多大的苦惱啊。”(1)尤西比烏斯:《君士坦丁傳》,林中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55頁。
狄奧多西王朝的皇帝不僅將基督教作為一種工具,更是將其逐漸上升并滲入到制度層面,用基督教塑造帝國的形象與思想,來達到穩固帝國的目的。當狄奧多西一世于379年應西帝格拉先(375—383年在位)之命掌控東方帝國的帝權之后,明確表示放棄羅馬皇帝之“最高祭司”的頭銜,表明其放棄羅馬傳統宗教,決心從羅馬諸神的侍奉者轉為基督教上帝之“仆從”的意向。381年,狄奧多西主持了君士坦丁堡主教公會議,重申了《尼西亞信經》中的原則,392年更是下令禁止任何場合向羅馬古代神祗獻祭,異教神廟一律關閉,使基督教成為帝國的國教;而狄奧多西二世面對帝國日益基督教化的現狀,在立法方面開始進一步涉及有關基督教政策的法令,其于438年頒布的16卷的《狄奧多西法典》中,專設一卷用于收錄關于基督教的法令,開啟了皇帝立法與基督教內涵的相互結合。(2)詳見Theodosiu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trans. by C. Phar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而真正利用基督教使皇權上升到一個新高度的是查士丁尼大帝。476年,羅馬西部地區被蠻族取而代之,給羅馬帝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此后羅馬ˉ拜占庭帝國的歷史便進入到一種“恢復往昔”與“面對現實”的矛盾循環的境遇之中,也為拜占庭帝國逐漸脫離古典羅馬的特質奠定了基礎。查士丁尼繼位后,以“一個帝國、一部法典和一個宗教”的戰略目標,通過多次“收復”戰爭、編纂新型法典和鎮壓尼卡起義,不僅打擊了帝國內外的諸多敵人,而且形成了以查士丁尼為核心,狄奧多拉、特里波尼安、貝利撒留等大批支持者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集團,特別在鎮壓了“尼卡起義”后,皇帝終于取得了對貴族的絕對控制,“他始終是一個獨立的君主,任何人都不能與他的權力相抗衡”,(3)A. A Vasiliev. Justin the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poch of Justinian I.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pp. 102-103.皇帝的權力進一步提升,標志著查士丁尼與古典主義傳統的決裂。
除了在軍事上取得成功,查士丁尼還希望借法律和信仰維護社會的穩定。他認為,“皇帝的威嚴光榮既需要兵器,也需要法律”“皇帝既是虔誠法律的伸張者,也是征服敵人的勝利者”,(4)J. B. Moyl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13, p. 1.因此基督教成為皇帝加強自我權力的有力手段,一方面,面對異教、異端勢力仍然在挑戰基督教絕對權威的現狀,查帝于529年下令關閉了宣傳和講授古希臘哲學(異教思想)的異教徒庇護所——雅典學園;另一方面,在奉行“政教協調”原則的前提下,他更加明確了“教會應該成為政府機構手中的有力武器,應盡一切努力使教會服從自己”(1)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 148.的主張,親自主持召開了第五次全基督教主教公會議,“強行軟禁了拒絕在‘三章案’辯論會文件上簽字的羅馬教宗維基里烏斯”,(2)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p. 150-153.這些事實表明查帝篤信絕對的權威,強調在秩序良好的國家中,皇權是至高無上的,教權要依附于皇權,皇帝可以用宗教的靈魂來塑造帝國的軀體,使其合二為一,于是才會有《法學階梯》的開篇“以我主耶穌基督之名”(3)J. B. Moyl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p. 1.來強調君王之立法與治國是上帝所賦予的,體現出皇帝自身權力威嚴與神圣,這也是對基督教經典中“君權神授”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但查士丁尼在位時大規模戰爭引發的國庫虧空和去世后帝國衰微帶來的外族壓境,終使其欲將地中海變成帝國“內湖”的宏圖大志也逐漸付之東流。6—8世紀,拜占庭帝國陷入內憂外患、群雄爭霸、災疫不斷的混亂時期。人們在困境面前的精神崩潰,加速了基督教所宣稱之“上帝憤怒”和“人生而有罪,要盡一生實行救贖”的教義精神在拜占庭帝國的傳播,也進一步推動了君權神圣觀念的形成。希拉克略王朝的皇帝在其新律中也借用基督的名義,但與查士丁尼不同的是,其更主要的方式是通過將君主形象與《圣經》中君王形象進行比擬的方式來達到神化皇權的目的。如希拉克略皇帝完全擊敗了波斯人后,為表其功績,宮廷詩人喬治在其《六日》的作品中,將希拉克略對波斯征戰的6年比喻為《舊約·創世紀》中的創世六日,而在其《十字架的復還》的詩篇中,他更是一改以往將希拉克略比擬為古典英雄的宣傳手法,將其描繪為基督教的君主,主要凸顯其630年奪回圣十字架,使其回歸到耶路撒冷的功績。(4)M. T. G. Humphreys, Law, Power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the Iconoclast Era c. 680-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2015, p. 32.這種形象展現出皇帝的威嚴、軍事首領的戰績和對基督教的虔誠。
717年,利奧三世建立伊蘇里亞王朝后,帝國境況已與2個世紀前的查帝統治時期大不相同,一方面,基督教已經融入到帝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在利奧三世的文治武功,內外兼修的努力治理下,帝國局勢趨于穩定,雖然領土面積進一步縮小,但國家集權得以完整,并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因此在面對剛剛復蘇的帝國,利奧三世需要強化基督教的精神統治,以進一步改造和穩定帝國局勢,達到重建帝國秩序的目的。
所以,利奧三世皇帝在《法律選編》開篇中,即公然打出了“以圣父、圣子、圣靈之名義:虔誠的羅馬皇帝利奧與君士坦丁(Eν oνoματι τοu πατρo? καi τοu υiοu καi τοuaγiου πνεuματο? Λεων καi Κωνσταντiνο? τιστοi βασιλεi? ρωμαiων)”的名號,不僅彰顯了伊蘇里亞人承嗣皇統的正統性,更是突出了帝位之合法與皇帝對神的虔誠,強調皇帝與上帝之間的緊密聯系,表明自身權力的神圣性:
我們的神、上帝、造物主創造了人,賦予其自由意志,并據先知所言“授其律法”以助之,以此使其明了萬事萬物中,何為可為,何為不可為,使他可以選擇前者成為被救贖者,摒棄后者而避免成為受懲者;沒有人可以置身圣戒之外,不遵守或藐視圣戒者,便會因其行為受到報應。(1)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p. 66.
可見,上帝是原初最偉大的立法者,其話語的權威是永恒的,正如《新約·馬太福音》第24章第35節所言,“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為了使法律更具有神圣性權威,《法律選編》將其改編為“上帝的圣諭的權威將不會過時(θεo?……τwν λoγων n δuναμι?……οu παρελεuσεται)”。法典中充斥著上帝永恒之言和對罪惡的明確闡釋,遵循上帝已經創造了人,并授予其律法,將帝國委任給了伊蘇里亞人的主旨。因此,《法律選編》明確表示,“正如上帝吩咐十二使徒之首的彼得一樣,上帝命令我們(皇帝)司牧他最忠實的羊群”(2)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pp. 66-67.,表明皇帝及其在法律中的形象不斷被神化。這次立法活動,借使徒中最權威的彼得之言頒行具有重要意義,皇帝被置于圣徒的繼承者,也就是基督教的繼承者的地位。法典中以廣而告之、勿容置疑的命令形式,要求基督教世界的領袖要關照其信徒,以便于他們可以從牧羊者基督那里獲得救贖。因此,皇帝不僅代表著擁有圣徒的權威,也有責任引導和保護其基督教的子民,《法律選編》的基督教化是在帝國基督教“君權神授”思想演變過程中,與君權強化之理念達成的一種契合與需求,這既是王權強化的一種表現,更是強化王權的一個結果。
三、政局動蕩不穩與緩解社會矛盾的需求
20世紀70年代,隨著美國學者彼得·布朗教授的《古代晚期世界:150—750年》出版,“古代晚期”的概念就此誕生。這一概念主要運用羅馬帝國“轉型理論”對統治學界長達200余年的“衰亡理論”發起挑戰,認為2—7世紀羅馬帝國的歷史進程并非走向衰亡,而是進入了從古典世界向中世紀過渡階段,“衰亡是指帝國西部省份的政治結構,而作為古代晚期文化核心所在的東地中海世界和近東地區卻沒有受到影響,甚至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存活下來的地區仍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偉大文明之一”。(3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 19.“)古代晚期”為學界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研究羅馬ˉ拜占庭的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體現出了帝國在“裂變—整合”、“危機—應對”的循環往復中,度過了帝國漫長的轉型與變革時期,而促發其轉變的核心動力便是3—8世紀的社會動蕩。
3—8世紀社會動蕩的第一個表現便是內外戰爭頻繁發生。自2世紀末,羅馬帝國對外征服步伐放緩,內外矛盾日益凸顯,吉本認為帝國的麻煩“是從180年馬克·奧勒留皇帝的駕崩開始的,該皇帝的逝世標志著一段和平時代、繁榮和良好的政府管理時期的結束”,(1)W. Treadgold, A Concise History of Byzantium, Palgrave Maciillan: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2001, p. 6.是所謂的“3世紀危機”爆發的節點,具體表現為這一時期內戰全面爆發,王位頻繁更替。據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統計,羅馬“從235年至284年這一段時期里,有過近24個皇帝,可只有一個是自然死亡”(2)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30頁。,其余都因戰爭和宮廷內爭而暴亡。
君士坦丁大帝在帝位之爭中以絕對的優勢獲得了勝利,通過內外改革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權的統治體系,穩定了局勢,此后的皇帝也沿用并不斷完善這一體系,但是由于長期以來帝國內部戰爭的影響,人口銳減,城市遭到破壞,整體實力受到極大地折損,帝國周圍的外族趁機給帝國施加壓力,東邊的波斯人,北邊的日耳曼人均對帝國疆域虎視眈眈,如朱利安皇帝統治時期,因對外戰爭屢遭敗績,不得不“將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小塊邊境地區割讓給了波斯”,而“伊利里亞的一些邊境地區也先后短暫陷于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掌控之中”,(3)W. Treadgold, A Concise History of Byzantium, p. 37.378年,哥特人進軍君士坦丁堡,雙方會戰于亞得里亞堡,結果“皇帝瓦倫斯在戰斗中被殺,羅馬軍隊徹底戰敗”(4)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I), p. 87.。
476年,蠻族首領奧多亞克罷黜了西部羅馬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羅馬帝國西半部地區皇統結束,此即歷史上經常強調的“西羅馬帝國的滅亡”的標志,也是羅馬周邊“蠻族”對羅馬帝國長期蠶食的最后一個階段,一個世紀之后倫巴第人進入意大利,才標志著蠻族對羅馬帝國西部入侵行動的最后完成。即使如此,東羅馬皇帝(拜占庭)試圖收復“失地”的“光復”之夢不僅沒有因此而破滅,反而使50年后登極的拜占庭皇帝更強烈地感受到恢復君士坦丁大帝之輝煌的迫切性。于是,527年登上皇位的查士丁尼皇帝,便積極投身于實現“一個帝國、一部法典和一個宗教”的戰略目標,對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實行了長達30余年的“光復”戰爭,并在他逝世之際,完成了再度使地中海變成羅馬帝國之內湖的偉業。但是大規模戰爭,也致使帝國耗損巨大,先是希拉克略王朝的皇帝在7世紀上半期的對波斯戰爭中失利,丟失了耶路撒冷的“真十字架”(5)Theophanes, Chronicle: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431.;而后戰勝了波斯人,志得意滿地奪回了“真十字架”,卻又很快在阿拉伯半島新興的阿拉伯人征服戰爭中一敗涂地,致使7世紀末的帝國面臨多方面危機難以自救。
除了戰亂,瘟疫、地震等自然災害的集中爆發,也成為“古代晚期”社會動蕩和帝國衰落的重要因素。早在“3世紀危機”前后,羅馬帝國就先后爆發了“安東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雖然這兩場瘟疫的具體傷亡情況已無法查證,但從史料零星記載及皇帝伽勒里烏斯死于后一場瘟疫的事實來看,其必定對帝國人口造成了巨大影響。之后的“查士丁尼瘟疫”當屬3—8世紀地中海世界影響最大的一次瘟疫了,對其情況的記載也最為詳盡。據普羅科比記載,這場瘟疫“起初死亡的人數較低”,但之后死亡的人數不斷攀升,再后來甚至上升到日均死亡5 000人,甚至有時會達到萬人及以上”,“在掩埋尸體時,開始還可以參加親人的葬禮,后來死者太多,導致全城處于混亂狀態,很多家庭整戶死亡,一些身份尊貴的人竟也因為瘟疫當中無勞動力可用而在死后多日無法掩埋。很多尸體被隨意地扔進塔樓,等尸體堆滿后再封頂,全城彌漫著一種惡臭”。(1)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I), trans. by H. B. Dewing.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4, pp. 465-469.這場瘟疫在帝國肆虐四月有余,其中三個月為死亡高峰期,僅君士坦丁堡按平均每日5 000人,共90日計算,死亡人數就至少高達45萬,帝國首都一時間成為死神橫行的真正人間地獄。之后瘟疫周期性、多城市爆發,如史家阿加西阿斯記載了558年瘟疫第二次爆發的情況,“那一年初春,瘟疫第二次來襲,肆虐帝國首都,奪取大批居民的性命,并從一個地方蔓延到另一個地方”(2)Agathias, The Histories 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trans. by J. D. Frendo,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1975, p. 231.。
與瘟疫相伴的還有地震的破壞,據學者唐尼統計,“自324年至1453年,拜占庭帝國1100余年的歷史中,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圍的大小地震共55次,僅6—8世紀就有15次”(3)G. Downey, “Earthquake at Constantinople and Vicinity AD 324-1453”, Speculum, 1955 (4), pp. 597-598.,525—740年間,大約每18年就有一次大地震,如526年帝國第三大城市安條克的地震破壞性就是極大的,“所有房屋與教堂都被震塌,城中的精美物品都被摧毀”(4)Theophanes, Chronicle: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p. 264.,“那些沒有來得及逃離房屋的都成為了一具具尸體”(5)John,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Vol. 90), trans. by R. H. Charl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916, p. 137.,“死亡人數約有25萬”(6)John Malas, (Vol. 18).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2.。而之后557年君士坦丁堡的地震中,“不僅毀壞了城中兩座城墻——君士坦丁城墻和狄奧多西城墻,還摧毀了大量的教堂,特別是赫布多蒙教堂(Hebdomon)教堂——即圣撒母耳教堂(St.Samuel)和周圍的一些教堂……該地震帶來的毀滅無一可以幸免”(7)Theophanes, Chronicle: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p. 339.。
可見,戰爭、瘟疫和地震等因素所造成的社會動蕩已經成為帝國“古代晚期”的帝國社會常態。因而就連查士丁尼大帝的輝煌統治時期,也被吉本批評:“戰爭、瘟疫和饑荒三重重災同時降臨在查士丁尼臣民的頭上,人口數量的減少成了他統治時期的一個極大污點”,(8)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黃宜思、黃雨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30頁。其不僅直接導致帝國人口銳減、經濟衰微和政局動蕩,更重要的是對帝國百姓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在戰爭、瘟疫和地震中,百姓直面的是死亡的威脅、流離的生活和不斷的苦難,看著周圍之人大批去世,城市境況日益破敗,饑荒生活逐漸臨近,百姓內心的恐慌、精神上的無助,在當時的史家記載中得到生動描述,例如在551年的亞歷山大大地震后,阿加西阿斯記載道,“所有居民,特別是年老之人都被眼前的境況驚到了……大家聚集街頭,紛紛陷入到因這場突如其來的事件所引發的極度恐慌中”,(1)Agathias, The Histories 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 trans. by J. D. Frendo, p. 48.而在559年君士坦丁堡的大災之后,不僅引發了“人們突然闖進商鋪和面包鋪進行哄搶,僅3個小時,城中的面包就被搶光”(2)武鵬、劉榕榕:《六世紀東地中海的地震災害造成的精神影響》,《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第180頁。情形的出現,還導致“謠傳查士丁尼已經去世,民眾陷入恐慌,官員信以為真,整個城市一度陷入極度混亂”(3)武鵬、劉榕榕:《六世紀東地中海的地震災害造成的精神影響》,《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第178頁。的局面。
面對生命的無助,一些民眾也試圖向帝國的古典諸神求助或者試圖去在希臘哲學理念中尋找應對之術。但是當災難來臨時,諸神的代言人、異教的祭司,卻無法對災難發生的緣由做出任何解釋,更甚之,許多祭司與宦官、富人竟然利用自己的優越地位迅速逃離疾疫流行之地,留下陷于更加恐慌之中的平民百姓于不顧;而希臘哲學所強調的非個人過程和自然規律,也無法解釋死亡突然不加選擇地降臨到老人孩子、富人窮人、好人壞人身上的原因。古代世界的神明在民眾迷茫、恐懼與面臨生死邊緣逐漸失去了其往日受尊崇的地位。基督教的“博愛”與“互助”精神、今生與來世的圖景以及行醫布道的慈善救助活動,卻為帝國百姓將精神上的疑惑指明了方向。
對于自然災害和社會激蕩,基督教擁有自己的解釋理論。在其看來,當時瘟疫等災害的發生,均是因為羅馬人做了錯事、行了惡舉所應得到的報應,例如在安東尼瘟疫爆發時,教會史家奧羅西烏斯從基督教的視角給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認為這是對馬克皇帝在高盧對基督徒進行迫害的懲罰,而對于這種懲罰,也并非不能得到解決和規避,只要民眾能努力“贖罪”便可以化解。所以,《圣經》中明確表明“義人必因信而生”(4)《新舊約全書·新約·羅馬書》(中文版),第168頁。,要求人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5)《新舊約全書·新約·羅馬書》(中文版),第82頁。,這里不僅對生死的原因做出了基督教神學的“合理”解釋,為死后的人描繪了“來生”的圖景,更為現世的人指明了要相互扶持、相互幫助的出路。因此,在這種教義思想的指引下,基督教會在實踐中將自己打造為關愛弱者的庇護所,6世紀后其慈善行為更加普遍,收容所、醫院、孤兒院、救濟所等專門的慈善機構開始建立,而民眾對于基督教的依賴和信任亦愈發強烈,據文獻記載,533年君士坦丁堡發生大地震后,“所有城中百姓都聚集到君士坦丁廣場進行祈禱”,(6)武鵬、劉榕榕:《六世紀東地中海的地震災害造成的精神影響》,《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第178頁。“安條克地震后數日的基督升天節,幸存的民眾也聚集到教堂前,在教士的帶領下,進行祈禱,以求上帝的拯救和獲得心靈的安慰”。(7)John,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Vol. 90), trans. by R. H. Charles, p. 137.
因此,自313年的“米蘭敕令”正式獲得合法地位,392年獲得國教地位后,4—8世紀間,作為皇帝穩定民心、抵御外敵的助力,民眾撫慰心靈、醫治創傷的藥劑,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在皇帝的支持和民眾的追捧下一路扶搖而上,至717年伊蘇里亞王朝建立,利奧三世登基后,已經完成了對帝國的基督化改造。但是利奧是在阿拉伯軍隊一路北上,日日進逼君士坦丁堡、帝國政權風雨飄搖的危難之際登上皇位的,作為對支持他上位的元老貴族勢力的承諾,他必須阻止敵軍于首都之外,穩定帝國政權、救助天災、安定民心,而首當其沖的問題,是解決長期以來天災人禍引起的帝國民眾思想混亂和信仰危機的問題。關于此,從726年利奧三世發起“禁止偶像崇拜”的禁令也可看出端倪,當時塞拉島(Thera)發生了火山噴發,影響地區甚廣,皇帝認為這是因圣像崇拜惹怒上帝所致,為了平復社會的混亂,安撫上帝的憤怒,利奧三世下令將都城“銅門”上的基督像取下,禁止偶像崇拜,恢復昔日十字架崇拜。但是令皇帝沒有想到的是,這次要禁止圣像崇拜的禁令,不僅沒有達到穩定民心的作用,還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混亂與反抗,帝國的民眾的思想再次陷入到危機之中。
在直接干預民眾信仰無果的情形下,利奧三世也注意到要真正實現帝國民眾思想的穩定,還需借助立法制度,特別是要著手運用羅馬帝國的立法傳統修復因社會動蕩造成的立法頹廢和社會秩序的混亂,解決在一個希臘化的帝國如何有效地將當年查士丁尼欽定的拉丁文法典付諸實施的問題。換言之,在現實社會的需求下,剛剛穩定不久的帝國,需要利奧三世在司法領域引入基督教的原則與精神,實現法典的基督教化和完全的希臘化,達到慰撫民心,穩定帝國秩序的目的。
于是利奧三世皇帝和他的兒子、共治者君士坦丁五世于740年決定制定新的、便利可行的基督教化的希臘文法典。他在《法律選編》的前言中突出了自己的意向和改造傳統立法原則的決心,并在全文中多處直接引用基督教的“公平”與“正義”理念,要求法官以基督的博愛精神執法立威。對那些蔑視公正和不義的法官,則引用《舊約·詩篇》第58章第1—2節中的內容進行嚴厲質問,“世人哪,你們所說之詞,真合公義嗎?施行審判,豈按正直嗎?不然你們是心中作惡,你們在地上稱出你們手所行的暴(εi αληθw? aρα δικαιοσuνην λαλεiτε, εuθεiα? κρiνατε τa? οi υiοi τwν aνθρwπων. καiγaρ εν καρδia aνομiαν εργaζεσθε εν τn γn, aδικiαν αi χεiρε? ?μwν συμπλεκουσιν.)”,對于賣官售爵者也援引《德訓篇》第7章第4—6節中的內容進行告誡:“不要向上主求做大官,也不要向君主求榮位;不要謀求做大官,怕你無力拔除不義(μ?τε παρaκυρiου nγεμονiαν ζητεiτωσαν, μ?τε παρa βασιλεω? καθεδραν δoξη? αiτεiτωσαν, μ?τε γiνεσθαι κριταi προαιρεiσθωσαν, aδικiα? οuδαμw? εξαiρειν iσχuοντε?)”,所以皇帝要求任職的法官“切莫據表象來斷案,要據公正判斷是非(μn κρiνετε κατ’ ?ψιν, aλλa τnν δικαiαν κρiσιν κρiνατε,πaση? δωροληψiα? aπεχεσθαι δiκαιον.)”。(1)E. F. Fresh field. A Manual of Roman Law the Ecloga published by the Emperors Leo III and Constantine V of Isasuria at Constantinople AD 726, pp. 68-70.此外,《法律選編》中還進一步落實了“仁愛”的舉措:如對死刑進行了嚴格限制,廢除了一些嚴酷的刑罰。可見,在經歷了基督教的快速融入發展及長期動蕩混亂的時期后,公正、正義與博愛無疑必然會成為帝國臣民安定內心,追求未來的重要精神藥劑,在此公正與博愛是融為一體的,在當時的境況下,前者是后者的基礎,若無前者,后者也只能是虛無不實的概念。
總之,在“古代晚期”社會急劇變化、百姓思想極度混亂的時期,基督教在與諸多異教信仰相互爭論和斗爭中,完成了自我理論與當時社會背景及民眾心理需求的緊密結合,具有了撫慰恐慌中百姓的功能,正如陳志強教授對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中所言,“廣泛出現的社會恐懼會改變人們正常的生活規律,導致人們對現存政治和國家看法的改變,進而導致社會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標準的改變,使人們更加篤信‘上帝’”,《法律選編》最終完成法律的基督教化,正是利奧三世皇帝應社會之需,用“上帝”之信仰來撫平社會動蕩的一種手段和表現。
四、余 論
行文至此,本文以《法律選編》為中心,基本上完成了對早期拜占庭立法基督教化的生成邏輯的考察與分析,對這一現象的出現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從上有王權加強的需要,自下有民眾慰藉的需求,上下二元的相互助力,促成了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形成路徑邏輯生成。
首先,早期拜占庭法律基督教化的形成,與基督教所含有的“君權神授”的思想符合了3—8世紀皇權強化的趨勢有很大關系。自公元前27年屋大維稱“奧古斯都”,羅馬的帝國建制日益明顯,加強王權和構建一套完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官僚統治體系成為帝國歷史發展的趨勢,期間利用宗教神化王權也成為各代皇帝的慣用手段。在帝國早期古典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屋大維擔任“大祭司”之職將自己塑造為諸神的代言人和宗教事務的最高權威,便開啟了這一進程,之后歷史上的多次基督教迫害,實質上是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引起的皇帝對個人權威喪失的擔心所致。但是隨著帝國模式漸成和基督教的日益完善,皇帝發現多神崇拜已經無法滿足帝國統一思想的需求,而講求“一神”和“君權神授”的基督教卻對王權加強和統一思想大有裨益,于是從311年的“伽勒里烏斯寬容敕令”頒布后,皇權與教權緊密扶持與配合構成了3—8世紀拜占庭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內容。利奧三世登基以后,面對帝國的內憂外患的混亂局面,也希望利用教權強調自身權力的神圣性與合法性,于是在《法律選編》的序言開篇便說明這部法典是“以圣父、圣子、圣靈,虔誠的皇帝利奧與君士坦丁之名”頒布的。這與查士丁尼《法學階梯》的開篇“以我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有本質的區別,前者將神與人共置一處,更加凸顯“君權神授”的意味,《法律選編》基督教化與其說是基督教發展的順勢結果,倒不如說其“君權神授”的思想和“一神教”的形態,適應了8世紀王權加強的社會需求。
其次,“古代晚期”因瘟疫、地震及戰亂所引發的社會動蕩,需要立法的基督教化來撫平社會和民眾遭受的創傷。“古代晚期”的帝國經歷了3世紀危機、蠻族入侵、大瘟疫和大地震等諸多天災人禍,導致帝國人口急劇下降、疆域面積不斷縮小,特別是災難中,面對死亡的威脅和生活的困苦,傳統的古典宗教信仰無法對突如其來的死亡做出合理的解釋,帝國民眾陷入到極度恐懼和信仰危機中,但是基督教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構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講求互助與博愛、公平與正義、今世與來世,賦予死亡以生命的意義。因此,大災大難面前,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適應于充斥著困苦、疾病和暴死的亂世思想和情感體系,其完整理論闡釋及實踐上的善舉——哪怕僅是最基本的護理,都可能極大地減少死亡率——都會使民眾在相互依存間獲得溫馨感覺,獲得在其他信仰中無法獲得的希望,對受到重創之后的民眾具有撫平創傷、維護穩定的功效。因此,利奧三世的《法律選編》引用了大量的基督教仁愛與公正原則,要求司法公平和追求刑罰人道,其目的就是希望以基督教的精神原則,安撫民眾的情緒,重塑百姓的信仰,這是民心之所向,更是社會之所需。
正是在“君權神授”理論的支持下和“安定民心”現實的需求下,早期拜占庭法律一步步將基督教的思想與原則融入到了法典之中,至8世紀伊蘇里亞王朝《法律選編》的頒布最終完成了這一過程。該法典以基督教化的形式,擔起了完成對帝王權力加強和撫平民眾心理創傷的使命,也因此被稱為拜占庭帝國第一部官修基督教的法典,拉開了中世紀拜占庭立法的序幕,而其在穩定社會局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之后馬其頓王朝“黃金時代”盛世局面的出現亦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