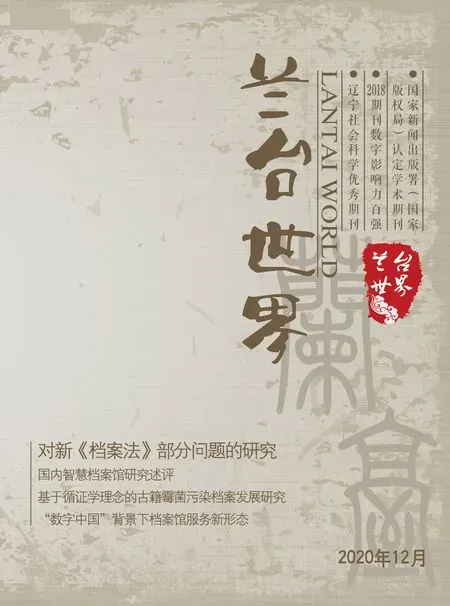“高校記憶”視角下的校園文化與檔案情感價值研究
張 靜 刁麗娜
著名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創“集體記憶”的概念,此后檔案學者開始發掘檔案記憶在社會學、文化學等諸多領域的發展演變,特別是其與文化建設之間的相互滲透。一些高等院校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會逐漸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園文化,這些文化的積累成為影響幾代人成長的“高校記憶”。目前,檔案館、校史館等機構大多表達的是學校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一段完整的大學歷史離不開豐富的學校教學與生活等具體細節。高校檔案記載著大學文化的變遷、傳承和發展,是大學特色辦學、文化傳承的寶貴資源,與其他信息資源相比具有獨特的文化資源屬性,是“高校記憶”的重要載體,在推動校園文化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高校檔案是高校文化的重要載體和發展產物,是實現大學文化傳承和延續的橋梁紐帶,而“高校記憶”工程是大學精神和情感的長期積淀。檔案情感價值理論的提出,為開發檔案情感價值、創新拓展檔案服務形式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和手段[1]。在新時代校園文化建設背景下開展“高校記憶”構建工作,深入發掘檔案中的情感價值,有助于更好地發揮“高校記憶”對校園文化的延續傳承、教學育人以及凝神聚力的作用[2]。高校檔案記憶觀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透視大學文化建設和檔案管理的新視角,基于“高校記憶”視域下探討檔案情感價值與檔案管理的關系,有利于推動檔案工作與校園文化建設的共同發展。
一、檔案情感價值研究的必要性
記憶是容易出錯的,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檔案被認為是記憶的創造者,而不是記錄者,個人記憶根植于社會語境,我們的記憶往往通過集體框架被重新解釋呈現。換言之,我們常常通過群體中的“足夠多的個人記憶重疊”來描述共同的感知。既然記憶被認為是不準確和不可信的,而檔案又是這些記憶的保存者,那么為什么人們要相信它們呢?
由于過去的事情永遠不可能被完全掌握,檔案工作者所能做的就是收集描述發生事情的材料,即使所保存的記憶是扭曲的或不正確的,它們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準確地描述一段歷史。這些記憶和故事展示了人們對一件事及其影響的直觀感受,當它們被比較、對比并與客觀事實相結合時,這些感覺和記憶有助于使研究人員更全面地了解歷史,從而實現更準確的歷史再現。
檔案為公眾和社會創造了豐富的情感體驗機會,理解檔案的情感價值有助于研究者理解歷史。檔案的情感價值是指檔案對人們所具有的情感方面的有用性,也就是人們由檔案內容或載體觸發的對歷史、記憶、文化和社會的情感體驗、情感共鳴等[3]。但由于情感具有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承認檔案情感價值可能會削弱檔案的公信力。
檔案工作者在促進檔案情感價值的實現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絕對客觀的檔案工作者是不存在的,但由于認識到情感的作用,通過一定的學習和訓練,他們應該更容易理解和承認自己的偏見,并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檔案工作者要傾注人文情感關懷,以制度化的形式在檔案收集、整理、鑒定、利用等業務實踐中落實情感價值,一方面挖掘潛藏情感需求,優化檔案工作業務環節,提供個性化、人性化的服務,另一方面自覺接受監督與評價,提供社會化檔案成果[4]。
檔案情感研究是情感理論與檔案領域相結合的全新研究領域,對檔案情感價值的探討,有利于檔案工作更好地服務于社會記憶構建和公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二、“高校記憶”視角下的校園文化與情感價值的聯系
“高校記憶”是承載學校過往、富含獨特人文精神的資源,能夠進一步充實館藏,彌補檔案的不足和缺失,使學校歷史的呈現更加豐滿。“高校記憶”以獨特的內容和形式生動地展現高校發展的歷史脈絡,較之于其他檔案材料更具鮮活的感染力和獨特的個性化情感,承載著大學精神等校園文化的精髓和靈魂,有力助推高校精神文化生態系統的建設[5]。
通過開展“高校記憶”構建工作,深入發掘檔案中的情感價值,將內化為個人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的大學精神提取出來,對于豐富檔案工作內涵和助推校園文化建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學的檔案館和宣傳部門通過開展各種外聯活動,包括展覽、演講和校慶等活動,向學生和家長傳達獨特的校園文化和價值觀,幫助人們了解校園文化的變遷和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借助數字展覽、博客、微信等數字時代催生的各種新興媒體,與廣大師生建立起密切聯系。通過保存、傳播和宣傳其歷史,高校能夠營造出一種強大而生動的文化認同,這種文化認同可以通過記錄歷史、傳統、校園建筑及各種其他材料來塑造和促進。通過這種方式將在校學生與校園歷史聯系起來,可以使學生們產生強烈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在他們畢業后仍能持續存在。當一個高校的檔案變成一個擁有文字記錄、圖像和紀念品等多種形式“美好記憶”的倉庫,會使學生、教師、員工和校友對母校充滿熱情。“高校記憶”能夠提供一種讓我們回到不同時代的方式,把今天的校園和往日的校園連接起來,成為幾代人之間凝聚力的源泉,并為了解校園的歷史變遷提供一個窗口[2]。
三、高校檔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傳統檔案工作追求理性、客觀的價值取向,而忽略了檔案的情感價值。檔案工作者要明確自己的責任和使命,充分認識情感價值在構建“高校記憶”中的重要作用,完成從信息的保管者到知識的管理者,再到記憶的建構者的角色轉變[6]。高校檔案工作者要站在保存和構建“高校記憶”的高度,突破現有的工作格局和工作方式,重新認識和定義檔案人員的職責。
1. 認識到角色定位的重要性。高校檔案工作者是“高校記憶”的一員,他們自己的記憶從一開始就在形成。檔案工作者通過評估來決定什么是保留的,什么是丟棄的,從而塑造未來,他們不再是通往學校歷史的橋梁,而是“高校記憶”的創造者。檔案工作者現在必須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權力,他們的作用關系到“高校記憶”的創造和使用。高校檔案工作者必須成為文獻工作者,而不僅僅是記錄的保存者。他們必須運用類似于歷史學家的技能和知識來預測未來檔案的用途,再加上他們對整個學校運作的高度熟悉,從而有能力創建一個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學校記錄。
2.培養檔案工作情感意識。在充分認識檔案具有情感價值后,培養自身對檔案工作的情感意識,并積極利用檔案情感價值在實踐中的影響,重塑檔案收集和利用等工作業務環節。檔案工作者應當盡力滿足大學不同群體的記憶及情感需求,適當擴大檔案收集范圍,特別是收集能夠引發情感互動的檔案進館,并選取能夠引發公眾情感共鳴的檔案進行開發,利用最新傳播媒介和互動手段建立觸動公眾情感認同和共鳴的途徑[7]。
3.保持情感的獨立與客觀。如果檔案工作者希望收集到代表性的文檔材料,除了在收集過程中一定要保持積極主動的姿態,還要在精神上與自己保持距離,或者至少認識到自身情感對工作的影響,這是一個成熟的檔案工作者應該具備的技能。在檔案收集中應區別中立和客觀這兩個概念。檔案工作者應該客觀地收集資料并保持專業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中立的。因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具有思想、情感和傾向,因而在檔案收集過程中不可能完全中立。情感和個人記憶可能會模糊檔案工作者在取舍檔案材料時的決策,特別是當記錄高校發展歷史過程中一些具有悲劇色彩的故事時,不可避免會受到個人記憶、媒體和其他因素的影響,這時更應該引起檔案工作者的注意。大學檔案工作者有責任記錄“高校記憶”,成為“高校記憶”的管理者,同時維護檔案作為歷史記錄存儲庫的使命[8]。
4.加強自我素質提升。目前,高校檔案工作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壓力,除了管理學校官方檔案的職責占用了大部分的專業時間、資源、空間和預算,隨著電子檔案等新媒體的興起,工作愈加繁重。此外,由于檔案專業人員編制相對變化不大,這就意味著要用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工作。對于檔案工作者來說,面對不斷變化的媒體和日益增加的檔案保管負擔,保持敏銳的洞察力,不斷提升自我能力素養是至關重要的。“高校記憶”視角下的檔案工作對檔案工作者的職業精神和專業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檔案工作者要站在構建學校集體記憶的高度,在工作中必須堅持全面的、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將檔案短期的查考利用價值和長期的構建記憶的文化價值相統一,將服務學校發展與以人為本相統一[6]。
“高校記憶”檔案工程構建任務復雜艱巨,需要不同層面和不同視角的思考與探索嘗試。情感價值理論為高校檔案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與思路,為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注入新活力。高校檔案工作者應該主動以情感價值理論為指導,以構建與強化“高校記憶”為目標,以校園精神文化建設為動力,將檔案情感價值的理念融入到“高校記憶”檔案發展的各個環節中去,不斷優化提升高校檔案的社會服務與社會記憶建構功能,滿足社會公眾的情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