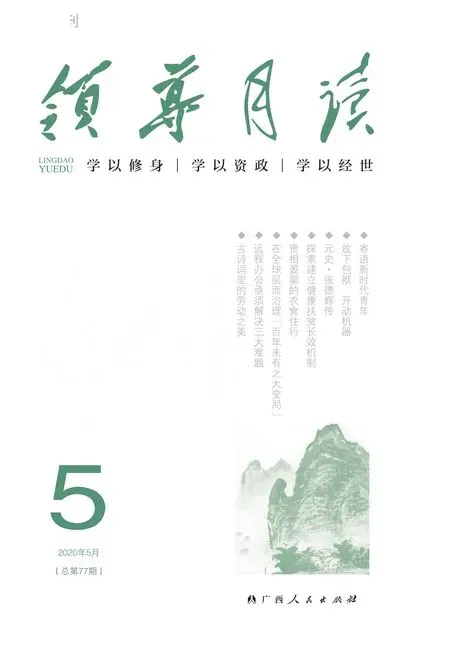在全球層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龐中英 卜永光
雖然全球治理的概念在冷戰結束后才開始被廣泛使用,但其實踐可以追溯至國際關系史上一些國家通過跨國協調解決共同問題的經驗。其中,19世紀“歐洲協和”所推動的國際治理及其帶來的“百年和平”,尤為值得重視。1945 年后,聯合國和國際經濟組織相繼誕生,當今時代背景下,在全球層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以史為鑒,在充分借鑒相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積極探尋當前全球治理困境的破解之道。
通過全球治理應對“大變局”的歷史經驗
19世紀的歐洲已經具有當代全球治理最為實質的內容和形式。美國學者米锃認為,全球治理是集體意圖的形成和維持,是各國對一起解決問題的共同承諾。從拿破侖被打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00年(1815—1914年)間,“歐洲協和”正是發揮了這樣一種作用。今天我們所談的全球治理,其在19 世紀的起源正是“歐洲協和”。在這100 年中,歐洲各國之間,尤其是“列強”為了解決關涉多方的共同問題而召開了許多國際會議,進行“面對面的外交”。這些國際會議被叫作“強國之間的協和”,即“歐洲協和”。
19 世紀的歐洲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和平的不可持續性。1815年,一度橫掃歐洲大陸、撼動諸大國統治的拿破侖被打敗,但和平并未自動產生。站在當時的歷史節點看,“重建的世界”向何處去,仍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歐洲面對的是一個空前的“大變局”。不過,從1815 年起的近100 年,歐洲卻大體上是和平的。為什么從17世紀以來戰亂不止的歐洲居然在19世紀享受了如此長時段的和平?研究人員普遍把這一和平歸功于作為國際制度或者國際秩序維護者的“歐洲協和”。
“歐洲協和”有很多陰暗面,例如各種不可告人的“秘密協議”。正是這些陰暗面導致了“歐洲協和”的最終失敗。在巴黎和會上,美國威爾遜政府揭露了“歐洲協和”的陰暗面。與之相比,1945年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中誕生的聯合國和國際經濟組織,植根于厚重的世界歷史(尤其是“歐洲協和”歷史)所提供的經驗和教訓。這些機構盡管不是“世界政府”,但卻是現代意義上在全球層面對超出一個國家范圍的問題與挑戰的集體治理或國際治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歐洲協和”的陰暗面,并在涉及范圍、涵蓋內容和對全球政治影響的深遠程度上大大超越了19世紀的“歐洲協和”。
站在冷戰結束的十字路口,有人主張和實踐“單極世界”,即由“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統治這個世界;有人主張“全球治理”。2017 年,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這個政府把自己嚴格區別于從老布什到奧巴馬的后冷戰時期的美國歷屆政府,號稱“讓美國再次偉大”,踐行“經濟民族主義”和“美國優先”,卻并不想繼續奉行后冷戰時期在美國主流價值觀主導下,以領導世界為核心的傳統外交政策,而是對其進行重大調整,包括接連退出一系列現有全球治理進程(尤其是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定)。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未必等于“美國放棄了世界領導”,但可以明確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治下,“單極世界”幾乎不再存在。
與此同時,強力崛起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給全球治理實踐帶來了嚴重沖擊。作為一種理論學說和行動主張的“全球治理”逐漸失去上升勢頭。2015年,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的歷史時刻,全球治理在形式上似乎達到了其高峰:在各國領導人參加的聯合國峰會上,以“改變我們的世界”為訴求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獲得通過;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巴黎協定》達成。但是,這些全球治理進展并沒有減輕人們對“全球治理的未來”的憂慮。2019年9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第74屆聯大演講中聲言對世界大分裂的可能性表示擔心。古特雷斯還指出,“氣候變化”,已經是一場“氣候危機”。2019年12月11日,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在運行了24 年后正式停擺。2019 年12 月15 日,由西班牙協助智利承辦的馬德里聯合國氣候大會在諸多談判目標(尤其是建立碳市場)上沒有達成協議。顯然,全球治理已陷入嚴重困境。
協和的關鍵性受到研究界的再發掘
面對包括中國崛起在內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一些有影響的研究者對協和的歷史經驗和基于這樣的歷史經驗產生的國際理論再次產生了濃厚興趣,認為“新協和”可能是治理21 世紀全球“大變局”的有效途徑。總體來看,當協和受到研究界再發掘并被置于全球治理的新語境中討論時,它在融入時代因素的過程中也實現了內涵更新:19 世紀的大國協和主要限于歐洲地區,新協和的范圍擴大到了全球層面,而亞洲則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國際協和的新重心;由于更多的國家以及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卷入全球事務中,新協和的參與主體變得更加多元;全球性問題的爆炸性增長讓新協和的議題領域大大拓展;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發展對協和的代表性與合法性提出了新要求,呼喚協和方式從大國密謀、強權專斷,走向更大范圍內以至全球性的平等磋商,但大國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仍然難以取代,而關于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協和的問題,則成為關注的焦點議題。
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澳大利亞學者較早主張21世紀的大國協和。2012年,曾擔任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主要起草者之一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學教授懷特在其著作《對華抉擇:為什么美國要分權》中率先提出了美國要與中國進行協和的重要建議,他認為,與中國分權,構建亞洲協和機制管控兩國可能的對抗,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兩國在地區和國際層面各領域的協和,才是美國唯一明智的選擇。也唯其如此,人類在21世紀才能繼續享有和平與繁榮。
在歐洲,德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米勒主持了題為“21世紀的大國協和——大國多邊主義和避免世界大戰”的“歐洲項目”。該項目共產生兩項重要成果,一份是公共政策報告《21世紀的國際協和》,于2014年在瑞士洛迦諾首發;一份是學術論文集《強國多邊主義和預防大戰:爭論21世紀的國際協和》。在米勒等人看來,國際體系中的權力更迭和轉移常與沖突相伴,在汲取19世紀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應以更廣泛的大國合作框架取代權力轉移理論中的雙邊“決斗”情勢,進而構建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邊安全機制。
在美國,著名的戰略研究智庫蘭德公司和老牌智庫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等研究機構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重要研究。蘭德公司在其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呼吁美國以19世紀的“歐洲協和”經驗為借鑒,在尊重既有規則和秩序的基礎上主動進行國際協和,進而構建穩定、可持續的世界新秩序。長期擔任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的著名學者理查德·哈斯將“歐洲協和”視為迄今為止人們在建立和維系國際秩序方面最成功的案例。他力主用新的協和應對當前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崩潰帶來的挑戰,認為當前世界正面臨著與19世紀中期相似的國際形勢,尤其需要汲取歷史教訓,在維系國際協和有效運轉的基礎上避免系統性危機的發生。
美國“退群”與全球治理的未來
特朗普上臺執政后,美國極力批評“全球治理”,并站在“全球治理”的對立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包括退出了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關鍵的多邊協議(如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在區域方面,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的態度和行動,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
不過,需要正確認識特朗普執政后美國的“退群”行動,以避免在判斷美國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時發生誤解。即便“退群”,美國因素實際上仍然滲透在當今大多數全球治理進程之中。那些美國退出或原本就不在其中的國際組織和多邊協議,美國與它們的關系仍然復雜。比如,美國并沒有參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卻“承認該《公約》的大部分內容為習慣國際法。它盡量遵守該《公約》,也希望其他國家這樣做”。在退出《巴黎協定》后,美國與《巴黎協定》之間的關系也類似于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關系。
即便是退出《巴黎協定》的特朗普政府,也并沒有脫離聯合國氣候變化治理進程。在馬德里氣候大會舉行前夕,美國決定派出由負責海洋及國際環境與科學事務的國務院官員瑪西亞·伯尼卡特率領的政府代表團參加大會。有人認為,盡管特朗普政府改變了美國的氣候政策,但是美國仍然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發揮著某種領導角色。
盡管如此,這些案例還是啟發人們思考這樣的問題:缺少了美國的國際協和還能否維系,進而形成沒有美國的全球治理?在多邊經貿合作領域,在被美國置于被動處境后,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已經在相對主動地探索這種可能性。在全球層面,加拿大和歐盟于2019 年7 月25 日共同宣布,建立一項臨時協定或者臨時機制,應對WTO 上訴機構面臨的危機。加拿大和歐盟呼吁其他WTO 成員加入這項開放的“臨時協定”。2019年12月11日,WTO上訴機構正式“停擺”。接下來,加拿大和歐盟帶頭的“臨時協定”能否發揮某種替代作用,值得繼續觀察。
鑒往方能知今,并為未來做好準備。當前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以通過加強全球治理來應對。如果國際社會多數國家能夠切實有效地維持和加強全球治理,21世紀的世界仍然可能享有長期的和平與繁榮。
隨筆:
沒有書籍的屋子,就像沒有靈魂的軀體。
——西塞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