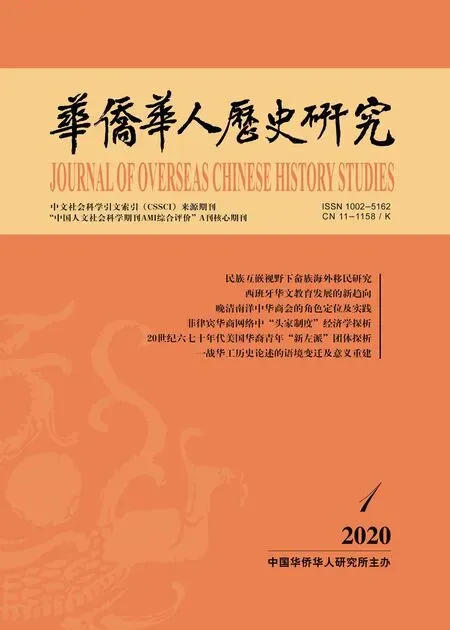晚清時期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角色定位及其實踐*
張亞光 沈 博
(北京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
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經濟秩序被打破,沿海省份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1]。受工業化沖擊,沿海大量人口外流,南洋成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據麥基昂(McKeown)統計,1846—1940 年,超過1900 萬中國人移民東南亞、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地區。[2]近代南洋社會中,“西人雖握其政權,而華人實擅其利柄。”[3]
近代南洋華商在組織、聯絡海外華僑方面多開先河。受殖民者壓迫和“商戰”思潮的影響,他們意識到商會之利。1906 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立,由此掀起海外商會組建熱潮。此后,中華商會成為嵌入當地社會的重要組織,在溝通與聯絡當地華人、協調華人群體與當地政府的關系、保障當地華人群體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文聚焦于晚清時期南洋地區各中華商會及其在維護、保障華人權益方面的貢獻。所論“南洋”大致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馬來半島和中南半島沿海地區等。將討論時域限于晚清,是因為晚清外交體系先天不足,商會發揮著近乎官方機構的作用,對當地華人的重要性更為突出。
一、晚清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研究簡述
近代中國商會史研究始于海外。[4]1978 年,章開沅在國內首提近代商會研究,馮崇德、徐鼎新等緊隨其后。[5]隨著商會檔案整理出版,國內商會史研究發展迅猛,目前多聚焦于商會的組織、社會屬性、與傳統行會和政府的關系及海外商會等。
海外商會史研究中,南洋中華商會頗受關注。盡管王韜、鄭觀應、黃遵憲等晚清文人和溫雄飛、胡炳熊、邱守愚等民國學者論及南洋華商,但較少討論南洋中華商會。海外學者多關注南洋華僑社團演化。[6]楊進發(Yong Ching Fatt)聚焦1900—1941 年間新加坡華人社會領袖,曾談及新加坡中華商會之成立;[7]戈德利(Michael R. Godley)討論清政府對南洋僑政時論及新加坡中華商會的角 色;[8]顏清煌分析新加坡總商會成為當地華人領導機構的過程;[9]筱崎香織(Shinozaki Kaori)探討1903 年檳城華人商務局成立背景及其過程;[10]菲瑟爾(Sikko Visscher)詳述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百年史;[11]劉宏關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亞洲華商網絡制度化過程中的作用。[12]在國內,除南洋華僑史著作外,[13]莊國土梳理海外中華總商會成立始末;[14]丁進軍整理晚清海外設立商會諸史料;[15]袁丁關注泰國中華總商會與日惹華僑商會之建立;[16]蔡少卿梳理澳大利亞悉尼中華商會史;[17]李秉萱等總結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研究現狀;[18]李慧芬關注1910 年以來泰國中華總商會之演變;[19]鄭成林等討論馬尼拉中華商會領導的西文簿記案抗爭運動;[20]朱英等則簡要回顧南洋中華商會研究。[21]多篇碩士、博士論文亦涉及晚清南洋商會問題。[22]
學界或從社會變遷視角看南洋中華商會,或進行個案研究;時段多涵蓋晚清民國乃至戰后。部分研究雖然聚焦于商會之成立,卻較少關注商會早期運行及其對當地華僑的影響。有鑒于此,本文將著重關注這一問題。
二、晚清南洋地區中華商會的成立及其角色定位
近代中西交流中,海外不少華商被當地殖民者歧視與排斥。受重商思潮影響,各地商人呼吁清政府準許設立商會。1903 年清政府設立商部,始倡商會。
(一)晚清南洋各地商會的組建
1904 年《奏定商會簡明章程》提到,“其南洋各商,以及日本、美國各埠華商較多者,亦即一體酌立總會、分會。”[23]1905 年冬,張振勛、時寶璋考察南洋商務,推動新加坡、檳榔嶼中華商務總會草創。1907 年冬,楊士琦出訪南洋,“海外華僑歡聲雷動,梭羅等埠先后設立商會。”[24]清政府一系列舉措取得明顯成效。
此前,南洋華商已開始探索組建商會的可能性。1897 年《利濟堂學報》曾報道新加坡華商組建商會的意愿。1906 年,新加坡華商率先申請創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此后,商會設立熱潮席卷南洋各大商埠,“海外僑商引領聞風,益臻踴躍。”[25]
清末南洋各地成立大小商會28 個。新加坡為“海南第一巨埠”[26],“南洋商務總匯”,[27]入會商號1206 個;巴達維亞是爪哇島“重要商埠,華商僑處其地戶口計五萬有余,商務夙稱繁盛”[28],近1700 個商號入會;越南“華民僑寓甚多”,“以南圻為出入之總匯”,[29]共2156 個商號入會。位于蘇門答臘島以東、爪哇島以北的萬里洞島“礦產以錫為大宗,雜貨藥材等商業亦盛興”,有1500 個商號入會。[30]中華商會基本遍布南洋各大商埠,以荷屬殖民地尤多;此外,商會面向南洋華商,各地商會成立存在“多米諾”骨牌效應。

表1 晚清時期南洋各地中華商務總會
(二)商會的角色定位
南洋中華商會充當多重角色。商會既是華商聯合組織,又承擔聯絡海外華僑、保障華僑權益的任務,還是海內外溝通的重要渠道。
1.適應近代“商戰”的商業聯合組織
近代,南洋華商既是殖民者的統治工具,[31]又是歐美商人的競爭對手。華商領略到西方商人群體競爭之強勁。《新加坡華商會館規程》提到,“近東西各國無不設有商會,章程周備,通財合力,所以壟斷權利,爭先取捷。”中國向來不重視商會,華商在市場中各自為政,“商務中一切利病既無從請求,而市貨盈虛,價情低漲,亦懵然罔覺。”[32]
“商戰”點燃華商創辦商會的熱情。當時新加坡華商苦于未能抱團實現信息互享,“平日商情渙散,鮮識共謀公益”,因此須建商會以“挽救情形”。[33]小呂宋中華商會在請呈中提到,“非聯合群里共圖公益,無以挽利權而抵漏卮。”[34]合釐華商奏請關防時提到,“華商值識漸開,亦知此商戰劇烈之時”,須辦商會才能生存。[35]北般鳥華商總會提到華商“自謀生理,各分畛域,勢渙業微,力孤情隔”,惟設商會才是“補救之方”。[36]巴達維亞華商總會強調商會宗旨為“整頓商務”“講求商學”“聯絡商界”“和協商情”“啟發商智”與“振興商利”。[37]
2.保障華僑權益的聯絡與維權機構
洋務運動后,晚清僑務由棄僑向護僑重僑轉變。19 世紀70 年代末,清政府任命胡璇澤為新加坡領事后,各處民商“深盼得一領事為維持”[38],以保障華僑權益。
由于國籍問題,領事護僑作用有限。1907 年日惹華商致清政府的書件提到,南洋“近因華官時有過從,大生疑忌,擬更定新律,認華僑為土籍,不許華官過問。”[39]可見領事設立縱有益處,亦難覆蓋全體華僑。同年,清外務部致農工商部的函件中提到,“領事權力又豈能遍庇眾僑”;商會“外人不禁”,“有領事之實而無領事之名”。[40]大臣錢恂亦認為,商會無須像領事任命那樣繁瑣,“若善誘而利導之,其效自鉅。”[41]
商會深知其在維護華僑權益方面的重要性。比如,蘇門答臘把東華商認為商戰劇烈,曾在商會成立前“迭議組織商會聯合團體,上以保國,下以保家”;而島上數萬名華僑分散各處,“情誼隔閡,亟宜設法聯絡,以廣招徠。”[42]日麗華商總會表示,日麗附近15 處商埠僑民“情誼隔閡,洵非設立華商總會,不足以資聯絡。”[43]北般鳥商會提到,當時清政府積極護僑,“于同胞之僑居他國者,尤深保護,設立商會且提倡之。”[44]商會成為晚清護僑的重要補充。
3.海內外溝通與交流的橋梁
商會是海內外互動的重要平臺。商會一方面向南洋各埠華僑傳達清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向國內輸送建設資金,加強海內外聯絡與信息交流。
1906 年,商部奏請設立新加坡中華商會時提到:其一,成立商會有助于開創新局面,“與內地破除隔膜,聲息相通”;其二,商會有助于為“內地農工路況各項要政得易招集華僑資本”。[45]討論小呂宋中華商會關防問題時,農工商部認為,設立商會有助于促進清政府與當地華僑華商的溝通。此前,文件需由當地華商經領事館詳請駐外大臣“轉呈核辦”,如此“往復稽遲,殊形不便”;若直接授予關防,則“簽印一切文件,即可徑呈,使益商民莫此為甚”。[46]
此外,南洋各商會負責人多與政府關系緊密。[47]新加坡中華商會首任總理是閩商廣東候補知府吳世奇;日麗中華商會總理張鴻南是二品頂戴、江西補用道;望加錫中華商會總理湯河清擁有花翎、副將銜;檳榔嶼中華商會總理紳商林克全亦擁有花翎、道銜。1909 年把東中華商會啟用關防的儀式上,“公舉盧君渭濱贊禮,先朝闕謝恩,次拜印”,“一切儀制,如督撫之揭篆然”,[48]啟用關防儀式如同官員受印儀式。部分中華商會總理還在當地殖民政府中擔任職務,譬如日麗中華商會首任總理張榮軒曾任雷珍蘭、瑪腰。①瑪腰(Mayor)、雷珍蘭(Letnan)是荷蘭殖民印尼時設立的華人事務官。由此可見南洋商會中官紳色彩濃厚。
從諸材料看,晚清南洋中華商會實際是半官方機構。一方面,它由南洋各埠華商集聚設立,屬自治商業組織;另一方面,章程及關防須由清政府審議,儼然是政府“下屬機構”[49]。
三、晚清南洋中華商會的實際運作
南洋地區中華商會不僅是商人自治組織,而且具有半官方色彩,在實際運作中,也充分體現了服務當地華商,促進海內外溝通交流等作用。
(一)服務當地華僑華商群體
南洋各商會積極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協調各方關系,積極為改善海外華僑境況而努力。
1.維護當地華商的商業利益,促進華商事業發展
由于族群、國家、制度和文化等種種障礙的存在,[50]南洋華商無時不受到“來自所在國政府和主流社會的排斥與壓力”[51]。商會成為華商應對外部壓力的重要組織。
以新加坡中華商會為例。1907 年初,商會討論新加坡港起貨巡差刁難當地華商的問題。各商號苦于沒有證據,難以起訴,為此約定“將銀幣自記暗號”,并要求商會向英國政府聲明,若之后巡差再行勒索,將進行起訴。同年,英國政府欲禁用北慕娘、沙羅越銅鐳。商會聞訊后立即開會,決議通過傳單布告華商界,要求“六月初一起,凡我市場,交易預先自行禁用,以免臨時忙迫自誤”;此外,商會積極聯絡當局,“懇英政府一律收回,以恤商艱”。英政府拒絕后,蔡子庸等一干人前往慕娘公司“商懇該經理人擔認銀項義務,由本會代為收換”。1911 年初,新加坡當局決定縮減洋煙稅而增加收入息稅,紳商各界反應激烈。商會召開特別大會,決議由商會擬稿、全新加坡紳商聯名蓋印,呈請當局“收回成命”。諸事可見商會維護當地華商權益之盡責態度。[52]
小呂宋中華商會亦積極保障當地華商權益。[53]1908 年秋,當地商人故意壓低苧麻華商出口商品的重量。商會表示抗議,并就此事進行交涉。1909 年,菲律賓要求“凡簿記,須以英、西或土等文字來記賬”。這是菲當局打擊華商、奪取商權的手段。[54]對此,商會牽頭致函菲律賓稅務局,“請準華僑用華文記賬”,開啟“西文簿記案”抗爭運動。
商會為爭取公道而四處交涉。譬如1909 年初,有兩位荷蘭婦女陷害華商賴有仁,誣告其盜竊,最終賴有仁被判三個月苦工。[55]巴達維亞商會積極活動,動員海內外力量向當局施壓。1909 年秋,商會總理吳淑達致電清廷外務部,懇請與荷蘭交涉,一是推翻賴有仁案判決,二是廢除荷商埠醫生強逼裸驗華僑苛例。[56]越南中華商會由于法國虐待華僑苛例亦致函上海商會,希望外務部和粵閩兩省總督共同交涉,保障華僑合法權益。[57]總之,南洋各埠中華商會在保障當地華商華僑權益方面不遺余力。
2.協調海外華僑內部社會關系
海外華僑社會有三類傳統組織:地緣性的會館、血緣性的宗祠和業緣性的公所。[58]這些組織一方面有助于華僑抱團自救,另一方面也造成團體間隔閡。為此,中華商會有助于協調華僑社會各團體關系。
再以新加坡為例。1906 年11 月,新加坡閩潮兩幫工人因爭渡發生口角而互毆。[59]商會議定解決方案,一方面會同警察巡視各街市,勸告雙方“照常復業”,另一方面登報廣布“勸告公啟”,“以息爭端”。然而,閩潮兩幫在11 月15 日、16 日再次沖突,甚至在“山園偏處以及海面一帶”,出現“毆搶”。商會連夜擬定議案,專門雇傭小輪船兩艘“梭巡海面護載客貨”,提請“海關派差攜巡”,[60]并派29 人分往各處勸解。最終,毆搶得以平息。
巴達維亞中華商務總會在總理、協理人選定問題上,明確要求粵人與閩人輪流擔任,“永遠為例,不得再議更改”,[61]以此避免破壞內部平衡。調停內部紛爭時,若粵商與閩商交涉,應當由總理、協理人集結粵閩雙方各半人數,方可評議。商會力圖協調各方華僑勢力均衡。
3.協調海外華僑與當地社會的關系
南洋各商會對外協調華僑與當地社會的關系,保障當地華僑合法權益。
仍以新加坡為例。1906 年,新加坡商議啟動疏浚港道、修筑堤岸工程,“惟是需費浩繁”,政府打算向“附近港一帶并離港三百英尺之屋業增收抽費”,以作貸款還息之用。商會召開會議,收集各方意見以向當局反映。1911 年,商會派陳若錦前往倫敦參與慶賀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典禮,并通告全埠華僑“懸旗張燈結彩同伸慶祝”。英政府專門以國王名義致函感謝商會。商會成為協調當地華僑與當局關系的重要渠道。[62]
暹羅中華商會在協調當地華僑華商與政府關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1910 年春,暹羅當局為增加稅源,將華僑人頭稅三年一征的舊例改為一年一收,“華僑無力遵繳”,引起不滿。6 月,曼谷華商罷市3 日。暹羅隨即“濫用警權”,“數日內濫捉無辜華僑七八百名,并沿途毆打所捉之人。”[63]暹羅中華商會趕緊聯合其他組織,與暹羅政府部門斡旋。[64]在多方努力下,事件最終得以平息。
小呂宋中華商務總會亦積極保障在菲華僑權益。[65]1907 年秋,菲律賓決議推行征米入口重稅,限制華僑入菲,商會表示抗議;年底,菲海關以感染目沙癥為由,禁止3000 多名華僑入關。商會據理抗爭,最終事情得以解決。商會積極與菲當局聯系,協商事關雙方之事。1909 年,菲律賓與商會討論取締擾亂華僑社會的某秘密華僑社團的問題。1911 年春,沓亞爾火山(Taal Volcano)爆發,“罹禍者頗多”。美駐菲陸軍檢殯及驗尸辦公處致商會公函,聲稱火山爆發中無華僑遇難。商會成為菲當局與華僑社會交涉的重要平臺。
4.重視慈善、福利事業
南洋各商會積極參與當地華僑社會的慈善、福利事業建設工作,改善當地華僑的生存環境。建設醫院和養老院、興辦學堂是常見形式。
以三寶壟中華商會為例。1908 年,由于中華會館事關華僑教育問題,在會館深陷經濟困難之際,商會承辦該會館并加以接濟,以支持會館工作的正常運轉。同年,當地政府擬解散三寶壟、雙溥的華僑養老院和貧民院。商會聞訊后召開特別會議,決議派柯遠芳與當地官員交涉養老院續辦一事。多次協商未果后,1910 年,商會自行籌資在雙溥創辦“慈善堂”,以救濟老無所依的僑胞。
梭羅中華商會重視商學教育。時任商會總理張先興提議商埠“平均糖價”,“每擔抽二角五分,以充商學經費。”[66]為此,他會同建原和棧、建昌棧、謙裕棧、錦茂棧和源裕昌等商議,并懇請日惹商會學堂幫忙游說當地糖商不要趁機破壞梭羅糖市,得到日惹糖商界支持。此事一方面可見商會熱心商學教育,另一方面可見南洋各商會間的交流。
小呂宋中華商會同樣積極參與慈善事業。1911 年,當地總領事建議商會與華僑教育會合作,保障教育經費。商會還討論教育會董事會選舉辦法,以更好開展工作。同年春天,沓亞爾火山爆發,商會積極關注火山爆發后的傷亡情況,并向難民捐獻6600 元。馬尼拉中路發生火災,商會亦向難民捐資100 元。南洋各商會力所能及地為當地華僑華商謀福利。[67]
(二)促進海內外信息與資源的交流
南洋各商會為南洋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創造條件,一方面響應清政府實業興國口號;另一方面密切關注國內動向,進行慈善賑災。
1.支持跨地域交流與實業合作
商會成為各地華僑交流的平臺。譬如,1908 年,檳榔嶼中華商會致函新加坡商會,希望就英政府“擬設三州府檢驗尸骸”一事同向當局“懇請注銷”。新加坡商會聞訊后爭取新加坡各華商支持。1910 年初冬,有新加坡商會會員提議在廈門設立華僑公會以保護回國華商,商會積極回應并致函南洋各商會,共商該事。1911 年春,受南洋多數商會委托,新加坡商會起草章程,由林文慶代呈農工商部和民政部,請求備案并頒發關防。新加坡商會還積極推進保障華商回國的工作。1906 年夏,商會擬頒發回華護照,制定章程并呈交清政府;1909 年夏,商會決議協同英方和同濟醫院共同“資遣殘廢貧弱回國”[68]。三寶壟中華商會支持華僑返回中國學習。1911 年,商會出資2000 元以補貼暨南學堂學生往返費用。
南洋各中華商會積極支持清政府發展工商業。1909 年,中國華商銀行發布集股通告,“中外云集響應,規模宏敞”。[69]新加坡中華商會積極聯絡南洋各埠。最終,新加坡中華商會認購100 萬;巴達維亞中華商會認購50 萬;渤良安中華商會認購25 萬;日惹中華商會認購25 萬;泗水中華商會認購100 萬;三寶壟中華商會認購50 萬;望加錫中華商會認購30 萬;坤甸中華商會認購20 萬;小呂宋中華商會認購40 萬。[70]以上認購占當時海內外總認購額的50.6%,占目標額的44%。不過,“適逢正元等莊紛紛倒閉,滬市萬分恐慌,以致投股未能足額”,[71]中國華商銀行未能成形。
1908 年,兩江總督端方上奏建議在南京創辦南洋勸業會,“以開風氣而勸農工”[72]。南洋勸業會公告發布后,新加坡中華商會支持會友經銷的土產貨物送往展會,或者由商會購買以便參展。南洋華商對此次勸業會亦極為關注。“各島工商擬來寧觀者有二百余人之多”,希望籍此“考查內地失業之狀況”,“聯絡外洋與內地之情誼”,其中包括泗水蔡奇鳳、蔡天良、蔡天和,渤良安游作舟,新加坡吳顯祿、陳觀伯等。南洋華商梁炳農“出萬金購勸業會元號入場券”,以支持勸業會開展。[73]經商會牽線搭橋,南洋華商與祖國家鄉聯系更加頻繁。
2.實現海內外同胞互幫互助
當內地或其他商埠遭遇自然災害時,南洋各商會群策群力,發揚海內外同胞互助精神。
1906 年冬,淮河“洪水為災”,“小民失所四百余萬”。新加坡中華商會聞訊后召開會議,林文慶動員各紳商捐款,要求每位會員至少捐10 元,各會員再動員身邊華僑捐款,“冀能集成巨款,以濟災區”。1908 年秋,廈門總商會向新加坡中華商會求賑閩南水災。新加坡商會聯合同濟醫院及閩粵兩幫“協力勸捐”,并向南洋其他商埠求助。鑒于內地“災難頻仍”,商會提議聯合閩粵各紳商設立“救災社會”組織,以資賑濟。[74]
其他南洋各商會亦積極參與其中。1908 年夏,廣東、江西等地發生水災,商會捐助廣東4713 元、江西6700 元,支持兩地災后工作。1909 年初,泉州再次發生水災,商會組建募捐委員會,陳三多任主任,負責向商埠各華僑募捐,前后勸募6620 元,交予廈門商會代賑。當地閩商還積極組織南洋閩僑救鄉會,聯絡南洋各埠閩籍華商,支持當地民眾維護治安秩序。三寶壟中華商會亦積極賑災。1907年,長江以北發生水災,鄭永昌集合董事會開募捐會,籌款12000 元,經匯豐銀行交由清廷農工商部代賑。1908 年夏,廣東水災;秋天,漳州水災。了解災情后,董事會動員華僑捐款,前期6000 元交由匯豐銀行代賑到廣東,后期4000 元交由匯豐銀行轉賑漳州。商會成為海外華僑與內地家鄉情感連通的重要平臺。南洋華商通過商會得以發揮規模力量支持祖國家鄉建設,滿足他們衣錦還鄉、建設家鄉的情感需求。
四、結語
盡管冠以“商會”名義,南洋各中華商會的作用與影響卻不局限于商業。商會不僅是商業聯合組織,更是維護海外華僑權益、增進海內外同胞交流的重要組織。南洋各商會之重要反襯出當時清政府之衰落。由于清政府在海外的護僑保僑作用有限,商會需承擔多元角色。商會“為僑社服務之成績如何,已盡量呈現于事實上,早為國人所共見”[75]。當時商會周年慶題詞時社會各方紛紛表達對南洋中華商會的認可,“商戰南針”“僑界南針”“僑胞喉舌”,“扶助祖國,造福僑 胞”[76]等評價就是顯證。正因各商會在初期發揮巨大作用,商會在海外華僑社會中的地位一致延續至今。
改革開放后,隨著新一批移民走向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商會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各地領事館的領事保護作用愈發明顯,各地商會無須再承擔多重責任。但是,海外華人商會仍是連通海內外的重要平臺,在商業合作、團結互助、文化交流和信息互通等方面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
[注釋]
[1][美]孔飛力著,李明歡譯:《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
[2] Adam, McKeown, “Global Migration, 1846-1940”,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04, 15(2).
[3] 王彥威、王亮輯編:《清季外交史料之光緒朝》卷210,民國20 年刊本,第14 頁。
[4] 如曾田三郎:《商會の成立》,《歷史學研究》1975 年第422 號; Coble, Parks M.,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Wellington K. K. Chan.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5] 馮崇德、曾凡桂:《辛亥革命時期的漢口商會》,湖北省歷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論文集》,武漢:武漢人民出版社,1981 年;徐鼎新:《舊中國商會溯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
[6] 如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南洋學會,1975 年;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 年;等等。
[7] Young Ching Fat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1900-1941”,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968, 9(2).
[8] Michael R. Godley, “The Late Ch’ing Courtship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5, 34(2).
[9] Yen Ching-hwang, “Ch’i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06-1911”, in Leo Suryadinata ed.,Southeast Asia Chinese and China: 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10] Shinozaki Kaori,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n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903: Protecting Chinese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Two States”,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6, 79(1).
[11] Sikko Visscher,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and Enthicity: A Histo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7.
[12] 劉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亞洲華商網絡的制度化》,《歷史研究》2000 年第1 期。
[13] 比如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黃滋生、何思兵:《菲律賓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年;黃昆福:《馬華商會史》,吉隆坡馬華商聯會,1974 年;等等。
[14] 莊國土:《論清末海外中華總商會的設立》,《南洋問題研究》1989 年第3 期。
[15] 丁進軍:《清末海外華商設立商會史料》,《歷史檔案》1995 年第1 期;丁進軍:《清末海外華商設立商會史料續編》,《歷史檔案》1997 年第2 期。
[16] 袁丁:《清政府與泰國中華總商會》,《東南亞》2000 年第2 期;袁丁:《清末印度尼西亞日惹華僑商會的建立》,郝時選主編:《海外華人研究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7]蔡少卿:《澳洲鳥修威雪梨中華商會研究(1902—1943)》,《江蘇社會科學》2005 年第4 期。
[18]李秉萱、孟慶梓:《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研究現狀述評》,《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3 期。[19]李慧芬:《試析泰國中華總商會的演變》,《八桂僑刊》2014 年第3 期。
[20] 鄭成林、賈俊英:《20 世紀早期菲律賓馬尼拉中華商會與西文簿記案》,《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4 期。
[21] 朱英、鄭成林、魏文享:《南洋中華商會研究:回顧與思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3 期。
[22] 禹如鍵:《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研究(1904—1954)》,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 年;石滄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史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潘少紅:《泰國華人社團史研究》,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年;賈俊英:《印度尼西亞中華商會研究(1907—1942)》,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 年;楊宇丹:《20 世紀初至60 年代新加坡、泰國中華總商會活動研究》,貴州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等等。
[23] 《奏定商會簡明章程二十六條》,《東方雜志》1904 年第1 期。
[24] 丁進軍:《清末海外華商設立商會史料》,《歷史檔案》1995 年第1 期。
[25] 《本部奏南洋檳榔嶼擬設中華商務總會折》,《商務官報》1907 年第1 期。
[26] 王彥威、王亮輯編:《清季外交史料之光緒朝》卷210,民國20 年刊本,第13 頁。
[27] 《商部奏新加坡創設中華商務總會請予立案折》,《東方雜志》1906 年第8 期。
[28] 《農工商部奏頒給巴達維亞中華商務總會關防折》,《北洋官報》1907 年第1430 期。
[29] 《本部具奏越南南圻商會援案請給關防折》,《商務官報》1909 年第24 期。
[30] 以上數據均出自農商部總務廳統計科:《中華民國元年第一次農商統計表》,中華書局,1914 年,第198~199 頁。
[31] 《王賡武:天下大勢,進退之間》,《瞭望東方周刊》2014 年第44 期。
[32] 《新加坡華商會館規程》,《利濟堂學報》1897 年第15 期。
[33] 《商部奏新加坡創設中華商務總會請予立案折》,《東方雜志》1906 年第8 期。[34] 《農工商部奏小呂宋中華商會援案請給關防折》,《政治官報》1907 年第63 期。
[35] 《農工商部南洋合釐埠華僑設立商務總會請準立案頒給關防折》,《政治官報》1907 年第97 期。
[36] 《農工商部奏南洋北般鳥設立商會援案請給關防折》,《政治官報》1909 年第566 期。
[37] 《巴達維亞華商總會試辦章程》,《商務官報》1907 年第11 期。
[38] 王彥威、王亮輯編:《清季外交史料之光緒朝》卷11,民國20 年刊本,第14 頁。
[39] 《南洋日惹華僑上農工商部稟》,《南陽官報》1907 年第88 期。
[40] 《日惹埠華商請設商會鈔呈會章并致農工商部函稿由》(光緒33 年4 月29 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02-13-003-01-027。
[41] 王彥威、王亮輯編:《清季外交史料之光緒朝》卷204,民國20 年刊本,第23~24 頁。
[42] 《南洋蘇門答臘把東商會照準頒給關防》,《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4 期。
[43] 《農工商部奏南洋蘇門答臘日麗埠設立中華商務總會請給關防折》,《政治官報》1909 年第734 期。
[44] 《南洋北班鳥商會請領關防問題》,《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4 期。
[45] 《商部奏新加坡創設中華商務總會請予立案折》,《東方雜志》1906 年第8 期。
[46] 《農工商部奏小呂宋中華商會援案請給關防折》,《政治官報》1907 年第63 期。
[47] Yen Ching-Hwang, “Ch’ing’s 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77-1912)”,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0, 1(2).
[48] 《爪哇把東華商總會啟用關防之盛舉》,《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13 期。
[49] 白吉爾:《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國資產階級》,《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4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
[50] 龍登高:《跨越市場的障礙:海外華商在國家、制度與文化之間》,科學出版社,2007 年。
[51] 龍登高:《海外華商非透明化經營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7 年第4 期。
[52] 《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七十五周年紀念(1906—1981)》,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81 年。
[53] 《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三十周年紀念刊(1904—1933)》,收錄于《民國時期福建華僑史料匯編》(第1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
[54] 彭洪濤:《菲律賓華僑西文簿記案》,《時事月刊》1921 年第6 期。
[55] 《巴達維亞華商總會為賴有仁案致本館函》,《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14 期。
[56] 《蘇門答剌華商會總理吳淑達等爲保守寸土雪奇冤除苛例三案事致外務部稟文》,收錄于《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澳門基金會出版,1999 年。
[57] 《越南華商會館致函上海商會之事實》,《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19 期。
[58] 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制》,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 年。
[59] 《商會勸告》,《叻報》第7429 號,1909 年11 月14 日。
[60] 《毆搶再續》,《叻報》第7431 號,1909 年11 月16 日。
[61] 《巴達維亞華商總會試辦章程》,《商務官報》1907 年第11 期。
[62] 《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七十五周年紀念(1906—1981)》,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81 年。
[63] 《電爭暹羅苛抽華僑身稅》,《廣益叢報》1910 年第239 期;《暹羅華僑之血淚書》,《時報》1910 年6 月21 日。
[64] 段立生:《泰國中華總商會簡史》,載于《中國與東南亞交流論集》,泰國大通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65] 《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三十周年紀念刊(1904—1933)》,收錄于《民國時期福建華僑史料匯編》(第1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
[66] 《巴達維亞華商總會為賴有仁案致本館函》,《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14 期。
[67] 《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三十周年紀念刊(1904—1933)》,收錄于《民國時期福建華僑史料匯編》(第1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
[68] 《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七十五周年紀念(1906—1981)》,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81 年。
[69] 《日惹中華商務總會為中國華商銀行事覆上海商務總會函》,《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3 期。
[70] 《中國華商銀行發起簽名冊》,《華商聯合報》1909 年第6 期。
[71] 《華商銀行解散之原因》,《福建商業公報》1911 年第17 期。
[72] 《江督端方奏擬南洋第一次勸業會官商合資試辦折》,《北洋官報》1908 年第1939 期。
[73] 《關于南洋勸業會事匯志》,《南洋群島商業研究會雜志》1910 年第2 期。
[74] 《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七十五周年紀念(1906—1981)》,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81 年。
[75] 《暹羅中華總商會紀念刊》,香港:商務印書館,1930 年。
[76] 《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三十周年紀念刊(1904—1933)》,《民國時期福建華僑史料匯編》(第14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