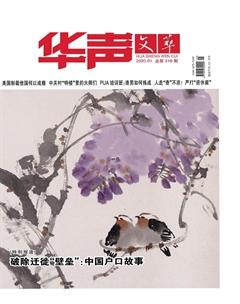施昕更:“良渚遺址”發現第一人
在發現良渚古城的背后,有一位青年不得不提,他就是“良渚遺址”發現第一人施昕更。而這個注定載入史冊的青年,并非考古科班出身,其一生短暫而傳奇。
非科班出身干起考古
施昕更原名施興根,1911年出生,浙江余杭縣良渚鎮人。雖然家境貧寒,但施昕更從小品學兼優,1926年中學畢業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他兼修國畫和西洋畫時,得到了敦煌藝術專家常書鴻的指導。
1929年,杭州舉辦了第一屆西湖博覽會,施昕更的繪畫功底派上了用場,當上了西湖博覽會藝術館管理員。因在博覽會上工作出色,1930年春夏之交,施昕更進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地質礦產組,從事地質礦產工作。除了繪圖,他在西湖邊、靈隱飛來峰、寶石山進行野外巖石標本采集,走上了考古之路。
如何發現“良渚遺址”
觸發機緣的原始事件,是當時博物館正對杭州一個叫古蕩的遺址進行發掘。1936年5月,古蕩發現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的消息傳出,施昕更立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心思細膩、反應機敏的他發現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老家良渚鎮一帶見過,感覺冥冥之中有一種聯系在牽引著他:古蕩考古發掘和杭縣北鄉的良渚鎮,歷史上會不會有什么聯系呢?
施昕更馬上回到故鄉良渚,終日在田野阡陌之間奔走。1936年11月3日,施昕更第三次摸底,有了突破,他于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干涸池底,發現了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帶回了杭州。得到館里的同意和支持后,本是從事地質礦產研究的他,立即轉手做起了良渚田野的考古發掘。
根據記載,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施昕更參考了各種考古材料,尤其受山東城子崖發掘報告啟示,悟及這些黑陶與城子崖黑陶文化為“同一文化系統的產物”,都是具有5000年歷史的文化遺址。
當時,不少考古遺址都以發現地命名,于是施昕更效仿此法,將此地命名為“良渚遺址”。
報告引起國內外矚目
1937年4月,施昕更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杭縣第二區遠古文化遺址試掘簡錄》,該文是最早刊登的、敘述最完整的有關良渚文化的專論,從此良渚文化開始撩開它神秘的面紗。
1937年春天,施昕更寫出了5萬余字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簡稱《良渚》)一書,制圖100余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獲,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施昕更憑借這部報告,以及在良渚文化考古方面的開創性工作,奠定了“良渚遺址的發現者”和“良渚文化的發現人”的學術地位。
就在《良渚》交稿以后,抗日戰爭爆發,書籍的印刷被迫中止。施昕更攜帶著這些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蘭溪、永康、松陽等地,在浙江省博物館館長董聿茂的呼吁和堅持下,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良渚》一書。
經過多次努力,1938年,此書正式問世,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矚目。后來因抗日戰爭的爆發,施昕更暫停了對古文化的發掘,加入到抗日救國中。
1939年5月,時任杭縣抗日自衛隊秘書的施昕更感染猩紅熱,因無力醫治,病逝于瑞安醫院,年僅28歲。
(摘自《茂名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