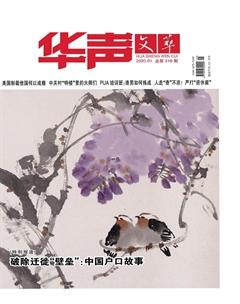求學哈佛讓我學會表達與呈現
王忞青
在哈佛讀研的那段日子是我思考力最蓬勃的時候,每天無數的問題在頭腦中如指數般生長。我像海綿一般汲取著無窮無盡的養分,日復一日地讀書、聽課、思考、寫作。
如果說《風雨哈佛路》這部電影在我幼小的心靈種下了一顆力量的種子,那么10年后,這顆種子終于在最適合的土壤里生根發芽。我常把哈佛比喻成一段勇者之旅的開始,因為我在這里經歷了對自己的覺知、對多元的探索、對挑戰的承接。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課是用“項目式學習”方式進行認知科學的研究。我的導師是哈佛教育學院著名的認知科學家,專門研究人類如何將因果關系認知運用到復雜問題的解決上。我清晰地記得,我在她的課上完成了60多頁紙的理論分析、教學項目設計與評估。那時,我是她課上唯一一名中國學生,難免會在文化語境方面存在心理弱勢,但我卻在那門課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滋養。
最開始,由于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背景知識,我選擇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好幾次試圖舉手發言都被前排的美國同學搶先了。幾節課下來,越發覺得物理距離直接影響了我的心理感受。于是我迅速調整策略,移到第一排正中間、與教授僅有1米之隔的空位。
這需要很大的勇氣,進入距離老師最近的視線,意味著整堂課(3小時)都得高度專注,隨時與教授有眼神和言語上的交互。但這也促使我做更充分的課前準備,從習慣于“精心組織語言后發言”到“一邊思考一邊表達”。一整學期的課程只圍繞一個項目,從選題、搭建框架、內容設計到不斷根據反饋來完善這個過程,對于那時的我來說是新奇的,甚至有些不可思議。
兩年后,導師高興地聯絡我說,她拿到了可以將我的課程設計落地中國的科研基金。自那以后,這個項目便從我個人的學習成果升級為有社會效應的工具包。
反觀這門課的體驗,我意識到在美國的文化語境下,主動去表達和呈現自己、得到關注、獲取資源,是非常必要的生存能力。
(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