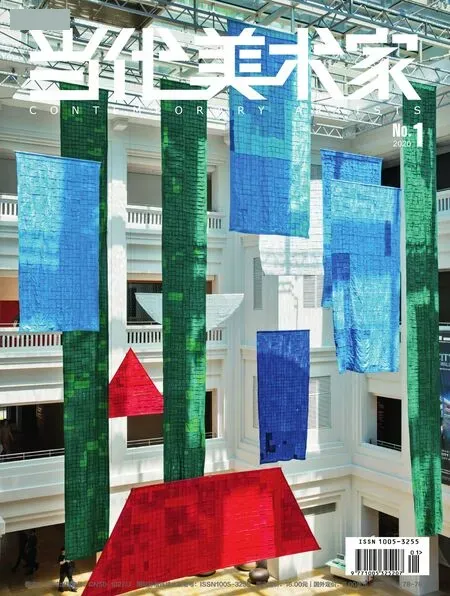擁抱時代的學院藝術
——吳洪亮訪談
吳洪亮 Wu Hongliang

1劉洪濤圣域紙本丙烯323cm×153cm20192019年羅中立獎學金獲獎作品
《當代美術家》(以下簡稱“當”):您作為2019年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策展人,以更宏大的國際視野來看,今天中國青年藝術的優勢和劣勢分別在哪里?
吳洪亮(以下簡稱“吳”):其實我覺得今天優勢和劣勢都談不上了。今天已經非常全球化了,尤其是“90后”這一批藝術家,他們在藝術的舞臺上已經初見端倪。當然作為年輕藝術家他們的作品,還有一些不夠成熟,可能還有一些資金和時間方面的限制,完成度有一些弱,但想法基本都呈現出來了。我覺得他們的一些想法,以及作品最終呈現的狀態,都是有很多亮點的。
以我接觸到的年輕的國內外藝術家來說,我越來越覺得他們之間沒有太大區別了。以前東方、中國和其他地方有太多不同,我覺得今天大家基本上處在一個平行的平臺上進行交流,一件作品被掛到網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網絡的發展抹平了地域間的差異。中國藝術家也好,其他國家的藝術家也好,大家處在一個快速增長的國家體系中,不少人吃到了國家發展的紅利,這是我們的優勢。當然很多年輕人還是覺得沒有錢,連創作的資金都沒有。當一個賺錢的藝術家,還是理想的、更具實驗性的藝術家,這是個人選擇。越國際化,選擇也可以越個人化,藝術家可以自己選擇更實驗性,還是偏商業性的發展方向,這兩種選擇不是全部割裂的,也有并行的部分。作為今天的中國年輕藝術家是幸福的,年輕人應該有效利用現在的形勢。現在中國給藝術提供了更多的空間、資金的支持,包括各種青年項目,藝術家們應該把各種平臺充分利用起來。
當:前幾年的青年藝術作品,主題普遍與個人經驗和內心情緒有關,有人認為缺乏對歷史和社會現實的關注,是青年藝術的一個短板。而近期的青年藝術作品中,出現了更多關注于歷史和社會現實的作品,這是否體現了青年藝術的成長與新的發展方向?
吳:我很希望青年藝術有這個方向,至少現在可以看到了。關于這個問題我曾經寫過一點文字,把它稱之為“小我”和“大我”的關系。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置疑,我們是不是生活在一個小時代,在這個小時代里安逸地過下去了。現在我覺得不是了。完成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策展工作后,我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趣的時代,“有趣”是指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現在全球面臨一個新的糾結——全球化受阻,各種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的出現都在提示我們,在未來的10年、20年可能無法再繼續停留在“小我”的世界了。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生活的時代,但可以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新一代的年輕藝術家,如果有這樣的愿望去擁抱大時代,用自己的眼睛和藝術的能量做出反應,甚至改變它,當然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畫過《礦工圖》的周思聰和只畫小孩、荷花的周思聰是不一樣的;畫過《格爾尼卡》的畢加索和沒有畫過《格爾尼卡》的畢加索是不一樣的。作為藝術家,在某種程度上有必要關注一些大問題,把自己置身于一個大時代體系中思考。當然這不是對每位藝術家的要求,但是如果藝術家有表達的沖動和愿望,可能對藝術來說會顯得更重要一些。
當:近幾年青年藝術家們創作的跨媒介作品和裝置作品有了更多的科技元素,您覺得這和現在國內學院教育的改革有沒有關系?
吳:肯定有關系。藝術的表達方式、傳播方法今天已經如此豐富了,我相信大多數的年輕人喜歡用更不一樣的呈現方式。這幾年我參加過很多青年藝術的評選活動,評委們開玩笑說最吃虧的就是那些架上繪畫的作品了,能入圍前五、前十非常不容易。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就是動的東西一定比靜止的更吸引人,至少能瞬間抓住眼球。這幾年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老了,我有時候可能會面對一幅20世紀的油畫或者國畫看很久,畫面后的底層力量在眼睛和思維中泛起,這股力量在提示我們,藝術除了沖擊力和吸引眼球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希望通過藝術家的創作和展覽能把這份感受傳遞給觀眾,這才可能會有一個更長遠的美術史,或者在歷史中體現這件藝術作品的價值。很多作品簡單地運用高科技,顯得好像很高端、前沿,這種作品是特別容易被消費的。如果作品只有技術,沒有精神性的核心支撐,打開它科技的外殼里面只有空氣,那么所有的“高科技”都會變成“低科技”,只看藝術作品中的科技就很可笑了,這完全沒有意義。如果哪件作品強調擁有某種技術,而不是藝術作品系統中的存在價值,它必然會被淘汰。今天年輕藝術家選擇什么樣的方式處理自己的作品,我覺得既重要也沒有那么重要,是不是有效、完整、極致地把思想內核呈現了出來,這才是重要的。
當:青年藝術家們面臨的創作選擇更加豐富——發達的資訊使他們更早地接觸到了不同的創作方式與作品媒介,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架上繪畫和雕塑的作品更加顯現了青年藝術家對藝術語言與本體的堅持與探索。他們的探索有沒有打動您的地方?
吳: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把繪畫和新技術對立起來。一幅傳統的水墨畫會打動你,可能畫面中只有幾塊石頭一片葉子,就這么幾筆,筆墨的魅力足夠讓你興奮,所以有人愿意在這條路上堅持探尋。尤其在中國繪畫系統中,這可能是最核心的部分,而“創新”有另一層含義。中國畫一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圖式上的創新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這一筆,是否能把能量留在紙上,還可以讓別人看明白。所以中國畫系統中的創新和西畫系統的創新,是各行其道的。
當:青年藝術家是當代藝術的重要組成群體與后備力量,獎學金制度與青年藝術評獎是推動、激勵青年藝術創作的有效助力。您覺得除了經濟方面的獎勵,此類活動還可以從哪些方面給予青年藝術家們有效的支持?
吳:我覺得更大的層面是精神上的。從事藝術行業的人,經濟上的窮是最常面對的問題,但直接的經濟支持能救一時,能救一世嗎?獲獎的那份榮譽可能給他一份信心,這是更重要的。作為前輩也好,獎項也好,選擇什么樣的藝術、什么樣藝術家是核心的概念和標準,在這樣的評審系統、資助系統中找到年輕藝術家的具有未來感的可能性。平臺搭得越高,給藝術家的信心就越大。也許因為獲得了一個獎項,本來想回家做個公司的小職員,突然發現我也許真的能當藝術家,在未來就真的實現了自己的藝術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