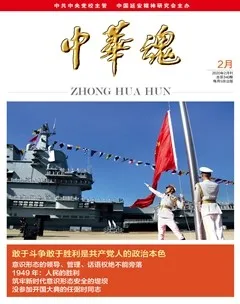難以忘卻的“上河工”
郭開國
老詞漸淡,新語不斷。
提起當年曾讓農村人既懼怕又無奈的“上河工”這詞,現在似乎早已被人們遺忘,甚至許多年輕人恐怕根本不知道這詞的意思。然而,這詞對于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且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工作在農村多年,后又加入水利行業的我來說,早已刻入腦海和融入到血液之中,這輩子肯定忘不了了。
獨往不群,滄海桑田。我的家鄉射陽縣是一個充滿傳奇的地方,元朝之前這里尚是一片波涌浪起的海域,后因黃河奪淮,泥沙裹夾,日積月累,由海而灘,灘久成陸,明初開始有人進入煎鹽、捕魚為生。歷史上,境內雖有經過上游多年傾泄沖刷而成的自然港道射陽河、新洋港,可由于沒有配套的水系及圩堤閘站管控,加之東有海潮襲擾,西有洪水為患,東潮西水交替危害。有史可查,僅明代中葉至清朝末年400年間,遭受“淹死居民無數”的滅頂潮災就達14次之多。先人們為能生存只得筑墩避潮,開浚河道,“引鹵就煎,運鹽入垣”。清末民初,民族實業家張謇、朱慶瀾、馮國璋、束勖嚴、邵志中及棄武從農的抗日民族英雄馬玉仁等人的進入,開河筑堤,建橋造閘,廢灶興墾,開始有了農業。然而,他們各自為政,缺乏統一規劃,水系混亂,溝河淺窄,抗災能力甚微。1931年水災,平地水深數尺,縣境盡成澤國。1939年潮災,沿海大喇叭一帶淹死居民愈萬人,毀壞條田20多萬畝。1942年4月射陽縣誕生時,全縣可耕農田尚不到50萬畝,且靠的是“望天收”“碰運氣”,人們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在毛澤東主席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后,在上級黨政組織重視及射陽縣委、政府努力之下,全縣一盤棋,統籌規劃設計,分塊施工實施,持續不懈在全縣掀起開河治水、興修水利的高潮。當時,國家貧窮,技術落后,一切都靠人海戰術,開河治水、興修水利也不例外。每到冬春農閑季節便是男女老少齊上陣,關門閉戶到工地,人工開挖,肩挑車推,至此便有了“上河工”這詞。
但凡參與或經歷過的人誰不知道,“上河工”這三字看似簡單輕巧,可它不僅浸滿了幾輩人的付出與汗水,而且也記載著許多人的奉獻與犧牲。走近黃海之濱,面對雄偉壯觀、環境優美,素有“蘇北第一閘”之稱的射陽河大閘,又有誰相信在那建國之初百廢待興之時,為防海水倒灌,保障蘇北里下河地區農業生產,是國家千方百計擠出財力重點投資興建的。在工程建設指揮部及原蘇聯專家組織指導下,所在地射陽出動數以萬計的青壯年,填河開塘、裁灣改道、抬石澆筑。工程總投資1596.2萬元,由淮河水利委員會勘測設計院設計,1955年9月21日開工,1956年5月21日竣工放水,僅用8個月時間就將這座擁有35孔,總寬達410.1米的大閘建成。如今這座閘不但使命依然,承擔著流域4036平方公里排澇、擋潮重任,而且以大閘為中心所轄地域還建成了全國知名的水利風景區。
說到風景區,熟知射陽到過射陽的人,又有誰不夸贊境內黃沙港兩岸大堆上那蜿蜒綿長、碧水映襯、高拔俊秀、枝繁葉茂、蔥郁青翠的水杉森林漂亮,甚至不惜力氣爬上大堆,徜徉其間,張開雙臂,盡情吸吮著林中新鮮的空氣。然而,眼前這條縣境流程41.6公里,河底高程負3.5米、寬90米的大港,竟然是射陽縣1971年冬至1973年春,先后兩次分別組織數萬民工,在原馬玉仁開挖的小溝基礎上擴浚開挖出來的。請大家注意哦!那時可沒有什么泥漿泵、推土機、挖掘機等水利工程施工機械設備,有的只是那響應號召、聽從指揮、戰天斗地的各級黨政干部和急切期盼不再遭受洪澇災害威脅的百姓群眾,靠的是他們一鍬鍬挖、一車車推、一擔擔挑出來的。
家住河畔不遠,年少好奇的我就曾目睹過施工現場,如今想來仍覺震撼不已。記得我是幾下決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爬上似山積土大堆上的。遠眺對岸能隱約看到擔土的人在艱難地攀爬,轉眼往下瞧頓感目眩,溝底太深了,下面挖土忙碌的人看去好似小不點。后來聽大人們說,從溝底到堆頂這上下距離有近500米,溝深堆高坡陡,一般人空手上來都很吃力,想像不出當年肚難吃飽、營養不足的民工們得靠多大毅力,堅持挑著一擔擔重達40公斤左右的濕泥爬上堆頂的。黃沙港的拓浚貫通,讓里下河地區排水流程縮短110公里,日平均流量達200多立方米每秒,排澇受益耕地面積有近200萬畝。
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著射陽縣不僅要解決上游雨澇下泄入海港道問題,而且還得修筑河堤與海堤防止澇水、海潮侵襲。事實上,縣境內堤防修筑河堤始于清代、海堤始于清末民初。經過1931年洪水、1939年潮災,大部分堤防被毀或殘缺不全。新中國誕生為修筑高標準堤防,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帶來了春天。特別是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全縣持續組織大規模的堤防修筑及其配套工程建設,到了80年代末已擁有海堤193.34公里、河堤509公里、圩堤2154.8公里。
在解決上游安全行洪和提升抗御海潮、澇水能力的同時,有著2783平方公里面積的射陽縣,又把建立完善河網配套水系,促進和保障農業豐產豐收擺上突出位置,堅持不懈組織工程實施,先后開挖出23條骨干河道、183條大溝、2446條中溝,建立起射陽河以北、運棉河兩岸、利民河兩岸、新民河兩岸、海河與串通河兩岸等5個引排獨立的區域,初步建成防洪、防澇、防旱、防漬水利工程體系。
回眸射陽縣的水利工程體系形成,怎不讓人感嘆國家的日益強大及歷任縣委、縣政府領導的科學決策和精心組織,在荒蕪的黃海灘涂堿地上創造了治水奇跡。然而,最值得贊佩和歷史銘記的應該是這里前赴后繼、全民上陣的射陽人,尤其是農村人。是他們在那吃不飽飯、穿不暖衣的年代里,憑著對建設新中國充滿憧憬、對上級黨政組織充滿信任、對未來美好生活充滿期待的不屈精神與動力,勒緊褲帶,不計得失,頑強拼命,不惜一切的“上河工”。
多年習慣成自然。每到冬春農閑時節,各家各戶早就準備好鐵鍬、推車、泥兜等工具,聽候調遣,隨時出發。身強力壯者不顧寒風凜冽、冰天雪地,離家住棚,走上新洋港裁灣、黃沙港開挖、海堤堆修筑等縣級“大河工”一線;正常勞力者則必須參加大溝拓浚、中溝開挖、堤防修筑等先“公社”后“鄉辦”級“中河工”會戰;即使婦女、年老者、放假中學生們,也要盡己之力、聽從安排,就近參與溝河拓浚、條排河開挖、渠堤修筑等先“大隊”后“村”級“小河工”勞動。“上河工”勞動靠的是體力和耐力,就說看似容易的挖大鍬,其實是幾人一齊挖,一個挨一個,那鍬頭大小偷不得半點刁懶,否則鍬鏵就跟不上趟子。工地上要說稍感輕巧一點的活計恐怕得是在岸上平垡頭這活,可那活通常是留給工程員、領隊干部或身體不適民工干的,一般人輪不到哦!
全民興修水利精神無疑十分可貴,可人們的年齡、體質、耐力畢竟不盡相同,讓大家一樣高強度、超負荷地參加水利勞動,有人因此受傷生病,甚至還有人一去無返將生命結束在工地上。這無形中使得許多人“聽水生畏”,害怕起“上河工”來。好在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及現代水利施工機械的興起,各級政府財政投資持續加大,河道拓浚、堤防修筑、積土運送等逐步實現了機械化,其施工效率是人工不能與之相比的。過去那聲勢浩大、全民發動,一年全縣實施水利工程土方也就在600-700萬立方米左右,而現在不聲不響、隨隨便便就能完成土方量上千萬立方米。如此,既不用出工又不用花錢,已至于“上河工”這詞漸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
念茲在茲,此心不越。誕生在黃海灘涂之上,之前靠吃著國家返銷糧過日子的射陽縣,就是憑著不斷科學治水和配套提升水利工程設施運行能力,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連續多年奪得“全國棉花生產狀元縣”和“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全國特色水產養殖大縣”等殊榮,所產的“射陽大米”、“青龍蒜薹”、“洋馬菊花”、“海河梨果”、“射陽蟹苗”等成為馳名大江南北的特色農產品。
飲水思源,真情難抑。憶往昔,鬼斧神工、泥沙淤積造就出射陽縣;看今朝,興修水利、引排自如造福了射陽人。我要說,在“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的射陽百萬人民心中,早已聳立起“不忘共產黨,感謝新中國”的無字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