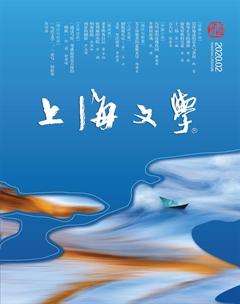“當代文學”:“重寫”的故事
陳培浩
人們常常忘記了一個概念得以成立背后的觀念裝置。某種意義上,離開相應的觀念裝置,任何概念都是無法理解的。比如“當代文學”,在中國大陸似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概念,但在歐洲、日韓甚至港澳臺地區,其內涵就顯得頗為模糊,也缺乏成為一門學科的可能。這些地區的讀者對于何謂“中國當代文學”經常是一頭霧水。因此,“中國當代文學”是一個必須打進引號里的概念,我們不僅要問“它是什么”,更要問“它是怎么來的”。多年前,洪子誠先生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當代文學”的概念》這篇文章中,洪先生敏銳地發現:“從1950年代后期開始,‘新文學的概念迅速被‘現代文學所取代,以‘現代文學史命名的著作紛紛出現。與此同時,一批冠以‘當代文學史或‘新中國文學名稱的評述1949年以后大陸文學的著作,也應運而生。”“當時的文學界賦予這兩個概念不同的含義,當文學界用‘現代文學來取代‘新文學時,事實上是在建立一種文學史‘時期的劃分方式,是在為當時所要確立的文學規范體系,通過對文學史的‘重寫來提出依據。”因此,“當代文學”并非在時間上自然承接“現代文學”出現的命名,它們是同一邏輯的產物。洪子誠指出,從“新文學”到“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命名轉變中,鑲嵌著從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轉換而來的“多層的‘文學等級劃分”。換言之,“新民主主義論”是塑造1949年之后“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裝置性話語。“新民主主義論”將中國的社會進程作了“舊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三分法描述,這三種社會形態在文學上各有對應。“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被視為舊民主主義社會的對應文學形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特別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宣告完成以后,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無疑不再適應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新要求了。因此,“當代文學”從其發生的語境看,是包含著鮮明的等級秩序的,“當代文學”作為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文學,被認為理所當然地高于“現代文學”;或者說,“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為了對這種等級秩序做出學術上乃至學科上的確認。
“當代文學”已經七十年,在不同階段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內涵所指和質的規定性。就其發生語境而言,它指發生在特定“社會主義”歷史語境下的文學;進入1980年代以后,隨著1950—1970年代“一體化”的文學體制被打破,“當代文學”也隨之發生重大轉型;而今天的讀者談“當代文學”,越來越用以泛指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或更窄化為“當下文學”,或具有“當代性的文學”。某種意義上,“當代文學史”就是一部不斷“重寫”的文學史。“當代文學”這一命名便是對“新文學”學術邏輯的重寫,而19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又是對1950—1970年代以“人民文學”為核心的“當代文學”的重寫;1990年代以來,“重寫‘重寫文學史”的呼聲和實踐此起彼伏。講述“當代文學”內部這個“重寫”的故事,可彰顯“當代文學”內部“人的文學”與“人民文學”這組矛盾催生的遞進、斷裂和轉型,并進一步思考“重寫”的倫理。
1
1988年7月,《上海文論》邀請當時的青年學者陳思和、王曉明在該刊主持“重寫文學史”欄目,該專欄從1988年第4期持續至1989年第6期,廣邀評論者對現當代文學領域重要作家趙樹理、柳青、郭小川、丁玲、茅盾、曹禺、胡風、何其芳及重要作品《子夜》《青春之歌》《女神》,重要流派“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進行重評。這便是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重寫文學史”事件。
將《上海文論》上的“重寫文學史”事件作為“當代文學”上的標志性節點,不是因為它得出了什么確鑿不移的結論,或是拿出了什么影響深遠的文學史著,而是因為它既關聯著“當代文學”一系列“重寫”實踐,又勾連著“當代文學”轉型時刻內在的辯駁和喧嘩。這個欄目并不滿足于作家作品重評這個層面,而是上升到“重寫文學史”的高度。這是因為,在世人的眼光中,重評作品代表的是一家之言,而“重寫文學史”代表的則是改天換地和蓋棺定論。“文學史”始終是一種具有權威性和權力意味的知識形式。他們用“重寫文學史”來命名欄目,不是因為他們托大不知天高地厚,而是他們就站在19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轉型的延長線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學斷裂和審美轉型吁求著理論上的總結,并最終要求以“文學史”形式給“新的崛起”以合法性確認。因此,用當下的話說,陳思和、王曉明的“重寫文學史”欄目,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可以放入“重寫文學史”譜系的首先是1985年由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位北大學者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1985年常被視為“當代文學”上具有界碑性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文學界的“尋根文學”、哲學界的“美學熱”和美術界的“85新潮”集結出場,文學研究界同樣不甘落后,貢獻了一個影響至今的概念——“20世紀中國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基于系統論和“世界主義”想像,要求打破既定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學科區隔,將“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把“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改造民族靈魂的總主題”、“‘悲涼的美感特征”、“藝術思維的現代化”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特征。這個概念的提出,可謂別開新聲、振聾發聵、應者如潮!如果說1950年代中后期,文學史研究界通過將“新文學”拆分為“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兩個階段而建立“當代文學”相對于“現代文學”的價值優先性的話;那么1985年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則通過拆除“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的學科藩籬來重置文學內部的價值坐標。新啟蒙、現代派和“人的文學”被凸顯出來,而左翼革命文學話語則被邊緣化了。
與“20世紀中國文學”有著相似“打通”思路的還有陳思和的“新文學整體觀”,區別在于,陳思和“整體觀”打通的是“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而黃子平三位學者則把“近代文學”一起打通,這就牽涉到新文學的起點問題。“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不但把1949作為“當代文學”的開端意義繞開了,同時也將“五四”作為新文學的起點意義也繞過了。1980年代初政治氣候雖然乍暖還寒,但蟄伏在藝術界卻是一股堅韌的人心思變的氛圍。這種變一點一滴,卻水滴石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朧詩潮,北島的“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呼應著歷史和社會的轉折而成一時之強音。“朦朧詩”最初是來自反對者的污名化命名,孰料卻在文學時勢浩浩蕩蕩的斗轉星移中,剔盡了污名成分,反成了對一種新審美的命名。時勢如此,連敵人的子彈都變成了新審美草船借來的箭矢。
文學時勢常常左右著人們的反應和思考。在1950—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文學”語境中,現代主義被視為頹廢、落伍的文學形式,是不健康的資產階級情調的流露。因此,1958年,走進新時代的馮至公開懺悔自己1940年代具有現代主義基因的《十四行集》“只表達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一些稀薄的、廉價的哀愁,很少接觸到廣大人民的苦難和斗爭”。但在1980年代初,即使在偏于正統派的老詩人徐遲(1960年代曾任《詩刊》副主編)那里,“現代派”也在“現代化”的掩護下找到了合法性出口:“不管怎樣,我們將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并且到那時候將出現我們現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學藝術。”曾經被進化論話語掃進歷史垃圾堆的“現代主義”,在1980年代的正統論述中借殼還魂,在彼時正當其時的社會“現代化”話語的掩護下枯木逢春。
在《重讀八十年代》一書中,朱偉特別提到了1980年代文學星空中的這些星星:1980、1981、1982年,《北京文學》發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紀事》和《故里雜記》。1984年《上海文學》發表了阿城的《棋王》;《收獲》發表了鄧友梅的《煙壺》。1985年,《上海文學》發表了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中國作家》發表了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人民文學》發表了韓少功的《爸爸爸》、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阿城的《孩子王》、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收獲》發表了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馬原的《西海無帆船》、莫言的《球狀閃電》、王蒙的《活動變人形》。1986年,《人民文學》發表了莫言的《紅高粱》;《十月》《上海文學》《鐘山》分別發表了王安憶的“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和《錦繡谷之戀》。1987年,《北京文學》發表了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收獲》發表了蘇童的《1934的逃亡》。1988年,《北京文學》發表了余華的《現實一種》……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種種可能》一詩寫道:“我偏愛很多此處沒有提及的事物/勝過很多我也沒有說到的事物。”誠然,列舉就是遺漏。無數名字以不在場的形式呼應著在場,共同構成了1980年代審美轉型過程中那種場的氛圍。
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初,王蒙就通過《布禮》《蝴蝶》《春之聲》《夜的眼》等小說,引起了一股“現代派”、“意識流”和藝術創新的爭論。198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一書,是年3月,讀罷此書的馮驥才在寫給李陀的信中說:“我急急渴渴要告訴你,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樣”,“在目前‘現代小說這塊園地還很少有人涉足的情況下,好像在空曠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風箏,多么叫人高興!”這是一個時代的心聲。
這種新的審美轉型,蟄伏著、涌動著,要求著理論上的辯護和正名。1980年代初,在文藝理論界也在努力別求新聲。錢谷融1950年代受到批判的“文學是人學”獲得正名,“人學”重新成了備受熱捧的話題。1980年代影響最大的文學理論思想當屬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和“主體性”理論,劉再復在理論上重新確認了寫作者面對世界和時代發聲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這是1980年代理論界對“文學是人學”的有力延伸:“人學”之“人”,既在于寫作者必須是一個獨立于形形色色龐然大物的“主體”,還在于這個“主體”必須有能力寫出豐富、復雜的組合性性格。這些都是對以往“二結合”“三突出”“高大全”的文藝原則的理論“重寫”。沒有1980年代熱烈蓬勃、一浪高過一浪的嶄新寫作實踐,沒有文學理論上新的闡釋和論述,就不可能有“重寫文學史”近于蓋棺定論的底氣。
經常被提到的,作為“重寫文學史”先聲,在1980年代大陸產生巨大影響的兩部文學史著——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特別是后者,被曠新年認為“構成了大陸19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最重要動力”。有趣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雖然引發爭議,以及一些老一輩學者的批評,比如王瑤就質疑“20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者為什么刻意不提或少提“左翼文學”,然而這種理論創新卻又得到了這些前輩學者私底下的支持。據陳思和回憶,“重寫文學史”欄目出來后,“編輯部怕得罪老先生,就去北京開了個座談會,結果老先生非常支持,王瑤先生、唐弢先生,包括我們的老師賈植芳、錢谷融、徐中玉都站出來支持,那么我們就放心了。”這是頗有意味的。我想說的是,“重寫文學史”并非一個偶然事件,它內在于1980年代的社會場域,像一艘思想的船只停泊于1980年代的文學水域,隨著1980年代整體觀念水位的上升而在1980年代末呼之欲出。
2
然而,“重寫”的故事并未結束。1980年代通過“重寫文學史”確立的新啟蒙話語在接下來的1990年代和新世紀遭到了新的理論挑戰,從而顯示了“人的文學”和“人民文學”這組矛盾的博弈依然纏繞在“當代文學”內部。
進入1990年代,中國社會再次面臨巨大的轉型,社會歷史語境的變遷,使新啟蒙話語迅速從人文學者倚仗的知識資源變成了被審視和反思的對象。發生在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顯見了彼時知識界在社會轉型來臨之際的迷惘和新知識話語的出場。在這場討論中,一些秉持后現代知識話語的青年學者開始登場。作為當年的新銳學者,陳曉明的知識背景迥然有別于1980年代主流,他非常自覺地將“人文精神”作為一種敘事和話語來看待:“人文關懷、終極價值等等,不過是知識分子講述的一種話語,與其說這是出于對現實的特別關切或勇于承擔文化的道義責任,不如說是他傾向于講述這種話語,傾向于認同這種知識。在這里,知識譜系學本身被人們遺忘,說話的‘人被認為是起決定支配作用的主體。”在此論述中,1980年代那種統一的整全的“人”終結了,代替為各種分層化話語的塑造物。另一位當年的后學才俊張頤武則將人文精神視為“最后的神話”,他對“人文精神”疾呼者無視“‘知識的有限性”,以為“任何學者只要具有了‘人文精神,就能穿透‘遮蔽,無限地掌握世界”的本質論神話提出尖銳的質疑。這種在當時一般讀者看來不無艱澀的后學知識方法如今已經成為學界主流,而這批攜帶著后學理論武器登臨學術界的新銳學者日后也如魚得水風光無限。
1990年代現當代文學界有一部書以其新的知識方法迅速獲得影響力,這便是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這部文集收錄了劉再復、林崗、唐小兵、劉禾、黃子平、戴錦華、孟悅、賀桂梅、李楊等學者對左翼大眾文藝的重讀文章,并貫穿了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再解讀”立場:“不再是單純地解釋現象或是滿足于發生學似的敘述,也不再是歸納意義或總結特征,而是要揭示出歷史文本后面的運作機制和意義結構。”從闡釋文本意義到解釋文本背后的意識形態運作機制的轉變,引領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型。在這本文集中,方法轉型背后并未顯露出明顯的價值轉向。換言之,“再解讀”提供了一種重新靠近在1980年代視域中嚴重貶值的左翼大眾文藝的學術路徑,卻并未有為左翼文學重估價值、重申合法性的訴求。然而,在日后的發展中,一種依靠知識考古方法,在方法和價值上反思1980年代“新啟蒙”,為“人民文學”重建合法性的新左翼文學史話語產生了不俗的影響。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和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視為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思潮在1990年代末結出的史著果實。雖然這兩部史著在方法論上很不相同——洪史明顯融合了1990年代知識轉型過程中的很多方法創新,諸如對文學制度研究的重視,對文學社會學和知識考古方法的納入——但洪史和陳史顯然都保留了鮮明的啟蒙論立場,這恰是這兩部著作被更年輕一代學者所質疑之處。雖然李楊、賀桂梅、曠新年等學者跟洪子誠具有學緣上的師承關系,治學路數受到洪子誠或深或淺的影響,他們對洪子誠文學史研究的貢獻也從不否認,但這些學者也并不諱言他們在審美立場上與秉持啟蒙論的洪子誠的差異甚至“斷裂”。李楊說“洪子誠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與我們這一代人并不相同。譬如說,他始終懷疑1950—1970年代的文學價值,對我提出的所謂1950—1970年代文學的‘文學性的觀點不以為然。雖然一直以1950—1970年代文學為研究對象,在他內心深處,他仍然認為以張愛玲為代表的1940年代文學成就要比1950—1970年代文學高得多,常被我譏評為有‘小資情結。而且更重要的是,對福柯、德里達等人對歷史與文本之間的關系的論述,他也始終心存疑慮。”
2012年,汪暉教授邀請美國斯坦福大學王斑教授在清華大學作講座,王斑在分析了趙樹理小說后發出這樣的質問:究竟趙樹理更先鋒,還是張愛玲更先鋒,趙樹理更新潮,還是張愛玲更新潮?站在新左派的立場上,并不難理解王斑教授的邏輯。在他看來,張愛玲在當代文學史上的重新出場,是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與1990年代市場化背景下小資話語合謀的結果,正是這種文學邏輯在趙樹理和張愛玲之間給出了“土氣”和“洋氣”的判定,從而掩蓋了趙樹理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文學”那種嶄新的現代性探索。事實上,1990年代末以來,以李楊、賀桂梅、曠新年、蔡翔等學者為代表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和對“1980年代文學”的知識考古,都包含著一種鮮明的為“社會主義文學”一辯和正名的立場。
這種被稱之為“新左派”文學史話語的學術路徑具有多個理論來源,其中既有福柯的知識譜系學,也有來自日本的竹內好的“作為方法的亞洲”。竹內好的學術思想鼓勵人們打破“亞洲/歐洲”的二元對立和以歐洲現代性作為唯一的、普遍的現代化道路的認知,從而在弱勢地區的獨特性和內在主體性中確立自身的現代性可能。1990年以來,一批中國學者在竹內好那里獲得啟發,紛紛通過趙樹理等中國左翼作家闡發“另類現代性”或“東方現代性”,為被1980年代啟蒙思潮驅逐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學正名,或者說為中國文學的革命現代性作為一條特殊道路的合法性論辯。竹內好所提倡的那種從對象內部發現主體性的思維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其他方面也產生了諸多啟發。以至于,“以某某為方法”在新世紀以來成了一個極其流行的研究思路。
循著重新發現“革命中國”內在主體性的思路,“新左派”學者嚴重質疑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將“社會主義文學”內在復雜性和豐富性一筆勾銷的做法。不過,在他們那里,“社會主義文學”常常不僅是研究對象,也是認同的對象。換言之,當他們意識到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同樣是某種意識形態塑造的結果時,他們在價值立場上更愿意回到“社會主義文學”那里。即使在所謂的“文學性”上,他們也否認“1980年代文學”高于“社會主義文學”。因為,在他們看來,并沒有純粹客觀的“文學性”,不存在作為化外之地的“文學本身”。換言之,對文學與文化政治關聯的強調使他們已經對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中做出的文學內外區分嗤之以鼻,這個理論曾經深刻地塑造了1980年代的文學認知。說到“文學性”,“新左派”學者很可能馬上會以“誰的文學性”反詰,他們的學術實踐也因此構成了對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再次“重寫”。
問題在于,不同時代的“文學性”觀念固然是其時代的奠基性話語和文化邏輯的產物,但不同時代的“文學性”難道斷然沒有一種可溝通性存在嗎?當今的學術場域,啟蒙論和新左翼的文學立場無法相互說服,文學標準看似多元實則混亂。后現代主義話語的加入使得“確定性”被嚴重質疑,在消解霸權的同時,其實把審美的標準也一并放棄了。今天,混亂失調可以假去中心化之名大行其道,語言腫瘤又可以假先鋒實驗的幌子招搖撞騙。“當代文學”的“重寫”,以及“重寫之重寫”的故事,最迫切的提問在于:來自不同文化邏輯的文學觀,該如何在更長的時段和更大的歷史視野中求得匯入漢語“偉大傳統”的可能?
3
1990年代以來,有兩個在中國影響巨大的概念需要我們重新打量。其一是福柯的話語。1990年代以來,福柯的“話語”理論不僅作為理論工具普遍地運用于中國大陸學界的各種文化分析中,更是作為一種思維方法被廣泛接受。福柯突破了語言學對“話語”的簡單定義,而將“話語”視為“一組陳述,這組陳述為談論或表征有關某一歷史時刻的特有話題提供一種語言和方法”。“話語”通過語言實現了對“知識”的生產。福柯“話語”理論打破了傳統透明的意義觀,傳統理論認為“意義”是存在于事物自身的,而“話語”理論則認為知識和意義都是特定文化邏輯下被建構和生產出來的。這種構成主義意義觀某種意義上戳破了1980年代“新啟蒙”的“主體論”神話,“主體”并非天然如此,福柯著名的判斷:不是人在言說“話語”,而是“話語”在言說人。福柯試圖揭示:人并沒有控制“話語”的主體性,相反,人不過是“話語”形塑的結果。與福柯的“話語”理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提出的“認識裝置”的概念。柄谷行人認為,任何被自明化的“風景”背后都頑固地存在著被抹去起源的“認識裝置”。柄谷行人這部研究日本現代文學的著作之所以在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其的思維方法與尋求學術轉型的中國學界產生共鳴。不妨這樣說,“認識裝置”是“話語”理論化入文學史研究的結果。它提醒研究者從表面的“風景”后撤,去尋找被時間和歷史切斷、掩蓋的蛛絲馬跡,其啟發性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看來,這種基于“構成主義”的認識論,帶來的并非只有洞見和啟發,它給中國學界帶來的最大困惑在于:當我們將所有“意義”都指認為某種“文化邏輯”的建構結果時,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抹平了“意義”之間的差別,也擱置了評價和整合不同“文化邏輯”的可能性。
新世紀以來,技術迭代加速了社會的轉型,每一次轉型都攜帶著新的文化邏輯對文學現場發出“重寫”的要求,甚至到了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程度。問題在于,每一次“重寫”都不徹底,只是多種新舊文化邏輯盤根錯節、相互對峙和駁詰,看似千原并立、千燈互照,實則鏡城里魔影重疊,小徑交叉而難覓去路。今天的這種文化語境和癥候,要求我們綜合“面向未來”和“面向傳統”二種眼光,探尋“重寫”的倫理。
19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再次重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后現代主義為方法的,這種方法質疑“意義”的一元論,發見了“新啟蒙”背后的話語建構性,轉而為“社會主義文學”辯護。無疑,這是一種學術的創新和推進。悖論在于,對“新啟蒙”的祛魅還同時伴隨著以復雜的學術包裝對“革命中國”的復魅。換言之,學術語言和范式推進了,審美立場卻翻烙餅式地回到了從前。“重寫”常常受制于很多當下性的文化動機,諸如被創新之狗追趕著的學術焦慮,諸如種種體制性的利益推動。但“重寫”能否在此之外,依然葆有一種相對超然的長時段眼光呢?“重寫”能否超脫于“人民文學/人的文學”、“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寫什么/怎么寫”這些短時段的二元框架,把不同時段的局限和洞見都包含在內,擬定出一份更兼容并蓄的遺產呢?
回到上面王斑教授的質問,趙樹理和張愛玲究竟誰更新潮一點呢?我的看法是,我們何必一定要回答這個問題。這個提問已經牢牢地將思域設定在“人民文學”和“人的文學”的二元對立中,站在“人民文學”的文化坐標中,使用“人民語言”的趙樹理代表了一種先進“方向”;而站在“新啟蒙”或“小資”的文化邏輯中,書寫生命“華美袍子里的虱子”更有高級感。這樣一來,非此即彼,可否換另一種提問方式?比如說,以百年甚至千年的視野看,哪些“現當代文學”會留下來?站在“傳統”的視野,“當代文學”將如何與江河壯闊的漢語文學傳統相銜接?站在“未來”的視野,“當代文學”將提供何種被時間珍重的價值?立于此在,卻從過去看到未來,這或許是“重寫”該具備的文化襟懷。有意義的“重寫”不是一次次地制造“斷裂”,卻變著花樣回到過去;有意義的“重寫”該深刻地切入“當代性”的焦慮,為當代創造一個真正的增量;有意義的“重寫”面向未來的變局和可能,卻不斬斷歷史連續性,而把“未來”融匯進生生不息的浩大傳統中去。
“人的文學”和“人民文學”,“啟蒙”和“革命”博弈至今,我們突然發現:“人學”和“人民學”的爭執不過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左右手互搏,它們居然來自于同一文化肌體。韓少功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人民學與自我學》中有趣地將這兩個命題關聯在一起。在他看來,“自我學”和“人民學”都是“人學”的一種路線,二者構成了一體兩面:“真正偉大的自我,無不富含人民的經驗、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聯感同身受的‘大我關切;同樣道理,真正偉大的人民,也必由一個個獨立、自由、強健、活潑、富有創造性的自我所組成。”我愿意把韓少功的文章當成對王斑的提問的隔空回答。我們何必在張愛玲和趙樹理身上決一高下呢?更富建設性的“重寫”應該尋找把他們文學道路中的“自我學”和“人民學”融合到一起的可能。事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寫作《長恨歌》的王安憶常常被歸入1990年代小資的“自我學”吧,但陳思和卻讀出了《長恨歌》里對王琦瑤們的“反諷”,并指認了王安憶寫作與“左翼文學”總體性的關聯;韓少功作為尋根文學的代表,應屬于“新啟蒙”吧,但他卻在1990年代成為著名的文化左派。真正有創造力的寫作者,總是被“當下性”的關切所指引,并努力超脫于標簽和潮流的規限。同樣,有創造力的研究,絕不應滿足于為學術而學術的顛覆和斷裂。站在更遠的立場看,“人的文學”和“人民文學”并非對手,或者說,社會的快速轉型已經為它們創造出共同的新對手。
進入新世紀以后,由于文學語境的變化,洪子誠先生多次感慨“當代文學”已經終結,李云雷的說法則是“新文學的終結”。作為當下文學的“當代文學”當然還在無限地順延下去,可是那種以“人學”為核心,包含著“自我學”和“人民學”的一體兩面的精神立場的文學已經在當下成為一種絕對的邊緣語言,一種社會學小語種。消費社會下無所不在的資本運作和技術神話所催生的速朽文本和碎片閱讀已經成為主流。此時,再站在“革命”或“啟蒙”的任一立場上進行“重寫”都顯得如此荒誕。從未有一個時刻如當下這樣,人文學遭遇了這樣的危機,最糟糕的結果不在于“文學”的定義被改寫,大量類型化的泛文化產品占據了以往“文學”的空間,人們將幽微、豐富和遼闊的精神體驗視為“人文主義”神話甚或騙局,而在于人本身很可能從根本上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悖論的是,這正是將技術神學化的當代人孜孜不倦地探索并為之歡呼的。
人學和科學之間攻防的實質是:科學不斷探索用技術取代人的可能性,而人學始終要使科學被囿限于為人服務的邊界中。事實是,今天的人學正在節節敗退,科學正在改寫人對于人不可被改寫部分的認知。在這個被稱為未來已來的時代,在這個技術神話已把人類引上一條不知所終的旅途的時代,真正的文學必須再次捍衛人學的尊嚴,以抵抗未來路上那頭斯芬克斯怪獸。因此,“重寫”便不意味著與過去的簡單決裂,而是把現在匯入由無數過去構成的傳統中。這個來自T.S.艾略特的觀點,依然啟示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