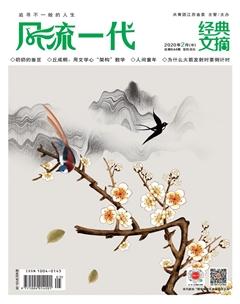惠特曼:游吟詩人的自由與浪漫
劉晗

2019年是美國現代詩歌之父沃爾特·惠特曼200周年誕辰,《波士頓評論》發表長文紀念這位美國文壇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作當數浪漫主義詩集《草葉集》 (Leaves of Grass),它也被譽為美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具有民族氣派的作品,突破了傳統的詩歌格律,開創了詩歌自由體的風格,在此后的詩壇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部舉世聞名的著作在1855年第一次問世時僅收錄了十二首,此后歷經多次增刪修改以及再版,直到惠特曼離世前,總共收錄了三百余首詩歌,可謂見證了惠特曼一生的創作歷程。其中一首名為《自己之歌》的詩歌長達一千三百多行,幾乎囊括了惠特曼的主要創作思想。
這部惠特曼傾其一生創作的作品,取材之廣泛令人嘆為觀止,歌頌民主自由的喜悅,抨擊農奴制度的罪惡,贊美自然偉大,傳送民眾的智慧,也可以說,他在身體力行以詩歌的形式記錄了美國的文明史。惠特曼將他對歌劇和天籟之音的熱愛用在了作品之中,多種意象和比喻頗具張力和表現,音韻性和節奏感。
“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長著草。”《草葉集》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草葉最為平凡,卻有著生生不息的頑強生命力,象征著當時正處于上升時期的美國,也是出身草根的詩人惠特曼代表底層民眾的一種發聲,這也是他終其一生的身體力行,仿佛他肩負著使命,心懷悲憫之心與苦難共鳴,為壓迫和奴役而吶喊,以先知的姿態暢想未來自由民主的美好圖景。從備受爭議到奉為國寶,《草葉集》的命運歷經了起伏跌宕,正如惠特曼曾在戰爭中出生入死,漂泊不定的一生。
美國精神:斜杠青年的跨界生活
從美國發布《獨立宣言》以來,在民眾心中就萌發了“自由、民主、人權”的種子。在此之后,一代代美國人堅信,他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擁有美好的生活,惠特曼也是“美國精神”的受益者。他出生于十九世紀初期紐約長島的一個村莊,成長于底層家庭的他只受過幾年教育,便開始負擔起養家的重任,父母、兄弟姐妹的一日三餐靠他的微薄收入,他做過郵差、勤雜工、木匠、泥水匠、抄寫員等等,又在印刷廠做排字工,然而生活的磨難并沒有削弱他的文學夢,尤其鐘情于荷馬、但丁、莎士比亞等作家的經典文本。
全靠自學成才的惠特曼在十六歲時重返學校,但并非以學生身份,而是以老師的身份站上了家鄉學校的講臺。對于文學的追求讓他開啟了寫作的職業生涯,辦報寫稿、采訪編輯忙得不亦樂乎,業余還抽空參加辯論協會。也許是職業使然,他喜歡走街串巷,熱衷于結交社會各階級的人們,曾是他的采訪對象的車夫、船員、漁民,后來都與他成了朋友。然而,對他更有吸引力的還是大自然的魅力,也為他后來的創作積累下不少素材。他最愛在海灘沙地撿拾海鷗蛋,劃船以及不知疲倦地走路。
不到二十歲的惠特曼換過無數次的工作,似乎每年的生活都是對人生的挑戰,也正是因為身處不同的環境,少年老成的他有著超越同齡人的心智和毅力,對事物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充滿浪漫氣息的意象和場景。“無論我去哪里,都能感受到人生的愛撫。”他有著詩人特有的多愁善感,還有小說家講故事的天賦,但遺憾的是,他早期的創作并未獲得評論界的太多關注。然而,寫作已經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時的他不是在寫作,就是走在為寫作而體驗生活的路上,走走停停,觀察途中的所見所聞,他著迷于戲劇表演,幾乎看遍了當時紅極一時演員的表演,情節的起伏、戲劇的唱腔都讓他受益匪淺。
四處游走的悠然自得給了惠特曼拓展視野,了解美國民眾生活的機會,這些無疑成為了他一生最寶貴的財富。他曾在一段演說中講道:“藝術作品以及所有真正的藝術家的光榮使命,就是將一切阻礙人們感受美感或是培養觀察美好事物的能力的東西全部掃除掉,讓人們感受到世界的真善美……倘若沒有真正自由的思想,就沒有真正的藝術家——因此,自由能夠讓藝術家獲得更多的創作空間,讓他們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與才華去進行創作。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藝術才能變成一種高尚且完美的作品。”在惠特曼看來,藝術值得他用一生的時間去探索,放飛自由,像他的創作那樣不拘一格。《草葉集》并非他心血來潮的即興之作,而是沉淀了他三十多年的經歷和思考,這部自費出版的小冊子起初在市場上沒有什么反響,直到他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作家愛默生的來信,愛默生給了《草葉集》很高的評價:“在美國文學史上還從來沒有人創作出像你這樣的作品。”這封信讓惠特曼備受鼓舞,也被收錄在了第二次印刷的《草葉集》之中,隨著版本的更新,惠特曼開始在詩壇小有名氣。然而,愛默生為他撰寫的宣傳語“我祝賀你踏上了一條偉大的創作之路”,也遭到了多方的詬病和指責。
自由至上:民主戰士的奔放書寫
時隔不久爆發了南北內戰,這場戰爭到后來演變成了一場消滅奴隸制的革命戰爭。惠特曼曾親眼目睹過奴隸買賣,便和弟弟喬治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志愿兵團,開始了長達兩年的志愿者工作,他試著動用自己的專長去照顧病患,以故事撫慰戰士受傷的心靈。
在他看來,情感的傳達甚至勝過藥物的療傷。少年時的惠特曼擁抱自由,青年時的他為了民主而戰,在那里,他先后與很多名戰士有過交談,有些人直到戰爭結束還和他保持著聯絡。在與死亡交鋒的陣營,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壓抑感,弟弟喬治一度被俘虜,戰爭的殘酷與傷員的疾苦讓他感同身受。正如惠特曼所說,“真正的戰爭是永遠都無法從書本上感受到的”,《擂鼓集》正是那時的心靈寫照,字里行間寫實的筆觸滲透著戰爭時期的緊張場景,志愿軍的斗志與激情,炮火連天震耳欲聾以及人流穿梭不息的戰地醫院。
戰后,惠特曼在印第安人事務局工作,空閑的時候就修改作品,當部長知道他就是《草葉集》的作者,覺得這本書充斥著不道德的言詞,立即將他解雇開除。惠特曼的朋友知道了他的遭遇后,紛紛聯系媒體為作品正名,風波過后不久他又在政府找到了差事,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惠特曼遭遇了事業上的滑鐵盧,但他卻表現得異常平靜,經歷過戰爭的生死洗禮,個人的坎坷與波折又算得了什么?當街上有人認出他時,惠特曼又表現得像孩子那般喜悅,浮華與虛榮向來不能打動他,他始終一個人生活,在外人看來他是孤獨的詩人,他卻享受獨自沉思的寧靜,永遠保持著最初的質樸與天真。
惠特曼渴望與友人精神上的交流,丁尼生、王爾德都先后與他有過長時間的書信往來。年過五旬的他開始感覺創作上的力不從心,母親的離世讓他悲痛欲絕,似乎只有友人的掛念和前來拜訪的年輕寫作者點燃他對文學的激情。每當他的身體狀況逐漸好轉,又拿起筆開始了創作,重新復歸自然的懷抱。
1892年初春,惠特曼與世長辭,長眠于哈利公墓。一百多年過去了,惠特曼的詩歌仍被世界各地的詩歌愛好者嘖嘖稱道,他始終觀照那些永恒偉大的事物,傳達原始的情感,在他的詩歌里,能讀到孩童的爛漫,成年的理性,老年的睿智,一種超然的灑脫。
(摘自《世界博覽》2019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