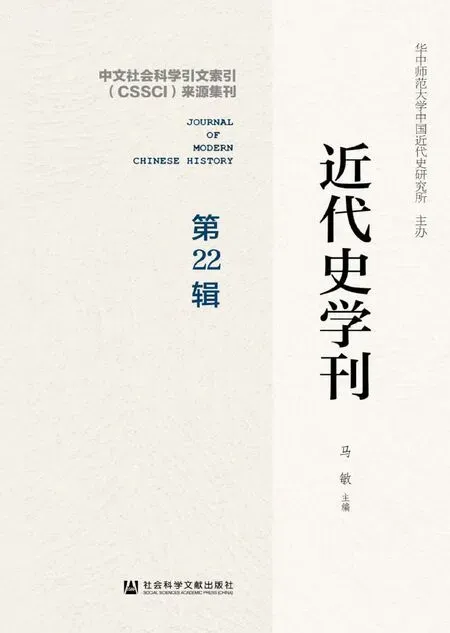新文化運動與屈原形象的解構重建
王余輝
內容提要 屈原形象在近代文化轉型中經歷了具有古今之變意義的解構與重構。傳統文化范疇內屈原形象與王權相聯系,被界定為忠君的“忠臣”。這一形象到清季開始受到質疑。新文化運動時期,伴隨著整理國故思潮的出現,屈原“忠臣”形象被系統解構。與此同時,屈原作為“人”,特別是作為文豪、詩人、文學家的“偉人”身份,被重建起來。屈原形象的變化,折射了中國近代文化轉型期新舊思想的交替,也見證了傳統歷史資源向現代轉化的努力。
傳統與現代之爭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歷來不乏學者關注。不過,關注現代思想的興起和傳統思想的消退者較多,而注目于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者卻較少,尤其對于新文化運動,很多人認定這場運動是全盤反傳統的“革故”運動和全盤西化的“鼎新”運動,忽略了其寓“再造文明”于“整理國故”的一面。實際上,在這場運動中,雖確有傳統與現代相割裂的一面,但也有在傳統文化資源上建構現代文化的一面。本文所力圖再現的傳統屈原形象的解構與現代屈原形象的重構,正是其中之一。①屈原形象問題已經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就歷代屈原詮釋所導致的屈原形象變化進行了有益探討,相關研究主要有〔美〕勞倫斯·A.施奈德《楚國狂人屈原與中國政治神話》(張嘯虎、蔡靖泉譯,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潘嘯龍《屈原評價的歷史審視》(《文學評論》1990年第4 期),金榮權《論兩千余年來屈原形象的歷史演變——兼及屈原精神與文化內涵》(《江漢論壇》2000年第7 期),李中華、鄒福清《屈原形象的歷史詮釋及其演變》[《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8年第1 期],等等。不過,相關研究多為從古至今的長程描述,對近代屈原形象的變化過程探討不夠,這正是本文所著力之處。
一 “忠臣”的消解
傳統屈原詮釋起于西漢,司馬遷較早論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①司馬遷:《史記》第8 冊,中華書局,2013,第2482 頁。有觀點認為這段話本是劉安《離騷傳》語,被后人摻入《屈原列傳》。見湯炳正《 〈屈原列傳〉 新探》,《文史》第1 輯,中華書局,1962,第35 頁。司馬遷以“忠”、“怨”定義屈原,為漢至清末的屈原詮釋定下了基調。班固、王逸、洪興祖、朱熹等后來者大都在“忠”和“怨”兩端發揮,不過,他們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基本上是闡揚屈原之“忠”,而掩蓋、抨擊其“怨”。概觀之,詮釋中“怨”往往被“忠”壓倒,“忠”居于主導地位,塑造了屈原“忠臣”的主流形象。屈原“忠臣”形象經層層建構,至明清時期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②參見潘嘯龍《屈原評價的歷史審視》,《文學評論》1990年第4 期。明末黃文煥說“千古忠臣,當推屈子為第一”,王夫之稱屈原為“千古獨絕之忠”,清人龔景瀚亦稱“屈子之忠,所以為萬古人臣之極”。③李誠、熊良智主編《楚辭評論集覽》,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308、344、423 頁。傳統屈原詮釋實際上服從于“忠君”這個最高倫理規范,屈原“忠臣”形象的建構與“忠君”倫理的發展大致同步。
清季以降,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興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傳統之風。反叛傳統屈原詮釋的新詮釋也開始萌發,梁啟超、王國維是早期代表人物。梁啟超在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說:“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④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5 號,1902年4月。王國維于1906年寫作《文學小言》,稱“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⑤王國維:《文學小言》,《教育世界》第139 號,1906年11月。又于次年撰《屈子文學之精神》,提出“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⑥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教育世界》第140 號,1907年1月。梁、王之論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已經具有不同往常的意義。傳統忠君詮釋是教化的重要內容,多以君臣大義注解《楚辭》,在指稱屈原時也往往冠以“忠臣”名號,屈原及其作品的地位、意義、影響基本是政治性的。然而,梁啟超、王國維使用一般、現代意義的“文豪”、“詩人”指稱,①傳統屈原詮釋中也有少數以“詩人”指稱屈原的做法,但與王國維具有本質區別。如漢人王逸說:“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見李誠、熊良智主編《楚辭評論集覽》,第23 頁。悄然替換、掩蓋了極富政治意義的傳統“忠臣”名號,并強調屈原在學術史、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已經開始有意反抗傳統詮釋,改寫屈原的形象。而且,這種反抗建立在全新的思想資源和價值依歸基礎上,也就是他們所接受的自由、民主等西方現代社會和國家觀念。簡言之,新詮釋開始對傳統詮釋的詞匯與價值均予以拋棄。不過,當時的反叛基本停留于詞匯與價值層面,尚未觸及深層學理,更多在隱性層面,尚未直接從正面解構“忠君”。
及至新文化運動時期,民主、科學逐漸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在這場激烈反對舊思想、倫理的思想革命中,傳統帝制與忠君倫理是一個反對焦點,孔子和儒家被認為是其護身符。如李大釗所言:“中國今日種種思潮運動,解放運動,哪一樣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運動?哪一樣不是打破孔子主義的運動?”“政治上民主主義(Democracy)的運動,乃是推翻父權的君主專制政治之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義之運動。”②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第7 卷第2 號,1920年1月。于是,孔子連同儒家被打倒,“忠臣”屈原亦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時人開始從學理上解構這位“千古忠臣”,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即是一位旗手。
1917年,在不啻為新文學運動宣言書的《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擬出八條主張,其中兩次論及屈原。一次是在第二條“不摹仿古人”處,“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一次是在第四條“不作無病之呻吟”處,胡適先解釋“無病之呻吟”道:“不思奮發有為,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然后提出,“吾惟愿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③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 卷第5 號,1917年1月。胡適的話很簡練,但至少能夠反映兩層意思。其一,篤信進化論的胡適將費舒特(費希特)一類與屈原一類做了新舊的區分,在價值上,認同新的費舒特類而排斥舊的屈原類。胡適所言“無病之呻吟”、“牢騷之音”,其實皆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屈原,也即否定了傳統那位有崇高地位的“千古忠臣”。其二,胡適不愿“今之文學家”做“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此間接表明他亦將屈原定位為“文學家”,而非傳統之忠臣。
兩年后,胡適正式發起“整理國故”運動,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使“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①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 卷第1 號,1919年12月。除了打破《詩經》的“經”字招牌,②徐雁平對胡適等人整理《詩經》有比較詳細的論述,見氏著《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110—159 頁。胡適亦將同樣具有“經”意義的《楚辭》和“忠臣”屈原納入“整理”范圍,反對態度越發明確,見于1922年發表并引起軒然大波的《讀〈楚辭〉》一文。③本段及下段引文均出自胡適《讀〈楚辭〉》,《讀書雜志》第1 期,1922年9月。胡適首先質疑式發問:“屈原是誰?”“《楚辭》是什么?”并以此分別作為兩個章節的標題,進行學理式回答。他以歷史眼光指出,“傳說的屈原是根據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是一種復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后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楚辭》的注家,自王逸直到洪興祖“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結果,屈原成為“理想的忠臣”(這個概括可謂一語中的),《楚辭》則變為“一部忠臣教科書”。胡適實際上審視了傳統詮釋的主要進程,很不客氣地將“忠臣”屈原的建構過程揭示出來,并幾乎全盤否定了西漢以來的《楚辭》注解。
在文章最后一節,胡適論述了“《楚辭》的文學價值”(也是作為小標題),提出“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它的文學興味來,然后《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胡適旗幟鮮明地反對、解構了長期流行的傳統“忠臣”屈原和《楚辭》注解,意圖還屈原一個真面目,還《楚辭》一個“文學”的真價值,這是屈原詮釋史上前所未有的改塑。事實上,胡適反對“忠臣”屈原的態度是如此強烈,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慣常的矯枉過正的態度,對歷史上本初的屈原也提出了質疑(但未絕對否定)。這被有些人看作胡適完全否定了屈原其人的存在,因此對胡進行了激烈、長期的聲討。④參見黃中模《現代楚辭批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胡適解構“忠臣”屈原的做法獲得了許多人的認同與效仿,謝無量很快在次年出版的《楚詞新論》一書中予以響應。謝氏特辟“楚詞評論家之評論”一章,以否定的語氣歷數從漢至清的代表性詮釋:劉安雖稱贊屈原,但有“一半文不對題”;班固“完全拿北學派的見解來批評屈原”;王逸注《離騷》“完全與經義相合”;朱熹“所講那些‘大義’的地方,免不了仍用他儒家的主觀見解,所以也是不能澈底知道屈原的真意”;明清時期如林云銘那些“‘高頭講章式’的批評派”則“把楚詞那整大段的美,完全失了”。結果便是,《楚辭》被歷來的注家“注壞”了,“單把屈原看成個忠臣義士,所以句句都說是喻君,篇篇都說是諷諫”。①謝無量:《楚詞新論》,商務印書館,1923,第69—76、60 頁。這實際上也是對“忠臣”屈原進行了一針見血的胡適式解構。
長期處于思想文化界中心位置的梁啟超頗能洞悉時情,對“忠臣”屈原的消解有敏銳而深刻的觀察。1922年,梁氏在回顧近五十年中國思想界“進化”路程時特別說:“如今‘新文化運動’這句話,成了一般讀書社會的口頭禪;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爭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②梁啟超:《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概論》,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第二編,申報館,1923,第3 頁。所謂要被推倒的“屈原”,正是指既有之“忠臣”屈原。事實上,1922年是于屈原詮釋具有重要節點意義的一年,胡適、梁啟超發表重要文本《讀〈楚辭〉》和《屈原研究》也是在這一年,胡、梁之論可視為屈原“忠臣”形象基本解構的標志。梁啟超此時也加大了反傳統詮釋的力度,直接從正面解構“忠君”。最關鍵的表述是:“人之情感萬端,豈有含‘忠君愛國’外即無所用其情者?若全書(《楚辭》)如王注所解,則屈原成為一虛偽者或鈍根者,而二十五篇悉變為方頭巾家之政論,更何文學價值之足言?……后世作者往往不為文學而從事文學,而恒謬托高義于文學以外。”此即明確批判了以王逸為代表的傳統注家之“忠君愛國”詮釋。相應的,梁將《楚辭》界定為“富于想象力之純文學”,號召僅取舊注的名物訓詁,但對于教化意旨則“宜悉屏勿觀”。③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周刊·書報介紹副刊》第8 期,1924年1月。這同胡適所呼吁的打破舊注、尋出《楚辭》的文學興味密切呼應。“純文學”一語很值得注意,此淡化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性,僅強調文學性的程度更深,其要旨也在于消解“忠臣”屈原。當然,解構舊屈原只是一個方面,與此同時,諸家也在積極建構新的屈原。
二 “人”的還原
“忠臣”屈原之層層建構、凸顯,建立在重重壓制屈原之“怨”的基礎上。一開始屈原之“怨”還被承認,盡管絕大多數人持極力批判態度,如宋儒朱熹說屈原之人“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批評屈原怨懟、偏激,不合乎儒家中庸之道。但到后來,明清儒士則直接否認屈原有“怨”,提出屈子自沉全源于“忠”,于是,屈原之“怨”基本被抹掉,其“忠”完全獨顯。①參見潘嘯龍《屈原評價的歷史審視》,《文學評論》1990年第4 期。最終樹立的“忠臣”屈原其實相當忠直淳厚、規矩端正,幾乎沒有怨懟、憤懣、不平、愁苦等負面和破壞性情緒,確如胡適所稱“理想的忠臣”,不能算是一個正常、健全的“人”。
與此相關聯,除了直接解構處于正統地位的“忠臣”屈原,反傳統詮釋還有“撥亂反正”的一面,即闡揚那個一直被壓制的“異端”屈原,或言屈原之“怨”。這個傾向在清末的新詮釋中已有初步反映,以魯迅最為突出。就在棄醫從文后不久,魯迅發表了一篇旨在歌頌西方拜倫、雪萊、普希金等摩羅派詩人的反抗精神的文章,其中,以復雜的心理論及屈原,一方面肯定屈原一反“常俗”,“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另一方面,批評屈原之文“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②令飛(魯迅):《摩羅詩力說》,《河南》第2 期,1908年2月。即批評屈原缺乏“反抗”精神。無論肯定還是批評,魯迅言論焦點都在傳統詮釋的“怨”上,且將“怨”替換為更具激烈和現代意味的“反抗”,盡管他不那么愿意承認屈原具有“反抗”精神。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20世紀初具有現代個人主義思想的魯迅這里,非但沒有指責屈原之“怨”,反而還嫌其“怨”之不夠。這已經與傳統詮釋指斥屈原之怨的態度截然對立。其時,魯迅已提出“立人”,強調立人之道“必尊個性而張精神”。③魯迅:《文化偏至論》,《墳》,魯迅全集出版社,1941,第52 頁。
新文化運動時期,諸家對屈原之“怨”的闡揚更進一步。在這場思想革命和啟蒙運動中,“人”的啟蒙是一個核心。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陳獨秀向青年所提六條要求的第一條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將傳統忠孝節義指為“奴隸之道德”,以“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由之人格”的“解放”相號召,提倡以“我”為本位。①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 卷第1 號,1915年9月。胡適大力推介以個人、個性、自由、反抗為核心意涵的易卜生主義,②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4 卷第6 號,1918年6月。“易卜生”確很快被廣泛接受,成為耳熟能詳的新人物和新名詞。③參見張春田《論五四時期的“易卜生熱”及其文化邏輯》,《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8年第1 期。要言之,新文化運動中,個人主義思潮澎湃,沖決綱常名教之網羅,追求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成為主旋律。④高力克:《新文化運動中的個人主義》,《史學月刊》2015年第11 期。題中之義,就是將舊綱常倫理化的“臣”還原、培塑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
在此過程中,那位“理想的忠臣”屈原自然是理想的詮釋對象。諸家積極將屈原由忠直淳厚、規矩端正的“忠臣”還原為“人”,詮釋屈原作為人應有的個性、情感、自由與獨立。五四青年郭沫若于1920年底創作的戲曲《湘累》,便是一份代表性文本。首先,在形式上,郭沫若讓屈原自己開口說話,且大量使用第一人稱“我”(計約143 次),突出了屈原作為“人”的主體性。在內容上,通過為屈原精心設計臺詞,使屈原具有一個正常的“人”的屬性:其一,具有自由意志,“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其二,具有抗爭精神,“你要叫我把這蓮佩扯壞,你要叫我把這荷冠折毀,這我可能忍耐嗎?”“我這么正直通靈的人,我能忍耐得去學娼家慣技?”其三,相信個人的力量和價值,“你怎見得我便不是揚子江……我的力量便不能匯成個無邊的大海嗎?你怎這么小視我?”其四,也具有哀愁情感,“我這深心中海一樣的哀愁,究竟可有破滅底一日嗎?”⑤郭沫若:《湘累》,《學藝》第2 卷第10 號,1921年4月。借助戲曲這種相對自由的特殊形式,郭沫若創造了一個“這么任性,這么激烈”的作為“人”的屈原。事實上,在這年初,郭沫若已經確立了“詩的創造是要創造‘人’”的創作觀念,⑥田壽昌、宗白華、郭沫若:《三葉集》,亞東圖書館,1920,第49 頁。對于創造屈原之“人”具有充分自覺。
除了前述直接從正面解構“忠君”,事實上,梁啟超在新文化運動后期對屈原進行了大量而頗具特色的詮釋,主要見于《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1920)、《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1922)、《屈原研究》(1922)、《要籍解題及其讀法》(1923)。其中有三個方面尤其顯著,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反對傳統“殉國說”(傳統“殉國說”的核心是“忠君”,與郭沫若等人在1930年代提出的“新殉國說”有本質區別),一般而多元地解釋屈原自殺。明清儒士將屈原自沉解釋為“殉國”、“殉社稷”,而不是因為抗爭、失望、痛苦等消極心態,以此作為“忠臣”屈原的重要支撐。梁啟超同樣提出,“研究屈原,應該拿他的自殺做出發點”,①梁啟超:《屈原研究》,《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華書局,2015,第55 頁。主旨卻與明清儒士針鋒相對。在詞語上,以一般意義的“自殺”代替了具有崇高意義的“殉國”等傳統詞語。梁提出了幾種說法,重新解釋屈原自殺。一是厭世,“屈子為極端厭世之人”,富有“厭世思想”。二是矛盾和苦悶,梁氏反復闡述屈原因矛盾而致的苦悶情感,如“其自殺之原因,乃感于人生問題之不能解決,不堪其苦悶”。這都是將“屈原”作為普通的“人”來看,讓屈原擁有正常“人”的情感——哪怕是消極的,深含解放屈原的意味。三是與“潔身說”類似的說法,認為屈原因“痛心疾首于人類之墮落”而死。②梁啟超:《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中華書局,2015,第1—39 頁。實際上,梁啟超對屈原自殺做了多種解釋,甚至顯得有些混亂,其意圖卻很明顯,旨在竭力避免傳統“殉國說”,打破建立在“殉國說”基礎上作為神一般的忠臣屈原,還屈原作為“人”的面目。
第二,改變屈原的關懷對象,以現代的“社會”代替傳統的“君”,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國家”。在傳統詮釋中,屈原的最高關懷對象是“君”,“忠君”是常見詞和主旨。但梁啟超早在1902年即開始從詞匯與價值層面做出改變,他當時接受的是自由、民主和現代國家觀念。而在《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屈原研究》這兩篇作品中,梁啟超幾乎完全拋棄傳統詞匯,同時,盡管也使用具有國家意義的“國難”、“祖國”、“國家”等概念(各使用1次),但使用更多的是超越國家意義的“社會”(23 次)、“人類”(2 次)、“世界”(3 次),尤以“社會”概念使用最為頻繁。③梁啟超:《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第1—39 頁;《屈原研究》,《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49—69 頁。梁啟超努力以大量新詞代替舊詞,意在說明,屈原不是忠君愛國的“臣”,而是一個“富于社會性的人”。④梁啟超:《屈原研究》,《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66 頁。事實上,“社會”與“個人”是一組不可分割的概念,談論“社會”時往往也在言說“個人”。有學者就注意到,梁啟超對社會和個人的提倡,或許還在陳獨秀、胡適等人之前,早在清末即提出相關意見,1915年時更明確說:“今日中國,凡百事業,與其望諸國家,不如望諸社會;與其望諸社會,又不如望諸個人。”①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第302 頁。比起“國家”,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梁啟超大概更重視“社會”和“個人”,這構成其屈原詮釋的思想背景。而且,《屈原研究》的大部分內容就是分析“屈原作品里頭體現出他的人格”,②梁啟超:《屈原研究》,《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67 頁。“人格”一詞也具有重要提示意義。
第三,暢談屈原的“個性”。郭沫若雖在《湘累》中刻畫了一位個性解放的屈原,但未明確以“個性”相稱。梁啟超則明確以“個性”來詮釋屈原。在《屈原研究》中,梁開篇便提出,“欲求表現個性的作品,頭一位就要研究屈原”。梁啟超認為,“屈原性格誠為極端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為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即以此。……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產此文學”,這其實是明確反駁大儒朱熹了。③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周刊:書報介紹副刊》第8 期,1924年1月。梁其實即點明了反駁對象,謂“司馬光謂屈原‘過于中庸,不可以訓’,故所作《通鑒》,削原事不載”。但將說“過于中庸”的人誤記為司馬光。朱、梁兩人都認識到屈原不合乎中庸之道,但評價截然相反。朱熹持否定態度,梁啟超卻高度肯定,強調屈原之“個性”對其文學的重要性。最有意思的是,梁將屈原與代表個人主義的易卜生相聯系,說“易卜生最喜歡講的一句話:All or nothing(要整個,不然寧可什么也沒有)。屈原正是這種見解”。④梁啟超:《屈原研究》,《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62 頁。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將屈原易卜生化了。質言之,梁啟超的大量詮釋,旨在建立一個作為“人”而非“忠臣”的新屈原,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屈原。
三 “偉人”身份的重建
當然,將屈原還原為“人”還是一個相對抽象的說法,因為屈原畢竟不是一般的“人”而已,他能夠傳揚兩千多年,也不單是因為他在憂憤中的自殉,還與他留下的不朽作品密不可分。那么,“忠臣”解構之后,屈原的具體身份應如何定位?新詮釋者提出了多個新指稱,其中,“文豪”、“詩人”、“文學家”是三個主要指稱。這就將屈原從政治國度轉移到文化國度,重新確立起他不同凡響的“偉人”地位。
如前所述,早在清末開始反叛傳統詮釋時,“文豪”、“詩人”已分別由梁啟超、王國維提出,稍后,“文學家”的指稱也開始使用。1903年,革命刊物《湖北學生界》上一篇名為《論支那文學與群治之關系》的文章,稱屈原“是支那愛國巨子亦文學家也”。①《論支那文學與群治之關系》,《湖北學生界》第5 期,1903年5月。“文學家”便是在替換“忠臣”的意義上使用。同期另一篇文章言“富于文學家之愛國心者,如屈原見放而作離騷”,也是將屈原視為文學家。②但燾:《黃梨洲》,《湖北學生界》第5 期,1903年5月。1912年的《中國國民的文學家》是較早以“文學家”入題的一篇文論,稱屈原為“我國最先的大文學家”。③《中國國民的文學家》,《少年雜志》第2 卷第5 號,1912年11月。至新文化運動時期,在深層解構“忠臣”屈原的同時,對新指稱的論述也越發集中和深入,接受和使用的人越趨廣泛,新指稱的使用也越加頻繁。關于“文豪”和“詩人”詮釋影響較大的,首推1916年謝無量《中國六大文豪》一書。謝氏以文學史的視野,從中國歷史上遴選出屈原、李白、杜甫等六位“足以代表一國之文學者”,稱譽為“六大文豪”。謝以屈原對后世的巨大影響為由,將其列為文豪之首,放在第一編進行論述(全書共六編,每人單成一編)。該書以“文豪”入題,又給予屈原顯要位置,很容易使人形成文豪屈原的深刻印象。
同時,謝無量重點詮釋了“詩人”概念。“屈原在文學上之價值”一章首先即提出了中心論點,“屈原者,古今愛國詩人之宗”,隨后從多方面進行具體論證,尤重復使用“古今愛國詩人之宗”一句,共計4 次,④謝無量:《中國六大文豪》,中華書局,1916,第7—14 頁。同樣使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謝氏詮釋出一位具有強烈“愛國精神”(當然是現代愛國精神)的屈原,這樣的屈原顯然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意味毫不下于傳統“忠臣”屈原,但謝所使用的指稱卻是文學性的“文豪”、“詩人”,且將屈原的價值完全視為“文學上之價值”。事實上,其中自覺避免“忠臣”等傳統概念,反叛與解構傳統詮釋的意味甚濃。另值一提的是,《中國六大文豪》最早發表在梁啟超任總撰述的《大中華》雜志,⑤謝無量:《中國六大文豪》,《大中華》1916年第3 期;《中國六大文豪(續)》,《大中華》1916年第9 期。同年由中華書局輯為單行本出版,至1933年發行第6 版,⑥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歷史·傳記·考古·地理)》(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第504 頁。頗能反映它受出版社和讀者的歡迎,為屈原作為文豪、詩人這樣一種新認知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可能。①胡懷琛《中國八大詩人》一書也具有相似的意義。該書以“詩人”入題,選取屈原、陶淵明等八位詩人,同樣將屈原作為中國詩人之首。該書其實從標題、體例、思路、措辭等方面均借鑒了謝無量《中國六大文豪》,也同樣是暢銷書,至1935年發行了第6 版,某種程度上而言,這是“詩人”屈原廣泛傳播的一個標志。見胡懷琛《中國八大詩人》,中華書局,1925,第1 頁。
新詮釋首先就影響到屈原與楚辭研究,促進相關研究在內容、方法、觀念的現代轉型,其中關于屈原的新定位多為“詩人”。另一個顯例是楚辭學研究新銳陸侃如。在1923年《屈原》一書中,陸氏開篇即將屈原定位為“中國最早的大詩人”。該書對屈原作為“詩人”的地位與影響進行了較多論述,如“我們再向后看看屈原以后五百年間的秦、漢文學。這一時期內的詩歌,可說全是受這位大詩人的影響”。②陸侃如:《屈原》,亞東圖書館,1923,第2、114—116 頁。稍后在《宋玉評傳》中,陸也多次論及“詩人”屈原,如“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優越的位置,是不用懷疑的。他是中國最早的大詩人”。③陸侃如:《宋玉》,亞東圖書館,1929,第19—20 頁。該書初稿于1923年12月脫稿。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陸同樣稱“大詩人屈原”。④陸侃如:《二南研究》,《國學論叢》第1 卷第1 號,1927年6月。事實上,1923年時,陸侃如年僅20 歲,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與其老師胡適交往密切)。從他的例子來看,通過出版、輿論和教育,有些青年學生對“新屈原”的接受與詮釋已經達到相當程度。
新詮釋也很快影響到范圍稍大的文學史的書寫,屈原的身份普遍被改寫,“詩人”也是常見指稱。比如鄭振鐸于1926年前后出版的《文學大綱》(共四大卷),這是中國較早的一部涵括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學史著作,其中一章專講“詩經與楚辭”,高度評價作為詩人的屈原:“屈原是《楚辭》中最偉大的一個作家……只有屈原是古代詩人中最有光榮之名的,最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一個。在中國上古文學史,要找出一個比他更偉大或可以與他比肩的詩人是不可能的。”“《楚辭》與《詩經》不同,它是詩人的創作,是詩人的理想的產品,是詩人自訴他的幽懷與愁郁。”⑤鄭振鐸:《文學大綱》第1 卷,商務印書館,1926,第295—296、314—315 頁。除了“詩人”,鄭振鐸也給屈原增加了“作家”的指稱。
“文學家”指稱的使用也很突出。比如,梁啟超在將屈原還原為“人”時,除了“文豪”,也基本將屈原定位為“文學家”,且對此反復詮釋。1921年《佛教之初輸入》說“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①梁啟超:《佛教之初輸入》,《改造》第3 卷第12 號,1921年8月。1922年9月《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其將來之責任》說:“在楚時,湖北發生一位大文學家之始祖,不獨在過去的文學界推他為第一,就是在現時數一數二,也恐怕無人勝過他。這位大文豪,就是屈原。”②《梁啟超在武大暑校講演紀》,《申報》1922年9月5日,第10 版。同年11月《屈原研究》開篇即說:“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1923年《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說:“屈原性格誠為極端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為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即以此。”在1927年前后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中,梁啟超更是數次論及。例如“屈原,人格偉大……又是文學家……在文學史上講他的地位是應該的”,“屈原和荷馬,兩個都是文學家”,“戰國作離騷等篇的屈原,確乎是有名的第一個文學家”。梁在其中提出為歷史上一百人作傳的設想,有思想家及其他學術家、政治家及其他事業家、文學家及其他藝術家三種類型,但特將屈原歸為文學家之列。③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商務印書館,1934,第71、87、142 頁。
事實上,這些學理論證和研究式的詮釋,使屈原“文豪”、“詩人”、“文學家”的新指稱能夠立得住腳。而且,相較于清末,以此三者指稱屈原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已是主流、慣常的做法。④新詮釋者之間也有觀念分歧,比如關于屈原是不是“愛國”就有爭議,但是,反傳統詮釋與“忠臣”屈原是他們的共同目標,在重新界定屈原時具有很強的一致性。這都意味著屈原詩人、文學家等新身份的基本定型,也意味著忠臣屈原的基本消解。還需特別指出的是,其中,除了謝無量、梁啟超、陸侃如等精英、專家群體外,還包括許多一般知識分子對新指稱的接受與使用(見表1),他們主要是一般青年、學生,甚至還有中學生,這相當值得注意。相比之下,謝無量等人多是以專著的形式,而他們詮釋的形式基本上是報刊文章。最大的區別是,精英的詮釋往往具有相對完整的思想形態和比較深入的學理論證,而一般人的詮釋則不那么完整、深入,他們多數只是抓住一些核心指稱、概念、詞語,并且往往具有比較明顯的模仿痕跡(精英其實成為一般人學習與模仿的對象,我們不難從一般人的詮釋中發現精英或明或暗的影子)。比如,朱維之《中國最早的文學家屈原》大量援引、化用了梁啟超的《屈原研究》,曹烜五《中國古代第一大詩人屈原》借鑒有陸侃如的《屈原》。沈志昂、龐翔勛、鄭杰、芳吉、汪蔚云均采用詩歌這種相對簡單的形式,重復使用“詩人”一詞,不脫空洞、單調之嫌,總體來看算不上上乘之作。

表1 1920年代一般知識分子使用新指稱舉例
但是,并不是說一般人這種抓取核心概念的做法和模仿沒有意義,正相反,實則其具有不容忽視的特殊意義。因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許多具有廣泛影響力和社會波及面的思想觀念的傳播,常常并非通過完整的思想形態和理論闡述文本,毋寧說是通過一系列乃至一個個似乎是孤立存在其實卻有各種關聯的詞語流通、潛移默化實現的。一般人并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這些詞語、概念所代表的知識和思想觀念的全部內容,同樣可以在通過閱讀、使用有關詞語與概念的無意識之中,接受一些片段的知識和傳播一種基本的價值觀念,參與推動一種社會思潮”。①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于“一般思想史”之認識》,《開放時代》2003年第4 期。一般人在擷取概念、詞語時并不隨意,他們往往選取的是自己認可的,且比較流行的,那么,被選取的概念、詞語便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而且,選取詞語、概念這個看似簡單的做法,卻是思想觀念廣泛傳播必不可少的過程。事實上,他們對核心概念比較敏銳,也善于利用,朱維之、曹烜五直接將“文學家”、“詩人”入題,沈志昂、龐翔勛、鄭杰、芳吉、汪蔚云則反復使用“詩人”一詞,以詩的形式來詮釋“詩人”,可謂很好地抓住了“詩人”概念。模仿這種可能被視為盲從的舉動,恰可以說明被模仿者的流行程度,而他們所模仿的正是新詮釋而非舊詮釋。應當說,朱維之等一般詮釋正是新屈原詮釋概念化、社會化、大眾化的主要形式和重要標志,更能深刻反映新屈原的定型和舊屈原的消解。
四 結語
清季民初,民族的危機與社會的動蕩此伏彼起,激發出新陳代謝的文化運動。屈原這一重要文化符號,必然要經受文化運動的考驗。傳統文化范疇內屈原形象是與王權相聯系的,被界定為“忠君”的“忠臣”。這一形象到清季開始受到質疑。新文化運動時期,伴隨著整理國故思潮的出現,流行千年的屈原“忠臣”形象被系統解構。②并不是說傳統詮釋詞匯就完全絕跡,少數人有時也繼續沿用“宗國”、“忠君愛國”、“忠臣”等詞,但使用頻率已經非常低,而且,基本僅在一般字面意義上使用,不再具備傳統詮釋的意識形態性。與此同時,屈原作為“人”,特別是作為文豪、詩人、文學家的“偉人”身份,被建構起來,實現了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這一案例再次印證,任何大型歷史運動都充滿復雜性。新文化運動并非絕對新舊割裂的“文化革命”,不能簡單以“全盤反傳統主義”或“全盤西化”蓋棺定論,它也包含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文化改良”內容。
當然,屈原形象的重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并未終結,到九一八事變后,民族主義思潮大興,屈原詩人身份被進一步結合民族國家意識建構,用“愛國”取代“忠君”,在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下恢復屈原在政治國度的角色,取得“偉大愛國詩人”的新身份,成為至今對屈原的經典評價方式。限于篇幅,這一階段的建構過程,擬另文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