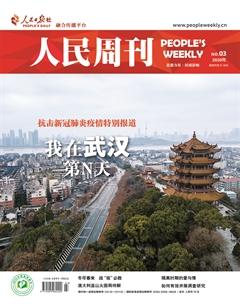鐘南山的家風
二水
要問這個春節出現在熱搜上最多的人是誰,應該非鐘南山莫屬。
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暴發初期,他一邊告訴公眾“盡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
他還曾多次前往北京,參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座談會,并第一個站出來直言疫情存在人傳人,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在他的主場——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他每天到醫院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專家組匯報省內重癥患者的病情,并逐一打電話詢問治療情況,給予臨床指導意見……
無論在廣州、武漢還是在北京,84歲的鐘南山一直為疫情奔走著。即使上了飛機,他也不肯休息,而是堅持工作,研究危重病人的治療方案,并認真地作記錄。
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在采訪中幾度哽咽,眼含淚光說:“全國幫忙,武漢是能夠過關的。”簡短的話語,成為老百姓心中的“定海神針”。
是什么樣的信念,讓這位年逾八旬的逆行者有自信和勇氣幫助武漢“過關”?又是怎樣的力量支撐著他毅然挑起千鈞重擔?
與妻子因體育結緣
鐘南山為疫情不停奔波的辛苦,妻子李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們能不能讓他多睡一會?”
但陪伴了鐘南山半個多世紀的她更深知,這個男人絕不會輕易下火線,“勸是勸不住的,因為他太在乎自己的病人了。”
李姨是周圍人對鐘南山妻子的稱呼,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叫李少芬,更鮮有人知她曾是籃球國手。
1952年,16歲的李少芬通過選拔成為中國女籃首批隊員之一。一年后,她隨隊參加在羅馬尼亞舉行的世界青年友誼運動會,那是她第一次參加國際大賽。可惜的是,女籃打得很糟糕。回到國內后,周恩來總理提出讓女籃姑娘們到蘇聯去學習球技。
在那之后的五年時間里,女籃每年都要在蘇聯訓練至少四五個月。除了訓練,她們還到東歐各個地方打比賽,以賽代練。
其間,謝晉導演拍攝了以女籃為原型的影片《女籃五號》,李少芬還曾在影片中客串過歡送“球員”的群眾。
漸漸地,李少芬的球技得到了提高,并成為國家隊的核心球員。因技術十分全面,場上的五個位置,她均可勝任。此外,她的中距離投籃十分精準,而且還是用單手跳投。
留蘇歸來后,李少芬和隊友們先后獲得了1963年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和1964年四國女籃賽的冠軍。
打出了成績的李少芬,自然成為其他國家球探相中的目標。一家由法國軍火商掌控的籃球俱樂部找到了她,“法國人當時給我開出了很高的薪水,還許諾帶我們一邊打比賽一邊周游世界。”但她拒絕了對方的邀請,一來是不想讓國家好不容易培養的體育人才流失,二來是她在當時已和鐘南山確定了戀愛關系。
鐘、李兩家原是世交,兩家家長是醫院的同事,但讓兩個年輕人真正走到一起的是體育。
1955年,鐘南山考入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醫療系,且成為一名田徑隊運動員。后來因為要參加全運會,為了加強訓練,他申請到訓練條件較好的國家隊訓練,這才有機會和同在北京訓練的李少芬熟絡起來。
自然而然,體育成為他們的共同話題,訓練場也成了他們的約會地點。
1963年底,李少芬與鐘南山在北京結婚。兩人的婚禮簡單而樸素,沒有婚紗和禮服,連婚房也是體委安排的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面除了一張床和簡單的家居用品,再無下腳的地方,但李少芬對此毫無怨言,與鐘南山過著幸福的日子。
1966年,李少芬從國家隊退役。本可以留京做教練的她,因考慮到公婆無人照料,主動提出回到廣東隊繼續打球。
直到1973年,38歲的李少芬正式告別運動員生涯,此后又擔任廣東女籃教練、中國籃協副主席等職務。1999年,她被選為新中國籃球運動員50杰之一。
如今,鐘南山和李少芬的子女也繼承了他們的衣缽。兒子鐘惟德做了一名醫生,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泌尿科主任醫師、國家級百千萬人才,同時也是醫院籃球隊的主力;女兒鐘惟月則繼承了優秀的運動基因,成為一名游泳運動員,獲得過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100米蝶泳冠軍,還曾在1994年打破短池蝶泳世界紀錄。
這樣一家子,唯有用“強悍”來形容了……

“在我的生活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父親”
名滿天下的鐘南山為人卻十分謙虛,常常說:“我不過就是一個大夫。”而這正源于他從父親那里繼承的醫術仁心。
鐘南山的父親鐘世藩是我國著名兒科專家,曾被世界衛生組織聘為醫學顧問。
當年,21歲的鐘世藩考入中國醫學界最高學府——北京協和醫學院。經過8年的專業深造,他在博士畢業后留校當了一名兒科醫生(同期入學的40人只有8人順利畢業)。
1946年,已在醫學界頗有名氣的鐘世藩被任命為廣州中央醫院(現廣東省人民醫院)院長,同時兼任兒科主任。
3年后,正值新中國成立前夕,蔣介石政府敗逃臺灣,想帶著鐘世藩等眾多醫學專家一起撤離。面對國民政府的威逼利誘,這位一身正氣的醫生不為所動,冒著生命危險拒絕前往臺灣,選擇留在大陸。
20世紀50年代,鐘世藩首創兒科病毒實驗室,這也是我國當時規格最高的臨床病毒實驗室。此前,他都是自費買小白鼠在自家頂樓做實驗,兒子鐘南山的醫學啟蒙就是從那里開始的。
除了做病毒研究,鐘世藩還堅持在每周二一早進行主任查房。在查房過程中,他會不時地向年輕醫生們提問。為了應對他的提問,醫生們會在查房前一天晚上開夜車跑圖書館查資料,還要找時間親自動手為患兒化驗檢查。
其實,鐘世藩的目的不是為了考倒醫生,而是希望年輕人能夠重視基本技能,不僅要動口,還要動手。他還要求,醫生的病例記錄要字跡端正,清楚易懂,匯報病情時必須脫稿,倒背如流。時至今日,這個查房傳統仍在延續著。
鐘世藩踏實勤懇的科研及工作作風、對待病人的親切態度,讓兒子鐘南山耳濡目染。
在鐘南山的記憶中,父親永遠是孜孜不倦、勤奮好學的人。鐘世藩晚年時,因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導致視力急劇下降,看東西非常費力。可他心系我國兒科診斷水平,即便是在眼疾非常嚴重的情況下,老人家堅持用一只手捂著一只眼睛,另一只手查閱大量國內外兒科資料,并結合自己幾十年的臨床經驗,歷時四年寫出了《兒科疾病鑒別診斷》。因考慮到許多基層醫生文化程度偏低,他在書中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文字。

鐘南山(后排右一)與家人的合影
鐘南山很心疼父親,勸父親說:“你年紀這么大了,寫得這么辛苦,就不要寫了吧!”父親一口回絕:“不要寫讓我干什么?讓我等死嗎?”
該書出版后,反響空前,一連加印了6版,被廣泛刊發給全國基層醫院。后來,鐘世藩得到1500元稿費,卻絲毫不留,拿出700元給了幫自己抄書的一位醫生,剩下的800元則用來幫助他人。
1987年,鐘世藩臨終前還在和鐘南山討論病毒相關的專業話題,并囑咐他,自己死后千萬不要開追悼會,節約大家的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可以說,父親的言行為鐘南山樹立了一生的榜樣:“在我的生活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父親鐘世藩。”
一家走出八位醫學專家
與父親鐘世藩相比,母親廖月琴及其家族的故事更具傳奇色彩。
廖月琴是國內護理學專家,也畢業于協和醫學院,曾被當時的衛生署派到美國波士頓學習高級護理。新中國成立后,她擔任過現中山醫科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是廣東省腫瘤醫院創始人之一。
廖月琴剛當副院長的那段期間,鐘南山常看見她去上夜校,讀的書也都是關于解剖、腫瘤的。鐘南山問母親學這些干嗎,當時已經50歲的廖月琴說,自己既然當了腫瘤醫院的領導,總不能連腫瘤是什么都不知道。
令人惋惜的是,廖月琴在“文革”期間不幸去世,離世時才56歲。
而從廖家走出來的醫學專家,不只廖月琴一位。
鐘南山的大姨媽廖素琴是上海第一醫院營養室主任,她的丈夫戴天佑是著名的肺科專家。他們的兒子,也就是鐘南山的表哥戴尅戎,是骨科生物力學專家,也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鐘南山的舅舅廖永廉是原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博士,回鼓浪嶼后成為廈門第二醫院內科主任,曾在1957年發現福建省第一例鉤端螺旋體病。他的妻子陳錦彩也是學習護理出身,參加過“八·一三淞滬會戰”戰地救護工作。待人熱情的陳錦彩一生熱心于鼓浪嶼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務和鄰里紅白事,大家都親切地稱她“廖醫生娘”。
也許是命中注定,廖氏家族中單是廖月琴這一系就有8位醫生,而且個個都在醫學界頗有建樹,這才是實至名歸的“醫學世家”!
最近幾年,人們經常討論何為名門。真正的名門,不是家財萬貫揮金如土,而是代際沿襲的精神財富,擔當國民棟梁的格局和能力。
鐘南山的家人們,正是從自己的家庭中汲取到無窮的力量與勇氣,并反哺于他們深愛的小家和大家。
父親曾對鐘南山說:“一個人,要在世界上留下點東西,那他在世界上就不算白活了。”如今,鐘南山對自己的后代說:“鐘家優良傳統有兩個,第一就是要永遠有執著的追求;第二是辦事要嚴謹,要實在。”
他們對后代的寄語,讓我們了解到一個人的成功與其良好的家風密不可分。
鐘南山繼承了父輩良好的家風,傳承了下去,并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子女在自己的崗位上為祖國和人民奉獻力量。
今年的春節有些不一樣。正是因為有這些舍小家為大家的人們,保護著中華民族這個大家,我們才能安穩度日。謝謝你們!
(環球人物微信公眾號2020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