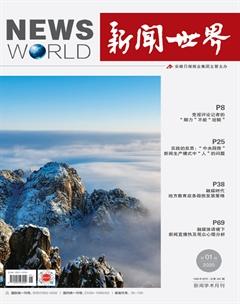“加標簽”對青年群體朋友圈自我呈現的影響
嚴嘉悅
【摘 ? ?要】微信朋友圈作為一個依賴好友關系建立起來的網絡平臺,形成了以“我”為中心的展演舞臺,“好友”即觀眾在展演過程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依靠“標簽”功能對“好友”進行關系定義和分類,更豐富了“我”在該網絡平臺的展演方式。通過對“朋友圈”主要使用者——青年群體的展演行為進行分析認為,面對不同的觀眾,其存在不同的展演行為,該過程存在“自我中心”向“他者中心”轉化的展演邏輯。
【關鍵詞】朋友圈;好友標簽;自我呈現
雪莉·特克爾認為:“青少年在Facebook上呈現出‘精致的自己,但同時這種精心設計的‘自我也帶來焦慮……我們對科技的期待越來越多,對彼此的期待卻越來越少,網絡促使我們處于‘群體性孤獨的狀態。”[1]由此觀之,青年作為微信用戶的主力軍越來越少發布朋友圈,甚至使用“三天可見”的功能來管理以往動態,與先前網絡上的自我呈現相比,青年用戶的微信朋友圈樣態正在變得更加復雜。本文依據戈夫曼的擬劇理論,結合相關網絡與自我呈現研究,運用深度訪談法,主要考察微信“好友系統”如何影響青年群體的網絡自我呈現。
一、朋友圈:作為舞臺的展演空間
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認為個人在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均為一種符號化的表達,該理論涉及“前臺”和“后臺”、“給予”和“流露”多個概念,又被稱為“印象管理”。董晨宇等將其主要概念運用于互聯網,認為該理論在互聯網中表現為具體語境的坍塌、“給予”的強化和“流露”的弱化、對觀眾的想象和隔離、以及網絡呈現模式化為一種以“物”來彰顯品位的展演方式。[2]
與其他社交媒體如微博、Facebook、Twitter等不同,微信作為以“我”為中心,輻射出好友系統的“強關系”平臺,在用戶關系上具有很強的聯結性,這與它的第一功能——信息溝通,相輔相成。仰賴“強關系”搭建起來的朋友圈承載著用戶的自我呈現,這種網絡上的日常展演包括使用文字、圖片、視頻進行表達,其他用戶也通過這種展演來補充對“我”的認識。
在這樣的表演環境中,“后臺”被無限放大,“前臺”被壓縮。向屏幕外不斷延伸的“后臺”讓使用者有更多的時間、更豐富的技術手段來對想展演的文字、圖片進行編輯,展現更趨于“精心設計的自我”;不僅如此,“前臺”的壓縮還表現在展演方式的弱化上。文字、圖片更多的是一種文本和符號的展演,缺少文本背后如神態、動作等的展現,即使是視頻,受發布時長的限制,使用者可以將想要被看見的部分篩選出來,剪輯掉不想展演的內容。在這樣的展演邏輯下,用戶有更多的空間來進行“印象管理”。
正如戈夫曼所言:“每一個人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是由他人(社會)的期待來限定的。”[3]互聯網中的呈現也是一個自我扮演和觀眾期待的協調過程,朋友圈中個人化的表達,受制于表演者如何想象屏幕背后的觀眾,并以此為依據呈現和調整自己的表演行為。
二、標簽:一種觀眾篩選和觀眾隔離策略
與費孝通描述的鄉土社會的結構相似,微信作為一種熟人社交,呈現出以“我”為中心,熟悉程度依次遞減的關系結構。作為觀眾的好友被“標簽化”,用戶可以使用“給”/“不給”某個分組的標簽觀看朋友圈,形成了觀眾篩選和隔離的作用。“標簽”這一功能不僅實現了對好友結構的分類,更與用戶在朋友圈的自我呈現行為直接相關。
微信的“朋友”可以按照與“我”的親疏關系進行簡單概括。但由于微信好友的添加方式是基于面對面,或者熟人的推薦,即使是“不熟的人”,也或多或少與“我”有著關系聯結。由此,微信好友呈現出相對的“強關系”結構,好友與“我”之間存在著關系的親疏差別。一般而言,用戶會按照社會角色將好友進行分類,涵蓋家人、親戚、同學、同事、老師等。
但這樣的分類方式并非是一成不變的。首先,關系的分類存在交叉和重合,某個觀眾可能出現在“我”不同的生活階段,擁有多個“身份標簽”。其次,這種關系具有流動性,隨著與某個好友關系增進或疏遠的變化,也存在著“標簽”的調整。由此,關系,更多的是親疏關系,決定了“我”在朋友圈展演的種種邏輯。
三、形象:基于親疏關系的自我呈現
Michikyan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年輕人在網絡中會呈現出不同的‘自我,包括‘真實自我、‘理想自我和‘消極自我。”[4]年輕人在朋友圈中展現出來的“自我”也并非完全統一的。本文隨機選取10位18-30歲的年輕人進行深度訪談后認為,其展現出的“自我”與“標簽”背后的觀眾有著很大的關聯。
(一)“安全的形象”而非“精心設計的自我”
一些研究認為,用戶會在朋友圈精心編輯圖片、設計文案,展現一個“精心設計的自我”,以此來維持自己在朋友心目中的精致形象。如雪莉·特克爾所述:“即便他試圖在Facebook上表現得‘誠實,也不能抗拒利用網站為自己盡量‘打造好形象的誘惑。”[5]
但事實發生了一些變化,多數受訪者表示:與以往相比,自己越來越不愿意在朋友圈發精心編輯的內容,反而更喜歡發一些輕松、日常的內容。“我把這樣的內容定義為‘無害的,這種浮光掠影的呈現使我覺得‘很安全(受訪者A)”;“我現在很少花精力去把朋友圈包裝得很精細,認為沒有必要(受訪者B)”。
相比經營朋友圈,這種日常而“安全的形象”變得更受年輕人的青睞。這種“安全”還體現在:屏蔽“此時此刻的社交關系”,即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在發朋友圈時會選擇屏蔽掉現在與“我”有關的人群。由于這些觀眾此刻與“我”休戚相關,所以更加需要去呈現一個“安全的形象”。同時,這種“安全”心理一定程度上也在消解自我展演的頻率和熱情:“一想到我發的朋友圈要設置麻煩的分組和屏蔽,我就懶得發了(受訪者C)。”
(二)面對“陌生人”:一種可有可無的呈現
這里的“陌生人”可以定義為:因為某種機緣巧合而短暫有過接觸的“好友關系”,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既沒有更多的聯系,也不太可能見面的人群。對于這類人群,受訪者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表演方式:一種是采取完全的“觀眾隔離”策略,用戶表示會“不讓這些人看我全部的朋友圈”。這是由于比較陌生的“弱關系”侵入了“強關系”的好友平臺,“我”選擇不對這些“陌生觀眾”進行任何表演;另一種是采取“漠不關心”的策略,表示“完全不會屏蔽這些人”,他們扮演了一種可有可無的“陌生人”角色,與現實中的“我”聯系十分稀疏,無論他們如何認知“我”,都不會對“我”的現實生活產生影響。基于此,“陌生人”扮演了一種可有可無的角色,用戶并不會特意去進行“自我印象管理”。
(三)“線上”親密關系:一種相對真實的情感呈現
親密關系在“我”的網絡表演中作為一種相當重要的觀眾而存在,受訪者紛紛表示有一個“標簽”專門設置為“關系好的人”,這一部分人群能夠看到“我”幾乎所有的朋友圈,在面對這類“標簽”的人群進行網絡自我呈現時,用戶更傾向于發布上述“安全的朋友圈”外的內容。例如相比于日常生活的白描,更多側重情感敘述。“有時候我會發一些很‘喪的內容,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見(受訪者D)”;“很多承載深度情感的朋友圈只有跟我關系好的人能看到(受訪者E)”。與需要“安全展演”的觀眾不同,關系親密的好友因為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觸更加頻繁,更了解我們,因此對這部分觀眾的自我呈現并非“安全”的“浮光掠影”,而是一定程度上的情感真實。
與此相反,“家人”這一日常交流頻繁、情感關系親密的人群卻總是被排除在“我”的朋友圈以外,甚至對這部分人群采取了完全的“觀眾隔離”。究其原因,家人作為朋友圈的觀眾往往不認為個體在進行一種展演,他們把從朋友圈獲得信息等同于真實的“我”,這與朋友圈情境下的呈現相沖突,因此經常被隔絕在觀眾之外。
結語
仰賴封閉的“好友系統”,微信形成了一種以“我”為中心,擴散出去的圈子,觀眾作為一種他者參與“我”朋友圈的展演。在展演過程中,個體首先以“自我”為中心進行展演內容的選擇,而此時的展演過程并未完成,需考慮到屏幕背后的觀眾接受程度,以此來調整自己的展演行為。這一過程從“自我中心”向“他者中心”進行轉移,觀眾在“我”的呈現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親疏關系直接影響了個體的展演方式。為朋友加上“標簽”,不僅僅定義了關系類型,也直接決定了個體的展演行為和展演邏輯。
注釋:
[1][5]雪莉·特克爾.群體性孤獨[M]. 周逵,劉菁荊 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2]董晨宇,丁依然.當戈夫曼遇到互聯網——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與表演[J].新聞與寫作,2018(01):56-62.
[3]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M]. 馮鋼 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Minas Michikyan,&Jessica Dennis &Kaveri Subrahmanyam.Can You Guess Who I Am? Real, Ideal,and False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Among Emerging Adults[J].Emerging Adulthood,2015,3(1):55-64.
(作者: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