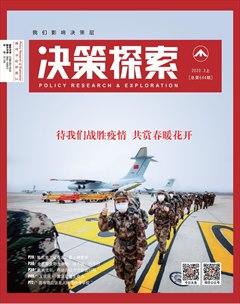磚雕門樓里的家風故事
陸士虎


清晨,旭日再一次鍍亮江南古鎮南潯。
頔塘(古運河)水宛如一道柔軟的綠綢環抱著古鎮,江南名園小蓮莊荷花迎著朝霞綻放,嘉業堂藏書樓里的古籍默默不語。霞光中,輕紗般的霧帳,給南潯抹上了一片水晶晶的秋色。
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潯古老的石板路上,串街走巷,尋根溯源,仿佛回到那發黃的方志所記載的崢嶸歲月。1842年,上海被辟為通商口岸以后,聰慧的南潯人憑借名甲天下的“輯里湖絲”,從家鄉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灘,與洋人做生意,涌現了一批巨富大賈,俗稱“四象八牛”,是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群體。這些名門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當我跨入一座座名門宅第,抬頭凝視著一座座磚雕門樓,仿佛與那些身穿長袍馬褂或西裝革履的先賢會晤,聆聽他們敘說百年滄桑的家風故事。
建筑雕刻可分為木雕、磚雕、石雕等,木頭與石頭是人類最早使用的兩種材料,人們對它有一種親切感;陶磚雖是人造物,但它是水、土和火的結晶,是人類最早的發明之一。用這些材料進行雕刻,其本身就是通過藝術注入生命,帶著人的情感。江南建筑如此,南潯也不例外。
南潯的宅第大多是多進式建筑,每一進都由磚墻隔離,每道磚墻都有墻門。墻門主要以磚、木、石為材料,平常人家一般采用木頭作門框,大戶人家則用石頭作門框,故稱為石庫墻門。石庫墻門內外一般都有磚雕裝飾,也有的只在門內或門外一面,俗稱磚雕門樓。
這些磚雕門樓上都刻有寓意深遠、造型生動、工藝精湛的圖案,且有醒目題詞。這些題詞,往往寄托了主人的思想理念、人生追求、治家宗旨等,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是主人的家訓或家風。如民國元老張靜江故居的“世守西銘”“有容乃大”,近代儒商名士張石銘舊居的“世德作求”“藍田毓秀”,近代著名書畫收藏家龐萊臣的“世澤遺安”“厚德載福”,民國北派畫壇領軍人物金家的“永建乃家”“心地芝蘭”,上海新世界主人邱家的“唯適之安”等,字里行間無不閃爍著主人對家庭和后代的企盼、祝愿及訓導、警示。
這些門樓上的題詞,有的來源于古代典故,有的是名人格言警句,有的是主人治家報國的座右銘,言簡意深,內涵豐厚。
經歷上百年的風雨,南潯不少門樓已經破損,甚至消失(有的門樓正在修復),僅僅是銘刻在歷史記憶中了。所幸這些人家的家訓家規家風還在,他們的后代子孫傳承和弘揚好家風的精神還在。
劉家孫子滿月不擺酒
劉鏞白手起家,憑著勤勞和智慧成為南潯“四象”之首富。按一般人的想象,這日子不知道該如何穿金戴銀、花天酒地了。恰恰相反,劉鏞對世道、對自己始終都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劉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積德而來的,自己沒有理由暴殄天物。平時生活很節儉,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吃飯時要吃完碗里最后一粒米的習慣。如果碗外粘了一粒米,一定要用手拈來放進嘴里,并且要求家人也這么做。他雖然很節儉,但卻花費巨資為祖宗建家廟、為家族辦義莊、為子孫辦私塾,自己并沒有留下什么豪宅。
劉鏞有著強烈的“惜福”“辟邪”觀念,時時以當年的艱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訓自勵,不愿過多地享受,而寧愿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賑災,多次獲得朝廷及地方的嘉獎。
他曾對兒子說:“天之予人福澤至不齊也,有以鐘愛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謹身節用,則一勺之福亦可以久延;縱欲妄為,雖盈鐘之福,一覆而立盡。世之暴殄者多夭,撙節者多壽。以吾所見,歷歷不爽……豈得謂天道無知乎?吾生平于飲食、服御均不求精美,明知區區者不足以傾吾家,誠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縱欲也。吾少也貧,親歷艱難,故事事不敢逾份。汝曹生時境已豐裕,夫豈知祖父艱難積累而始有今日耶?”據《先考通奉府君年譜》記載,他常常告誡兒孫勿忘昔日之艱辛,勿忘祖先的恩德,要小心處世,凡事不可過分。
劉鏞的第一個孫子劉承干生下來之后,全家人對這個長孫視為掌上明珠,準備滿月時大大慶祝一番。劉鏞卻出乎意料地說:“滿月酒不擺了,這錢用于賑災吧!”
眾人嘩然,但又不好直說。
聞此消息,長子劉安瀾的岳父邱仙槎、劉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趕來勸說劉鏞。
劉鏞搖搖頭,長嘆一聲道:“我是從一把尺起家的,從一把尺上看到財富的誘惑,嘗試著去掙一點錢,沒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禍,是禍躲不過……為子孫造福,我不愿鋪張浪費,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輩們不要太奢華……”
有了孫子劉承干后,劉鏞的募捐義舉更大方了,捐資賑災不計其數。但他對自己仍十分節儉,患有胃病,卻不診治,直到晚年時才在家人的勸告下服些補品。
張家“世德作求”的注解
南潯“四象”之張氏一門,走出了兩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毀家紓難資助孫中山革命的“民國奇人”張靜江,一位是帶著山海般的財富走向市場和書齋,最終成為傳統商人和文化人的張石銘。
張石銘(1871—1928年),名鈞衡,字石銘,號適園主人。他和張靜江都是張頌賢(字竹齋)的孫子。其父張寶慶(字質甫)是張頌賢的長子,張石銘是張寶慶的獨子,故為張頌賢的長子長孫。可惜他父親體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綿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繆荃孫《張封公家傳》)。那時張石銘才16歲,南恒和的大小家事仍由母親桂太夫人掌握。1903年分家時,32歲的他獨自繼承了大房的全部遺產,身價上千萬,這就使他收藏書畫、建造園林大宅和興辦工商實體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張石銘舊居正廳上懸掛著清末狀元張謇所書“懿德堂”匾額。“懿德堂”的由來,說的是張石銘對母親十分孝敬,遵循古訓“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還有一副抱柱聯“羅浮括倉神仙所宅,圖書金石作述之林”,是清末宣統皇帝的老師鄭孝胥所書,上聯是說張氏舊居的建筑很豪華、精致,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樣;下聯贊許張氏的人生愛好,金石、碑刻、藏書無所不能。花廳正上方懸掛著“以適其志”匾額(現為仿制品),為康有為所書,出自張翰(字季鷹,江蘇松江人,西晉文學家,齊王執政時任大司馬)“人生貴得適志”之意。其時皇叔爭權,禍難不斷,史稱“八王之亂”。張翰預見齊王將敗,推托思莼羹,鱸魚燴,即回故土。不久,齊王被殺。
父親的遺言,從此銘刻在顧乾麟心上,成為他人生的坐標。因家境所迫,他不得已中斷學業,進入顧氏家族的怡和公司工作。為了更好地子承父業,在經營企業方面缺乏經驗的他決定從基層做起,從粗活干起,名義上是“見習經理”,實際上只是一名練習生,月薪僅20元。每日過磅棉花、廢絲、牛皮和羊皮,身兼學徒、賬房、倉庫保管員和經理等職。經過十余年打拼,中落的家業終于得以重振。
1939年,已成為怡和公司總經理的顧乾麟看到,日軍的侵華戰爭使上海物價飛漲,不少成績優異的中學生因家境貧困無力繼續升學,自己所在的怡和公司打包廠只想招5名實習生,竟然收到200多份申請書。這些求職者,大多數是因為付不起學費而輟學的孩子,其中有許多成績很優秀的學生。想到自己當年有過同樣的失學之痛苦,再聯想到父親臨終前的囑咐,顧乾麟決定遵循父親“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遺訓,以父親的名字在上海創立了“叔蘋獎學金”,專門資助那些身陷窘境的貧困學子。
“叔蘋獎學金”除資助貧困學生全部學費和書雜費外,對學習成績特別優秀的學生還資助膳宿費。此外,得獎學生還可在指定診所享受免費醫療,在專門為他們設立的校外活動中心借閱圖書,做物理、化學實驗,學習打字、速記、護理、縫紉等技能,以及組織文化娛樂、體育、參觀游覽活動等,使他們獲得了在當時學校教育中得不到的、比較全面的教育和鍛煉。中學畢業升入大學、大學畢業出國深造的優秀得獎學生,可繼續獲得獎學金和資助。從1939年至1949年十年間,“叔蘋獎學金”共舉辦二十期,資助貧苦學生達1100多人。
20世紀50年代中期,因某些歷史原因,獎學金被迫中斷。到1986年,顧老先生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又在上海恢復了中斷30多年的“叔蘋獎學金”,繼而又將獎學金擴展到北京和南潯等地,形成從中學、師范、大專院校到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獎學金系列化。
為使“叔蘋獎學金”持久地辦下去,顧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著在上海出席市政協七屆四次會議的機會,在上海錦江飯店委托叔蘋同學會的宗必澤口述關于“叔蘋獎學金事業繼承人”的遺囑,指定次子顧家麒(浙江省政協委員、著名外科醫生)作為繼承人。1995年,顧乾麟先生又慨捐港幣1000萬元作為增補獎學基金之用。目前,“叔蘋獎學金”已成為我國私人創辦歷史最長、受獎學生最多、設置學校最廣的獎學金。
顧乾麟并不是頂級富豪,在上海他只是略有資產,在香港更只能算小富而已,卻傾心盡力踐行父親“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遺訓捐資助學,令人欽佩敬仰。為此,顧乾麟本人過著簡樸的生活,自己和家庭開支甚為節儉。曾在香港為顧乾麟夫婦保健治療的董元吉(“叔蘋獎學金”第8期得獎同學)回憶過這樣的細節:顧乾麟先生平時在家用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極普通的家常菜,兩葷兩素一湯,到香港后60余年一如既往。1986年,董元吉發現他的一套深綠色西裝褲腿前面有個黃豆大的破洞,提醒他不要穿了,顧先生回答說:“我已經70多歲了,還買啥新西裝,馬馬虎虎,省省算了。”
我坐在大橋下的小亭里,小船的櫓槳聲把我從歷史的記憶里拉回。眼前的古鎮南潯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下,讓我回到童年,只是常給我講“四象八牛”傳奇故事的老母親早已不在了,但那些南潯的老家風依然清晰可見,那些傳承和弘揚家訓家風的精神仍綿延不絕。今天,我們重拾這份傳統精神力量,深入挖掘和整理家訓家規家風的寶貴遺存,充分激發“最美家庭”的乘數效應,無疑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