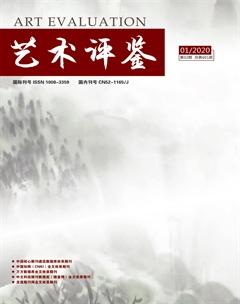宋代翎毛畫與17世紀西方飛禽畫創作思想之比較
高飛
摘要:宋代翎毛畫追求生動活潑,而17世紀的西方飛禽畫則追求寫實逼真,二者同為追求真,但一個追求生動,一個直面死亡,本文試圖通過分析二者的文化背景來闡釋東西方審美的差異性。特別從東西方的宇宙中心觀和生死觀兩方面進行闡述,強調東方的以人為中心和西方的以神為中心,以及東方的對于生的追求和西方的對于死的思考。
關鍵詞:翎毛? 飛禽? 生? 死
中圖分類號:J20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02-0025-03
一、起源與概念界定
中國翎毛畫的起源可追溯到石器時代的《罐魚石斧圖》,而西方的飛禽畫最早則出現在公元4世紀時期的龐貝壁畫中。本文將翎毛畫界定為宋代花鳥畫中的翎毛畫,即包含鳥類禽類的花鳥畫。將飛禽畫則界定為17世紀西方靜物畫中的飛禽類繪畫,即包含鳥類禽類的靜物畫等。花鳥畫作為獨立的學科,是在唐代確立起來的,卻是在宋代開始繁榮起來。以宋代院體畫為代表的花鳥畫,追求生動形象,富貴華麗,可謂開創了花鳥畫的一個新的高峰。并且,花鳥畫中的鳥類,即翎毛,是最為常見的題材之一,且活潑靈動,仿佛真實的鳥兒躍然于畫紙之上,給人以真實而美的享受。靜物畫形成于 16 世紀后期,不同時期和流派的靜物畫呈現出不同的題材取向,西方經典靜物畫以 17 世紀的荷蘭最具成就。 [1]以荷蘭畫家為代表的靜物畫中出現了大量的獵物,其中包括死去的天鵝、鷓鴣、鸚鵡、野生飛禽等。這些死去的飛禽有胸口淌著血的、有雙腳用繩子緊繃倒掛于墻上的,也有扭曲著脖子被攤在餐桌上的,畫面充斥著凝重、厚實、沉穩的氣息。一個生機勃勃,一個沉重憂郁,因此本文將宋代翎毛畫與17世紀西方靜物畫中的飛禽畫相比較頗具代表性。
中國畫中的花鳥畫常與西方靜物畫中的花卉禽鳥相類比,同時花卉與禽鳥作為繪畫題材,東西方在表現方式上呈現出迥異的風格。本文由藝術面貌的差異反推其藝術創作思想的差異,特別從宇宙中心觀和生死觀兩方面將二者在創作思想上的異同點予以簡略探討。
二、宇宙中心觀比較
宋代完成了儒學復興,產生了新儒學。“理氣論”是宋代新儒學中重要的哲學問題。而這里的“理”,主要是規律的意思,以“理”為宇宙本根,是事物之根本。理學家說明了宇宙天地萬物能夠生成的原因是“理”,畫家描繪自然萬物也就必須知其“理”。雖然說宋代理學家對“理氣論”的詮釋最終是為了給儒家倫理道德學說找到了宇宙本體論上的理論基礎,但是對“理”的提倡,講求致知,窮理對繪畫美學產生的影響是重要的。
在中國的理學思想中是不存在鬼神的,沒有西方宗教中對于上帝的崇拜,理學思想討論的內容始終是以“人”為中心的,例如人的道德、人格、修養等。以“人”為中心的中國理學思想塑造的世界觀強調,“理”是外在于人的“無限存在”,但人是極其短暫的“有限存在”。人們能夠掌控的僅僅是有限的幾十年的時間,這短暫的生命對于高于自己有限生命的“無限存在”顯得極其渺小。“死亡”亦是高于人有限生命的“無限存在”。因此,宋人恐懼對于死亡的無知以及對于死亡的無法掌控。然而正是因為生命的短暫和美好,人們極力地謳歌生命的偉大和奇妙。在歷史的長河中,每一個短暫的生命都為這無限的歷史長河增添了幾分絢麗的色彩,因此宋人筆下的花鳥是豐富多彩的,是生機勃勃的。如宋徽宗的《芙蓉錦雞圖》,畫中的錦雞羽毛光滑鮮亮,眼睛望向上角的一對正在嬉戲的彩蝶。錦雞似乎被對面的一雙蝴蝶緊緊地吸引著,眼睛炯炯有神,仿佛呼之欲出。以人為中心的中國理學思想,強調生命正因為短暫易逝而顯得格外美好,宋人筆下的翎毛更是漫漫歷史長河中短暫而絢麗的顏色。
而西方文化中,特別是在基督教影響下的文化是以神為中心的。顯然,神是超越時間限制的不會死亡的存在。更加關鍵的是,基督教中的神可以使人因為信靠神而進入永恒的生命中,也就是說人可以永遠不死,因此,在基督教影響下的西方文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而絲毫不必避諱談論關于“死”的問題。恰恰相反,基督教強調只有正視死亡才是一個人獲得新生命的開始,正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時,以神為中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強調世界是上帝創造的,萬物本來的形狀和特性就是最好的,人們無需改變什么,接受上帝所創造的一切,包括枯萎、凋謝、饑餓和死亡。[2]在畫面上真實地再現生命循環的規律,便是對創造者和受造物最大的尊重。
靜物畫創作中的藝術觀念的表達,既是特定歷史時期社會趣味的一種反映,同時也是作為創作主體的藝術家的一種個人行為。傳統的靜物畫基本上以體現某種宗教和人文精神為內核。[2]17世紀的西方剛剛經歷過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藝術觀念也開始改變。藝術家們從原來的對死亡的懼怕,變為堅信死后有一個更加令人向往的天堂,因此才能夠更加從容地面對死亡,直視出現在畫面中的各類枯萎凋零的生命,表現在繪畫題材上,則是出現了一大批描繪餐桌上的死去的飛禽等死亡動物的繪畫題材。如威廉·范·埃爾斯特的作品《雞與兔》,描繪的是倒掛于墻上的野雞和兔子。
以人為中心的理宋代學思想與以神為中心的西方宗教思想,墊定了中西方不同的宇宙中心觀的差異。中國生活一直遵循著經驗性的倫理道德規范,西方生活始終圍繞著宗教,以致雙方繪畫走向不同的方向,呈現不同的繪畫面貌。[3]
三、生死觀比較
以人為中心的宋代文化認為,人終有一死,死亡意味著生命的終結。中國歷史上對于死人名字的禁忌一直存在,因為缺乏科學知識,通常把死亡視為恐怖的、神秘的。死亡在宋代文化中被視為禁忌,因此在訃告中通常不會直接提及死亡,而是會使用隱喻或者委婉語進行替代[4]。中國的避諱文化,便對死亡避而不談,以此削減因死亡而產生的恐懼。中國人不僅忌諱談死,也忌諱在畫面上表現死亡的東西。因此在宋代翎毛畫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死去的鳥類,都是充滿生機,活潑靈動的禽鳥,它們或活躍在枝頭,或戲玩于叢中,或展翅于高空,時而銜著果蟲,時而飲于湖水。因此,宋代的翎毛畫是充滿生機的,是鮮活生動的,是禽鳥最真實的生活記錄,每一幅畫都像是在自然界抓拍的一個場景。因此,宋代文化基于對死亡的避諱,以及對生命力的追求,誕生了一批批優秀的栩栩如生的宋代工筆花鳥畫。
而在西方的靜物畫中,特別是16世紀中后期,靜物畫逐漸完善起來,象征和寓意成為主角。如在花卉或者水果的構圖中放上頭骨,代表生與死的對立,有時則更微妙,如水果的金黃色表皮上的疵痕、玫瑰花上落下的一片花瓣、正被火燒盡的蠟燭等等,畫家們時常關注那些象征生命和美稍縱即逝寓意的物像。以荷蘭靜物畫為代表,出現大量的死去的鳥類、兔子等動物,這些動物的表情真實地反映著死亡的氣息和面貌,畫家不再刻意美化黑暗、血腥的畫面,而是真實的表達。出現在這一時期的表現“虛空”主題的靜物畫,與中世紀基督教思想也有著直接聯系。[2]可以說,正是由于由1517年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還原了圣經真實的含義,而不再成為統治者恐嚇人們的工具,圣經解釋權不再歸教皇所有,而是每一位愿意相信上帝的信徒。宗教改革為人們揭開了真理真正的含義,將人們從死亡的恐懼中解救出來。他們不再活在“因行為稱義”的絕望中,而活在“因信稱義”的內心的平安之中,并且相信那位死去的耶穌已經通過死亡戰勝了死亡,因此,他們可以坦然地面對死亡。
同時,宗教改革回歸圣經真理,賦予了被造物真正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無論是生的或是死的,是干凈的或是骯臟的,是完整的或是殘缺的,是光明的或是黑暗的,都可以作為繪畫素材融入畫家的作品中。他們每日所目睹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創造物,它們都很重要。[5]
四、結語
宋代翎毛畫與17世紀的西方飛禽畫之所以風格迥異,是因為二者生長的土壤不同。前者在以人為本的理學滋養下,追求生動活潑,避諱死亡,宋代對于死亡題材的繪畫可以說是空缺的;而后者則在基督教影響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敢于直面死亡,因此死亡題材的繪畫在西方可謂盛行一時。東西方都追求寫實傳神,但在方式上表現的各有特色。中國文化應在保持繪畫語言的基礎上,多一些對生死的思考,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人們不必避諱死亡,相反應該正視死亡,由生死問題引導人們更多地思考人怎樣可以更好地活著,進而豐富中國繪畫的題材和內涵。
參考文獻:
[1]恩剛.荷蘭靜物畫題材與構圖特點的研究[J].美術大觀,2017,(04).
[2]焦燕清.靜物畫的高度——西方名家作品精選[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3]周瑩.相似語境下——中國花鳥畫與西方靜物畫風格比較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17年.
[4]周麗麗.禁忌詞的避諱——中德訃告中“死亡”概念隱喻比較研究[D].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17年.
[5][美]弗蘭西斯·薛華.前車可鑒——西方思想文化的興衰[M].梁祖永,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