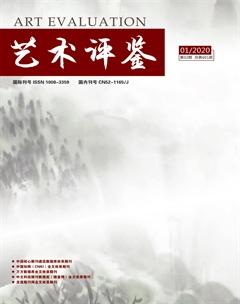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框架下中國人物畫創作新范式的探索
張閆博宇
摘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富強之時,藝術也肩負著對內提升民族性,對外彰顯國家形象的重要作用。全球文化大交融語境下,中國水墨人物未來的發展方向卻產生了迷茫與扭曲。在順應時代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冷靜反省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擁有民族性的世界藝術應是何種形式,我們的美術教育又存在哪些局限性,自身發展方向在哪里?藝術作為中國的名片,新時代精神下的民族性必不可少。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民族性? ?美育? ?美學
中圖分類號:J20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02-0032-0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心血與智慧的結晶,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貫徹執行這一理論體系有著更為重大的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框架下的藝術創作就成為對外彰顯國家形象的重要文化途徑。在20世紀40年代,西方世界藝術中心從巴黎轉移到紐約,抽象表現主義至此成為了美利堅藝術的符號,作為美國國家形象一度對世界各國藝術、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中國藝術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畫作為我國美學的“感性顯現”,貫穿中國藝術發展的始終,成為了符號化的藝術形式。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界定
現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是怎樣的形式呢?它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經歷了左翼文藝運動的錘煉,經歷了延安文藝精神的形成與提升,經歷了充滿挫折而又斗志昂揚的社會主義文藝精神建構,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巨大變化,并在今天由習總書記“中國夢”的理念賦予其新的內涵。
這里,我們應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進行界定:一是民族傳統美學的“中和之美”,即中庸和諧之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強調和諧文化。我們必須為人民群眾提供積極向上、和諧健康的藝術產品。二是把握傳統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即馬克思“審美生產”或“審美實踐”的美學理論思想。當今,人民經濟繁榮,生活富裕,社會出現了精神異化,但馬克思美學卻對此現象進行批判與反駁,這為我國從經濟型社會向審美型社會轉變提供了依據。三是毛澤東延安藝術座談精神強調“文藝必須將為人民服務作為目標與出發點”。這一講話的內容是我們今后藝術發展的大方向。四是習近平對于“知行合一”的論述。即理論聯系實際,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學以致用。在藝術創作中,做到藝術與人民相聯系,注重藝術作品對人民大眾的“言傳身教”。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歐洲“左派”美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的啟示,如布萊希特在戲劇中注重人與社會關系的建立,使觀者身臨其境;本雅明對翻譯終極目的的闡述,認為翻譯應表現語言之間的互補關系,鏡像在我國藝術中,映射出藝術應反映社會存在的不足,對人民大眾起教化作用;蘇珊·桑塔格主張藝術作品揭示生活本質;格羅皮烏斯主張:建筑要隨著時代向前發展,必須創造屬于這個時代的新建筑。
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學一定是吸收了中華民族傳統優良文化的,一定是吸收了國外現當代美學精髓的,一定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
二、內容與形式之間關系的重新厘定
筆墨語言一直是中國藝術創作的命脈,當代國內青年藝術家對于人物畫形式的選擇卻始終徘徊不前。美術理論家王琦先生說:“使內容服從于形式,這是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最大分歧”[1]。在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沖擊下,中國傳統水墨人物畫產生了過度夸張變形的態勢,甚至出現了高度抽象化的傾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和抽象表現的矛盾依舊存在。
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文藝工作者寄予了殷切期望并對社會主義文藝發展提出了四點要求:“‘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用積極的文藝歌頌人民,‘用精湛的藝術推動文化創新發展,‘用高尚的文藝引領社會風尚”[2]。如今東西方文化相互融合,作為文藝工作者應認真思考當代民族藝術的形式選擇,在這一問題上徐悲鴻、蔣兆和以及劉奎齡為我們創作新范式提供了借鑒,他們將西方的技法融入中國傳統水墨畫中,劉奎齡更是從西方古典主義、文藝復興、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甚至印象派中汲取營養。《愚公移山圖》運用了傳統文化題材創作出大眾喜聞樂見的畫作,在中西文化大融合背景下,民族性也得到了體現。徐悲鴻對中國畫做出的貢獻可謂給“救亡圖存”的中國人民一劑強心針,讓世界了解中國藝術,彰顯我國的志氣與底蘊。
習總書記多次對文藝工作者強調:“堅定自信、展示力量,讓中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2]。因此我們要牢記“不忘初心、服務人民”的使命。抽象表現是一種舶來品,歷史較短,形式本身變成內容,服務資本主義布爾喬亞階級,代表了典型的自由主義立場,人民大眾在觀賞抽象表現藝術時很難與作者發生共鳴,也不能體會作者的創作心理。而當代中國人物畫重技法而輕內涵,作品完全是作者內心狀態的抒發,題材空泛,側面反應出當代藝術家對民族性沒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不知何為民族性。
現如今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大國,世界不同文化對中國藝術的沖擊是巨大的,“文革”后的深刻反思與西方“藥”救中國“病”的思想誤讀,使中國當代藝術變得“畸形”,藝術家盲目推崇模仿西方抽象表現,國內抽象表現變成一種“無主題”藝術。21世紀的中國向兩個一百年目標努力,“世界文化大家庭”語境下機遇與風險并存,寫實、表現,個體精神、大眾審美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們。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美的藝術形式,要立足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審美立場,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提煉西方藝術的精華,將中國傳統文人詩意與筆墨情趣融合,創作出易于群眾理解且有民族烙印的“視覺符號”。
三、當代中國人物畫造型的新方向
關于民族性在中國人物畫中的滲透一直是我所關注的問題,到底怎樣的藝術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屬于我們本民族的藝術呢?回首歷史的長河,古人仿佛給了我們一把衡量的“尺子”。秦始皇兵馬俑運用傳統人物寫實技巧塑造出各不相同的陶俑,嚴格模擬實物,氣勢恢宏;隋唐時期,吳道子率先將由西域傳來的人物立體畫法“凹凸法”運用在繪畫中,在中國傳入犍陀羅佛教色彩文化后,吳道子將人物畫化入了一個新的個體中[3];楊惠之是唐代第一個將寫實風格引入雕塑中的人,創作中捕捉風貌并加以典型化夸張融入作品中,從而達到形神畢露[4];明清時期曾鯨的“沒骨法”也被稱為“凹凸法”。他塑造的人物肖像真實細膩, 形象極富立體感[5];郎世寧以西洋繪畫筆法“雜糅”中國傳統繪畫;我們未來的方向是任伯年的博采眾長還是徐悲鴻和蔣兆和對于水墨人物的新定義?中國人物畫中民族性與西方文化融合的點在哪里?孔新苗教授對此問題表達了看法:“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實踐證明了在中國社會的歷史、經濟、政治發展現實中,客觀地要求在審美文化生活中保持一種‘主導趣味是必要的,它在宏觀上是中華民族社會發展進程的必然,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境況需求”[6],這種主導就是民族性。
中國藝術的歷史比歐洲久遠,現代西方藝術進入國內后,我們仿佛在思想意識解放后偏離了曾經的軌道。雖說徐悲鴻與蔣兆和將水墨寫實人物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我們也要清楚的捕捉到兩人在今天看來所存在的局限性。二人的水墨人物充滿了西方的明暗感,人物過于追求比例、透視、光影的表現從而喧賓奪主,繪畫呈西方寫實,使原本的民族性減弱了。例如:徐悲鴻的《山鬼圖》中,人物通過明暗關系表現體積,畫面對光的運用、陰影部分的處理、畫面整體的寫實性讓我們不禁與法國古典主義相聯系。蔣兆和的《阿Q像》,阿Q面部的明暗處理、體積塑造、塊面表現是西方造型藝術影響下的結果,甚至阿Q頭上的青筋都刻畫的惟妙惟肖,整體來看水墨已然變成了素描,寫意味已經幾乎不在了。簡言之,兩人均受西方繪畫影響,中西技法結合方面略顯僵硬,西方輪廓線/中國畫獨立審美線條、服飾暈染、傳統衣紋線條處理的“矛盾”,使畫面呈現出原始與生硬,創作中自覺意識表現就因此缺失了。正如孔新苗教授所說:“無論前衛作品所針對的中國社會與現實生活問題、所使用的形象符號多么具有直觀指向性,其藝術表達形式的‘陌生化,往往被國內大眾直觀地視為對西方的某種的‘模仿”[7]。
徐悲鴻與蔣兆和對于中國水墨人物畫的貢獻自然是非凡的,回歸現如今人物畫創作,當代藝術家甚至還落后于徐蔣二人,畫面中民族性與中國傳統風味的表達早已被西方具有視覺沖擊力的表現藝術所代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藝術的語境中,畫家民族性缺失成為制約我國傳統文化傳播的根源問題。孔新苗教授也對藝術與國家形象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今天我們提出藝術中國家形象的命題,正表征了對這一歷史性課題的承擔:超越東西方的二元對立,在當代世界多極化的格局中發現中國形象的世界性意義”[8]。
中國在21世紀已然成為世界大國之一,在世界經濟、政治中的話語權愈加重要。不可否認,“五四”運動后,中國藝術一直將西方作為自己走向“現代”藝術的參照物,當今美術人才選拔和課程制定也以西方的素描色彩、蘇聯的繪畫方式、西方抽象表現作為標準,幾乎每一位剛踏入藝術領域的學生都以寫實技巧和西方形式構成觀念作為評判“美”的標準,從而忽略了我國傳統文人畫抒發內心情感與“書畫同源”的美妙之處。國畫審美性缺失必然導致如今中國傳統美育的不完整。
在之后的美術教育培訓機制上,筆者以為首先可施行“雙軌制”,即加強寫意技法訓練,開設理論課程,提高學生思想文化水平,保證理論與實踐相協調,增加作品的內涵與充實性。
再者,現代藝術家、教師、學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下,描繪著所謂的崇高,藝術從而與生活斷裂,表現出無病呻吟,東拼西湊的藝術形式,導致駕馭大題材能力不夠,對主旋律的表現幼稚化、教條化、膚淺化。以美院近幾年的作品為例:畫面多表現宿舍睡覺吃飯,食堂聽歌嬉戲等空洞干癟無內涵的場景。面對此問題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應轉變思想、深入生活、進入基層,切身體會各個階層的辛酸苦辣,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洪流,真切體驗勞動、奮斗的內涵,在真實的勞動人民及其事例中體會什么是勞動價值,站在人民的立場與境遇中,才能創造出與人民群眾形成共鳴的作品。
反思自身,我們當代的美術生在創作過程中甚至不如庫爾貝從現實中取材使藝術回歸真實,不如米勒真正從農民角度以純樸親切的藝術語言創作人民大眾所喜愛的作品,也不如陳丹青深入西藏感受藏民生活,最終呈現給世人震撼的《西藏組圖》。雖然庫爾貝與米勒對于我們當代藝術有著啟示作用,但是和現如今相比缺少了先進的馬克思理論指導,所以擁有先進理論指導與明確文化方向的今天,我們理應超越前人。
綜上所述,我們在創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繪畫時要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包容西方優秀文化,同時也不能讓洋文化“淹沒”了我們的民族性,在多維視角中做到文化自信,摒棄國際文化西方中心論的觀點,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創造出“中國特色現代美育”和“中國特色藝術表達”,讓繪畫兼得中國精神與時代精神。
參考文獻:
[1]王琦.現代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藝術[J].美術研究,1958,(01).
[2]習近平總書記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講話引發熱烈反響[DB/OL].新華網,2016-12-01.
[3]吳帶當風[DB/OL].中國新聞網,2013-10-28.
[4]董樂意.“塑圣”楊惠之的雕塑藝術[J].南陽理工學院學報,2009,(02).
[5]黃碧波.明末畫家曾鯨的人物“肖像”藝術成就探微[J].蘭臺世界.2014.(18).
[6]孔新苗.中西美術比較[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7]孔新苗.境遇·鏡像——中國美術與“國家形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孔新苗.歷史·現實·鏡像——關于當代美術與“國家形象”的思考[J].美術,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