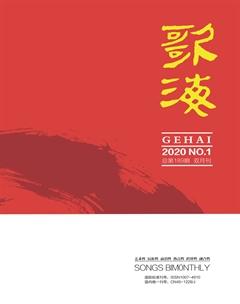只爭朝夕,不負韶華
周強
尖尖小荷,嶄露頭角
從藝前,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我便認識了張樹萍。我和她小時候都就讀于桂林市解放西路小學,她比我早三屆,我是個小學弟。
在我的心目中,解放西路小學是個藝術搖籃,20世紀70年代,這個學校的文藝活動開展得相當活躍,有鼓樂隊、舞蹈隊、戲曲隊、合唱隊,每年校內必有十次以上的文藝活動。
我剛進學校讀一年級,就被這個學校頻繁的文藝活動吸引了,每次都羨慕地看著高年級的學哥學姐們在臺上演出,從而也認識了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張樹萍。那個時候她就充分展露了極高的藝術天賦和素質,一折《智取威虎山》——深山問苦的小常寶,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唱腔身段惟妙惟肖,表演與現在戲校里專業三年級的學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成了每次全市文藝匯演的小紅角。兩年之后,張樹萍升學進了桂林三中念初中,我又以《沙家浜》——軍民魚水情延續著這個學校的戲曲傳統。
在我升學進三中的同年,張樹萍就考入廣西藝術學校桂劇班學習專業戲曲表演。無獨有偶,我也于三年后考入桂林市戲曲學校桂劇班學戲。
1983年,我還是個戲校三年級學生的時候,張樹萍所在的廣西藝術學校桂劇班來桂林匯報演出,在《白蛇傳》——“斷橋”一折里唱演白素貞。也就是從那個時候,我們知道了這個班里的幾位“科里紅”——兩萍一倩。
1987年,我從戲校畢業到桂林市桂劇團工作,又與張樹萍成了同事,相似的從藝經歷,讓我幾乎成了她的追隨者、效仿者。此后的30多年,我們一起見證了桂林市桂劇團的發展、變革、成就、輝煌。
勇立潮頭,當仁不讓
1989年,廣西舉辦首屆青年戲曲演員大賽。那一年,張樹萍剛生完孩子還沒斷奶。她挑戰自我,選了一出唱舞并重的桂劇傳統劇目《失子成瘋》,繁重的水袖舞蹈,末了還有個很吃功的技巧“硬僵尸”。這是個武旦、刺殺旦的技術活,人人都勸她別玩這個,畢竟是個剛生完孩子的人。她愣是憑著股要強不服輸的倔勁,把這個戲生生啃了下來,一舉奪魁,這個成績,也成了她藝術道路上的新起點。
1990年,廣西第三屆戲劇展演舉辦,從湖北請來了赫赫有名的戲曲導演余笑予,排演新編桂劇《瑤妃傳奇》。
余笑予導演堪稱梨園界“奇才”,行內出身,原是楚劇演員,后做了戲曲導演,成功作品數不勝數。余笑予過人之處便是善于發揮演員優點,因材施教,揚長避短。一出《瑤妃傳奇》之后,不用說作為主演的張樹萍,即便是我們這些在邊上的配角龍套都如升入一個大專班回爐再造,受益匪淺。那個時候,我們更加羨慕張樹萍能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得到余笑予的一對一指教,頓時藝術水準、素質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提高,更使我們可望不可及。
《瑤妃傳奇》在廣西劇展中驚人一鳴之后,陸續參加了全國各大戲劇展演和賽事,幾乎囊括了那個時期的所有獎項,實現了多項零的突破,桂林市桂劇團也在全國戲曲院團中聲名鵲起。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自此之后,一連串的好運都降落在張樹萍的身上。《風采壯妹》《未了情》《漓江燕》等幾部大型新編劇目,榮獲了“五個一”工程獎和“文華獎”“梅花獎”,一時間,她成了全廣西戲曲界家喻戶曉的獲獎大戶。
榮譽背后是付出,付出不為人知的艱辛與努力;榮譽之后是思索,思索舞臺藝術的發展和未來。為此,張樹萍先后赴上海戲劇學院及中國戲曲學院學習深造,在上海,她結識了導師盧昂。盧昂對于中國戲劇舞臺藝術的研究、見解給予了張樹萍在戲曲藝術發展中的思索和困頓極大的幫助,如醍醐灌頂。她如饑似渴地吮吸著學院派理論知識的養分,為地方戲曲藝術的發展尋求一條光明之路。
2009年,作為廣西戲曲領軍人,張樹萍扛起了桂劇藝術傳承發展大旗,擔任桂林市桂劇團團長。
桂林市桂劇團建團近70年來,人才輩出,碩果累累,突破性的傳承發展,是張樹萍認定的道路方向。上任伊始,她從上海請來了著名編劇李莉和著名戲曲導演石玉昆,共商如何根據本地歷史文化創作排演大型桂劇劇目《靈渠長歌》。她憑借多年的舞臺藝術經驗,遍訪名師各地求學,開闊的視野,注定出手不凡。這個劇目從開始的立意到舞臺呈現,無不令人眼界大開,在廣西戲劇展演的眾多劇目中脫穎而出。桂林市桂劇團持續獨立潮頭,延續著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的神話,成為全區同行翹楚。
銳意進取,再創輝煌
2012年,在全國藝術院團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促動下,桂林市三個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合并為桂林市戲劇創作研究院,張樹萍出任該院第一任院長。
兩個戲曲劇種,一個曲種,根本同源,相通相生。張樹萍率領新團隊,發揚合作精神,從三個劇、曲種精妙出發,取其同,存其異,力求三并舉,齊開花。院團合并第一年便創作了大型桂劇《何香凝》,大型彩調劇《一品油茶七品官》,其后更是廣納賢士,首開先河,與廣西著名作家、編導張仁勝合作,全院通力排演大型方言話劇《龍隱居》,響應桂林市委市政府提出“尋找桂林文化力量,挖掘桂林文化價值”的號召,大力挖掘、宣傳、推廣桂林歷史文化名城的抗戰文化底蘊。
桂林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歷史文化名城,作為桂林市專業藝術團體的領頭人,張樹萍清醒地認識到,打造一張桂林地方藝術的名片,把桂林文化藝術推向世界大舞臺乃當務之急。
2014年,張樹萍在院領導班子業務策劃會上提出:合理利用資源,將原曲藝廳改建為一個有格調、有品位的高端小劇場,打造一臺集桂劇、彩調、曲藝為一體的綜合藝術精品——《桂林有戲》,與旅游市場緊密結合,提升地方藝術價值,讓《桂林有戲》成為一個向世界宣傳、推廣桂林山水文化、歷史文化以及地方人文的窗口。這個提議在班子會上一經碰撞,一拍即合,將《桂林有戲》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山水旅游名城的新名片。桂林市缺少的正是這樣一張文化名片。隨即會上便布置下達任務,我作為該項目的主創人員之一也全程見證了這一品牌項目的成型與成功。
這臺藝術精品創作歷時近五年,從立意、篩選、雛形,為破而立,再破再立,張樹萍帶領主創團隊以及全院上下,反復打磨,精益求精,力求從細微處見真功。
張樹萍在日常業務工作中常說:與高手合作,過程最重要,結果卻在其次,在過程中學習,鍛煉自己,提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和最大的收獲。
為使《桂林有戲》從節目到環境能有一個協調統一的整體呈現,張樹萍從上海戲劇學院請來韓生院長為《桂林有戲》擔任舞美設計,從劇場的每一根臺柱,每一道邊幕甚至到一磚一瓦,不厭其煩地與韓院長交流溝通,使《桂林有戲》劇場的每一個角度都透露出精致的大寫意的藝術神韻。
隨即又從北京請來富有先鋒小劇場運作經驗的李卓群創作團隊,對整臺劇節目加以提升細化,在整體連貫性、唯美性和統一細化上做出全面調整,從包裝到推廣作出精密的宣傳計劃。經過不斷地精雕細刻,于2017年底亮相。初次登臺,驚艷全場,一時全城上下以能一睹《桂林有戲》芳容津津樂道。作為先鋒小劇場運作模式的成功范例,《桂林有戲》不僅在桂林一炮打響,2019年還前往自治區首府南寧、首都北京國家大劇院作匯報演出,盛況空前。
2018年,張樹萍以敏銳的藝術眼光捕捉、構思,決定在桂林市抗戰文化上下功夫、做文章。因此再度與北京李卓群團隊合作,打造一部舞臺新劇——大型新編桂劇《破陣曲》,再一次掀起抗戰文化熱潮。《破陣曲》一劇,張樹萍站在新的藝術高度,力排眾議,一改以往戲曲傳統中一角到底的表現形式,堅持以群像式再現模式表現抗戰期間,全國各地文化名人云集桂林小城,在震驚中外的“西南劇展”活動中,以筆作刀,以劇為矛,用文化的力量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壯舉。
劇本結構在張樹萍與北京李卓群團隊幾度碰撞中產生火花,達成共識。大師級的音樂創作,殿堂級的舞美設計,明星級的創作陣容,堪稱頂級聯合。創作過程中,張樹萍反復提醒我們創作團隊:只有我們桂林的桂劇人才準確地知道我們的劇要說什么樣的話,該演什么樣的事,該塑造什么樣的人物。不能人云亦云,沒有屬于我們自己的文化自信,只會停滯不前,永遠達不到一個新的高度。
整個創作團隊在張樹萍的帶領下,常常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展開研討。該劇最終在廣西第十屆戲劇展演中再次奪魁,創造了桂林市在該賽事中八連冠的佳績。2019年,《破陣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獻禮劇目再次進京匯演,把桂林市戲劇創作研究院推上國家舞臺。
傳統古老的戲曲藝術底蘊深厚,博大精深,是舞臺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張樹萍清醒地認識到傳承傳統戲曲藝術的重要性、必要性,深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迫在眉睫,繼而把新的工作重心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和普及中。她四處奔走呼吁,尋求、利用社會資源,力圖從意義以及實質上遵循“保護性傳承、傳承性普及、普及性發展”的良性模式,積極健康地推進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這項提議也得到了桂林市委市政府以及自治區相關領導的支持贊同。
天道酬勤。張樹萍為這一偉大工程的努力終于傳來佳音,申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館項目列入國家一百座“非遺”館重點工程項目。如今已落成于桂林西山腳下的“非遺”館開館在即,一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即將面世,我們期待這一壯舉將桂林市的歷史文化再次推上新起點、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