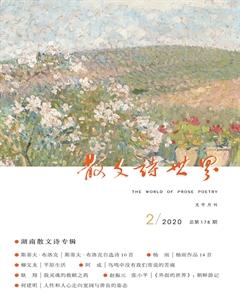人類最初的懺悔與鶴(組章)
趙應
不食,甘地的主義
圣雄甘地的不食,時隔多年,我依舊放心不下。
“我看見一百萬噸的死亡如此寬闊”,除了你,這種修辭手法至今仍無幾人能夠熟練使用——
或許,只不過是誰的痛苦被人為地無限夸大了,同時也被羞辱了(青年人群中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流言擾亂四季。如恒河之水暴怒泛濫,造成沿岸平民死傷無數。
一切風沙都將使下一個雨季的收獲兇吉難測。
一切宣言,必將借機更加興風作浪(青年人群中再次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而我依舊盤踞在中國黃土高原腹地的草地上言語滔滔,頭顱高昂。
“站著說話不腰疼。”——你說簡直豈有此理,那就不妨前來印度與我終日閑庭對坐吧。
或者我們一時興起,把釋迦牟尼當年用過的鍋灶瓢盆統統都打碎,然后振臂一甩,將它們全部丟給黃河長江珠江雅魯藏布江一帶的乞討者們(青年人群中有人高高拋出一捧恒河沙)。
不食。一人緊盯著受傷匍匐在地的麻雀,準備伺機而動。
不食。第二人轉變身姿左右突進,三兩下躍上了自我保護意識的最前線。
不食。第三人把自己被毆打脫落的牙齒從舌苔上緩慢地輸送了出來,隨后吐到地上。
不食。谷物們在鹽堿地歡慶,又一次安然度過腐爛危機。
不食。真正的國難不分國籍,是地球一手培植出草木專政,偽裝各地草原的安定與清潔(青年人群中暗影重重但見一人紅暈低垂)。
人類最初的懺悔與鶴
道可道……醫院的鶴暗藏怒火,石碑也可縫補死者肉體,兒時的蹺蹺板通宵達旦地運轉。
好孩兒化身擅入都市的羔羊,好在年輕,尚可躺在床上與電子產品共度余生。
最初的草木與蝴蝶依舊優雅如刀。
一些鮮花遍插在故土的水泥石臺,一些似是而非的鶴肉腐爛在開春時刻,成為一群終日圍簇在一臺簡易收音機旁想象戰爭場景的和平情報員。
鐵尖木扁擔敲打往日人類威嚴,像敲打一只四下漏水的黑陶罐,好孩兒抱著鶴藏身其中。
鶴,在你親自為我拭去眼淚之日,一場深埋人類意識流中的大暈眩集中爆發。
北方大澤遍布受孕的苔蘚和鳥卵,在靈與肉的更深遠處,我的懺悔,我的鶴,載舟亦覆舟。
唯我一人,停杯投箸不能食:前世用石頭筑屋,今生豎起慰靈碑。
行者的象征和待遇
正午時趴在黃河大橋的護欄上被大風吹,黃河在水上漂而我高懸在半空中。
一心想要跳下去,成為不追名不逐利的跳水冠軍,成為急需水分的黃土高原。
泛濫的行者們究竟是怎樣在逆風中茁壯成長?要知道,他們幾乎從不直接參與當地風土人情的記憶建設,《徐霞客游記》也不會。
傍晚我在一家臟亂差的鐵路招待所下榻,前路選擇太多,反使人手忙腳亂。
長夜漫漫,內心的爭斗逐步落空:你我行走其中,左右逢源,痛苦萬分;風景區們也雛鳴,也吃肉,它們生老病死,在行者的勞累奔馳中倍感愉悅。
你在路上走,路也在你身上走;行路的斷裂,猶如行者陰暗的生活:懦弱無需張揚,檔案自有體察。
象征本身即意味著被象征事物本體的不確定性,乃至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