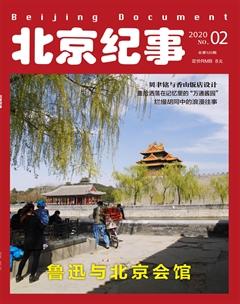潮白河閘橋的得失
金克亮

幸存的進水閘橋

泄水閘舊照

進水閘橋頂部

蘇莊水文站碑
20世紀20年代初,在順義蘇莊村東,潮白河上曾建有一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用以攔截、疏泄潮白河水,并向北運河輸水,運送貨物。據說,這項工程是當時北方最大的水利樞紐,由美國水利專家羅斯、顧斯設計并督建,故稱“洋橋”。這座水利樞紐工程還牽涉了幾個重要人物,一是時任北洋政府的大總統徐世昌,另一位是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熊希齡,還有京兆尹(相當于北京市長)劉夢庚,順義縣知事唐肯等。
為何修建閘橋
潮白河是京東的一條大河,歷史上水災頻發,給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極大損失。為治理潮白河水患,兩岸人民和相關機構多次對潮白河進行疏浚、筑堤、整治。“洋橋”,是建于潮白河上的一處水利設施,它建于民國十一年(1922年),至民國十三年(1924年)竣工,共耗資250萬元。當地人講,該款項為庚子賠款。
《民國順義縣志》載“……白河泛濫,潰決無定,有自在河之稱。自光緒三十年(1904年),由李遂店潰岸南流。經通縣、香河、武清至寶坻,蓄成水澤,寶邑受害者三四百村。”李遂店,在蘇莊北二里遠。舊時,由于時政不佳,疏于治理,潮白河經常從李遂處潰岸決堤,給下游帶來巨大的災害。1904年這場大水,致潮白河改道,奪箭桿河道流入,時人稱改道的潮白河為“新白河”,而潮白河故道遂廢棄。之后,當時政府在李遂處多次筑壩障水,但屢筑屢毀,潮白河水災仍頻。
1918年,京兆各縣水災,潮白河肆虐,流經之處蓄成水澤,而寶坻縣受災尤為嚴重。于是,由寶坻士紳發起,順義、通縣、三河、香河、武清等13縣的民眾積極響應,集體去北京請愿,吁請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治理潮白河。
1922年,熊希齡被特派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后事宜,撫恤流亡,賑濟災民,成立“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熊希齡,湖南鳳凰縣人,他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在當時也是大名鼎鼎,后轉向慈善和水利事業。熊希齡召集沿河各縣鎮的民眾、鄉紳、水利人員討論治河辦法。又派出專門人員調查潮白河水的流向、流量,勘察地形、討論治河辦法,并召開專門會議,決定在蘇莊村東潮白河上建一座水利樞紐。該工程分為兩部分,即在潮白河主河道上修建一座泄水閘,在泄水閘北修建一座進水閘,并在進水閘外開挖一條引河。
泄水閘在潮白河的主河道上,東西向,共30孔,全長210米有余。水底至閘頂高8.5米,頂寬6米,水泥澆筑而成,設鐵閘門、墜閘洋灰錘,傳動鐵輪54個,上可行人。進水閘在泄水閘北,引河入口,南北向,10孔,寬高大致與泄水閘相同。也設鐵閘門,墜閘洋灰錘,鐵輪52個。
引河在進水閘外,通過進水閘把潮白河水引入引河。引河從進水閘向西,至盧各莊折向南,全長7公里、寬50米、占地37頃多、流量600立方米/秒,向南至通縣平家疃,入已廢棄的潮白河故道,以減少潮白河水流量,并向北運河輸水,利用引河水運送貨物。修建時從附近村子征地,地分三等,甲種地每畝45元、乙種地每畝35元、丙種地每畝25元。修建時遇到墳地,遷一座墳25元。整個工程設計復雜,規模宏大,于1924年建成。
閘橋竣工后,民眾曾在進水閘和泄水閘之間立有一碑。碑文開頭曰:嗚呼!白水泛濫,肆虐千里,土地、稼禾、房屋、牲畜被淹,人民流離……下面的內容大致為:潮白河水歷年給人民帶來災難,京東十三縣的民眾曾聚集商議敦請民國大總統徐世昌治理水患,當時政府出資聘請美水利專家設計,征集民夫,購物購料修建閘橋,以及閘橋、引河的作用,所用材料、人工等。
修建這座閘橋,開挖引河,共耗資250萬元。我們看看當時的物價,1920年—1926年,北京物價較上海低,每斤大米5分多一點,豬肉0.14至0.15元一斤,一銀元可買兩丈藍士林布,可吃一頓涮羊肉,買20張公園門票,戲劇電影票2至3張,報紙零售3分一份。如果以大米計算,建“洋橋”的費用可買大米4000多萬斤。
閘橋的作用
閘橋投入運行后,汛期時,潮白河水漲滿,主河道上的泄水閘便打開閘門向下游泄水。30孔閘門一齊提起放水,飛花濺浪,波濤洶涌,卷起千堆雪,聲聞數里,景致蔚為壯觀,為順義當時一景,稱“洋橋破浪”,《民國順義縣志》有照片。曾有人寫詩贊曰:“長橋橫臥碧溪頭,操縱能叫石不流。引水有方通渤海,空槽無際做沙洲……”
而在枯水季節,潮白河泄水閘放下閘門蓄水。河床水滿后,北側的進水閘打開閘門進水,水經進水閘流入引河入潮白河故道。當時潮白河上游許多縣份運送糧食、木材、皮貨、干鮮果品及其他貨物的商船,多是由這里經過進水閘入引河運至通縣碼頭卸貨,時人稱引河為“銅幫鐵底運糧河”。枯水季節,水較淺,貨船至此,行走困難。這時,船上的人跳下船,只留下船老大掌舵,其他的人抄起纖繩彎腰拉纖。
為對閘橋進行維護、管理,當時的政府還在村北設立管理機構,修了一座建筑。建筑為歐式,房前有走廊,很有氣勢,村人稱這里為“洋房子”或“水衙門”。當時,大門口掛有三塊牌子,分別為“順義水文站”“河北省造林區”“閘橋管理站”,還有一名姚姓巡警也住在這里。每天,巡警對閘橋、引河進行巡視、看管,處理一些日常事務。閘橋管理人員則根據水勢情況,提閘放閘,泄水蓄水,水文站的人員查看水勢、流量、含沙量、水位,記錄水文資料,造林的人員負責巡視管理林區。
引河通航后,兩岸種植樹木,二里種植柳樹,二里種植桑樹,又二里種植杈子樹。春意新生時,綠植層層疊疊,春意盎然,被稱為“引堤疊翠”,是民國時一景。而北京、通縣都有人坐船來此踏春、賞青、摘桑葚。
因“洋橋”的修建,貨船停泊,蘇莊成了交通要道。河東河西的人們走親訪友、看戲走會,運送貨物的驢垛子、駱駝隊都要通過“洋橋”,這里日夜駝鈴聲不斷。蘇莊也因此而繁華起來,村里辦起了點心鋪、雞蛋公司、飯店、馬車店、饅頭鋪、雜貨鋪、黑白鐵、皮貨攤、早點、應時水果鋪等攤位。
1926年,直奉戰爭,奉系軍閥占據了潮白河東,直系馮玉祥占據了河西,上游從牛欄山至蘇莊兩岸都駐扎了軍隊,兩軍都挖戰壕,修筑工事,隔河對峙。后奉軍撤退時,怕直系軍隊追擊,奉軍將領命人在閘橋東埋設炸藥,炸毀了東側的一孔閘橋的橋面,閘橋又見證了這次歷史事件。
閘橋被沖毀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京東暴雨成災,上游山洪暴發,大雨滂沱,水勢洶涌。《懷柔縣志》對1939年的大水有詳細記述:七八兩月,有三次大的降雨。第一次為7月9—16日,降雨量為300毫米以上;第二次為7月24—28日,降雨量為360毫米以上;第三次在8月11—13日,降雨量較前兩次略少。在第二次降雨過程中,潮白河上游于26日起暴發山洪,蘇莊水閘洪峰流量達1.5萬立方米/秒,水閘被洪水沖毀。
而據當地人講,當時大水洶涌,急需向下游泄水。但下游有羅姓人,在河邊有很多土地,為使大水不致淹沒其在下游的大片土地,派人持槍來到閘橋,阻止看橋的人提閘放水。后因暴雨不停,水勢上漲太快,閘橋上游的河水已達極限,水災已成定局。看守人員提閘時,閘板及絞索已被上游沖來的木料、樹枝、柴草等塞住,閘板不能提起。大水越積越多,泄水閘正當潮白河主河道,承受不住大水的沖擊,一聲巨響,閘橋被洶涌的大水沖毀21孔,只剩9孔。這座修建時間長,耗費大量資金、人工、材料的水利設施遂告廢棄。
1958年大煉鋼鐵,殘留的泄水閘被炸毀,上面的閘板、鋼筋、鐵輪等金屬都被拆下來煉了鋼鐵。至此,泄水閘完全消失,只剩下引河入口上的10孔進水閘,歲月滄桑,進水閘表面水泥剝落,下端已被泥沙掩埋,周邊長滿荒草,但還基本保存原樣。
修建閘橋的得與失

平靜的潮白河水
這座閘橋從建成、使用至沖毀,歷時15年。它為北運河輸水,減輕潮白河水患,往北京運送貨物,確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耗費大量資金、材料、人工的閘橋為什么這么短的時間被沖毀?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設計者對潮白河水歷年的水量、水災、危害缺乏整體的把握,因此,建好的閘橋不能抵御更大洪水的沖擊。
二、閘橋選址不當。把閘橋選在蘇莊,那么,蘇莊以上的順義河段、懷柔、密云等約百里的河段大水如何解決?顯然,這座閘橋對以上河段毫無作用。據親歷過民國二十八年大水的老人講,站在順義舊城東門高阜處,肆虐的潮白河水達幾里寬,水面上漂浮著木料、家具、樹、柴草、死人,順義城北門進水,人們進出城門要乘木槽、竹筏等。
三、閘橋的通水能力有多大,未見記載,我們可以看看潮白河道的承載能力。據建國后修成的《順義縣志》載:潮白河水多年平均流量1309立方米/秒。而《懷柔縣志》對1939年大水的記述:蘇莊水閘洪峰流量達1.5萬立方米/秒,是常年流量的十幾倍,水閘被洪水沖毀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可見,水閘抗洪水沖擊能力差,洪水是閘橋沖毀的主要原因。
四、1958年修建密云水庫,把庫址選在密云,就是考慮到了在此修庫建壩,可以容納上游更大的水量,有計劃向下游輸水,可以保證下游不發生水災,可見,后者是經過了周密的勘測、設計、論證的。
五、當時技術落后,施工時不按要求修建,留下隱患。據村中曾修過閘橋的人講:施工時,由于潮白河水中流沙太多,施工中泥沙清理完,立刻又有流沙流過來,將挖好的坑流平。再清再流,清理泥沙工作進展緩慢。因流沙太多,工程在很長時間都沒有進展,施工中的民工都疲憊不堪。中方負責施工的官員向外方監理要求,每天如此工作沒有效率,不如就此投石澆筑。后終因工程進展慢,流沙太多,外方監理見流沙清理緩慢,民工又都很疲勞,只好轉身走了。這時,施工人員一擁而上,把籠好的石料投進水里,而后澆筑施工,造成了工程的質量不能保證。
而今,仍然有些喜歡歷史的人來這里考察,鉤沉歷史。有些騎行的人們到了這里也下車觀看、游玩、拍照。有誰會想到,荒郊野外,這樣一座殘破的建筑,會和一些歷史事件、歷史名人聯系在一起,還折射出民國時期社會、經濟、科技、民生、水文、自然災害等方方面面。
(編輯·劉穎)
5149847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