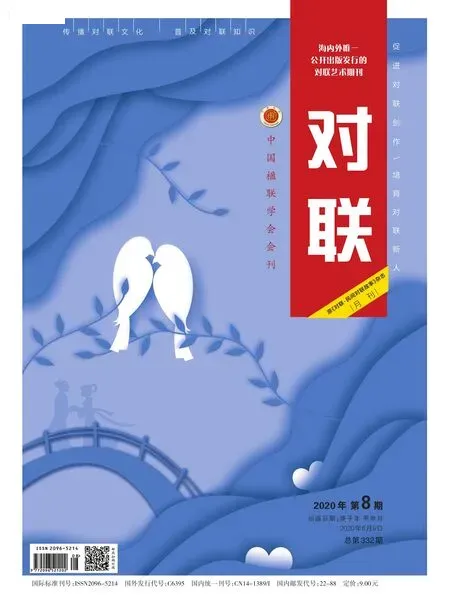從容中道 以樂正心
——王褒《洞簫賦》析要兼談古代樂論
□李牧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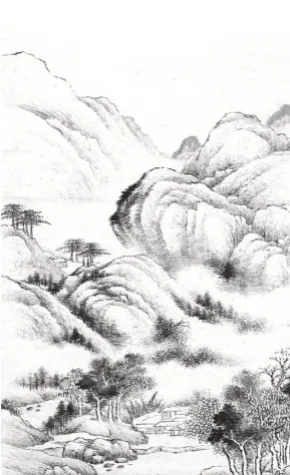
王 褒 字子淵,是漢代的辭賦名家,主要活躍在宣帝時期,與后來的揚雄(字子云)同為四川人,并稱『淵云』。他的人生開場秀,是小試牛刀的應邀為益州刺史王襄寫了一些歌功頌圣的馬屁詩,這些詩被有意編成歌來傳唱,最終傳到了宣帝耳朵里,正中其下懷。于是,王褒也順理成章地被刺史舉薦給了宣帝,并應詔寫了一篇《圣主得賢臣頌》,表達了『圣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的觀點,算是把之前拍的馬屁又系統化、理論化了一下,變成了升級版。自此后,他當上了御用文人,成為了職業拍馬者,但有游獵,輒為歌頌。后來他奉命陪侍身體抱恙而健忘的太子,并早晚誦讀一些奇文和自己的作品,居然幫助太子把病給治好了,并讓太子從此對他的《甘泉賦》和《洞簫賦》情有獨鐘,念念不忘。有這么可圈可點的幾件事,王褒自然在青史和皇帝心目中擁有了一席之地,以至于他病逝在奉使去益州祭祀的路上后,宣帝還深表惋惜。
盡管在王褒之前,已有人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涉及過音樂類的題材,比如枚乘就在《七發》中寫過古琴,有資料顯示他寫過《笙賦》(已佚亡,一說《琴賦》,或即《七發》中之片段,有爭議),但《洞簫賦》應該算得上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獨立成篇的音樂賦,它引發了后人對一個賦類的創作。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洞簫,不是后世的單管簫,而是不封底的排簫。賦文從洞簫的制作材料竹子及其成長環境說起,講到制作工藝、演奏技藝,再講到藝術魅力和道德感化,最后總結陳詞,整個結構非常巧妙和完整。在講竹子的成長環境時,既有所傍山體跌宕起伏的氣勢;也有天地四時陽光雨露的滋潤,所謂『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更有寡鶴、春禽、秋蜩與玄猿等與洞簫音質相應的飛禽走獸的蹤跡與影響。這竹子也真是吸足了天地間的精華靈氣,天籟與地籟共同造就影響了人籟簫聲的根性,三籟貫通,合而為一。
有了上等的原材料,『于是般匠施巧,夔妃準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能工巧匠負責制作,樂界大神負責正音,無論是外形裝飾,還是音色音準,都是極品,無可挑剔。一句『鄰菌繚糾,羅鱗捷獵』正好印證了這洞簫就是排簫無疑。至于演奏者,則是專業的盲人樂師,『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體勢,暗于白黑之貌形。憤伊郁而酷 ,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洞簫的音色深沉悠遠,最適合寄托悲思綿愁,而盲人演奏者更能專心致志,且自帶憂愁特質,兩者搭配,相得益彰。不得不說,王褒寫洞簫,正是認準了它『悲』的音色特質。
那么,演奏效果如何呢?作者綜合運用了襯托、夸張、比喻、擬人、通感等多種修辭手法,對此作了極力的鋪陳渲染。聽巨音則『若慈父之畜子』,聽妙聲則『若孝子之事父』『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聽一曲音樂,就能想到父慈子孝之類的,這分明是受到儒家禮樂思想的熏陶啊!更生動的還在后面:『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強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鐘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這簫聲的感化力是如此之強,以至于能讓貪財者變得清廉,殘暴者放下怨恨,強橫者心生仁義,讓鐘子期、伯牙、師襄、嚴春這樣的古代音樂高手都自嘆弗如,讓顏叔子這樣意志堅定者動心,讓丹朱、商均、夏桀、盜跖這類人改性,這得有多高深的藝術造詣和功力才行!更有甚者,連動物也在感召范圍之內,『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轉,瞪瞢忘食』,這一段畫面感非常強,且不失詼諧,特別適合腦補,想象力如此豐富,不服不行!
這種修辭手法并非王褒首創和獨有,在他之前、之后都有不少文人運用過。比如宋玉的《神女賦》中描述神女時寫道:『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枚乘《七發》中渲染古琴的效果時寫道:『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漢樂府《陌上桑》中形容羅敷之美時寫道:『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三國阮瑀的《箏賦》中說:『伯牙能琴,于茲為朦。皦懌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此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魏晉成公綏的《嘯賦》云:『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寧子檢手而嘆息。鐘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再后來如唐李白的《大鵬賦》、舒元輿的《牡丹賦》,乃至曹雪芹筆下的《芙蓉女兒誄》中,都有這種句子,不勝枚舉。綜合來看,王褒《洞簫賦》的謀篇布局,顯然受到了枚乘《七發》中音樂片段的影響,簡直是如出一轍。
體現《洞簫賦》核心思想的有兩句話,一句是『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另一句則是『亂曰』里的『從容中道,樂不淫兮』。從這兩句可以看出賦文內涵與儒家禮樂思想的高度契合。《禮記·樂記》中主張『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它認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樂本身就是相輔相成的,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這是闡述禮樂的社會教化功用。這種『音樂療法』之所以能夠起到真正的作用,在于它相對充分地認識到了音樂與人心的交互作用,并形成了一套相對系統的認知理論,『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啴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禮記·樂記》)。《黃帝內經》也精辟地闡述了人的五臟與五音的對應關系。
正是因為認識到了人心與音樂的這種相互影響的關系,在這個基礎上,高明的人不僅能夠辨音、識音,根據音樂的風格和特性來認識一個地方、國家或者時代的施政狀況與風俗人情,也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音樂來改善人心,達到移情化性、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人有善惡之別,世有治亂之異,音有德溺之分,禮樂之道,法天則地,合于中道,并教人以道來制欲節情,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記·樂記》)。音樂療法理論上來說,既可以治一人之病,也可以治一國之病,從這個角度而言,通過誦賦來為太子治病,不足為奇。可以想象,若誦讀之際,還有宮廷樂師現場洞簫伴奏,效果當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