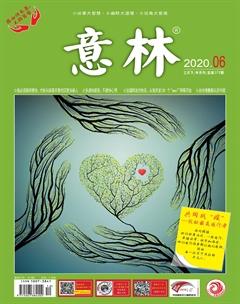在哈佛重新認識中國
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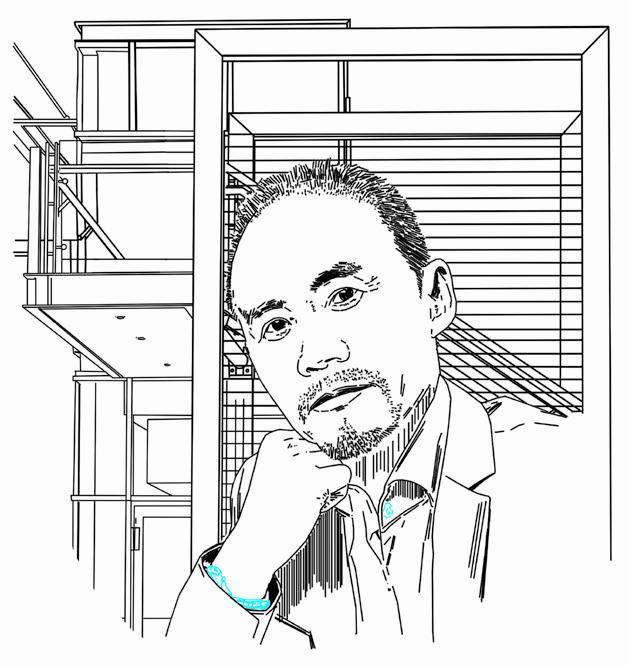
在哈佛的第三學期,我選聽了一門特別的課程——《中國古典道德與政治理論》,授課的是普鳴教授。這門課成了我在哈佛期間收獲最大的一門課。
普鳴教授認為,21世紀的美國人和2500年前的中國人一樣,都面臨自我中心的困惑。他希望通過中國哲學思想賦予美國人具體的、革命性的理念,指引他們成為好人,并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
我看到,美國精英階層,尤其是學術精英已經在系統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并對此普遍持一種客觀、肯定的態度。不僅哈佛、斯坦福、哥倫比亞等名牌學府,很多其他的美國大學都設有專門研究中國的機構。
我作為一名中國企業家來到哈佛,希望進行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學習,從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學了這門課后,我發現自己不僅對西方文化不甚了解,對東方文化也不甚了解。我才意識到,自己不僅要系統地了解西方文化,更要系統地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這樣才知道哪些是該吸收的,哪些是該舍棄的,哪些是需要結合的。這樣的心態,才是屬于未來的。思想轉變之后,我開始心平氣和地看中國問題,理解中國的現狀也容易多了。
2007年年底,基于對市場變化的判斷,萬科決定將2008年的計劃開工量縮減38%,并調低廣州萬科金色康苑項目的價格。2007年12月13日,我在清華大學國際交流中心參加“中英低收入人群住房解決方案比較研究”新聞發布會。記者問:“樓市拐點是否出現了?”我說:“我認可你關于‘拐點論的說法。”
“拐點論”就此將萬科卷入了一場風波。萬科因此受到了房地產同行、地方政府的巨大壓力和公開排斥。在某市,一些已經購買了萬科產品的準業主,覺得自己房子還沒到手,開發商就降價,有情緒,沖進售樓處干擾銷售,警察來了,卻只是維持秩序。當時,我認為政府的行為就是不作為,覺得中國沒有契約精神。
原來我理解的契約精神,第一是要自愿,一定是在自由、平等、自愿的原則上達成的契約;第二,契約應該得到執行;第三,如果不執行,對于違約方有懲罰條款,對于損失方有補償條款。
但在哈佛上了普鳴教授的課之后,我對中國傳統的契約精神有了新的認識:中國傳統社會是有契約精神的,但與西方有很大不同。區別主要有兩點:一是保人制,擔保人的連帶責任非常重。二是同情弱者原則。比如,中國某個歷史時期的地契買賣,除了有保人制以外,還會規定,如果賣方想贖回是可以贖回的,而且是按原價。這就明顯是偏向弱者的。因為如果按西方契約精神,第一,是否能贖回,要看買方是否愿意;第二,贖回肯定是按市場價。
同情弱者原則,對經濟社會追求的效率價值沒什么好處,但它追求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公平,又與西方社會的某些價值觀是一致的。只不過西方在關注弱者時,用的是第三種力量,即慈善、公益的方式,而在中國,政府充當了這一角色。
回頭看“拐點論”風波,我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但經營上怎么解決呢?我想到的一種可能性,就是利用各種節日,用優惠政策進行促銷,既不違背現代契約精神,又尊重中國傳統文化。
有了哈佛的經歷后,我開始正視、理解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并深入思考作為一個中國人,該如何在其中掌握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