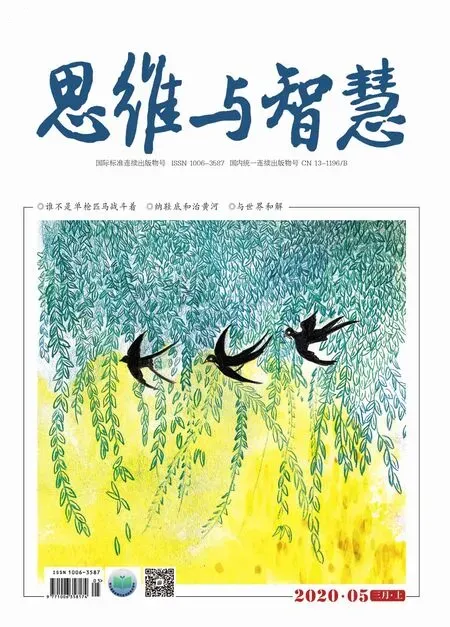瓦有魂魄
●李 曉
這些年時常回老家,差不多都是靜悄悄一個人,因為我回去,是要看那一片屋上起伏的青瓦。一個人獨坐山梁,看青瓦,我冥想很深,有時幻化成一只停留在青瓦上啁啾的鳥。
我老家那些房上的青瓦,如今,和房頂上的老煙囪一樣,漸漸消逝在天光云影之下。我用凝望的目光,把它嵌入到記憶的瞳孔里儲藏,成為永久故鄉的一部分。
我老家房上的青瓦,也是土瓦。據說從西周開始零星使用,自東周廣為傳延。
我看見最老的瓦,也只有一百多年歷史。那是在一個古鎮子上,風一吹,吊腳樓上的房頂,那青瓦上的鳥糞,簌簌而落,我也沒躲閃,撲進到嘴里幾粒。那次,間接嘗到了瓦的一點味道,因為那鳥糞畢竟在瓦上風雨里浸透和纏綿過。它有一點苦,有一些澀,這像我一直咀嚼過的那些人生況味。
在我故鄉鄉場野外,有一燒瓦的瓦窯。一個少年,曾經望著爐火熊熊,那些泥土做成的瓦,我似乎聽見它們在火中的嘶鳴。泥土轉世為瓦,這些瓦,被一些喝了高粱酒、紅苕酒的漢子挑到山坡上、溝壑里、大樹旁堆下,把瓦一片一片蓋上房頂,成為新房。
就在那些瓦下,我的鄉下親人,還有老鄉,他們卑微而倔犟地生活著,在泥土里匍匐、翻滾,最后,歸隱于泥土。所以,我似乎一直相信宿命的存在,在青瓦覆蓋的小小房屋下,他們的人生,也默默地被覆蓋。
前年我回到老家村子,整個村莊在風里孱弱地呼號,像我寫詩的一張紙那樣薄了。整個村莊,就剩下了不到一百號人,他們,堅守著,如在守魂。梁老漢,就是守護村莊最老的一個人,他八十七歲了。
我想在梁老漢家住一晚。梁老漢還腿腳麻利,用柴火燒飯,用土碗盛菜。梁老漢往土灶里添柴時,騰起一股煙,從灶里急著飄蕩出來,躥上梁頂,從青瓦的縫里撲出去,與天空中的霧靄匯合。晚上,下起了雨,我同梁老漢閑聊,聽瓦上雨聲,想起一些流光,如安魂曲。
第二天早晨,我一個人坐在山坡上,望著梁老漢那青瓦房頂,那些層疊的瓦,如在蒼涼之水里,老魚起伏的鱗。這老瓦房,經過了那么多年風霜雨雪的飄搖,還像梁老漢一樣健在著。梁老漢帶著得意的神情告訴我,有一年不遠處遇到了泥石流,房子居然沒被沖垮。這就像一些卑微之人的命,賤,但頑強。青瓦上,有深深淺淺的青苔覆蓋,瓦被浸透得草一樣的顏色。我有一種沖動,坐到房頂上去,喝一碗老酒,醉了,就把青瓦當床睡去。
我想起城里的詩人老馬,有一年看到大水從逶迤群山而來,因為要修電站,老城的下半身,就要在波濤之下睡去。老馬就一個人提了酒,坐到了他祖上留下的瓦房頂上,他邊喝邊哭,邊喝邊唱,手舞足蹈。我就在瓦屋下,守護著我的這個詩人朋友。這城里的一些人,他們把馬詩人當做一頭怪獸,我得把他視作一頭熊貓,好好保護起來。
而今,在老馬的書房,還有幾片瓦,那是他從老屋頂上搶救回來的。有一天,我去看他,老馬出去跑步了,他要鍛煉,減脂肪,減欲望。門沒鎖,他似乎知道我要來,那是一個大霧天氣。我推開門,在他書房,我摩挲著那青瓦,都感覺到有老馬的多少掌紋了。望著那青瓦,我一時恍惚,想起多年以前,它在爐火里的冶烤,滾燙的溫度,而今,冷卻在一個懷舊者的房間。我在老馬那里看見一句詩,他說,火焰一旦凝固,就成了白色,比如水里,就有白色火焰。那么,泥土呢,它在翻滾的大火里,冷下來后,是不是就是這瓦的顏色,被氤氳時光洗染,流光浸泡,成了青,黑,褐色……
老馬回來告訴我,他感覺自己活得就像這老瓦一樣,人生從喧嘩到沉寂,從沸騰到冷卻,到最后,自己把自己收藏,安放。
聽老馬這么一說,我忽地感到,瓦是有魂魄的,它伴隨著人世有情人,成為時間重量的一部分,成為命運涌流的一部分。